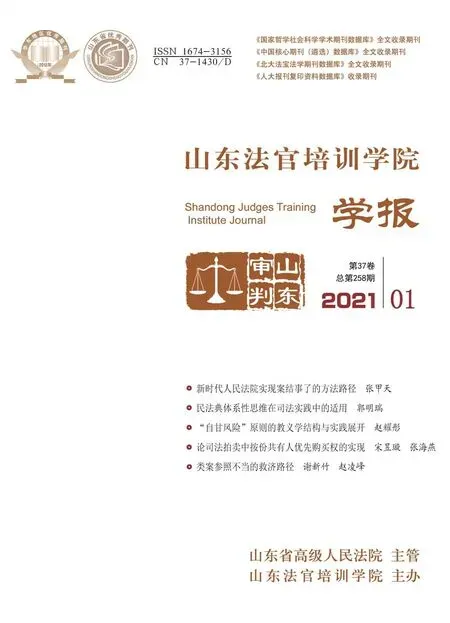情勢變更規則下重新協商的困境與出路
——以《民法典》第533條之適用為視角
邱波 楊慶堂
我國《民法典》創設重新協商程序,賦予情勢變更規則新的內涵,有學者稱之為“最值得稱道的創新”①劉承韙:《民法典合同編的立法建議》,載《社會科學文摘》2020年第2期。。重新協商程序屬于情勢變更制度下的新規則,盡管司法機關以前也偶有提及,②參見沈德詠主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合同法司法解釋(二)理解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193頁。但僅屬對法律適用的指導,不具有普遍強制性,畢竟其沒有上升到立法的高度。我國立法機關在《民法典》編纂中,對情勢變更的規則體系進行了重要調整,首次在法律文件中規定了重新協商程序。重新協商程序將改變涉情勢變更案件的司法認定路徑,司法機關在法律適用時,需要仔細思考情勢變化之后重新協商程序的提出條件、主體要求、舉證責任、程序銜接、后續效果等問題。然而,《民法典》第533條對重新協商規則的模糊設計顯然不足以滿足司法機關的實際需要,從法律適用程序到實體糾紛解決,司法機關在面對具體個案時,如何妥當處理重新協商的程序與實體問題,將成為未來司法機關工作中的難點。為此,筆者結合辦理合同糾紛案件的實踐經驗,探討情勢變更制度下重新協商的困境,論證重新協商程序理論上的正當性,探索重新協商的具體制度與適用規則。
一、實踐觀察:情勢變更下重新協商程序適用的現實困境
情勢變更制度自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以下簡稱《合同法司法解釋(二)》)施行以來,在司法實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此次《民法典》在情勢變更制度中加入重新協商程序,以期解決原有制度面臨的多重困境。
(一)涉情勢變更案件的司法實踐困境
為了更好論證,筆者從中國裁判文書網選取所在的上海法院自2014年1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所有包含情勢變更的訴請或者抗辯理由的案件共計305件。①中國裁判文書網自2014年1月1日起運行,故筆者選取自2014年1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期間以“情勢變更(全文)+合同糾紛(民事案由)+S市”和“情事變更(全文)+合同糾紛(民事案由)+S市”分別篩選出上海市審理的各類案件裁判文書282篇、29篇,其中重復5篇,有效文書共計305篇。經過分析,發現司法實踐中存在以下現象。
1.涉情勢變更案件裁判文書說理不足。筆者在分析大量裁判文書之后發現,盡管當事人在訴訟中提出情勢變更的訴請或者抗辯,但是法官在裁判文書說理部分,沒有直接回應情勢變更問題的文書共計181件,占比59.3%,這凸顯了法官在涉情勢變更案件中尚未足夠重視說理問題,以致大量案件當事人上訴或者申請再審。
2.涉情勢變更案件的服判息訴率較低。在所有涉情勢變更案件中,一審案件161件,上訴與申請再審案件合計144件,這表明一審案件數量與上訴及申請再審案件數量比值接近1:1。換言之,絕大部分案件判決之后,當事人不服裁判結果選擇提起上訴或者申請再審。當事人不認同法院的裁判以致服判息訴率較低,這表明鼓勵當事人在合同糾紛中自主進行重新協商極有必要,能夠大幅度減少訴累。
3.原有情勢變更規則下當事人重新協商的積極性不高。在筆者統計的文書中,當事人在情勢發生變化之后進行重新協商的案件共計169件,占比55.4%。其中,當事人曾表示多次協商的案件僅88件,占比28.9%。換言之,近一半的案件中當事人并未在情勢變化后重新協商。這表明當事人選擇主動重新協商的積極性并不高,在合同糾紛案件中重新協商并未引起足夠的重視,這顯示出立法機關制定重新協商規定的緊迫性和及時性。
4.司法認定情勢變更的比例極低。筆者所統計的305篇裁判文書中,法官認定符合情勢變更原則的案件僅17件,占比5.6%。換言之,94.4%的案件并不真正符合法律規定的情勢變更原則。對于這部分案件,法官完全可以向當事人釋明認定情勢變更之繁瑣流程,①參見沈志先主編:《合同案件審判精要》,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94頁。鼓勵當事人通過重新協商解決爭議,而并非必須通過司法機關介入解決。
(二)重新協商程序的制度困境
雖然《民法典》首次規定了重新協商程序,改變了情勢變更規則體系,但重新協商的具體規則并不明確,法律適用存在一定難度。由于沒有詳細的配套規則,法官認識不統一,司法機關只能在個案中裁量,極易造成司法認定的混亂。
1.重新協商的提出主體模糊難定。盡管《民法典》第533條規定發生情勢變更之后,受不利影響的一方當事人可以提出重新協商,但具體案件中哪方“受不利影響”很難判定。在上海市閔行區人民法院(2016)滬0112民初8817號某房屋買賣合同糾紛案件中,一方面,違約方因為購房政策變化而無資格新購房屋,如果強行履行合同將致其無房可住;另一方面,守約方認為其已支付大部分對價,耗費大量時間和精力,且房價漲幅很大,如果合同不履行,對他明顯不公平,本案中雙方均遭受了重大不利影響。一般來說,重大不利影響通常表現為對價障礙,即對價關系不平衡、不平等且已動搖了合同基礎,若執行該對價關系則明顯不公平,這種不公平可能是對收款方而言,也可能是對付款方而言。②參見茆榮華主編:《〈民法典〉適用于司法實務》,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342頁。合同履行過程之中,由于沒有中立的裁判者,誰是法律規定的受不利影響的當事人,存在模糊性。
2.重新協商程序與調解程序的銜接有待優化。司法實踐中,一般在出現了合同糾紛之后,當事人之間不能夠自行成功協商的情況下,可以請求社會調解組織等第三方主持調解,在無法達成調解之后才可能訴至法院。法院正式立案之前,立案部門通常還會再安排特約調解員、人民調解員等主持訴前調解,以求在訴前解決爭議。③參見李少平主編:《最高人民法院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意見和特邀調解規定的理解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7年版,第10-12頁。當事人接受調解是否可以認為其已經履行了重新協商義務存在疑問,如何理順當事人自行協商程序、社會調解組織的調解程序、法院訴前調解程序和訴訟程序的銜接問題,有待進一步探索與優化。
3.重新協商程序性質存在爭議。有學者稱重新協商程序為再磋商義務,認為這是一種不真正義務,④參見王利明:《情事變更制度若干問題探討——兼評〈民法典合同編(草案)〉(二審稿)第323條》,載《法商研究》2019年第3期。也有學者認為重新協商是真正義務與雙方義務,⑤參見謝鴻飛:《民法典合同編總則的立法技術與制度安排》,載《河南社會科學》2017年第6期。還有學者認為該義務是一種附隨義務。①參見劉善華:《日本和德國法上的再交涉義務及對我國合同法的啟示》,載《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6期。此外,另有學者則認為,將重新協商程序理解成為義務,將加重當事人的負擔,不如認為其系一種權利,具體來說就是形成權。②參見張素華、寧園:《論情勢變更原則中的再交涉權利》,載《清華法學》2019年第3期。如果認為它是一種不真正義務,則義務人不履行相關義務將承擔權利減損或喪失等不利后果。③參見王澤鑒:《債法原理(第二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88-89頁。如果認為它是一種權利,那么這到底是什么權利?如果當事人不行使該權利,系其自由處分權利的行為,并不當然引發不利法律后果,那么《民法典》創設重新協商制度意義何在?法律的模糊性以及學者們的認識分歧,本也無可厚非,只是這將給司法機關帶來極大的困惑。
4.司法職權主義干預的先天缺陷。域外立法對情勢變更較多持謹慎態度,如法國在2016年之前一般不允許法官適用情勢變更原則,即使在債法現代化改革之后,也是采取有限的情勢變更制度,④參見李貝:《法國債法改革對我國民法典制定的啟示意義》,載《交大法學》2017年第2期。“對于普通法國家而言,重大市場變化很少(如果有的話)是豁免合同義務的基礎……英國法院持這種立場,即在商業合同中將合同確定性置于對義務人的寬容之上。”⑤Ba?ak Ba?o?lu (ed.),The Effects of Financial Crises on the Binding Force of Contracts - Renegotiation,Rescission or Revision,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Switzerland,2016,pp.285-286.我國《民法典》第533條雖然制定重新協商制度,但是法官職權主義色彩依舊濃厚,新法不強制要求重新協商程序前置,受不利影響的一方當事人未經重新協商,仍可以直接請求法院變更或者解除合同。可見立法者仍然認可司法機關提前直接介入合同糾紛的正當性,重新協商不過是可選擇性程序,與德日法律中的強制再磋商規定不可同日而語。
二、正本清源:情勢變更規則下重新協商程序的應然之意
我國情勢變更原則與《國際商事合同通則》的“艱難情形規則”類似,本就是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在合同關系中的具體運用,⑥參見殷武:《〈國際商事合同通則〉的“艱難情形規則”對我國合同法的借鑒意義》,載《社會科學家》2005年第1期。只不過“艱難情形”更加通俗易懂。我國《民法典》確立的重新協商程序,同樣也積極參考了《國際商事合同通則》《歐洲合同法原則》等域外規則,重新協商程序實為情勢變更規則不可或缺的部分。
(一)重新協商程序有效緩和情勢變更與不可抗力之適用沖突
學界、實務界普遍認同不可抗力和情勢變更原則在實踐中難以區分,⑦參見劉承韙、許中緣、張金海:《“民法典合同編(草案)二審稿修改”筆談》,載《法治研究》2019年第3期。立法者選擇了在新的情勢變更規則體系中承認不可抗力的適用性,這是《民法典》的重要制度創新。在不可抗力可以作為情勢變更事由之后,立法者賦予不可抗力除免責事由之外的情勢變更內涵,重新協商程序有時正好可以緩和二者之適用沖突。①參見韓世遠:《情事變更若干問題研究》,載《中外法學》2014年第3期。如果不可抗力發生,受不利影響的一方當事人認為繼續履行原合同顯失公平,但其又確有繼續交易的意愿,原有合同法律規則難以滿足當事人的這種需求。即使合同各方都愿意繼續合作,也需要經歷先解除合同、再進行磋商、再訂立合同的復雜流程,徒增交易成本。重新協商程序使得合同各方即使遭遇不可抗力也可以自行協商、變更履行,不至于解除合同,這使得原本難以調和的不可抗力規則和情勢變更原則更加圓融,留給當事人足夠空間協商,也給司法機關留足空間避免直接干預合同關系。
(二)重新協商程序是調和程序正義和實體正義的重要方法
在原有情勢變更制度中,繼續履行合同將對一方當事人“明顯不公平或者不能實現合同目的”,該當事人可不經協商直接向法院提起訴訟以變更或者解除合同,起訴的一方當事人程序權利之行使,導致被訴方當事人倉促應訴而完全沒有重新協商的機會。由于當事人職業、所處環境、知識背景等所限,被訴一方當事人不一定完全知悉對方當事人已經遭遇如價格劇烈波動、政策發生重大變化等情勢變更的情形,且被訴人也不一定會拒絕重新協商,畢竟對其自身也有不利。原有規則在協商事實未發生之前,預設被訴當事人是“壞人”的身份,對實際情況在所不問。司法機關的介入時間節點太過靠前,阻斷了市場主體的正常溝通協商,從被訴一方當事人的角度來說,司法機關的突然介入使其只能被動應訴。被訴一方當事人在起訴前、起訴時兩個階段主動協商的權利沒有制度保障,無法申辯,只能消極應訴,對其難稱公平,也容易激化合同各方的矛盾。《民法典》規定重新協商程序的前置,在程序上,為各方當事人留足自主協商的合理時間、空間,減少司法機關過早介入,保障被訴方的程序權利;在實體上,各方當事人既可以重新協商修改合同條款,也可以訂立新的合同,還可以選擇解除合同等,合同的內容能夠更加客觀地反映經濟環境等因素變化所帶來的影響。“契約自由的技術形式規定……具有程序性,乃至實現程序正義,經由磋商合意而訂立的契約在一定程度得以保障契約內容的妥當性。”②王澤鑒:《債法原理(第二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頁。重新協商程序恰能較好解決原有情勢變更制度的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調和問題。
(三)重新協商程序是減少司法干預的必要手段
從市場經濟人的邏輯來看,如果當事人面臨不利的突發情況,一般都會主動和另一方當事人進行積極協商,以避免自己損失擴大,這符合商業慣例。《民法典》中明確規定重新協商程序,肯定不是對業已存在的商業慣例進行宣示性的重申,否則就是疊床架屋——多此一舉,該制度更大的用意還在于減少司法機關過度干預經濟生活。有學者早提出中肯的建議,“《合同法司法解釋(二)》中已賦予法官極大的自由裁量權,但并未規定其具體的判定標準,這種情形下易造成濫用職權之嫌。”①于震:《對完善我國情勢變更原則的思考》,載《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4期。《民法典》將重新協商程序置于合同糾紛之后與司法介入之前的時間節點,將矛盾糾紛與司法處理有效隔離,為當事人自行解決問題留足空間。即使最后審結案件后發現本案不符合情勢變更的條件,當事人之間的重新協商仍頗有價值,一是因為合同各方在重新協商中所形成的方案只要不屬于無效情形,法官都可以直接認可,僅需對難以達成一致的部分條款進行局部調整即可,大大提高了審理效率;二是即便不符合情勢變更的情形,合同條款由當事人通過自行協商形成,也能大大提高當事人履行合同的意愿,而無需法院強力干預。
(四)重新協商程序的理論基礎是誠實信用原則與關系契約理論
所謂誠實信用,是市場經濟活動中形成的道德規則,在不損害他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②參見梁慧星:《民法總論》,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273頁。由于情勢變更的原因,當事人可以重新對合同的相應條款進行再次磋商、調整,這并不違反嚴守合同的理念,而是充分遵守誠實信用原則的表現。“這里的主要問題在于兩個基本原則之間存在沖突:嚴守合同和情勢變更……因此,要做到合理與公平,以避免不公正待遇,因為在情況發生重大變化后,按字面意義執行合同可能會導致不公平。”③Ba?ak Ba?o?lu (ed.),The Effects of Financial Crises on the Binding Force of Contracts - Renegotiation,Rescission or Revision,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Switzerland,2016,p.291.重新協商的過程本來就是一個利益相互博弈的過程,避免出現明顯不公平的情況,這正是合同法所賴以存在的誠實信用原則之彰顯。同時,關系契約理論認為,契約當事人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信賴的社會關系,在這一關系中存在實際發揮作用的社會規范,再交涉義務就屬于這樣一種規范,它是契約關系轉向下一階段的必經過程。④參見張素華、寧園:《論情勢變更原則中的再交涉權利》,載《清華法學》2019年第3期。換言之,合同各方當事人在合同的訂立、履行、磋商等活動中形成的契約關系屬于一種特別的社會關系,與其他社會關系無異,在當事人簽訂合同之后,沒有一方會真的希望合同無效或者被撤銷,否則前期花費大量成本的談判、磋商將變得毫無意義,所以各方當事人實質上已經形成了具有共同利益的整體。當發生情勢變更時,當事人之間憑借這種特殊的社會關系,基于各方的利益訴求,更容易對某些合同條款作出相應的調整,不至于使一方過分地承擔損失和另一方超常獲取利益,而令這種特殊的社會關系瀕于破碎。即便利益平衡的狀態被打破,合同各方當事人也有基礎修復這種社會關系,進行重新協商,使原有即將破裂的合同關系恢復為正常的合同關系,“關系契約理論的核心是將合同的中心從合意轉化為當事人之間的社會關系。”①參見謝鴻飛:《合同法學的新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2014年版,第38-39頁。
三、路徑選擇:重新協商程序之制度設計
重新協商程序如何設計才能更好實現司法便民、降低司法成本、實現公平正義等目的,是在《民法典》頒行之后司法機關迫切需要考慮的問題。筆者對重新協商程序從宏觀流程構架與微觀規則設計兩個方面進行制度塑造,試圖探索重新協商程序的適用規則。
(一)重新協商程序的宏觀流程構架
如前文所述,將重新協商認定為一種不真正義務較妥,義務人僅對不履行該義務以致損失擴大的部分承擔責任。因為不真正義務不以違反法律義務為前提,系行為人對自己利益的維護照顧有所疏懈,故依誠實信用及公平原則,按照過錯程度承擔減免賠償額的不利益。②參見王澤鑒:《損害賠償》,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309頁。若一方履行重新協商程序,則止損義務流轉至對方,此時對方應承擔該義務,僅當雙方均依誠實信用原則重新協商無果,則進入下一階段。另一方面,也需要考慮協商成本問題,“合同糾紛救濟措施的效率取決于當違約出現時各方可以重新協商的難易程度。……如果重新協商成本足夠低,那么任何救濟措施都是有效的。”③Craswell,Richard,Contract Remedies,Renegotiation,and the Theory of Efficient Breach,61 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 629,629-670(1988).
1.重新協商程序流程設計的整體思路
由于受不利影響的一方當事人本來就已經因不利情勢變更而遭受損失,處于合同弱勢地位,如果沒有法律之力作為后盾,對方當事人很有可能不會配合重新協商。筆者認為,重新協商程序實施的思路應是止損責任在合同當事方之間因義務履行而有序移轉,即受不利影響的一方履行了重新協商義務,那么基于誠實信用原則,對方當事人也應配合重新協商,避免合同各方的損失繼續擴大,對于不配合重新協商所帶來的損失擴大的責任應由該當事人承擔。在域外判例中也是如此,在美國俄亥俄州沙克高地市政法院審理的SHAKER BUILDING CO.v.FEDERAL LIME & STONE CO.一案中,法官闡明,在本案長期租賃合同的糾紛中,在非違約方未采取合理措施以至于未能避免某些損害后果發生的情況下,違約方可說明多次磋商無果且證明這些損失,以相應減少違約損害賠償金。④參見美國俄亥俄州沙克高地市政法院28 Ohio Misc.246 (1971)。各方當事人在合理期限內協商未果,均可向法院提起訴訟,訴訟中的重新協商便無止損義務的約束,各方當事人可以同意法官主持的調解或者和解,也可以不同意,無法達成一致意見時由法院依職權作出裁判。
2.重新協商程序的詳細步驟
關系契約理論強調將合同關系與人情關系的密切聯系,①參見【日】內田貴:《契約的再生》,胡寶海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頁。在設計重新協商具體步驟時應著重考慮調解工作,這與司法實踐的思路也是相同的。如果情勢變更發生,當事人在訂立合同時均無法預見,也未作出相應的約定,受不利影響的一方認為足以影響合同履行的基礎,就應該認可提出重新協商程序的必要性,并非等到司法機關確認符合情勢變更原則之后,才能反過來認定前面重新協商程序符合法律規定。如果一方怠于履行重新協商的義務,有違誠實信用原則,導致合同未履行的損失擴大,應承擔相應責任。反之,如果積極協商,此時有關止損的義務則從積極主張的一方當事人轉至另一方當事人。具體步驟如下:
(1)自行重新協商。重新協商程序是各方當事人之間的一種合同協商程序,對于出現情勢變更的情形,只要各方之間予以認可,協商調整相關合同條款均可。
(2)第三方組織調解。受不利影響的當事人在無法自行協商的情況下,可以請求第三方調解組織,包括專業調解機構、基層司法行政機關、基層自治組織等主持調解,各方當事人應積極磋商、協商解決。
(3)法院訴前調解。司法機關在收到當事人訴狀之后,一般都會先行引導當事人訴前調解,在一些可調性比較高的案件中,要充分釋法明理,利用合同各方當事人的息訴心理,使各方當事人盡量重新協商、調解和解。②參見沈志先主編:《訴訟調解》,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頁。重新協商程序更能體現當事人的意思自治,相較法官主導之下的剛性裁判更能夠發揮當事人的主體作用,既能節約司法成本,也能提升當事人履行合同的意愿。
(4)訴訟程序。立案后,法官在對相關案件作出裁判之前,如果能夠在訴訟中調解或者和解的,法官應積極促成當事人達成一致,對合同的履行條款進行再斟酌、再磋商。實在無協商一致可能的,法官可以參考各方當事人在此前重新協商程序中形成的最接近達成的方案作出裁判,以確保當事人服判息訴,提高各方當事人合同履行意愿。
(二)重新協商程序的微觀規則設計
1.基本思路:將原有司法指導意見與《民法典》新規定有機結合
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當前形勢下審理民商事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法發〔2009〕40號)(以下簡稱《指導意見》)早已提出“在訴訟過程中,人民法院要積極引導當事人重新協商,改訂合同;重新協商不成的,爭取調解解決。”換言之,司法機關在很早之前已經注意到重新協商程序在司法實踐中的應用,但是沒有上升到立法的高度,僅僅是法官辦案指導,不具有強制適用性。《指導意見》明確了訴訟過程中適用重新協商程序,但訴訟之外的程序如何進行,尚存疑問。筆者認為,在具體司法解釋出臺前,司法機關在個案審理中可以參考《指導意見》“引導協商,爭取調解”的基本原則,準確理解《民法典》新規定。在出現動搖合同基礎的事由發生之后,繼續履行合同對一方當事人顯失公平的情況下,受不利影響的當事人應本著誠實信用積極與對方當事人重新協商、修改合同,對方當事人亦應以誠實信用為原則配合對方當事人解決爭議。在域外判例中也是如此,在美國康涅狄格州地方法院審理的RANDWHITNEY CONTAINERBOARD v.TOWN OF MONTVILLE一案中,法官認為,盡管原告辯稱善意協商的義務可能僅源于合同對善意協商的明確約定,但法院認為該論點必然與合同法蘊含的理念不一致,《美國合同法重述(第二版)》認可當事人應善意協商以重新修改合同之當然義務。①參見美國康涅狄格州地方法院289 F.Supp.2d 62 (2003)。如果當事人重新協商不成,可以爭取第三方組織主持調解,還可以請求法院開展訴前調解。訴前調解不成功,進入訴訟程序后,法院仍然可以按照《指導意見》繼續開展調解,向各方當事人做好釋法明理工作,使之對糾紛有清醒認識與預判。窮盡各種方法之后,各方仍無達成協議之可能,法院才能對糾紛作出裁判。將原有《指導意見》的基本原則與《民法典》的新規定有機結合,應成為司法機關正確適用重新協商程序的基本思路。
2.協商條件:重新協商程序的前置標準不宜過嚴
如上文所述,由于符合情勢變更原則的案件僅占樣本總量的5.6%,如果嚴格要求只有符合情勢變更原則才能夠提出重新協商程序,既是對《民法典》第533條的錯誤理解,也是對當事人的苛刻要求,還會出現邏輯上的矛盾之處。細言之,是否屬于情勢變更需要法院來作出判斷,但是,當事人在出現客觀情況變化之后提起重新協商之時,此時合同糾紛根本沒有進入司法程序,又何來法院認定情勢變更?筆者認為,解決該問題就必須要認識到,提起重新協商請求的條件不應該以法官的認識為標準,而應以普通人的認識為標準。原因有三:其一,從法律規定來看,合同糾紛發生后,只是客觀情況出現了變化,是否構成合同基礎條件變化有無預見是否屬于商業風險是否明顯不公平等,均需法院綜合評判,在法官尚未審理時,客觀上只能由當事人按照普通人的認識標準來判斷;其二,從程序上來看,進入訴訟程序,法院認定了案件符合情勢變更原則,才會有相應的裁判,進入訴訟程序之前的所有磋商行為,均可以稱之為因情況變化而重新協商,符合第533條的規定;其三,即使客觀情況變化并不符合情勢變更的法律規定,但是符合當事人通過事前約定或者事后重新協商所確定的情勢變更情形,亦可成為法官據以變更或者解除合同的根據,而并非需要完全符合情勢變更法定標準。上海市金山區人民法院(2019)滬0116民初6581號民事判決書認為,各方當事人明確約定,在原告投資期間,如果出現項目因為不可抗力第三人或情勢變更需要終止經營的情況(如租賃到期、經營困難、政策調整、商業環境變化等),被告承諾自原告知道或應當知道上述原因之日起6個月內根據原告要求回購原告的投資份額,回購價格為投資本金。結合本院依法采納的證據和當事人的當庭陳述可以認定,被告的確存在經營困難的情況,已符合各方約定的條件。所以,情勢變更事由也可以由當事人之間約定,并非只能依照法律規定。
3.提出主體:違約方解除權之認可
守約方在情勢變更的情況下提出合同變更或者解除的重新協商請求或者訴訟請求,其權利的正當性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司法實踐中,更為常見的是違約方以情勢變更為由提出合同變更或者解除之訴。筆者所統計的305件案件中,17件符合情勢變更原則,其中系違約方提出解除合同訴請的案件共11件,占比64.7%,說明涉情勢變更案件中,違約方更有提出重新協商的可能性。重新協商程序并未對提起磋商請求的當事人身份作出限制,既可以是違約方提出也可以是守約方提出,即使合理期限內協商未果,當事人還可以提出變更合同條款的訴訟,也可以提出解除合同的訴訟。值得注意的是《民法典》第533條情勢變更條款與第580條第2款履行不能條款的銜接問題。在此之前,在合同陷入僵局的情況下,由于《合同法》第110條履行不能條款并未直接規定違約方解除權,違約方一般按照情勢變更規則請求變更或者解除合同,這成為違約方解除合同的重要途徑。《民法典》頒行后,違約一方不僅可以按照第533條情勢變更條款修改或者解除合同,還可以按照第580條請求解除合同以解決合同僵局的問題。從平衡各方利益的角度而言,重新協商制度可以在不解除合同的前提下實現爭議解決,似乎更能較好地解決合同僵局問題,且即使重新協商不成,合同當事人之間還有訴訟調解、訴訟和解、法院裁判變更或者解除的方案可以選擇,為各方當事人留足意思自治的空間。
4.合理期限:重新協商的時間限制
為防止合同當事人利用重新協商惡意拖延,《民法典》第533條規定了重新協商的合理期限,但此處的“合理期限”又是一處難點。重新協商程序必須是發生在特殊情事變化之后,受不利影響的一方當事人提出重新協商,合理期限內協商不成才可以請求司法機關介入。原則上,重新協商的合理期間應是訴訟之前的期間,從受不利影響的一方當事人提出時開始起算,至雙方無法協商一致而提起訴訟為終止。重新協商程序是在進入司法程序之前而進行,包括當事人請求由第三方組織所主持的調解活動,其期間屬于重新協商的合理期限。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指導意見》的要求,即使在訴訟中法官仍應引導當事人重新協商、爭取調解,由此可知,司法機關對重新協商持開放態度,故正式立案之前的相互磋商、在法院立案部門訴前調解、與其他第三方組織的調解等,只要符合誠實信用原則,其期間均屬第533條意義上的合理期限。合理期間經過,使得受不利影響的一方當事人以其已盡合理磋商義務,而可向法院提出訴請,不用承擔損失擴大帶來的不利后果。有學者甚至認為,受不利影響的一方當事人擁有中止履行抗辯權,如“日本債權法改正基本方針已承認,在進行再交涉的相當期間,債務人可以拒絕自己債務的履行”①韓世遠:《情事變更若干問題研究》,載《中外法學》2014年第3期。。由此可知,重新協商合理期限的功能遠不止防范惡意拖延合同義務的履行,隨著司法實踐的發展,法官可能依誠實信用與公平原則創造出其他的制度功能。
5.舉證責任:重新協商程序的焦點
如前文所述,目前有學者認為重新協商是一種不真正義務,如果當事人不履行該義務,對于損失擴大等要承擔責任。在義務論的觀點下,受不利影響的當事人有舉證責任,證明其已盡到了重新協商義務,不應承擔損失擴大之責任。也有學者認為重新協商程序的提出是一種形成權,換言之,在舉證責任方面,受不利影響的當事人不用舉證證明自己已經行使了相關權利,因為一般程序性權利可以由其自由處分。重新協商程序的定性直接影響了法庭調查、舉證質證與裁判文書說理。尤其在裁判文書說理中,如果認為當事人存在重新協商義務而未履行,應承擔相應不利后果,則法官必須明確闡述相關理由。反之,如果當事人存在重新協商權利而未行使,則法官對于這樣的事實可以描述也可以不描述。從解釋論的角度來看,該制度的設計目的就在于試圖解決合同糾紛中司法過度介入的問題,轉而將合同爭議交由當事人協商解決。再者,在德國法上,“有賴司法案例提示,學者們認為當事方有責任重新協商解決爭議,并且只有當他們未能達成協議才被允許訴諸法院。”②B.S.Markesinis,Hannes Unberath,Angus Johnston.The German Law of Contract A Comparative Treatise.Oxford and Portland (Oregon): Hart Publishing,2006,p.333.在德國法、日本法上,“基本上都把再交涉義務定位為訴訟上行使合同變更請求權和解除請求權之前,必須要歷經完成的步驟,是以促進當事人的自主交涉為目的的行為規范,是合同法上的法定義務和實體義務”③劉善華:《日本和德國法上的再交涉義務及對我國合同法的啟示》,載《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6期。,違反再交涉義務要承擔相應責任。所以,在制度選擇上,筆者認為義務論觀點更符合立法目的和域外法治經驗,義務人應對其已履行相應義務承擔舉證責任,否則將承擔舉證不利的后果。
6.變更效果:新舊合同之辨
情勢變更之下,當事人對合同相關條款的變更,是形成了新的合同還是算舊的合同,對合同責任會產生重大影響。重新協商所形成的合同,如果改變了原有合同成立的基本要素,比如主體、標的物、數量等,那么應當認定為訂立了新的合同。如果只是對原有合同其他要素的改動,比如價格、履行期限、履行地點等,那么應當認定為變更后的合同仍然是原有合同。相應的,通過重新協商形成的新合同中,如果當事人在協商過程中存在故意或者重大過失導致合同無效、被撤銷等,那么需要承擔的是締約過失責任。反之,如果通過重新協商形成的合同仍是舊合同,當事人在協商過程中存在故意或者重大過失導致瑕疵履行或者合同被解除等,需要承擔的是違約責任。有學者說,情勢變更原則“具有二次效力:第一次的效力是維持原合同關系,只變更某些內容,以排除情勢變更導致的不公平結果。第二次效力是指當第一次的效力尚不足以排除不公平的結果時,則采取消滅原合同關系的方法以恢復公平。”①戴愛民:《情勢變更原則淺析》,載中國法院網2003年09月17日,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03/09/id/82058.shtml。筆者認為,“二次效力說”指的是我國原有情勢變更制度的效果,這已被學界和實務界詬病許久,《民法典》下新的情勢變更原則應如有的學者所言,“情事變更原則的第一重效果是再交涉義務,第二重效果為合同內容變更,第三重效果為合同解除權。”②劉善華:《日本和德國法上的再交涉義務及對我國合同法的啟示》,載《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6期。“三次效力說”更加符合我國《民法典》的制度設計。
結 語
重新協商程序在我國尚未建立具體規則體系,司法機關在沒有明確法律規定的情況下,可以參照《指導意見》中“引導協商,爭取調解”的精神,正確適用《民法典》的新規定,不應對重新協商程序的提出條件設定過于嚴苛的要求。合同基礎是否已經動搖、是否預見、誰是受不利影響一方當事人等前置條件,合議庭的法官之間尚存爭議,更何況當事人。后續協商流程也應充分尊重當事人作為合同主體的自主性,盡量通過調解或者和解等方式達成一致意見,在程序設計上減少“有形之手”的干預,讓當事人發揮積極作用。“再協商義務的重要意義在于以動態視角觀察合同法的世界,取代了實體法秩序的靜態視角,從而使得合同關系不再只是合同成立時的固定的文字表達,而是在雙方當事人的相互交涉過程中形成并不斷發生變化的利益狀態。”③劉承韙:《民法典合同編的立法建議》,載《社會科學文摘》2020年第2期。重新協商是《民法典》中的新事物,人們對于事物的認識總是在不斷的自我否定中尋找出路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