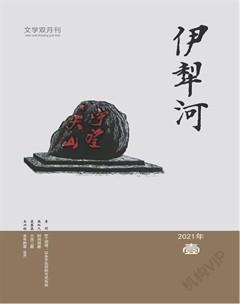斷裂的故鄉
中秋,仰望那一輪皎潔的明月,沐浴著月輝,思緒翩翩。
每次想起故鄉,總有一種斬不斷理還亂的鄉思盤繞心頭,我們這些疆二代的故鄉和上輩有關。而我們的孩子,疆三代的故鄉,又和我們在新疆的家纏繞。
隔代鄉愁,早已在我們身上悄然發生。
1
祖母出生在北京城里時,還有皇帝的年號。
她是滿族佟氏,清代官員佟氏占了半朝。祖父家姓愛新覺羅,他的家族有皇家血統。
祖父在我幼年時就去世了。小時候,祖母來來回回總是給我們講大青狗的故事,那只可敬的大青狗用自己的命,營救了先祖。滿族人不殺狗,不戴狗皮帽子,不吃狗肉,以祭奠它宿命般的犧牲。
從祖母的故事里,我懵懂知道努爾哈赤是我們的先祖,他波浪迭起的生平,充滿了曲折,使平常的家譜,有了峰巒般的懸念。先祖的身影撲朔迷離,循回不已,照看天地,環繞著我。
我成長的那個年代,兒童讀物、小人書都十分罕見,除了課本,一切都過濾得非常干凈,頭腦也像街道一樣光禿禿的。祖母的故事宛如潺潺流動的細水,有風吹過,它就會呼喚出嶄新的生命。
父親是支援邊疆建設才來到新疆的。祖父、祖母還有姑姑是在自然災害那年,投奔父親來到新疆。
我對故鄉的最早認知,是從祖母的故事里。祖母經常給我說起故鄉古塘溝的生活,他們在屯子里算是大戶人家。
過去的人家,時興大門大戶,人一多,事情也多,祖父家堂兄弟九個,幾十口子人,大大小小,公婆姑嫂妯娌,關系復雜,得講規矩,有家法管著。
一大家子人,每天九個妯娌輪流做飯侍奉阿瑪、厄么(滿語:爸爸、媽媽)。每個妯娌的性子吝不相同,有的要強,有的懶饞,有的滑頭賣嘴,有的老實悶頭干活。祖母是個委曲忍讓的人,心里有疙瘩解不開時,老太爺,一哈唬,亦便會消停一陣子。
祖母的講述彌漫著淡淡的鄉愁,她在尋找熟悉的聲音,故鄉的氣息。
我在新疆出生,是一個土生土長的疆二代。小時候,我們住在一棟棟兵營式的連排房。這兒沒有親戚,沒有老宅院,單薄、孤零零的,一家人相依為命。
長大了,咀嚼祖母的故事,像是被泥水泡過,被雨水淋過,被汗水浸過,被淚水染過,甚至是被用心捂過,是那樣的苦澀、酸楚、熾熱和沉重。
在那場突如其來的風暴席卷大地時,父親的家族也受到了沖擊。“皇族身份”成為一個不定時炸彈,便隱姓改名,換了族別。
直到落實民族政策,我們才恢復了族別。父親擔心恢復滿姓會攪亂他后半生的生活,便沒有在戶籍上更改滿姓,只是在去世的家人墓碑上刻下我們滿姓。
我對那個祖母和我父親曾經生活過的地方,心生朦朧的期待和模糊的恐懼。生命的經緯,是血脈的織錦,吸引著我與故鄉續接緣分。
2
1982年,父親送生病的支邊青年回天津,帶上我回東北老家。
這是我第一次回老家。我們坐的綠皮火車,車窗邊,我看著茂密的樹林緩緩向后退去,聽火車與鐵軌嗤嗤地碰撞。走走停停,走了三天兩夜,才到老家。
父親在天津站下了火車去送人,我獨自在沈陽下車,又轉乘公交車到撫順。下車,一眼就認出了人群中接我的姑父。小時候姑父來過新疆,可能是城市生活的緣故吧,姑父相貌一點沒變。
我跟著姑父穿過一幢幢樓房,眼花繚亂。我生活的地方每日所見盡是土塊房,見了這樣直直方方的樓房,便覺精致,心生好感。
一進門,姑姑擺好了飯桌正等著我呢。東北米,透著亮、特別香,不就菜都能吃下去。姑姑看著我吃得這么香,又給我添了一碗,“新疆米少,來這你就多吃點吧。”
見到煤氣灶、自來水,就連上廁所也可以在房間里,對當時的我來說,都新奇的不得了。我們那兒要到井里挑水,拉風箱燒柴火做飯,尤其是上廁所,要到幾百米外的旱廁去。晚上就更難了,膽小,路邊的墻頭,樹影,大坑,總覺得有什么東西在那里藏著,害怕極了,我沒有姐妹,連個陪伴都沒有。
姑姑在新疆工作生活過八年,六十年代末調回撫順在十三中學當教師。姑姑和父親感情甚好,對我們也特別親。表弟龍、表妹暉還是小學生,他們洋氣極了,也好看極了,很討人喜愛。
雖然我不熟悉這里任何一條道路,不認識老家除姑姑家外的任何人,但在我心中,這里就是我的故鄉,對它有著與生俱來的親切與牽掛。
父親從天津回到老家,我先回新疆了。后來聽父親說,他見了他的堂弟溥波、堂哥英宇和小時候的玩伴。父親少小離家參加抗美援朝,后又到新疆支邊,再聚首已近天命。當初的少年,如今都已經兩鬢斑白,相視感慨萬千。
故鄉,于父親乃根之所在,是漂泊千里后的歸巢。
父親去古塘溝拜祭祖墳。故鄉的風物,已然遙遠,先人們原先交付給他們的屯子已面目全非。
老宅院不復存在,熟悉的鄰家少年和那滾動在村道的鐵環,都變成了記憶里的幻覺。村舍寂靜,年少時最熟悉的生活也在消逝……
那些與故鄉有關的零碎記憶,拼湊不了一個完整的童年。
2015年,我第二次回故鄉,看到它從過去的“共和國長子”、重工業重鎮漸漸地變成了大批人員下崗,年輕人逐漸外流的現狀。
表弟龍、表妹暉都已成家立業,初次見到他們還是個孩子,如今他們的孩子都長大了。表妹帶我去農家樂品嘗東北特色風味,表弟帶我去了新賓滿族自治縣永陵尋根。
寒冷的早上,原野白雪皚皚,嘴里呼著白白的哈氣。我們來到永陵,這里是我們皇家祖墳所在地,蘇子河靜靜地流淌,啟運山護衛在它的身后。
當我步入陵寢圣地,皇家祖陵的脈絡在閃爍,這里涵納我的天地,環繞我的萬物,都是我的祖先。我回旋于心室的血液,與數千年前他們的體溫和心跳有關,也把我從虛無中搭救出來,使我成為祖先的后人。
赫圖阿拉城,我踩著雪,咯吱咯吱地響,滿院子白亮亮的,雪下得很厚。在索羅桿下,我們敬拜了神鳥。
索羅桿已成為東北滿族傳統民居的一大特色,每年都要舉行立桿大祭。祭祀時村里路過的陌生人,只要在索羅桿前磕個頭,就可以進院吃肉,吃得越多,主人家越高興。
此刻,我仿佛聽到了冰層下的蘇子河回蕩著古戰場的戰馬嘶鳴,是我的祖先阻止了一場毀滅性的兇險戰火。他用劍裝訂了險些散失的族譜,血脈一直延伸到此時,我的心跳、我的懷想、我對他隔世的感恩,一瞬間洶涌而出。
3
家,是生命開始的地方。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我算是個土生土長的新疆人。當我到內地出差或旅游時,有人問我,你是哪里人?從我的嘴邊都會輕巧地流出一個地名:新疆。
——那是你的故鄉嗎?
我說,不是。然后要解釋一番:父輩到新疆支邊,自己是疆二代。我的祖籍是遼寧撫順。
這是一份關于靈魂的拷問,它不動聲色地發生在我身上。故鄉給予我的雙重身份,照亮了我內心深處的困惑。
如果說我的故鄉是新疆,我只能報出上溯一代的姓名。這里沒有祖宅所居之地,沒有祠堂祖墳所在之地,沒有那些故紙舊墨留痕之地,這里終究是一處沒有根脈的所在。
我的祖籍,離我萬里,我與那里的關聯終究隨著祖母的去世被割斷。故事幻滅了,我會想起那個遙遠而陌生的地方是父輩們的故鄉,那里已是我回不去的故鄉。
我的孩子是疆三代,出生在新疆,上學在四川,定居在北京,她十幾歲就遠離了這里。對她而言,她的父輩、祖父輩是新疆人。
其實,年輕人隨著城市化發展和人口流動,大都離開家鄉開始在更大的城市扎下根來,與故鄉之間只有一根脆弱的細線聯結。隨著老一輩人逐漸逝去,那根細線,終將會崩斷在時光深處。
我不知道該如何定義故鄉,這讓我陷入思考中——
那個我稱之為故鄉的地方在別處,在時間另一個神秘斷層里。愈是苦思冥想,愈覺得故鄉實在是讓人放不下而又道不明。
我的靈魂深處感知,自己在故鄉與異鄉之間游離,誰能說清從哪兒開始分歧?從哪兒重又開始交叉?只是一處牽著我的靈魂漫步,引著我的腳步狂奔。另一處拽著我內心深處的細線,讓我午夜夢回時牽腸掛肚。
故鄉亦成了異鄉,而異鄉慢慢地變成了故鄉。故鄉已不只是地理意義上的存在,更是精神意義上的存在。
很多年以后,故鄉的概念也許變得更模糊,爹娘出生的地方,我們長大的地方,孩子扎根的地方,都將會以不同的經緯度被重新界定。
可是,我們還是會耐心地做一個家譜,標注上這些地方的親人們,和他們所經歷的悲歡離合……
·作者簡介·
趙毓芬,新疆作家協會會員、博州作家協會秘書長,博樂市作家協會副主席。作品散見《雪蓮》《湖北作家》《新疆日報》等報刊,出版散文集《炊煙掠過窗外》。
消息
2020年12月26日上午,《伊犁河》漢文編輯部在伊犁州文聯五樓召開編委擴大會議,《伊犁河》(漢文)部分編委及伊犁州作家代表共20余人參加了會議。與會人員聽取了2020年《伊犁河》(漢文)辦刊情況的通報,并對今后的辦刊方向、定位、欄目設置等建言獻策。與會者一致認為,作為一個地方老牌文學刊物,應多角度展現伊犁的文學藝術成就和特色,講好伊犁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