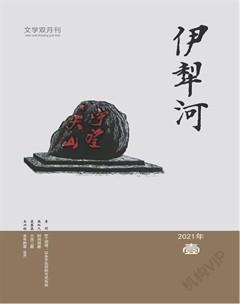偏差的深處
正午的太陽照在客廳的側墻上。
我把手插在褲子的口袋里,站在門廳向里四下打量,先以嗅覺獲取第一直覺。我媽做保潔工作,這是她的一個客戶家。她瞄了一眼門廳地上說,你也不用換拖鞋了。鞋柜前,橫七豎八一大灘鞋,一只銀灰色高跟女鞋,斜踩進一只棕色男鞋里,信息量很大。
客廳沒什么新意,米灰色真皮沙發,圍著棕紅色實木茶幾。昏昏沉沉,亂七八糟,彌漫著一股甜膩的腐壞味,是茶幾上幾根發黑的香蕉發出的。我用腳把地上的一條毛巾,勾到沙發上。然后去打開了一扇窗,窗臺上放著一只方正的大號玻璃煙灰缸,一堆煙蒂被一杯茶襲擊過,茶葉混著煙灰濺到玻璃上,在窗臺上流出一灘黑黃水漬,旁邊倒著一只白瓷水杯。邱曉云快離婚了吧,我問。
我媽沒聽到似的拿著臟衣筐,從沙發背后扯出一條黑色半身裙和一件條紋襯衣,轉身要走,腳下一絆,又從沙發下扯出件粉色浴袍。卻轉向我發起了脾氣說,別一天神神叨叨的,多管閑事。
我走到電視旁的置物架前,繼續說,邱曉云不愿離婚,但她老公八成移情別戀了。置物架上擺著個木質相框,里面是一對中年夫妻并肩站在雪地里的合影。女人向男人偏著頭,男人戴著墨鏡向另一邊微揚起下巴。
你是哪只眼睛看出來的?我媽不耐煩地問。我向那個相框偏了下頭說,這個被摔過,上面的玻璃沒有了,照片是被撕了又重新粘在一起的,應該是邱曉云干的,女人都這樣,所以……我又環顧了一下四周,聳了聳肩。我確信,這是一個婚姻失敗者的家。
有這功夫瞎猜,不如幫你媽一起干活。她把我推到了一邊,拿著臟衣筐去了衛生間。
邱曉云又不給我工錢,我為什么要干活,我低聲嘟嚷著。我需要時間,發現更多證明直覺的蛛絲馬跡。我又去廚房轉了一圈,從保溫杯上的茶銹,垃圾筒里食品袋以及水槽里的碗筷得出結論,男主人有些日子沒回來了,可憐的女強人已有了抑郁傾向。然后我又拐進了書房。我扯著嗓子問,媽,你把鳳緒阿姨介紹給她了?
你不是有那什么基因嗎,不會自己看嗎?她的回答略有遲疑,語氣也不堅定。
燒香拜佛一定不是緣起鳳緒阿姨,但她們現在肯定有來往。我說著來到衛生間,把手抱在了胸前,又補充了一句,那個叫偵探基因。
邱曉云是個律師,堂堂律師會信她?她用了一個探索性的問句,一個假命題。
律師只能證明她是法律方面的專業人士,其他方面她仍然只是個普通人,事實上,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講,像她這種循規蹈矩的、刻板理性思考的人,反而容易……我省略了后半句。
我媽則板平了臉,把分揀好的衣服塞進了洗衣機。嫌棄地說,你一個小姑娘,天天腦子里都想的啥亂七八糟的東西。
你們這些頑固的老家伙恨不能永遠霸占世界,自己不學習,還阻止別人進步。
她抬手要打我,我一閃身,手機鈴聲響了起來。我得去赴同學的約了。
我撲過去強行跟她貼了一下臉,笑嘻嘻地說,剛才那個老家伙不是說你,有我這樣聰明過人的女兒,你可不是一般人。她把我推開,讓我趕緊滾蛋。我到了門口又叫了聲,邱曉云是個專打離婚官司的律師,沒錯吧。她在我關門的瞬間,懶懶地說了句,都沒猜錯。
我全說對了,而我只是一個金融專業的大三學生。我走了后,她盡可以不必裝出煩我的樣子,盡可以得意地大笑了。然后,她又會陷入迷惑,女兒是從哪里看出來邱曉云跟鳳緒有瓜葛的?
她會先放下手里的活。
書房的門對著一張電腦桌的側面,桌上沒有電腦,鋪著金黃色亮閃閃的大約是緞子做的桌布,上面擺著一尊陶瓷制的觀音菩薩。前面是只銅制小香爐,屋頂被熏出一圈黃漬。一年前她初次來做清潔,就是這番情景。桌上方的架子上放了幾本經書和一個塑料筐,里面放著佛珠掛件和手串,還是她上次給歸置到一處的。桌下放著蒲團。對面是窗,窗下是個大書桌。書桌一側放著個小型打印機,亂七八糟到處都是紙。中間放著個臺歷,除了這個月的星期三都被紅筆圈了起來之外,多一個字都沒有寫。旁邊的大書架上全是法律方面的書,地上掉的也是紙。她把那紙撿起來,看到是份離婚協議書。可是,鳳緒到底在這里留下什么了?
鳳緒是和我媽一起長大的好友,倆人在同一年淪為了單身母親。那時她的兒子六歲,我四歲。她兒子三歲被診斷為自閉癥后,她就沒過過一天好日子,最后忍無可忍離了婚。她的前夫家族有企業,離婚后每月都給她一筆不薄的撫養費,她不用去工作,專心給孩子治病。我家是我的警察爸爸犧牲了,撫恤金給了我奶奶看病,我媽在企業里的工資微薄,我們娘倆的日子過得捉襟見肘。我媽和鳳緒倆人,在親友們的嘴里,是上天待人公平的佐證,一個有錢沒有健康的孩子,一個沒錢有健康的孩子。
鳳緒離婚后,第一件事是給兒子改名字,原來叫博知,婆家花錢取的,已成了笑話。她改名叫了“石頭”,老話說賤名好養活。隨后她就領著兒子出門了,全國各地大醫院已跑遍,這次她找了一家知名的特殊學校,租房陪著石頭上了三年學,回來后,用樓房換了城郊一套平房大院,大門一鎖說是順其自然了。
那時我八歲,石頭十歲。某天有人給我媽打來電話,說在街上遇到了鳳緒,說她的樣子像是神經了。其實之前,我媽也覺著鳳緒有點不大對。石頭長得漂亮像鳳緒,一雙大眼睛占了半張臉,可是那雙眼睛絕不肯與另一雙眼睛有交集,哪怕是硬逼上去,他也會讓目光由四周流淌出去。每次有人做這種嘗試,他都樂不可支。鳳緒像有了重大發現似的,抓住我媽說,你看石頭的眼睛,他不是一般人。我媽心說,石頭是自閉癥病人啊。她非得讓我媽仔細看石頭的眼睛,一遍遍地見人就說。難不成,真出了問題?
我媽帶上我去了鳳緒家。走到巷口,就聽到正在變聲期的石頭,在院子里交替發出公鴨和母雞般的尖叫聲。我媽一路小跑去敲開了門,只見鳳緒拎了根竹條,說石頭給院子里的菜地澆水,才出的苗都要給淹死了。石頭兩只手捂著耳朵,尖叫著說,我哭了。你不哭,你看這是誰來了?鳳緒用竹條指著我媽問。石頭繼續捂著耳朵尖叫,鳳緒揚起竹條作勢要打他。他一邊逃跑一邊向我媽望了望,叫道,小姨來了。那個是誰啊?鳳緒又指著我問。是阿姨,石頭拖著哭腔答。是妹妹啊,你忘了?我媽攔住鳳緒的竹條,教石頭叫我,妹妹。叫妹妹,石頭捂著耳朵尖叫道。是妹妹,沒有“叫”,鳳緒氣得又舉起了竹條。石頭叫道,沒有叫。不懂事的我,笑得直不起腰來。
我媽把鳳緒推進了屋里。屋里一轉圈的白墻上,整齊地貼滿了石頭寫的字。石頭很愿意寫字,幾大本小學生字帖全讓他寫滿了,一筆一畫比我寫得都好。他認的字不比我少,會背的古詩比我還多。你說千山鳥飛絕,他會接出萬徑人蹤滅。你說福如東海,他會接壽比南山。你說今年過節不收禮,他會接收禮只收腦白金。你問他這是什么字,他只要心情不壞,都能答出來。但是你要問他今天吃了什么飯?媽媽干什么去了?你幾歲了?他全都答不出來。他對這個世界止步于刻板的認識。
鳳緒跟我媽說,石頭突然不愿再寫字了,開始從早到晚地看體育頻道,不讓他看,他就要去院子里給地澆水,沒完沒了。正說著,石頭也進了屋,徑直去拿起了電視遙控器,打開電視的體育頻道。正在播乒乓球賽,他坐在那里搖頭晃腦地看起來。你們看他的眼睛,鳳緒推了一把我媽,又推一把我說,石頭的眼睛是瞎的,他是個能看見東西的瞎子。我媽抓住鳳緒的手,讓她別胡思亂想。鳳緒卻偏過頭,專注地望著石頭的眼睛,一邊跟著他的節奏搖晃起來。
鳳緒阿姨,我說道,哥哥不是瞎子,他就像沒有連網的電腦。她吃驚地瞪著我,眼睛一亮道,你可真聰明啊,說得對。你放心啊,他早晚能連上網,我說。她一把把我抱進了懷里。我體會著溫暖的懷抱,心花怒放,說,哥哥多幸福,都不用學習。我掙開她的手,機智地從石頭的手里搶走了電視遙控器,關了電視。向石頭叫道,你抓不到我就別看電視。我跑到了門口,石頭才遲鈍地啊啊叫了起來。你去抓妹妹啊,鳳緒對石頭說。石頭只是坐在那里啊啊地叫。你看,鳳緒拍著我媽的腿說,石頭哭了,他著急了,可是臉上還在笑。石頭的確是一張笑臉掛著眼淚,他從來都是一幅笑著的樣子,害怕是笑著的,生氣是笑著的,他沒有第二種表情。我媽并不覺著這有什么特別的意義,但鳳緒微微抽動的嘴角和滿是渴求的眼睛,使我想起等待公布成績時的,一些同學的臉,他們慌張地盼望著奇跡。我媽覺著鳳緒只是這樣也沒關系,我卻有一種即將看到另一種奇跡的預感。
鳳緒開始瘋狂地托人買各種書,學習。從科學的人類的起源,到哲學的人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從心理學的記錄夢境尋找集體無意識,到排空一切私心雜念的佛家入定。她說是因為石頭一成不變的笑臉,和我的那句,哥哥就像沒有連網的電腦,給了她啟發。這是她后來告訴我的。
她收拾出了一間屋子,把能引起石頭注意力的東西都放在那里。進門正墻上是特去廣告公司做的一幅畫,是一輪紅太陽斜掛在天上,下面是一片高樓大廈的暗影。原圖是在一幅掛歷上,石頭看到那張畫樂不可支,簡直戳到了他的笑穴,百試不爽。她開始研究那幅畫,還找各種畫給石頭看,看他的反應。
石頭過生日,鳳緒叫親友們去家里吃飯。葡萄架下兩張小方桌一拼,廚房有人炒菜,菜地里有小孩子們嬉戲玩鬧,一片祥和。她抱了本比磚頭還厚的心理學,圍著她嗑瓜子的幾位姊妹,把書接過去傳看。哪里能看得懂,卻被書頁空白處她密密麻麻的小字給鎮住了。
鳳緒讓大家參觀了那間特別的屋子,然后回到飯桌上。她挺起脖子,從鼻子里幽幽地嗯一聲后,才開始說話。我在她身旁騎在一個小板凳上,她這刻意做出的樣子,讓我替她覺得羞。她提高了的聲音微微顫抖著,像鐵片刮過玻璃般刺耳,開始講起人類思維的組成,講考古的意義。我偷眼看了看其他人,大家都面帶一種膽戰心驚的歉意,小心地吃著盤子里的菜,偶爾點頭假裝聽懂了。她說自己最推崇的是瑞士心理學家榮格,說夢是潛意識通向意識的橋梁,說解夢的意義非常重大。就像是土坑里拔出了一座泰山,一群凡人仰視得幾乎要背過氣去。我希望她能快點停下來,快點變回正常人,我的頭發根都豎了起來。石頭把一盤涼拌肚絲拉到面前,搖頭晃腦吃得津津有味。我媽或許也是無法直視鳳緒,一臉喜悅地看著石頭,像是確定石頭就要得救了。我忽然想起,自己從前以為向地下去挖,可以挖到美國的天空。
鳳緒的長發貼著頭皮順著臉披下來,從眉骨到顴骨到腮骨,一張臉骨骼分明。沒有化妝搽粉的臉是黃的,頭發也是焦黃的,又穿了件麻黃的襯衣,像一尊神秘族群的木雕,比如印地安人什么的。這樣一個人,說著一個個聞所未聞的詞,有一股怪異的不可冒犯的氣勢。而我覺著她像是在演戲,十分過頭的戲。
有人小心翼翼地問,石頭又怎么能說出他的夢呢?她抿嘴一笑,大概正在等這個問題。她說,能引起石頭興趣的畫,等同于石頭做的夢,譬如那幅畫。但是那畫又該怎么解讀?她垂眼觀看了片刻說,石頭再次證明了,人類對太陽的崇拜與生俱來,石頭代表了未開化的那群人。有一個阿姨響亮地拍起了巴掌,搖著頭嘖嘖贊嘆。我問,什么叫未開化的那群人?她回答說也就是原始人。我驚駭地想,石頭竟然是原始人。
吃過飯出來,大家都恍恍惚惚的,好一會兒都沒人說話。有車從一旁經過,打了很響的喇叭,才都醒過來。
石頭真能治好嗎?以前從沒聽說過有這種病,都是這上化肥的菜吃壞了。一個人說。
這病一直都有吧,不就是天生的傻子嗎?現在給起個自閉癥的名字。另一個人說。
鳳緒說這屬心理疾病,她現在就是照著心理病在給石頭治。我媽說。
石頭不是生下來就有這病的嗎?那時候能有心理?有人不服道。
各種先進儀器都給石頭照過了,腦子一點問題都沒有。我媽堅定地說。
我一遍遍地大聲說,石頭是原始人,原始人是治不好的。沒人理我。
到最后,大家還是由一個“命”字結束了對話。“命”這個字是萬能的,天經地義的,涵蓋無數意義的。是來源也是歸宿。
接著事情發生了奇妙地轉變,鳳緒開始神一般地存在了。
先是有人去找她解夢,后逐漸都找她算起了命。從親友到路人。名聲逐漸傳了出去。石頭每天要睡到中午才肯起床,所以鳳緒只給出上午兩個小時。某天在廠里,有人問我媽,是不是有個患自閉癥的外甥?我媽答,是啊。工友說,城郊有個很厲害的通靈大師,專治這種病,說是從國外回來的,每天早上通靈兩個小時,好多大老板都去找她。我媽大膽地問,是姓石嗎?工友答,沒錯。
我媽頗為自豪地把這一傳聞告訴了鳳緒。鳳緒對通靈大師這種說法感到很意外,一邊謙虛地說,是很多人來找她,其實也就是隨便談談心,也沒想過要收費,但總有人扔下錢就跑。我媽好奇地問外國的通靈是干什么的?跟中國的神婆跳大神的一個路數嗎?她的臉上極快地閃過一絲不悅,搖頭說完全不一樣,跳大神是騙人的,通靈可不一樣。然后又不向下說了,仿佛是要守住一個秘密。她向后抖了抖頭發,微微笑著的樣子,像是《西游記》里的觀音站上了云端。而我又想起那天她講話的情形,雞皮疙瘩又冒了出來。我沒法想象她竟然征服了那么多的人,并有了廣大的名氣。我不知道自己哪里出了問題,事實上,我因為寫警察爸爸的作文,而感受到體內有他人不具備的偵察能力。
我心情復雜地看著石頭,他又在看戲劇節目了,笑呵呵地不斷為電視里咿咿呀呀的大花臉鼓掌。他竟然和丑陋的原始人一樣,我長大了可能會是個女偵探,我暗暗決定長大后跟石頭結婚,給他做飯、洗衣照顧他。他太可憐了,卻又長得那么好看。
兩年后我就完全放棄了這個荒唐的想法。
那是一個夏日的上午,石頭忽然倒地抽搐口吐白沫。鳳緒急忙用毛巾包了筷子塞進石頭嘴里,一邊打了急救電話。我媽下班后跑去醫院,鳳緒仍沒有緩過神來。抓著她的手說,我原想最差像養豬一樣,養他一輩子,沒想到……她把頭垂到胸口,使勁搖著說,真能那樣倒好了。她頭發中分梳了條細長辮子在背后,穿著棕底紅花的長袍,胸前是長長短短各種鏈子,像個走出叢林的女酋長。那天是有幾個客人從她家出去,在院子外面倒車時發生了剮蹭,就嚷嚷著吵了起來,還拼命按起了車喇叭。石頭在睡夢中被吵醒,先叫了起來。鳳緒也是聽慣了他叫,但見他叫了半天不出來,過去就見石頭倒在地上在抽搐。
醫生說是癲痛,是由自閉癥誘發的。鳳緒不明白。醫生說自閉癥是由腦神經受損或者異常造成的,隨著生長發育尤其進入青春期,受到外界的刺激就容易伴隨出現癲痛癥狀。鳳緒突然情緒失控了,憤怒地對醫生說,石頭的大腦沒有毛病,她相信石頭是個天才,他只是在表達方面與我們不在同一個層面,存在偏差。我媽拉住激動的鳳緒,向醫生說,鳳緒記錄了幾大本筆記,研究石頭的行為。醫生又打量了下鳳緒的裝束,說他能理解鳳緒,但是請鳳緒相信科學。鳳緒的眼淚流了出來,用顫抖的聲音問,什么叫科學?心理學不是科學嗎?醫生讓她冷靜一下,說科學是唯物主義,說直白點就是用看得見摸得著的事實證據來說話,而心理學分很多流派,他沒有過多的研究,不做評價。醫生微微地搖了下頭,低頭開起了處方。他專注下筆的樣子,分明全是不屑。
醫生說,石頭除了服藥之外,還要給他一個安靜平和的環境,從飲食到生活作息,都要避免給他刺激,以降低癲痛發作風險。鳳緒扯著身上累贅的袍子,仰著頭從醫院走出來,我媽預備跟她說話時,發現她的眼淚一串一串地順著臉掉到裙子上。鳳緒又重新鎖上了她家的大門。
我媽得空就去看鳳緒,說鳳緒仍在堅持自己的研究,但精神狀態差了很多。石頭又在睡夢中發作了兩次,她在石頭身旁拉著他的手睡,哪里能睡得著!她越發的瘦了下去,一雙大眼睛深陷在眼窩里,白頭發也開始生了出來。
轉眼就過年了,親友們聚在一起吃團圓飯,發現石頭開始主動粘人了。他笑瞇著眼,貼著某個女親戚坐下,伸出手去摸人家的胳膊,人家的腿。然后又湊上去聞人家的味道。他雖有了一米七的身高,仍是細瘦的孩子。親戚問石頭,這是誰啊?她有什么味道啊?石頭咯咯地笑而不答。直到他去摸人家胸的時候,鳳緒才急忙把他的手打開。
年過完不久的一天,鳳緒忽然打電話叫我媽去她家里。我媽問有什么事?鳳緒支吾了半天后說,石頭發情了。我媽一時不知道發情是什么意思,以為是聽岔了,讓鳳緒再說一遍。鳳緒咬牙切齒地叫了句,發情了,就掛斷了電話。我媽愣了片刻,猛地把電話旁的我推了一個趔趄,漲紅著臉大聲喝斥我,誰讓你在這里聽電話的?然后像要甩掉什么臟東西似的,又推了我一把,就出門去了鳳緒家。我莫名其妙地受到了羞辱性的驚嚇,一定是石頭干了很壞且見不得人的事,且與我有千絲萬縷的關系,難道她們洞悉了我想跟石頭結婚的念頭?我頓感羞愧不已,石頭這樣的原始人是絕不能要了。
我媽以為鳳緒的家會像世界大戰后的混亂廢墟,去了才發現一切如常。鳳緒一臉的難堪,黑眼圈和眼袋越發嚴重了。我媽剛坐下,石頭就搖頭晃腦地走了出來,手里拿著把剪刀。鳳緒讓石頭把剪刀放下,石頭很聽話。把剪刀認真地放下后,緊貼著我媽坐了下來。要換到前一天,我媽都會非常高興地抱抱石頭的肩,這時候卻雞皮疙瘩起了一身。隨后石頭就抬起了手,手碰到我媽的前一刻,鳳緒已舉起了竹條大聲道,把手放下去,不許摸。石頭拖著哭腔道,把手放下去。然而,鳳緒剛把竹條放下,轉頭的一瞬間,石頭的手摸到了我媽的腿。我媽立刻在石頭的手上狠狠打了一巴掌。鳳緒舉起竹條響亮地在茶幾上打了下去。石頭哼哼著重復道,把手放下去,拿起電視遙控器坐到了角落的沙發里。
電視頻道一直在石頭手底下變換,最后停在了一場網球賽上。石頭前后搖著身體,專注地看著。鳳緒讓我媽看石頭的眉毛,其實我媽一進門就發現了,石頭的兩條眉毛干干凈凈的,禿了。鳳緒說石頭最近又迷上了剪刀,拿著剪刀到處剪線頭,明面上的剪完又把衣服翻過來剪。然后剪胳膊腿上的汗毛,之后對著鏡子把眉毛剪了。我媽還未表達出她的詫異,鳳緒繼續道,她中午睡了一會兒,起來發現石頭脫了褲子對著窗,在剪他檔里的陰毛。
石頭像聽懂了她們的話,咯咯地笑出了聲。鳳緒突然站起身,憤怒地對石頭叫道,把手拿起來。只見石頭兩只手捂在檔里,一邊笑一邊快速地揉搓著。鳳緒拿起竹條就沖了過去。石頭急忙站起身,抱住頭叫,把手拿起來。鳳緒從沙發背后扯出一個塑料袋,從里面拿出一塊花布,拿起剪刀剪了幾個小口,用力將布撕扯得亂七八糟,然后一把甩給了石頭。石頭搖頭晃腦地拿起布看了看,過去拿過剪刀,翹起蘭花指端坐在那里,開始專注地一根一根地剪起了線頭。
我媽目瞪口呆。鳳緒疲憊不堪地坐進了沙發,用手蒙住臉說,我這到底是什么命啊!隨后,她放下手望著地說,幾天前,她發現石頭總在他房間不出來,把他叫出來,不一會兒他又鉆進去。中午她做好了飯,不見石頭出來吃,就進去看他。發現石頭全身包裹著被子,卷成一團在床與墻的夾角里,發出很低的嗯嗯聲。她當時只覺著不是好事,猜是石頭捉了小貓小狗藏在了被子里,怕石頭要了小東西的命。便一把扯掉了他身上的被子,她沒看到小貓小狗,只看到石頭滿面通紅抓著他的命根子,急劇地喘著氣。鳳緒說她當時就崩潰了。人的本能不會因為沒有人傳授,沒有人引導,就消失不存在。所有人都把石頭當小孩子,都只想著怎么能教會他自立,卻忘了他已長成了一個男人。鳳緒說,她羞躁得無地自容,想一頭撞死算了。她馬上跑了出來,不知道是該阻止他,還是由著他。可是隨后就聽到聲音不對,進去看時,石頭的癲痛又發作了。我媽見過石頭病發后的樣子,躺在床上只有出氣沒有進氣,眼睛直往上翻,每發作一次都要好多天才能緩過來。醫生說,任何一種興奮都可能刺激引起病發。
鳳緒不得不全天二十四小時看著石頭。心理學一點都用不上嗎?我媽小心地問。鳳緒無力地搖了搖頭說,這不是心病!隨手從茶幾下抽出一本心理學書來,翻開只見里面大標題,以及略大一些的字,都被用筆改了,把心改成了必,把大改成天,把子改成王,更多地是改成了不存在的字。有些地方還被剪了。她的那些書都當作了石頭的安慰品,只要他能安靜下來,由著他去。他還看畫嗎?我媽向旁邊的房間揚了揚臉問。實話告訴你,他早就不看了,只要讓他看,他就捂上眼睛,鳳緒嘆了口氣說,咱們以后不提這個。
那之后的長達幾年的時間,我媽都不再帶我去鳳緒家,甚至都不對我提起他們。我莫名且罪惡的羞恥心,也不許我跟她聊起他們。但是,我還是從她與他人的聊天中,竊取了那些事。
鳳緒又帶著石頭到外省去治癲痛病了,說是在背后的脊椎上埋藥,每隔兩三年去一次。石頭長到了一米九,親友們感嘆石頭長得這樣好,五官像極了某個明星。但背后又說,人的氣質遠比長相重要,石頭雖然五官精致,可是那張呈現幻想狀的笑臉,讓人很難用英俊帥氣類的詞匯。鳳緒逐步教會了石頭坐固定線路的公交車,教會了石頭在超市拿想吃的東西要付錢,癲痛也控制得很好,他很配合吃藥。可是不知道是不是藥的緣故,石頭越來越不愿走出屋門了,一天十幾個小時躺在床上。
我再次看到石頭時,他歪倒在充滿汗腥味的床上,目光呆滯卻滿面笑容,叫我媽小姨,叫我阿姨。他的臉蒼白而略顯浮腫,已比多年前膨大了很多,唇上有小胡子,白哲的皮膚上覆蓋著濃重的汗毛。幾年沒見,我們都長大了,我已經知道笑多了會累,他永遠不會知道。我媽教石頭叫我,妹妹。他對著一旁的空氣懶懶地說了聲,妹妹。又繼續看電視。我早已聽說了石頭怪異的嗜好,他刻意搜索出信號源極差的頻道出來看。果然,電視里是受了嚴重干擾的畫面,是很早以前錄制的大合唱,深紅的幕布前,整齊的幾排穿白紗長裙和黑色禮服的人,聲音斷斷續續地傳出來,好像是黃河大合唱,畫面時而彩色時而黑白。我不禁想到了一部名叫《信號》的韓劇,死去的人從遙遠的從前,用無線電波向現在的人發出信號。我忽然醍醐灌頂,緊張地問鳳緒阿姨,石頭看這個,不會是在傳遞什么信號吧?心理學里沒有嗎?他究竟想說什么?
鳳緒站在我身后,把手搭在我的肩上捏了捏,平靜地說,他是在傳遞信號,他說他是個壞掉的機頂盒,不能正常地接收信號,所以也沒法正常對外播放。電視里各種雜音混亂的時斷時續,影像與雪花交替忽隱忽現。我無法反駁,雖然我期望有一個神秘世界,被我這樣一個天才神探破解。
鳳緒已把那間屋子里的畫全部清理了,請了一尊佛供在了那里。她說愛因斯坦在他的自傳里說過,他不是一個宗教信徒,但如果他是的話,他愿意是個佛教徒。我對佛教知之甚少,只記得武俠片里常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記得“隨緣”兩字。學校老師說,很多人信教都是形式主義的自我安慰,是一種信仰偏差。鳳緒又是什么呢?我覺著她這么多年一直都在各種偏差的路上,我媽不許我對鳳緒說,說鳳緒半輩子的好時光都是用在了石頭身上,誰又忍心說她什么。
其實別說親友,就連鳳緒的前夫都對她佩服,他親自操持著翻新整修了鳳緒娘倆的平房大院。特意修了一面玻璃墻,讓石頭躺在床上也能曬到太陽,還改造了一間古色古香的會客室。他帶著老婆孩子一起來看鳳緒和石頭,他又生了兩個女兒,一家四口從鳳緒的院子里走出來,鳳緒站在門前送他們,那情景看著倒也不使人心酸。因為他的現任老婆長得不好看,兩個女兒同樣不好看。鳳緒直直地挺立在那里,嘴角的那一抹微笑,一直掛在那里,直到他們的豪車看不見了。我媽說,鳳緒贏了。
鳳緒的頭發白了一多半,梳光了在腦后挽了一個髻,加上清瘦俊秀的模樣,很有些道骨仙風,親友們都說她天生該是個道姑。她早已又打開了她家的大門,并再次聲名遠揚。外面有說是算命,有說是心理治療,有說是通靈,她自己堅稱只是聊天會友。
那么,鳳緒究竟在邱曉云家里留下了什么?
晚上回到家,我媽也顧不得擺出要鎮住我的冷臉,讓我立刻就告訴她。我說,我看到觀音托在手里的水瓶,就知道了。她臉上先現出驚奇,隨后給了我腦門一巴掌。我又耍了她,她知道。好吧,我說要安慰一個人的不幸,必會舉出另一個不幸的人,以我媽的性格,向邱曉云講鳳緒的故事是必然的。她狠狠瞪著我,我忙又說,以邱曉云現在混亂的感情狀態,一定會病急亂投醫,鳳緒無疑是一個非常好的人選。她點了點頭問,那憑什么說她們倆最近有來往?我答,因為臺歷上被圈的星期三。她皺起眉,不明所以。我鄭重地繼續說,心理學家、精神分析學派創始人弗洛伊德在1902年創立“星期三心理學會”,星期三成為很多精神科醫生、心理咨詢師用來開會的日子,以示紀念,這樣一個有儀式感的日子,很適合對付邱曉云這類人,鎮得住。她撇著嘴揚起了臉,片刻后抬起手豎起了大拇指。
·作者簡介·
流瓶兒,本名劉愛萍,新疆七零后,現居博樂市。獲第三屆西部文學獎小說獎。作品見《西部》《清明》《綠洲》《伊犁河》《雨花》《中篇小說選刊》《文藝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