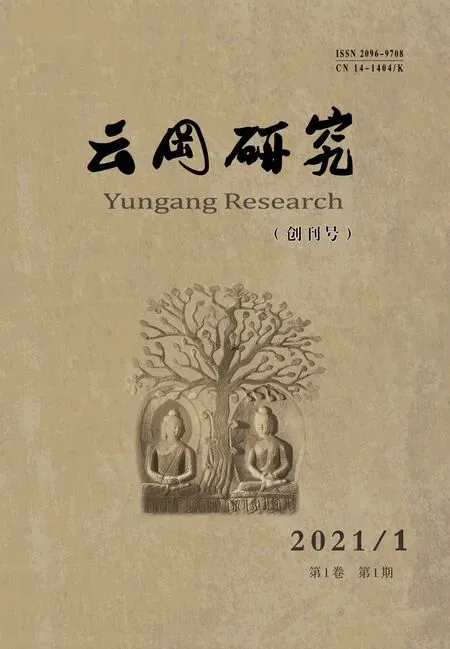應縣木塔《稱贊大乘功德經》應依《遼藏》雕印
胡玉平,杜成輝,,馬志強
(1.四川文理學院圖書館,四川 達州 635000;2.山西大同大學云岡文化生態研究院,山西 大同 037009)
應縣木塔秘藏中共發現有刻經47卷,其中12卷有千字文帙號,多數研究者認為這12卷全部屬于《遼藏》(也稱《契丹藏》)。這12卷帶千字文帙號的經卷均為卷子本,款式為硬黃紙卷軸裝,完整者軸、桿、縹帶、別子俱存,其中5卷有卷首畫,3卷蓋有藏經戳記。在這之前,《遼藏》在世間無傳本,被稱作“虛幻的大藏經”,而應縣木塔遼代秘藏的發現,使這一重要經藏重見天日。[1](前言,P12)
在12卷有千字文帙號的經卷中,編號為6(為行文方便,以下簡稱M6①M為拼音木塔秘藏之首字母。,其他共出經卷編號同)的《稱贊大乘功德經·一·女》(以下簡稱《稱贊大乘功德經》),千字文編號為“女”,“一”為版碼,根據題記和規制等,可以確定此經為單刻經。
一、題記標明該經為私刻經
M6《稱贊大乘功德經》紙質為硬黃紙,卷軸裝,包首微殘,其余完好,軸、桿、縹帶均系原物。該經卷末有刻經題記,云:
燕臺圣壽寺慈氏殿主,講《法華經》、傳菩薩戒懺悔沙門道譔,曾閱前經,備詢故事,曰:“大乘者,諸佛至真了義究竟之說也。不思議解脫,寧可述矣。先圣既至極稱贊,末葉宜激勵流通。庶幾報諸佛恩,除小乘病,最極最大,至微至妙,利國利家,濟時濟物,無如此經也。”道譔遭逢圣代,幸偶遺風,敢雕無上之經,溥示有緣之眾。所愿:
見聞隨喜者,舍小根而趣大機;讀誦歸依者,得清涼而除熱惱。
時統和貳拾壹祀,癸卯歲季春月蓂生五葉記。
弘業寺釋迦佛舍利塔主沙門智云書。
穆咸寧、趙守俊、李存讓、樊遵四人共彫(雕)。[1](敘錄,P27)
《稱贊大乘功德經》是三藏法師玄奘于唐永徽五年(654年)所譯,又名《顯說謗法業障經》,此卷系燕京圣壽寺沙門道譔組織雕刻。宋朝建立初年,與遼朝戰事不斷。宋太祖開寶元年(968年)和開寶二年,兩次出兵進攻北漢,都因遼朝出兵援助,無功而返。開寶九年(976年),宋軍第三次進攻北漢,不料兩個月后太祖趙匡胤駕崩,遼朝又出兵支援北漢,新登基的趙光義只得下令撤兵。太平興國四年(979年),宋太宗趙光義親自統兵進攻北漢,包圍太原城,擊潰遼朝援軍,迫使北漢投降,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面宣告結束。太宗趁滅北漢之勢,從太原出發北伐,一度收復河北易州和涿州。太宗下令圍攻燕京,宋軍與遼軍在高粱河畔展開激戰,趙光義親臨戰場,結果中箭受傷,乘驢車倉惶撤離,北伐失敗。雍熙三年(986年),宋太宗乘遼朝新君初立之機,派三路大軍北伐,以圖收復燕云十六州,結果慘敗。遼圣宗統和二十一年(宋咸平六年,1003年),遼宋兩國于定、宋二州激戰,這時宋朝新刻的大藏經(《開寶藏》)不會贈予遼朝;為了顏面,遼藏也不會以敵國宋藏之帙號給自己的大藏經編次,故此經所附千字文集帙號“女”,只能源于遼朝新藏——即已有官刻《大藏經》,為道譔刻經所據。[1](前言,P28)道譔是遼圣宗時人,燕臺(即燕京,今北京)圣壽寺慈氏殿主,講《法華經》、傳菩薩戒懺悔沙門,主持資刻《稱贊大乘功德經》。燕京圣壽寺在昊天寺西北,寺之故基為遼統軍鄴王宅,開泰六年(1017年)改為開泰寺。此經在木塔所出經卷中最為完整,刻經時間、地點、資刻人、書寫人、刻工等記錄最為翔實,對于研究遼代的雕版印刷業和《遼藏》的雕印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關于此經是否屬于《遼藏》,研究者中一直存在爭議。多數學者根據經在卷首經名下刻有千字文編號“女”,而認為該經屬于《遼藏》。如1982年閻文儒、傅振倫、鄭恩淮在《山西應縣佛宮寺釋迎塔發現的〈契丹藏〉和遼代刻經》中,認為此經屬于《遼藏》,從卷尾題記可以推知《契丹藏》是在遼圣宗耶律隆緒統和年間用漢字書寫雕印于遼的南京(今北京)。[2]1986年張暢耕、畢素娟在《論遼朝大藏經的雕印》一文中,一方面認為其乃私刻單經,另一方面認為其是準官版大藏經覆刻,實際上仍認為其屬于《遼藏》。[3]1991年張暢耕、鄭恩淮、畢素娟在《應縣木塔遼代秘藏·前言》中,將該經列入《遼藏》,并認為“統和廿一年沙門道譔復刻的《稱贊大乘功德經一女》的發現,確證遼藏始雕于圣宗統和時期”。[1](前言,P12)史樹青、張暢耕、畢素娟、鄭恩淮、馮鵬生、傅振倫在《應縣木塔遼代秘藏·敘錄》中,也持同樣的觀點。[1](敘錄,P28)而1983年羅炤在《〈契丹藏〉的雕印年代》中,則認為《稱贊大乘功德經》尾題明確記載系燕臺圣壽寺沙門道譔私刻單經,不是官版《遼藏》(《契丹藏》),[4]之后1992年又在《有關〈契丹藏〉的幾個問題》中進一步表明了此觀點。[5]1994年日本學者竺沙雅章在《由新出資料所見之遼代佛教》中,也認為該經不屬于《契丹藏》,主張其可能是僧侶私人用品。[6]方廣锠在《第三種遼藏探幽》一文中,也基本同意羅炤和竺沙雅章的觀點。[7]
目前只有一些間接的證據表明《遼藏》可能雕印于遼圣宗統和年間(983—1012年),尚未發現能夠證明遼圣宗太平年間(1021—1031年)雕印《遼藏》的實物資料。《稱贊大乘功德經》卷尾的刻經題記標明,此經并不屬于《遼藏》,而是單刻經卷。
二、《稱贊大乘功德經》與《遼藏》規制不同
木塔秘藏中12卷有千字文帙號的刻經中,目前可確定屬于《遼藏》的有7卷,分為兩種版本。分別為M1《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四十七·垂》,M7《大法炬陀羅尼經卷第十三·靡》,M8《大方便佛報恩經卷第一·欲字號》,M9《中阿含經卷第三十八·凊》,M10《阿毗達磨發智論卷第十三·弟字號》,M11《佛說大乘圣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一卷·刻》,M12《一切佛菩薩名集卷第六·勿》,其特點是上下單線邊框,在開頭用一行小字注明經名卷次、板碼及千字文編號,每紙經文27行,行16—18字。其中M8《大方便佛報恩經卷第一·欲字號》、M10《阿毗達磨發智論卷第十三·弟字號》的標碼方式與其他各經又有不同,應為另一種版本。其它包括M2《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二十四·愛》、M3《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二十六·愛》、M4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五十一·首》,其共同特點是上下雙線邊框,每紙第l、2行行間雕印經名、卷次、版碼、軼號,每紙經文28行、行15字,羅炤認為其為另一種版本的《契丹藏》,或者是復刻《契丹藏》的單刻經,并改變了方式(板式)。[5]竺沙雅章則認為不能肯定它們是否大藏經本,由于3卷均標有朱點,主張其可能是僧侶私人用品,實際上主張這3卷《華嚴經》是另刻單經。方廣锠贊同竺沙雅章的觀點,也主張其為另刻單經。[7]因這3卷為同一部經典,故其為單刻經的可能性較大。另外2卷,M5《妙法蓮華經卷第二·在》每版刻有小字“第二”及版碼,M6《稱贊大乘功德經·女》則只有小字版碼,羅炤和竺沙雅章均認為其不屬于《遼藏》。
從版式來看,M6《稱贊大乘功德經·女》在第1紙卷首經名下刻印版碼,在第2、3紙的第1、2行行間上方刻印版碼,在第4紙末、第5紙第6行下也刻印版碼,但未刻經題、卷次和帙號,卷尾經題下亦無帙號,與《遼藏》的版式不同。該經有“女”字帙號,說明它的底本是從某部依千字文編次的大藏經中選出來,加以復刻,甚至可能是以某一大藏的復寫或復刻本單經為底本,再加雕刻或復刻。從中、晚唐和五代的經錄可知,當時存在著多種依千字文編次的大藏經。至于應縣木塔的《稱贊大乘功德經》依作底本的究竟是哪一種,道譔未言明,我們也無從知曉。在沒有證據證明此經所據的底本是所謂《統和藏》的情況下,無法確定它與《遼藏》之間的關系。[5]
一般來說,大藏經版片,由于卷帙浩繁,數量巨大,為了便于管理,查閱歸放,不致混淆,每塊版片上一定會標注經名卷次、帙號、片序號等內容。而另刻單經,則根據情況不同而有區別。如果經文篇幅不大,版片不多,則往往僅注序號。如果僅有幾片,容易區別,也有不標注版片序號的。但如果經文篇幅較大,版片較多,也有進一步標注經名卷次的。如果另刻單經的底本來自大藏經,則往往有照刻千字文帙號的。M6《稱贊大乘功德經·女》共5紙,也即僅有5塊版片,只在第一紙第一行經名下刻千字文帙號“女”,其他各紙則僅有版片序號,序號位置也不固定,無經名卷次和帙號,由此可以肯定,該經與《遼藏》規制不同,故不屬于《遼藏》,應屬另刻單經,其千字文帙號說明它的底本應源自某一大藏經。
M6《稱贊大乘功德經》規制也與其他經卷不同。其經框高 21.8cm,版廣 52.7—53.5cm米,紙縱27.8cm,總長275.3cm。每紙28行,每行字數也不一致,行17字者24行,行16字者69行,行15字者21行。與同出的其他帶有千字文帙號的經卷相比,形體略小。[1](敘錄,P27)如M7《大法炬陀羅尼經卷第十三》,千字文編號“靡”,框高22cm,版廣53—54cm,紙縱29.5cm,現存總長865.7cm。全卷共17紙,前有卷首畫,經文16紙,每紙27行,行17字者296行,行18字者50行,行16字者47行。[8](P167)此經經背有“神坡云泉院藏經記”長方朱印,可基本確定其為大藏經即《遼藏》。畢素娟認為“私刻本《稱贊大乘功德經·女》因其保留了同卷《遼藏》原貌,故將其視為《遼藏》覆刻本。”[9](P354)此觀點難以成立,因為其版式并非標準的《大藏經》版式,最多為復刻本。
該經有可能根據《統和藏》刻印,而當時統和藏或許只是寫經,尚未刻印,或許只刻印了前480帙,5048卷的初印本,具體情況目前尚難確定。金皇統八年(1148年)《宜州廳峪道院復建藏經千人邑碑》云:“凡所貯藏有五千四十八卷,故名曰《藏經》。廳峪者,乃遼時耶律詳袞家之墳所也。其家世積善,遂卜地以建佛宮,置以《藏經》。”[10](P1389-1390)時趙城金藏尚未雕印,其藏經應為《遼藏》。可知《遼藏》有5048卷,此當為《遼藏》初藏的卷數,后來續有增補,達到了579帙,約6000卷。何梅研究認為,《遼藏》乃依《開元錄·入藏錄》進行編目,《遼藏》與《隨函錄》之間沒有什么關系,并非象一些學者認為的那樣依《隨函錄》進行編目。[11]因此《遼藏》初藏和《開寶藏》初藏一樣,均以《開元釋教錄》入藏經目為底本,也為480帙,5048卷。
我國刻印佛教經典全藏始于宋太祖開寶年間(968—976年)。《開寶藏》初藏于開寶四年(971年)在益州(今四川成都)開雕,因當時江南尚未平復,剛收復不久的益州為宋朝轄境內造紙業和印刷業最發達的地區。至太平興國八年(983年)時雕畢,共費時12年,所刻以《開元錄》入藏之經為限,共480帙,5048卷,版片多達13萬余塊。而此時宋朝已收復江南,于是將刻好的版片運到都城東京開封太平興國寺印造流通。《開寶藏》為卷軸式,每版23行,每卷中行字不一,多為每行14字,版首刻經題、版號、帙號等;卷末有雕造年月干支題記。后來新譯佛經也陸續雕版,一起刊印流通,還添刻新入藏的東土著作及《貞元錄》各經,數量增至653帙,6620余卷,其印本成為之后中國官私刻藏以及高麗和日本刻藏的準據。M6《稱贊大乘功德經》版式與《開寶藏》差別較大,非依《開寶藏》覆刻或復刻。
《開寶藏》首刻全藏印本在北宋雍熙元年(984年)由日本沙門奝然傳入日本。此后經過三次比較重要的校勘修訂和不斷增入宋代新譯及《貞元釋教錄》入藏的典籍,形成三個不同的版本:①咸平修訂本,為北宋端拱二年(989年)到咸平(998—1003年)年間的校訂本;②天禧修訂本,為北宋天禧(1017—1021年)初年校訂本,于乾興元年(1022年)傳入契丹(遼國)和高麗;③熙寧修訂本,為北宋熙寧四年(1071年)的校訂本,于元豐六年(1083年)傳入高麗。熙寧以后,陸續有新譯本增入,到北宋末年,積累到653帙,6628余卷,增入173帙,1580余卷。《開寶藏》全藏久已無傳,現存殘卷皆硬黃紙印,卷軸裝,開寶年間雕刻,多印刷于崇寧、大觀(1102—1110年)時。《開寶藏》以書法端麗嚴謹,雕刻精良著稱,并用宋代官用文書的黃麻紙精工刷印,為宋版精品,彌足珍貴。《開寶藏》與《遼藏》現存數量大體相當,均為10余卷,但《開寶藏》存卷印刷時間晚于《遼藏》存卷。
三、《稱贊大乘功德經》為復刻單經
《開寶藏》和《契丹藏》(《遼藏》)俱為官版,由國家出資,因此并無施資人,在經版上也不鐫刻工姓名。《稱贊大乘功德經》卷末既有施資人,又有刻工姓名,也與官版《大藏經》的特征不符。宋神宗元豐三年(1080年),由沖真、普明、咸暉等主持,在福州東禪寺募款開雕大藏經,至宋徽宗崇寧二年(1103年)竣工,前后歷時23年,共雕印6434卷,580函,經折裝。今傳世的東禪寺大藏經本《華嚴經》卷80有“福州東禪院等覺院住持慧空大師沖真于元豐三年庚申歲謹募眾緣,開雕大藏經版一副,上祝今上皇帝圣壽無窮,國泰民安,法輪常轉”[12](P55)題記,說明了刻經緣起,是為上祝皇帝圣壽無窮,國泰民安,故此經得名《崇寧萬壽大藏》,是我國民間募刻大藏經的開始,也是藏經改為經折裝(又稱梵筴裝)的濫觴。該藏為私刻,偶有題記屬于正常,但遼藏為官刻,不應有私人資刻題記。
以藏經本為底本的另刻單經有兩種情況:一種是覆刻(也作復刻),即將某種藏經的印本紙張反貼在版片上,磨去紙張,留下字痕,然后按照字痕雕版。南京金陵刻經處至今仍保留這一工藝。按照這種方式刻成的典籍,版式、風格與底本基本一致,甚至可以亂真。《初刻高麗藏》、《趙城藏》的大部分經本都是《開寶藏》的覆刻本,因此,它們的文字風格乃至字間距都保持一致。另一種是以某種藏經的經本為底本,重新書寫上版,再予雕版(有時也稱復刻,實為重新雕刻,但不同于覆刻)。按照這種方式重新雕刻的典籍,與原底本的版式或許一致,或許不一致;風格則肯定難以保持一致。[7]
從《稱贊大乘功德經》刻本的情況來看,因其規格和《遼藏》不同,不可能是《遼藏》的覆刻本,只可能是《遼藏》的重刻本,其所依據的版本,很可能就是480帙的《遼藏》初藏本,而此本很可能就是一些學者所主張的《統和本》,雕刻于遼圣宗統和年間。“女”在千字文中順序為161,正好在初藏480帙的覆蓋范圍內。
《開寶藏》在卷末刻有雕造年代,如1959年在山西孝義縣興福寺發現的《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581,千字文帙號“李”,卷末有“大宋開寶五年壬申歲(972年)奉敕雕造”字樣;現存山西高平市文博館的《大云經請雨品第六十四》,千字文帙號“大”,卷末雕“大宋開寶六年癸酉歲(973年)奉敕雕造”字樣。與《開寶藏》不同,《遼藏》印版不刻雕刻年代,史料中也無記載,故目前對《遼藏》的開刻時間尚難確定。
《開寶藏》現存13卷,標準的版式為每紙23行,行14字。從應縣木塔的《契丹藏》零卷和大安九年(1093年)以后依照《契丹藏》為底本復刻的小版房山石經可以看出,《契丹藏》的版式為每紙27行,行17字,間有行18、16字者。[13]與二者相比,M6《稱贊大乘功德經》的版式更接近《契丹藏》。羅炤認為《契丹藏》雖然晚于《開寶藏》數十年,其前480帙所據的底本卻早于、優于《開寶藏》的底本,其經文、版式均反映了《開元錄藏》的面貌,因此,在漢文佛教大藏經的歷史上,《契丹藏》的價值和地位應高于《開寶藏》。[13]筆者認為兩種藏經互有優劣,其價值和地位不相上下。
M6《稱贊大乘功德經》的4刻名工中,趙守俊和樊遵也見于其它遼代刻經。與M6《稱贊大乘功德經》同出之M18《妙法蓮花經卷第四(甲)》,卷首畫右上角有牌記:“燕京雕歷日趙守俊并長男少男同雕記”,說明趙守俊的主要職業是雕刻日歷,其所以雕刻此經,是為了出售獲利,因為《妙法蓮華經》需求量巨大,故其在雕刻日歷之余,也雕刻單編刻經,趙守俊父子3人皆從事雕刻業。此趙守俊與M6《稱贊大乘功德經》的刻工趙守俊當是一人。題記中不見印經院之名,說明當時遼朝可能尚未設立印經院。當然由于二經為私刻,非由印經院組織雕刻,故不能完全排除設立印經院的可能。在內蒙古巴林右旗慶州白塔發現的遼代刻經《佛形像中安置法舍利記》(小字版)中,其中1卷標有“燕京憫忠寺抄主無礙大師門人苾蒭智光集”(原文缺“苾”字,據圖版補),“統和二十五年(1007年)歲次丁未五月十五日記,樊遵雕,始平龐可昇書”。[14]此樊遵為統和時人,與M6《稱贊大乘功德經》中的刻工樊遵應為一人。另2卷亦有“燕京憫忠寺抄主無礙大師門人苾蒭智光集”,后記中有:“開泰十年(1021年)二月福先寺講經論比丘志淵依燕本雕印散施。”二種版刻相校,開泰版結尾缺“證辱”2字,余皆相合。福先寺為遼上京佛寺,志淵雕印、散施的這一卷,從字體、版式等方面分析,似雕印于上京地區而非燕京。[14]《佛形像中安置法舍利記》也不屬于《遼藏》。從這兩位刻工來看,其所雕刻之M18《妙法蓮花經卷第四(甲)》和《佛形像中安置法舍利記》俱屬單編刻經,他們4人合雕的M6《稱贊大乘功德經》,根據各種特征來看,也不屬于《大藏經》(《遼藏》),而只能是依據《大藏經》或者其它單編刻經復刻的經卷。但因其有千字文編號“女”,說明其源于某部《大藏經》,至于是否依據《遼藏》,尚需進一步考證。
四、《稱贊大乘功德經》依《遼藏》雕印
據羅炤先生考證,《契丹藏》有卷裝本和冊裝本兩種類型,在應縣木塔的10卷卷裝本《契丹藏》中,又可能分屬于兩種不同的版本。[5]他認為《契丹藏》前后有兩個版本:一為統和本,一為重熙-咸雍本。統和本共505帙,編校主持人詮明,目錄為《開元釋教錄·入藏錄》及詮明所撰《續開元釋教錄》(三卷)。重熙-咸雍本共579帙,編校主持人可能是覺苑,目錄是某太保大師(可能即覺苑)所撰《(契丹藏)入藏錄》。[15]至于505帙的統和本《契丹藏》,是新雕版印刷,還是僅僅搜集《開元錄藏》及其后續經典,重加編訂謄錄,但未雕版,因缺物證及文獻記載,尚難以斷定。道譔私雕《稱贊大乘功德經》不能計為統和本《契丹藏》。遼興宗重熙年間,對大藏經“復加校證”,制成新版,共579帙,比《開元錄藏》多出99帙,增添五分之一強。羅炤先生根據北京西北郊大覺寺《陽臺山清水院創造藏經記》及《遼史·道宗本紀》咸雍四年的有關記載推斷,這一新版完成于咸雍四年(1068年),故稱之為《契丹藏》重熙-咸雍本。[15]
目前我國僅存的貯藏遼藏的佛殿——山西大同華嚴寺薄伽教藏殿,其梁架題記有:“維重熙七年,歲次戊寅,玖月甲午朔,十五日戊申午時建。”說明該殿建于遼興宗重熙七年(1038年),所藏的大藏經應為《契丹藏》印本,而不是抄本。重熙七年上距遼圣宗駕崩的太平十一年(1031年)不過7年,其時《遼藏》已經雕成,由此推斷,《契丹藏》初藏應開雕于遼圣宗統和至太平年間。因此《契丹藏》咸雍四年之后方雕畢印刷流通的應當為二版。
與M6《稱贊大乘功德經》同出的單經《上生經疏科文》,共14紙,未避遼諱。卷首題刻“燕臺憫忠寺沙門詮明改定”,卷末有“時統和八年歲次庚寅八月癸卯朔十五日戊午故記,燕京仰山寺前楊家印造,所有講贊功德,回施法界有情”題記,可知此經刊印于遼圣宗統和八年(990年),這是目前發現的已知年代最早的遼代印刷品。燕臺憫忠寺即今北京法源寺之前身,建于武則天萬歲通天元年(696年),遼時為燕京首剎,詮明駐此弘法,并于統和八年建釋迦太子殿一座。[16]憫忠寺鈔主無礙大師詮明(高麗義天《新編諸宗教藏總錄》稱詮曉,舊名詮明,可能為避諱而改)為遼圣宗時名僧,著述豐富,曾主持遼朝大藏經的編纂。[1](敘錄,P43)仰山寺據《元一統志》輯本卷一載:“在大都(今北京)舊城歸厚坊。佛殿題梁乃遼穆宗應歷十一年(961年)歲次辛酉八月十五日建”。[17]該經保存完整,印刷質量上乘,說明在統和八年時遼朝印刷業已具規模,有私坊刻印佛經出售。在同出之M44《法華經玄贊會古通今新抄卷第二》卷末題記云:“四十七紙,三司左都押衙南肅二十二紙,孫守節等四十七人同雕。伏愿:上資圣主,下蔭四生。聞法眾流,多聰圣惠。龍花同遇,覺道齊登。法界有情,增益利樂。”[1](敘錄,P46)M45《法華經玄贊會古通今新鈔卷第六》卷尾有:“五十六紙,云州節度副使張肅一紙,李壽三紙,許延玉五紙,應州副使李胤兩紙,趙俊等四十五人同雕。伏愿:上資圣主,下蔭四生。聞法眾流,多聰圣惠。龍花同遇,覺道齊登。法界有情,增益利樂。”[1](敘錄,P47)可知當時刻工人數眾多。
內蒙古慶州白塔出土的卷軸裝《妙法蓮華經》后載,此經“取則于圣壽寺藏”,始于“開泰二年(1013年)六月一日”,“請處士樊承遵放(於)法華座主藏院內起手雕板”,“開泰五年(1016年)”,“方始了畢”。由“法華座主弟子惟德述新雕小字法華經記”,“時開泰六年四月八日續記”,可知這部《法華經》開泰六年(1017年)付印散施。[14]圣壽寺在燕京,即道譔所在的寺院。開泰上承統和,統和三十年(1012年)十一月,改元為開泰元年。因開泰元年的使用時間只有一個多月,開泰二年(1013年)六月一日與統和三十年(1012年)十一月僅相隔半年多。此卷《妙法蓮華經》的開雕只比M6《稱贊大乘功德經》晚十年,卷中明載“取則于圣壽寺藏”,說明在燕京圣壽寺確實存有《大藏經》,且此經藏當為刻經《遼藏》,如果是抄本,就不會被刻本“取則”。因雕刻大藏經耗時頗長,故其應開雕于開泰二年(1013年)之前,也即圣宗統和年間(983—1012年),藏經當為《統和藏》。《妙法蓮華經》收錄于《遼藏》,慶州白塔出土的卷軸裝《妙法蓮華經》雖沒有千字文帙號,但作為復刻單經,不標帙號也是正常的,不能因此就認為其依照的不是大藏經。此題記為《統和藏》的存在提供了有力證據。因此推測M6《稱贊大乘功德經》依據《統和藏》復刻,并非無稽之談。
在木塔秘藏中,既有帶千字文編號的M5《妙法蓮華經卷第二·在》,也有多種不帶千字文編號的《妙法蓮華經》刻本,這些不帶千字文編號的刻本當為單刻經。在圣壽寺所存經卷的情況可能也類似,通常情況下還是難以確定慶州白塔出土的《妙法蓮華經》究竟是取則于圣壽寺所藏的《大藏經》還是單刻經。但由“取則于圣壽寺藏”,可以肯定圣壽寺確實存有《大藏經》,因為“藏”專指大藏經,慶州白塔出土的《妙法蓮華經》應取則于圣壽寺大藏經。則道譔依本寺所藏之大藏經復刻《稱贊大乘功德經》也在情理之中,正因為取則于本寺所藏的大藏經,所以在題記中也就不必言明。果真如此的話,則《遼藏》當雕刻于統和二十一年(1003年)之前,大約開雕于統和初年。
有意思的是,遼圣宗統和元年(983年)正好當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年),而太平興國八年乃《開寶藏》初藏雕畢之年,因此《遼藏》應最早雕刻于統和初年,不會更早。二者開雕時間相距不遠,即在《開寶藏》初藏經十二年雕刻完工后不久,《遼藏》即開始雕刻。《遼藏》的開雕肯定是受到了《開寶藏》的啟發,但其并非依照《開寶藏》雕印。如前所述,《開寶藏》在宋真宗乾興元年(遼圣宗太平二年,1022年)方傳入契丹,而據慶州白塔出土的卷軸裝《妙法蓮華經》,開泰二年(1013年)之前,遼朝已有印本大藏經,故而《遼藏》初藏雕印于統和(983—1012年)時期的可能性很高。當然此觀點正確與否,尚待新資料的發現來驗證。
結語
作為最早的遼代印刷品之一,M6《稱贊大乘功德經》雖為單刻經,但對于研究《遼藏》的雕印仍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如此精美的印刷品,如果不是取則于已經雕印的大藏經,而是取則于抄本的話,其大可不必在卷首標明其千字文帙號,因為作為單印本,其據抄本標出千字文帙號并無意義。通常情況下,只有在根據印本覆刻或復刻時,才會有時保留印本的一些原始信息,如千字文帙號和雕刻年月等,以標明其依據。根據出土實物資料,基本上可以確定《遼藏》初藏雕印于遼圣宗統和時期,但因現存遼藏未標明雕刻年月,此推斷是否正確,尚需進一步的考古發現來證明。文中牽強不妥之處,敬請方家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