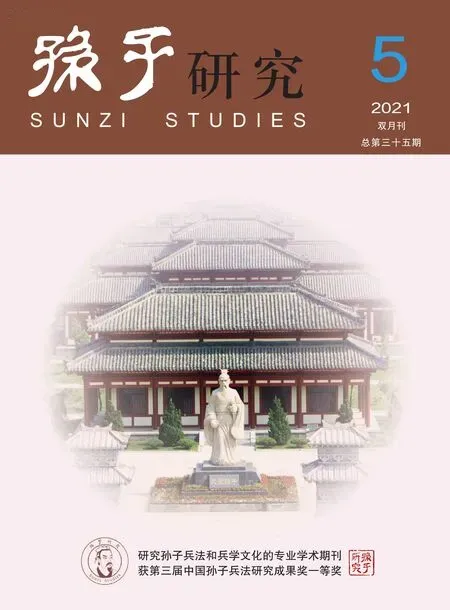中國共產黨領導天津革命斗爭中體現的兵學謀略
徐 勇 付琳雅
自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在黨的領導下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奮斗中,百年間天津社會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近現代革命活動中得到了輝煌成就,在當代社會主義建設中得到了顯著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經濟社會全面進步,生活環境得到有效改善。其中,各個階段的天津革命活動和發展歷程都與兵學謀略深度契合,黨在每個歷史節點上的卓有成效的領導,無不閃爍著兵學智慧的光芒。
一、建黨前李大釗、張太雷等人在天津的革命活動
《孫子·計篇》指出:“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這句話說出了政治的本質,成功的政治就是讓民眾認同和擁護國家領導者的主張,從而達到人們心甘情愿地為國家目標的實現付出性命,而不懼危難,不顧險阻。建黨前,李大釗、張太雷等人在天津積極投身革命活動,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傳道”者。正是在他們的努力下,馬克思主義在天津迅速地傳播開來,也培養了一大批愿意為實現理想而獻身、不懼生死的青年愛國者。
《黃石公三略·下略》中說:“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獲天下之福。”這句話中以“危”與“安”、“憂”與“樂”、“禍”與“福”的三組對比,論述了賢者之才與時代重任的辯證關系。能夠在遭遇社會危機之時力挽狂瀾的人,才能保證一方的平安;能夠消除社會民眾憂患的人,才能享受眾人所享的快樂;能夠拯救社會民眾免于災禍之苦的人,才能獲得眾人的尊敬與祝福。反過來,在社會處于危難之際、憂患之間、災禍之中,飽受煎熬的民眾必然期盼著被智者賢者救于水火之中,社會的安定、幸福與和平需要能人志士的守護和捍衛。從這兩方面來看,少數的賢者既具有造福社會的卓越能力,又承擔著報效國家的時代責任。古人樸素的辯證法中體現著仁人志士修身治國平天下的邏輯認識和社會期待。
20世紀初的天津,與全中國一樣都在探索救國圖強的出路。李大釗和張太雷等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最早接觸馬克思主義,并成了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李大釗和張太雷積極在天津組織革命活動,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進一步強化了革命力量,促進了進步團體的建立。1907年至1913年的6年間,李大釗在天津讀書,就讀于天津北洋法政學堂。1916年,李大釗回到祖國,成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1〕十月革命爆發后,李大釗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思想,長期在《言治》《新青年》等雜志發表社論文章,并與天津學界充分聯絡和交往,涉及北洋大學、南開中學、北洋政法專門學校的廣大學生,天津新中學會、中國學會的會員和參與者,以及中華書局等文化機構的工作人員,促成馬克思主義思想在天津知識分子中的傳播。〔2〕天津廣大進步青年受到李大釗的啟發,開始對馬克思主義道路和中國革命充滿信心。
在新思想的感召和馬列主義的影響下,天津廣大進步青年學生積極投身新的革命實踐,極大地推動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在天津的開展。1918年,以京津兩地學生為主的“學生救國會”成立。其中,作為北洋大學學生代表,張太雷廣泛組織天津學生,成功發動了反對段祺瑞政府賣國行為的示威請愿活動。五四運動爆發兩日后,天津學生代表組成了聲勢浩大的示威請愿隊伍,其中包括天津十多所中等學校的學生代表和北洋大學的學生代表。由近千人組成的示威請愿隊伍聚集在北洋大學的禮堂,強烈抨擊日本帝國主義、軍國主義的惡劣行徑和侵略野心,對北洋政府屈辱賣國的行徑進行強烈譴責,以此聲援北京學生。〔3〕
在大規模示威活動的推動下,反帝愛國的革命熱潮不斷高漲,天津進步青年學生組織在革命實踐中日益壯大,在早期革命實踐中,天津學子發揮了應有的作用。天津學界的團結和努力,促進了進步刊物的創辦、刊發和流傳,促進了區域性進步組織和團體的建立、發展,天津學生聯合會、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等由天津學生組成的愛國組織正是在這一歷史時期成立和發展起來的。隨著進步組織的創立,天津地區的示威活動和馬克思主義思想宣傳活動以更高頻次開展,對社會各界群眾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同時,天津學生團體積極拓展與北京、上海等城市學生組織的交流與合作,在全國范圍內協同共進,積極配合開展革命斗爭。天津反帝愛國運動的熱潮也促進了海外學子的歸國和投入革命實踐。五四運動爆發時,周恩來正在日本讀書。當他聽說了南開學校創辦大學部(今南開大學)的消息,立即決定回國求學并投入到反帝愛國運動的熱潮之中。周恩來回國后,積極參與并領導天津學生界開展革命活動。《天津學生聯合會報》在1919年創刊,發刊詞《革心!革新!》由周恩來撰寫并于7月21日刊發。同年9月16日,周恩來充分團結天津學生界的精英,并與天津學生聯合會等學生組織的骨干成員共同創立覺悟社,參與創建覺悟社的人員包括鄧穎超、郭隆真、劉清揚等人。以天津學生為主的進步團體覺悟社在天津學生愛國運動組織和發動中發揮了核心作用。
進步團體的成立,強化了革命力量,成為馬克思主義思想在天津傳播的前沿陣地。隨著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深入傳播,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熱情逐漸高漲,愛國主義運動在全社會范圍內以更廣泛的形式開展。1919年10月10日,在南開大學操場舉行的請愿活動,參與者包括社會各界和各行業人士,社會影響力得到進一步提高。這次示威活動由周恩來等人組織和發起。1920年1月 29日,在周恩來等骨干的組織下,天津數千名學生組成示威請愿隊伍,向北洋政府抗議。〔4〕
二、建黨初期在天津的組織建設和活動
《孫子·計篇》中說:“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任何事情都需要預先準備,扎實的基礎和充分準備是做事成功的必要條件。特別是軍事方面,關系到國家安危,更要做到籌劃在先,分析縝密,計劃周全,預先做好充分準備,謀定而后動。中國古代兵家歷來有先勝而后求戰的兵學謀略傳統。《何博士備論·楚漢論》提出:“然天下卒歸之者,蓋能收人之智而任之不疑也。”其中特別申明,戰爭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是任人唯賢、用而不疑。兵學,表面上探討的是戰事,本質上討論的是人事。將領的任用、隊伍的士氣、戰略的判斷等至關重要的方面,都是人在其中發揮著關鍵作用。回顧歷史,楚漢之爭,楚霸王項羽的軍事實力更為強大,卻敗于漢高祖劉邦,這其中留下了深刻的經驗教訓。項羽縱然兵力強盛,勇猛剛勁,但在智斗與用人方面不如劉邦。軍事的較量是全過程的,而非單純的瞬間力量對比。項羽以勇勝,而劉邦以智斗,在較量的過程中,項羽的軍事實力和優勢未能最大化地發揮。而反觀劉邦,雖然客觀上實力不如項羽,但在調度安排和謀略謀劃方面比項羽謹慎而老成得多,善于任人,依靠眾人的智慧取得了戰爭的最終勝利。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天津革命活動和黨團組織建設穩步開展,特別是培養了一批人才,壯大了革命隊伍,在黨成立初期,為日后革命力量的進一步發展和革命活動的逐步高漲做了思想上、組織上的充分準備。9月,按照中共一大決議和會議精神,革命活動首先在工人階級中深入推進和充分開展起來。為促進工人群眾革命運動的長期化和規范化,天津成立了第一所專門面向工人階級的學校,名為天津工余補習學校。工人學校創辦后隨即成了黨領導和發起工人群眾運動的重要組織和機構依托。天津工人學校的創辦離不開天津黨組織的指導和北洋法政專門學校等教育部門及其工作人員的幫助,其中教師于樹德和安體誠參與策劃和組織,積極促成工人學校的建立。次年,為促進工人運動的深入開展,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在天津成立支部,進一步增強工人群眾的勞動保護意識和政治參與能力,從而促進了勞動立法運動在天津工人群眾中廣泛開展,進一步提高了工人群眾參與運動的規模性、宣傳的廣泛性和影響的深入性。〔5〕
天津黨組織的發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充分的群眾基礎和組織建設上逐步發展而來的。在黨組織正式成立之前,天津相關組織工作由社會主義青年團開展。天津社會主義青年團小組自1920年10月成立以來,以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為目標,積極開展革命工作,被共產國際認為是“比較徹底的中國青年組織的楷模”〔6〕。天津社會主義青年團地委于1924年3月重新成立。至同年9月,經過多年的組織建設和人才培養,天津黨員人數近20 名,基本具備了天津地方黨組織成立的條件。〔7〕
1924年9月,中共天津地委成立,隨即為天津地區的革命運動注入了強大的領導力、凝聚力和影響力。革命運動在社會各界廣泛開展,工人、農民、學生和婦女都加入到革命運動中,革命運動深入到紡織、鐵路等各個經濟領域和行業,革命思想在社會各界得到傳播,黨員發展工作和革命骨干培養工作在各行業中扎實推進,從而壯大了革命的力量。受到五卅慘案的直接刺激,天津革命運動于1925年掀起了高潮。6月5日,在天津地委的領導下,天津第一次市民大會召開,萬余名市民參加大會,其中包括教師、學生等社會各界群眾;五天后,天津反帝愛國力量團結起來,成立天津各界聯合會,由此天津各個愛國團體和社會各個領域、階層的反帝愛國人士聯合起來了,在聯合會主席團主席鄧穎超的帶領下,聯合會充分動員社會各界愛國群眾和反帝團體參與組織革命活動,先后在全天津市范圍內動員和組織了三次大規模的群眾性革命運動,展現了極大的斗爭熱情和革命信心。
三、抗日戰爭時期中共在天津領導的城市斗爭和武裝反抗
《孫子·謀攻篇》中云:“故知勝有五,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識眾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孫子·形篇》也說:“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中國傳統兵學對預先判斷勝負十分重視,孫武在《孫子·謀攻篇》中指出的“知勝”就是指對戰爭勝負的預判,是中國傳統兵學在勝負預判方面的典型代表作品。他在勝負預判中提出的五個方面,不僅對戰事判斷具有指導意義,還對取得戰爭的“全勝”具有指導意義。“知勝”的五個方面,也就是獲得“全勝”的五個必要條件。這五個方面是對軍事實力的綜合判斷,既包括客觀的軍事水平,也包括主觀的作戰能力,五者相互間沒有涇渭分明的界限,但又相互區別,互為前提,互相補充。五者以各不相同的組合方式構成了形形色色的戰局。通過有效觀察和了解孫武提出的五個要素,可以實現對戰事結果的預判。另外,在戰事中的攻與守方面,孫武的見解也是非常深刻的。他認為,高水平防守的關鍵在于自身的隱蔽,良好的隱蔽可以令敵人的攻擊無用武之地;而有效進攻的重點是迅捷靈活,快速進擊,出其不意,使敵人防不勝防。抗日戰爭時期中共在天津領導的城市斗爭和武裝反抗,就與《孫子兵法》的上述論述暗合,深刻體現了兵家謀略的精妙之處。
抗戰全面爆發后,黨中央制定了關于淪陷區工作的總方針。中共天津黨組織貫徹落實黨中央的方針政策,尤其注重黨中央政策與天津實際相結合,在實踐中逐漸形成了符合天津抗日實際的戰斗策略和方法,最大限度地保證了天津各民族、社會各界人民的利益。一方面,為提高天津抗日武裝的作戰能力,準備靈活機動的進攻,抗日游擊根據地在天津敵后農村建立和發展起來。在敵后抗日游擊根據地的建設中,注重黨的組織建設和政治建設,以黨組織為核心機動高效開展敵后抗日斗爭。另一方面,在城市工作方面,為增強自身的隱蔽、堅守,訓練精良的黨員干部在敵占區執行潛伏工作,中共晉察冀分局及天津周圍地區根據地的黨委在天津敵占區從未停止工作,敵占區地下組織的重建為抗日活動的開展創造了條件,天津城市潛伏工作得到開展,抗日思想廣為宣傳,并且收集情報,運送抗戰物資,為抗戰戰略反攻階段的勝利筑牢根基。〔8〕
四、黨在平津戰役前后的重要作用
《孫子·形篇》指出:“是故勝兵先勝而后求戰,敗兵先戰而后求勝。”《孫子·虛實篇》中說:“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六韜·龍韜·兵征》云:“勝負之征,精神先見。”《尉繚子·兵談第二》中有:“兵如總木,弩如羊角,民人無不騰陵張膽,絕乎疑慮,堂堂決而去。”古代兵學作品中多次強調“先勝”,這經過戰爭實踐的檢驗,成了一條重要的軍事原則。“先勝”意味著先為自身的勝利創造條件,然后尋求時機擊敗敵人。相反地,企求在戰爭中僥幸取勝的軍隊,往往落得失敗的境地。先勝的條件簡單來說指的是戰爭上的準備。為取得勝利,作為高級將領或者軍隊統帥,對于敵我雙方的真實情況要盡可能了解,然后針對實際形勢制定合適的戰略方針,有目的性地彌補自身短板的同時,并利用對方弱點為自身創造勝利的條件。此處的戰爭準備,不僅僅局限于軍備和物資方面,還應包括制度管理、獎罰激勵、盟友聯合、軍事技術創新等多個方面,從而達到取勝的目標,達到保全自己、消滅敵人的目的。只有在充分的準備下,戰事才會有全勝的把握。實現全勝的最高目標,在充分準備的基礎上,指揮者應把握戰局的主動權,充分發揮自身軍隊的最大優勢,隨時保持戰場上的殺伐果決和靈活機動。傳統兵學尤為強調攻防之道,攻與防是戰爭中不可或缺的兩個方面,要掌握進攻與防守的時機,把控戰事節奏,也要制定有效的進攻與防守戰略戰術,確保階段性安全。此外,無論古今中外,士氣低落和斗志昂揚兩種精神狀態,就使各自的命運被確定了。中國傳統兵學強調軍隊精神和氣勢的培養,上至將帥,下至士兵,唯有舍生忘死的決心、至死不渝的品質,才能夠在戰場上將成熟的兵略變成實際的勝利。
在平津戰役前后,黨中央充分發揮了總領全局的領導核心作用,使得天津和北平相繼以最小損失解放。天津戰役是一場關鍵的城市攻堅戰。鑒于遼沈戰役局勢發展之快,黨中央當機立斷,決定部署東北和華北地區的解放軍合力解放東北和華北地區。〔9〕經過東北和華北解放軍的英勇作戰,天津人民最終于1949年1月15日迎來解放。可以說,天津解放為北京和平解放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也是推動全國革命勝利的重要一步。為解放天津,中國人民解放軍與敵人正面作戰,殲敵超過13 萬人。為配合正面軍事進攻,天津地下黨組織積極發揮作用,開辟了解放天津的第二條戰線。第二條戰線的開辟,充分符合和貫徹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最大程度地保衛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財產安全,盡可能地和平解放,以最低的代價取得勝利的成果。〔10〕天津第二條戰線在解放天津的過程中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天津地下黨組織通過各種渠道打探軍事、政治和經濟情報,特別是深入敵人內部搜集了城防設施等重要防御信息,甚至拿到了當時天津的城防圖,使解放軍得以精準打擊國民黨自以為固若金湯的城防體系。因此,當時民間流傳著“解放軍的炮彈有眼睛,不打老百姓,專打國民黨”的說法。〔11〕
五、解放初期黨在天津領導的經濟建設和工商業改造
《孫子·軍爭篇》指出:“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孫子·九變篇》說:“是故智者之慮,必雜于利害。雜于利而務可信也,雜于害而患可解也。”在軍事理論中,戰爭不僅僅包含戰場上的事件,還包含著后勤保障、物資儲備等戰備條件。在戰爭時期,戰備條件是取得戰爭勝利的必要保障;在和平時期,戰備條件是保衛國家安全的必要手段。沒有良好的戰備和后勤保障,一切行動都會因缺乏物質基礎而失去意義。孫子對物質的儲備、運輸也十分重視。孫子提出的“雜于利害”思想,其指導意義不僅僅限于軍事領域。其核心要義是以辯證的眼光看待利與害及其關系,在辯證分析的基礎上預判,從而能夠在事情未發生之前提前做出準備。面對順利的情況,細心發現容易忽略的問題,保持自身優勢;在遇到困難時,綜合審視時局,保持必要的信心,在困局中發揮主動性,創造勝利的條件。
天津解放后,國民經濟生活亟待恢復,進行適當的經濟建設、促進區域經濟發展成為天津解放后的首要任務之一。1949年春,在黨中央的安排下,劉少奇將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精神帶到天津,深入天津工廠等基層生產單位講話,為解放之初的天津在經濟恢復和社會發展方面給予了前瞻性的指導。在黨中央的指導下,天津社會得到了一定的恢復和發展,特別是在經濟與民生方面。在國營經濟方面,民主改革深入實施,國營企業調整改革,國營經濟顯現活力;建立和完善勞動生產領域的法律法規,促進勞資糾紛的解決,保護私營經濟的活力,以法律法規護航城市經濟恢復與發展;應對物價波動,實施統一財經,合理調節勞動生產領域的勞資關系,工商業的產銷關系;以物資交流會的方式促進城市與鄉村的物資交流,以工業博覽會的方式體現天津區域經濟優勢,重點打造天津作為華北地區經濟中心的優勢,發揮其工商業物資的集散和交流功能。解放之后,天津的工商業、對外貿易得以迅速恢復和發展。根據工商局統計,6月至7月,天津主要工業生產行業達到解放前的水平;私營工商業發展勢頭良好,至9月,經合法審批營業的私營工商戶達3800 戶,相比4月初增加近12 倍。〔12〕
六、新中國成立后黨在天津進行的反腐敗斗爭
《六韜·文韜·賞罰》中有:“凡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六韜·文韜》中還說:“殺貴大,賞貴小。”《尉繚子·制談第三》也說:“明賞于前,決罰于后,是以發能中利,動則有功。”古代兵家都講求賞罰分明,有功必獎,有過必懲。賞罰對于軍隊管理來說是一種正負相結合的激勵措施,而充分發揮獎賞與懲戒效能的關鍵之處在于有令必行。如果有令不通,或有令不行,勢必會造成法度失信于人,在管理上又何談以法度制約和激勵人心呢?對于違反規定者,無論戰功如何,懲戒絕不姑息;而對于有功之人,無論出身如何,應有的獎賞必須按規定兌現。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令行禁止,紀律嚴明。尉繚子與其他古代兵家一樣,認為只有做到事先明確獎賞標準,事后懲罰堅決果斷,才能避免軍隊管理中的散亂不受約束的問題。紀律嚴明、賞罰清晰的部隊,在戰場上必能發揮充分的效能,取得勝利。這些在新中國成立后天津的反腐敗斗爭中表現得非常明顯。
新中國成立初期,貪污腐化問題在增產節約運動和國民經濟恢復的過程中逐漸顯露。1951年,按照中共中央決定,“三反”運動迅速在全社會展開,天津對市內各級黨組織、國家機關、公營企業單位和人民團體進行嚴格調查,查處了一批有貪污行為的干部。其中,因在公職期間嚴重貪污和挪用公款,被依法公審并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有曾任中共天津地委書記的劉青山,以及曾任天津行署專員的張子善。〔13〕黨自成立特別是在全國執政以來,尤其重視反腐倡廉建設,“三反”運動是黨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的反腐倡廉建設的初戰,天津劉青山、張子善的案件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全國第一件影響力極大的貪腐案件,教育了黨員干部,依法嚴懲了貪污腐敗人員,維護了黨和國家干部隊伍的先進性和純潔性。〔14〕
隨著“三反”運動的深入,不僅貪污腐敗的公職人員得到了嚴懲,也使官商勾結的不良社會現象暴露出來,國家資產流失的問題受到了關注。根據黨中央指示精神,為整頓經濟發展中的不良之風,全國大中城市開展“五反”運動。“五反”運動主要針對行賄、偷稅漏稅、偷工減料、盜騙國家財產、盜竊國家經濟情報五項私營工商業中常見的違法行為。黨中央對于“五反”運動與“三反”運動的指導采取明顯的區別策略,一方面以指導和幫助的方式爭取絕大多數資本家,而對于極少數最反動的資本家采取孤立和打擊措施。而且,對于“五反”運動的開展,黨中央特別強調,各個城市在開展斗爭的過程中,應保證合法、合規經濟生活的正常運行。其中,毛澤東在2月15日起草的《中央關于“五反”中對各類資本家的處理意見》中特別提到,對于守法工商戶要鼓勵照常營業,尤其要求天津“五反”斗爭工作必須于2月內完成。黨中央對于“五反”運動的指導張弛有度,不但整頓了工商業的風氣,強調了守法經營的規范,為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條件,而且維護了社會穩定,推動了民主監督和民主改革的進程,營造了風清氣正的優良社會風氣。
七、在抗擊自然災害和抗震救災中天津黨組織的作為
《孫子·地形篇》提出:“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國之寶也。”《孫子·九地篇》說:“合于利而動,不合于利而止。”《尉繚子·治本第十一》則認為:“蒼蒼之天,莫知其極,帝王之君,誰為法則?往世不可及,來世不可待,求己者也。”中國傳統兵學重視“將德”,最早全面論述將領的才能和品質的兵學思想家是孫武。他認為優秀將領的追求不在于功勞與名聲,也不畏懼承擔責任和承認錯誤,其使命是保衛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以維護國家利益為己任。孫武認為一名優秀的指揮者應該具備管理能力,還應該具備忠誠、盡職、勇敢、無私等重要品質。軍隊之外,國家管理之中,對于干部的要求和對于將領的要求是類似的。隨著時代的發展,黨員干部被時代賦予了更多新的要求。但新的時代要求的出現,并不意味著與傳統的割裂。在新的時代環境下,可以說孫子在兩千多年前論述的將領品質,對于今天的領導干部而言,依然有值得學習之處。孫子的意思是,衡量是否要發動戰事、戰爭資源投入程度、戰事規模大小、交戰時間長短的核心標準是唯一的:利益的有無或大小,這一點任何時候都不能動搖。尉繚子從樸素的唯物主義觀點出發,他主張以現實情況為準繩,為既定目標積極努力,在謀得勝利的過程中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
天津地處九河下梢,歷來水患災害嚴重。1963年8月初,一場特大洪水向天津人民襲來,水勢洶涌,海河上游各個河系的水流大量涌入地勢低洼處,給天津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帶來了威脅。8日,中共天津市委根據黨中央的指示緊急部署防汛抗洪工作,爭分奪秒筑堤御洪。因洪勢兇猛,天津市委于12日緊急動員全體黨員帶領群眾抗洪,成功抵御了14日的第一次洪峰。18日,天津市委進行第二次全市動員。全體黨員積極響應,第一時間參與抗洪斗爭,不畏辛勞,團結奉獻,帶領解放軍和群眾做足了抵御二次洪峰的工事準備。在黨的帶領和各方的支持下,天津人民眾志成城,成功抵御了特大洪水自然災害,將災害中的居民生命和財產安全損失降到了最低。〔15〕
1976年7月28日,天津市受到河北省唐山、豐南地區7.8 級大地震的嚴重波及,遭受人員傷亡和經濟損失嚴重。據統計,7月28日至8月12日,全市受災嚴重,死亡人數超過2 萬人,重傷人員超過3 萬人,受到破壞的房屋1 億余平方米,直接和間接經濟損失總計超過75 億元。〔16〕強烈地震一小時左右,天津市委迅速開展受災情況調查和救災物資和人員安排工作。約5 個小時后,市委領導分別帶隊親臨現場指揮抗震救災工作,同廣大人民群眾并肩作戰。地震發生后的兩天內,市委緊急派出醫療隊前往寧河、漢沽等重災區,先后派出的3 批醫療隊共677 名醫護人員。截至災后第五天,全市投入到救災工作中的人員包括民兵30 余萬人,以及醫務人員超過3 萬人。〔17〕面對此次特大災情,天津黨組織經受住了考驗,涌現出崔志成、劉志湖、王振祥等一批沖鋒在救災一線的優秀黨員干部。〔18〕在黨組織的帶領下,天津人民在抗震救災斗爭中表現出勇敢堅強的民族品質,妥善安置了受災群眾,并迅速恢復了交通干線的暢通。
八、改革開放以來黨領導天津人民的奮斗歷程
《司馬法·定爵》說:“順天,阜財,懌眾、利地、右兵,是謂五德。”《黃石公三略·上略》認為:“夫為國之道,恃賢與民。”文中的“五德”具體來說指的是把握時機、順應形勢,創造財富、發展經濟,福澤百姓、利益共享,發展農林、肥沃土地,發展軍事、加強軍備。這實際上就是進行改革的五個方面,古代兵家的見解至今仍有可借鑒之處。只有任用賢才,依靠民眾,政令才不會失誤,事業才大有希望。治軍與治國是一個道理。
自改革開放以來,天津市歷屆市委、市政府嚴格貫徹落實黨中央的指示精神和國務院制定的方針政策。經過長期的改革,天津不但經濟社會發展取得大幅進步,而且城市綜合實力得到了顯著增強。城市的健康快速發展突出表現在經濟生活的多個方面:經濟總量表現出較大增幅,經濟發展質量和水平顯著提高;行業和企業升級轉型不斷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時俱進、不斷完善;研發投入占比升高,創新實力和能力較同級別城市更為突出。〔19〕
百年來,天津從近代走向現代,從苦難到站立,從百廢待興到蓬勃發展,與國家一道經歷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歷史跨越。這有賴于黨中央的堅強領導,有賴于歷屆天津市委、市政府的帶領,有賴于一代又一代共產黨員的不懈奮斗,有賴于廣大天津人民的自強不息、艱苦奮斗。黨在天津的革命活動和百年奮斗歷程與天津大地上發生的驚人巨變充分展現出中國共產黨的可靠性、馬克思主義的先進性,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當前,中國已經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正意氣風發地朝著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與黨緊緊在一起的天津,一定能再創輝煌,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不懈奮斗,為國家發展和人民福祉做出新的貢獻。
【注釋】
〔1〕張紹祖:《李大釗與天津黨團組織的創建》,《天津政協》2011年第4 期。
〔2〕夏靜雷:《馬克思主義在天津早期傳播的歷史考察》,《北京黨史》2020年第2 期。
〔3〕〔5〕中共天津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共天津歷史簡明讀本》,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4〕李俐:《周恩來與天津》,《求知》2020年第2 期。
〔6〕孟罡:《張太雷在天津的革命生涯》,《求知》2018年第1 期。
〔7〕劉云光:《中共天津地方組織創建與早期革命活動》,《求知》2014年第1 期。
〔8〕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華北治安戰(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9〕金沖及:《毛澤東與蔣介石如何應對平津戰役》,《領導文萃》2018年第8 期。
〔10〕〔11〕王悅:《平津戰役中的天津地下黨》,《黨史博覽》2020年第4 期。
〔12〕劉勇:《建國初期劉少奇在天津的經濟政策》,《經濟與法治》2013年第5 期。
〔13〕王振良:《荏苒芳華洋樓背后的故事》,天津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1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研究組:《開國領袖畫傳:毛澤東》,遼寧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15〕天津市檔案館編:《天津地區重大自然災害實錄》,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6〕天津市檔案館館藏資料。
〔17〕劉小榮:《1966——1976年的天津》,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
〔18〕天津人民出版社編:《毛澤東思想育英雄天津市抗震救災英雄譜》,天津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19〕中共天津市委黨校課題組:《改革開放40年天津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性成就和經驗啟示》,《理論與現代化》2019年第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