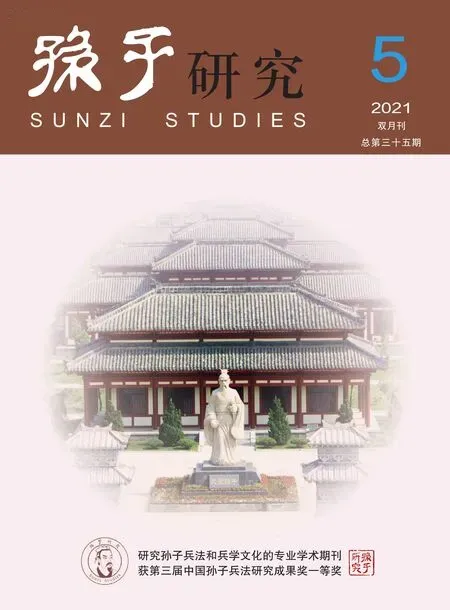孫中山與《孫子兵法》
扈光珉 扈 瀟
孫中山先生是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在舊中國錯綜復雜的環境中,面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李鴻章語),奮起革命,幾十年如一日,前赴后繼,生命不息、戰斗不止,先后領導、指揮了大大小小二十多次武裝起義。在他的革命生涯中,武裝反抗反動勢力是最基本的形式,并先后擔任過海陸軍大元帥、非常大元帥、陸海空軍大元帥,創辦了著名的黃埔軍校,著有《十年國防計劃》《軍人精神教育》等軍事學論著,李浴日稱之為“偉大軍事家”〔1〕。豐富的軍事斗爭實踐、復雜的軍事斗爭環境,領導策劃了幾十次的武裝起義,決定了孫中山與《孫子兵法》注定會結下不解之緣。在他的上海故居藏書目錄中,就有《孫子兵法》以及《孫子十家注》。孫中山讀《孫子兵法》,是把它當作哲學著作來研究的。孫子研究專家李浴日曾說,孫中山先生“對于我國古代各家兵法,亦有精湛研究,就中以孫子兵法為最”〔2〕。但他一生奔波革命,沒有時間系統回憶與《孫子兵法》的關系,現在我們只有通過他的革命實踐及其報告演說來研究推斷、勾勒出這位偉人與這部經典之間的關系。不當之處,敬請指正。
一、孫中山接觸《孫子兵法》的過程
孫中山接觸研究《孫子兵法》從時間上劃分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
1、接觸知曉《孫子兵法》階段(1875—1885年)
1875年,9 歲的孫中山進入私塾讀書。村塾設立在本村馮氏宗祠里,老師姓王,教授中國古代啟蒙教材如“四書”“五經”等。兒童教材里,有本叫《幼學瓊林》的小冊子,里面記述了文臣武將,其中包括姜太公、黃石公、司馬穰苴、孫臏、吳起、韓信等軍事家及其著作。但可惜的是沒有提到孫武,沒有提到《十三篇》,因此推斷這時的孫中山雖然知道了兵法,但可能還不知道《孫子兵法十三篇》。
孫中山小時候對軍事故事很感興趣,尤其愛聽洪秀全的故事。村上有位曾參加過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馮爽觀,常常向村童講述洪秀全領導金田起義、定都天京、北伐、西征等故事。當講到太平天國不幸失敗時,孫中山很失望,但他很崇拜洪秀全,自稱作“洪秀全第二”〔3〕。
1879年9月,孫中山跟著哥哥到檀香山的意奧蘭尼學校學習,這是所西式教會學校,課程有英語、歷史、數理化等,學校還開設了兵式體操,深得孫中山的喜愛。在這期間,為了提高國學水平,他特別聘請了杜南先生作為自己的華文教師,為他講授中國的傳統文化,因此他的國學在這個時期取得了長足進步。從他學習經史子集的經歷中,可知孫中山這時可能已經了解到了孫子及其兵法。
1883年7月孫中山由檀香山回到村里,這時他已經長成青年才俊。回到村里后,按照兵法套路為村里的年輕人設計了一個“走兵馬”的游戲,把參加游戲的青少年分成兩隊,一隊做兵,一隊做賊,兵與賊兩隊互相追捉,哪一方捉的多就勝利。這實際上反映了孫中山的軍事興趣與指揮能力。
從以上孫中山讀書的經歷、興趣和老師教授課程及其自學的情況看,他在1879年至1885年這個時段可能已經知道了孫子及其兵法《十三篇》。
2、學習《孫子兵法》內容階段(1885—1894年)
1885年中法戰爭后,孫中山立志傾覆清朝,創立民國。從這時開始,他更加注重研究中國歷史。而真正對《孫子兵法》的內容有更多的熟知,應該是1886年在廣州博濟醫院學習期間。他一邊學習醫學,一邊自己花錢購買了二十四史,認真學習、仔細研讀。由于他求知若渴,腦子聰靈、過目不忘,很快對二十四史爛熟于心,對于其中的一些事件、故事情節都十分熟悉,以至于同學隨機抽出幾冊進行考問時,竟然可以對答無誤,被稱為“通天曉”〔4〕。
《史記》是二十四史的第一部,記載上下五千年的歷史,不論是史料價值,還是寫作藝術都堪稱“絕唱”。孫子就是在《史記》中被最早且比較系統記載的。這部書中,比較有名的篇章是《項羽本紀》,“破釜沉舟”“鴻門宴”等著名故事均出自此篇。而在記述大將韓信生平事跡的《淮陰侯列傳》中,也多次引用《孫子兵法》的內容。如在井陘之戰前李左車給陳余的建議中大量引用了兵法術語。可以肯定,孫中山此時認真閱讀了《孫子吳起列傳》,知道了孫武及其兵法《十三篇》。同時,他也從《項羽本紀》《淮陰侯列傳》《伍子胥列傳》等名篇中體會到更多《孫子兵法》的內容。二十四史的第二部是《漢書》,在《漢書·藝文志》中有《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及圖的記載。因此可以比較肯定地說,通過閱讀《史記》《漢書》,孫中山此時已經熟知部分《孫子兵法》的內容了。
3、研究運用《孫子兵法》階段(1894—1925年)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后,孫中山有感于國勢頹廢,立志富國強兵,對《孫子兵法》進行了認真研讀。1894 他在上李鴻章書中就明確表示:特別留心于富國強兵之道。〔5〕鄭觀應作為孫中山的同鄉與前輩,孫中山深受鄭觀應的影響。他多次拜訪鄭觀應先生,學習他的進步思想,并討論救國救民的真理。在鄭觀應的影響下,孫中山全身心致力于救國和改革、革命的事業。孫中山還認真研讀了鄭觀應的《盛世危言》,這本書對他有著極其深刻的影響。在《盛世危言》中,提到孫武及其兵法的地方很多,其中就有兵制的專門論述,而且還創造性地引用了《孫子兵法》中“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的名言。《盛世危言》中說:“何言乎知彼己?知己知彼,百戰百勝。”〔6〕孫中山對此名言記得非常牢固。1921年他在《軍人精神教育》中仍然將“知己”放在“知彼”之前,可見影響之遠。
1897年孫中山批評清政府把兵書、兵法列入禁書的做法。作為清朝的反叛者,政府的禁書,憑孫中山的性格也會認真研讀與研究。
在這一階段,無論是謀劃革命暴動,還是演說鼓動,孫中山對《孫子兵法》中的名言要義,順手拈來,脫口而出。1895年2月在準備廣州起義時,就制定了“兵貴精,不貴多”的原則。1903年,孫中山在東京秘密組織成立了“革命軍事學校”,聘用日野為校長,小室健次郎大尉為助教,學科除普通兵學及制造盒子炸彈外,尤注重于散兵戰術的傳授。其中,普通兵學可能也包括了孫子兵法。
1921年12月10日在桂林對滇贛粵軍進行的《軍人精神教育》的演說中,孫中山提出了軍人精神“三要素”,即智、仁、勇,并要求每一個革命的軍人、現代的軍人,都要養成這三種精神,唯有如此,才可以救民救國。但同時認為軍人是要在戰場上拼搏打仗,甚至是流血犧牲的,因此還要練成高超的技藝,主要有五個方面:命中精準,隱伏保護自己,吃苦耐勞,奔跑走路,能過艱苦生活。〔7〕
1923年12月9日,孫中山在廣州大七營對國民黨員的演說中活學活用了《勢篇》的語言,對“勢”進行了形象表述。他把革命力量比作山上的大石頭,如果一旦有人引動,就會形成不可遏制之勢。1924年6月16日在陸軍軍官學校開學典禮的演說中,孫中山則基本是直接引用了《孫子兵法》的語言。他說:“古時的兵法都說是‘倍則攻之,十則圍之’〔8〕。由此可以肯定地說,孫中山此時已經對《孫子兵法》有了比較多的了解和研究。
二、孫中山在革命生涯中對《孫子兵法》的戰略運用
孫中山對《孫子兵法》的戰略運用,就是活用其原理,根據實際情況運用其精髓要義,去解決政治、軍事、外交等方面的問題,這方面的運用可以概括為“廟算”“致 和”“造 勢”“伐 交”“創 新”“攻 心”“共濟”7 個方面。
(一)廟算
《孫子兵法》首篇就是講預測、廟算,并指出“廟算”多者勝。所謂“廟算”,就是事前的籌劃、運籌、分析、預測。孫中山在革命生涯中,每臨起義、和談等大事,他都從時局國情、民族命運、人心向背出發,進行精準的“廟算”,充分顯示他過人的洞察力和預判力。
下面試舉幾個反映孫中山先生精準“廟算”的具體事例。早在1904年,他就信心百倍地預測清朝必然滅亡。1910年3月至5月,孫中山先生對時局、國運作出了三個預言。
首先,孫中山充滿信心地斷言:清朝政府已經奄奄一息、茍延殘喘、搖搖欲墜,不出幾年,漢族就會奮起,推翻清政府。
孫中山的第二個預言是:新軍將是革命勝利的決定性力量。當時中國的軍隊有36 個鎮,他們之中有很多具有革命思想、贊成革命運動的進步青年,只要善于發動、運用他們,他們就會反過來為革命服務。
孫中山的第三個預言是:中國革命成功后,將建立共和國。中國推翻了清朝帝國的專制統治后,一旦成立共和國,將會發展為世界上“最繁榮的國家之一”。〔9〕
果然不出所料,這幾個“廟算”很快被證實了。
孫中山表現出超強“廟算”能力的,還有擘畫三峽一事: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孫中山認為中國會迎來建設高潮,于是就對國家建設進行了調研考察。經過考察研究,1919年發表了《實業計劃》一文。在這篇著名文章中,孫中山首次提出了開發三峽的設想。這是領袖人物對三峽夢的最早論述。1924年他又對三峽的開發建設作出了詳細的規劃、設想。這都充分體現了孫中山先生超強的預見智慧、“廟算”能力。
(二)致和
我們都知道,孫子雖然是個軍事家,《孫子兵法》是指導戰爭的,但中國人骨子里是個熱愛和平的民族,孫子也可以說是和平的大師,他講究“慎戰”,追求“不戰”,其最高境界是“不戰而屈人之兵”。孫子的和平思想被孫中山先生繼承并發揚光大。
孫中山認為,革命戰爭的目的不是流血,而是仁義和平。他多次強調指出:“如果中國人能夠自主,他們即會證明是世界上最愛好和平的民族。”〔10〕孫中山是英雄的中國人民的杰出的代表,他身上流淌著中國人民愛好和平的血液,傳承著中華民族愛好和平的基因。正是在和平奮斗救中國的思想指導下,孫中山才能在辛亥革命后,以國家利益為重,以民族和平為要,不計個人名利,退位以求和平。對于孫中山先生的退位,在當時的條件下,也正是運用孫子兵法“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最好選擇。
當時的情況是:從10月10日武昌起義首義到12月18日南北議和談判開始之前,在宣布獨立的18 個省中,被袁世凱直接或間接控制的省占半數以上,而且袁世凱的部隊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紀律嚴格、指揮統一、內部一致。而所謂革命黨控制的省份,一是內部紛爭,政府內、軍內、黨內意見并不一致;二是經費奇缺,中華民國成立定都南京后國庫里只剩下10 塊大洋,連維持運轉都十分困難,怎么與袁世凱進行戰爭?在這種情況下,硬拼硬打,沒有任何的把握,甚至可以說是死路一條。而進行議和,不戰而達到革命目的,推翻帝制,創立共和,是最佳選擇。對此,孫中山心中十分清楚,說得也很明白,他說:“我也知道袁世凱不可信,但我們可以因勢利導,借勢而為,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貴族專制之滿洲,則賢于用兵十萬。”〔11〕這正是孫中山致和的遠見卓識。
現在回頭看看創立共和的過程,便深知孫中山先生對《孫子兵法》運用得是多么嫻熟。
一是利而誘之。為了利誘袁世凱就范,孫中山多次公開表示:如果袁世凱擁護共和、結束帝制,就讓袁世凱當大總統,而且前面不用加“臨時”。這一方面給袁世凱抱了一個大熱罐子,為了當大總統,就必須加速逼迫清帝退位;同時也斷絕了袁世凱繼承“清朝法統”、自己做皇帝的夢想。因為孫中山的態度是,結束帝制,袁世凱才能當大總統。
二是兩手對兩手。孫中山承諾讓袁世凱當大總統后,并不是消極避讓、等待和平,而是用革命的兩手對待袁世凱反革命的兩手。為此,孫中山繼續按照計劃組建革命政府,事實上形成南北政權對峙的局面。他還提出了袁世凱當大總統的三個條件:清帝遜位,國內和平,列國承認民國政府。對此袁世凱惱羞成怒,發兵圍攻南京。革命政府也毫不示弱,孫中山親自就任北伐總指揮,立即興師北伐,革命軍勢如破竹,一直打到徐州。面對此種情況,袁世凱又提出新的方案,即革命政府與清政府同時解散,在天津另行成立民國政府。孫中山隨即強硬表示:革命黨人決不接受。同時啟動了對袁世凱的行刺計劃,袁世凱險些喪命。此舉令袁世凱感到毛骨悚然、不寒而栗,被迫接受革命黨的條件。
三是順勢而為。早在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之前,南北已經開始議和、談判。如果不承認這個事實就會被孤立。革命黨內部,和談勢力相當強大。汪精衛甚至指責孫中山:“你不贊成和議,是舍不得總統嗎?”黃興也因缺乏軍事力量而“忍辱勸孫將總統禪位于袁”。〔12〕由此可以看出,議和已經成為當時的大趨勢,孫中山先生明透大勢,因勢利導,最終才成就了共和大業。
(三)造勢
從實踐上來說,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歷程就是一個造勢、借勢、用勢的過程。在武昌起義前,他麾下沒有一兵一卒,他以革命家的膽略、百折不撓的毅力,不畏艱難、屢敗屢起,這個革命過程,就是一個造勢、順勢、用勢的過程。因此他對造勢非常重視,論及勢的作用,他說:“夫時勢者,人事之變遷也;自然者,天理之一定也。”〔13〕
孫中山所講的勢,筆者理解有四層次的意思:一是勢既是自然的,也是社會的;二是勢一旦形成,是銳不可當的;三是一定要因勢作為;四是勢是可以創造的、烘托的。在革命的過程中,他著重從三個方面進行了造勢。
一是連續暴動,前赴后繼。生命不息,戰斗不止,屢挫屢奮,屢敗屢起。面對兇惡的敵人,每到一地都宣傳革命,進行籌款、造勢,在實踐上舉行了多次百折不撓、可歌可泣的武裝起義,辛亥革命前就達十多次。正是不停戰斗,不斷起義,才延續了革命的薪火,形成了革命運動的燎原之勢,最終點燃了武昌起義的熊熊烈火。
二是奔波五洲,鼓動革命。從1879年去夏威夷王國、1895年去日本開始,孫中山先生足跡踏遍五湖四海,凡有華僑的地方就有他的身影,每到一地就進行演說、宣傳革命、開展革命活動,因此他在華僑中有著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三是海外論戰,鼓動革命。革命派以《民報》為陣地,與改良派在思想理論戰線上展開了一場空前的革命與改良的大論戰。通過與改良派的論戰,宣傳了革命理論,對海內進步人士進行啟蒙。這一系列的革命活動,最終形成了推翻清朝統治的浩浩洪流。
他自己曾總結說:“文奔走國事,三十余年,畢生精力盡瘁于斯;精誠無間,百折不回,滿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窮途之困苦所不能撓,吾志所向,一往無前,愈挫愈奮,再接再厲;用能鼓動風潮,造成時勢。”〔14〕正是這種愈挫愈奮、再接再厲的精神,讓孫中山的革命事業風生水起。團結廣大的革命黨人造成時勢,營造新的革命勢能,使其對清王朝具有極大沖擊力、震撼力和破壞力。
(四)伐交
我們知道《孫子兵法》核心思想之一就是“伐謀”“伐交”,它的名言就有“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孫中山在革命生涯中,平衡列強關系,與列強打交道,進行外交活動是他的工作重心之一。在武昌起義前,可以說他的大部分精力用在游說于列國之中,此即“伐交”。他說:“革命的成功與否,就古今中外的歷史看起來,一靠武力,一靠外交力。外交力幫助武力,好像左手幫助右手一樣。所以革命的成功與否,外交的關系是很重大的。”〔15〕實際上,孫中山先生在革命生涯中,游歷五洲,跑遍四海,鼓動革命,籌款募捐,其本身也是一個“伐交”的過程。并在這個過程中,與西方主要國家的有些政要、政黨建立了良好的關系,結識了許多進步人士。武昌起義后,他認為“乃以此時吾當盡力于革命事業者,不在疆場之上,而在樽俎之間,所得效力為更大也”〔16〕。因此他不辭辛勞,從美國到歐洲,爭取到了列強對中國武昌起義后建立的新生革命政權,采取暫不干涉的“中立”政策,從而避免新生革命政權因被列強和清朝夾擊而陷入困境。從這個意義上說,孫中山也是運用“伐交”戰略的成功典型。
(五)創新
如果把孫中山的四十年革命生涯用《孫子兵法》的一句話來概括的話,用“踐墨隨敵”是最確切不過了。因為他的一生就是根據敵情、客觀情況變化,不斷追求真理、不斷超越自己、不斷與時俱進、不斷走向新高度的一生。
孫中山名文,字載之,號日新。我們知道古人名字是父母取的,但號是自己對自己性格、追求、目標、本性的一種刻畫。孫中山取號為“日新”,本身就反映了他與日俱進的品性。這號來源于中國古代文化中的日新又新的追求,也真切反映了孫中山的人生軌跡,真切反映了他追求真理永不停步的品質。
早在1894年,孫中山就以一介平民身份上書李鴻章,提出富國強兵的改革主張,表現出了一個熱血青年的家國情懷和遠大志向;隨后赴檀香山組織近代中國第一個民主革命團體——興中會。
1895年,孫中山開始實踐他推翻清政府的宏愿,發動廣州起義。起義失敗后,孫中山被官方懸賞通緝,開始流亡奔波宣傳革命。
1905年,為壯大革命力量,孫中山聯合華興會、光復會等創立了中國第一個全國性的資產階級革命政黨——中國同盟會,初步建立起了反對清政府的革命統一戰線。
1911年10月10日,在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影響下,武昌軍人舉行了起義。后來,孫中山運用高超智慧領導辛亥革命,推翻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國。
1924年1月,孫中山首創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掀起了大革命的高潮。總之,他以“知之維艱”的精神不斷自我革新,不斷追求新的高度,不斷邁向新的目標,是勇于革新、不斷進取的楷模。
(六)攻心
人心向背自古就是成敗關鍵。孫中山致力革命運動,自然不會忽略了祖傳的“攻心為上”的思想戰術。孫中山相信人心是決定成敗的重要力量,他認為如果進行革命行動而欠缺人民心力,無異于無源之水、無根之木,因此十分重視爭取人心的工作。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的革命過程就是爭取人心、點亮心靈的過程。他主要做了三方面工作:
一是積極演說,爭取人心。孫中山是一位杰出的演說家,為了宣傳革命思想,發動社會輿論,他曾多次發表公開演說,并取得了良好效果。《孫中山全集》中的文章多數是其演講的稿子。孫中山在演講時,聲情并茂,很具有煽動力,以至于人們送他個外號叫“孫大炮”。這一綽號從褒義上來講,就是說他的演說、鼓動就像武器一樣具有殺傷力。
二是散發書冊,浸潤人心。除了公開發表演說外,孫中山還特別注重利用有形的宣傳武器,例如散發傳單、小冊子等。例如,1904年他在美國,感覺美國華僑革命意識比較淡薄,風氣閉塞,對革命熱情不高,于是就印刷《革命軍》廣泛散發,到處宣傳。“不及半載,知識為之大進,此書之力多焉。”〔17〕
三是輿論宣傳,教化人心。報刊活動為孫中山的輿論實踐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英國及國內上海等多地媒體報道此事,使孫中山名聲大振,成為輿論關注的領袖人物。1905年,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創辦機關報《民報》,除與資產階級改良派進行論戰外,主要精力用于宣傳三民主義,大造革命輿論,鼓動開展革命,起到了教化人心的作用。可以看出,孫中山先生把“治心”作為一個中心工作環節,積極努力,很好地起到了教化人心、化風成俗的作用,由此推動了革命運動的蓬勃開展。
(七)共濟
團結同心、同舟共濟、和衷共濟,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孫中山繼承了中華民族的優秀基因,在革命生涯中,一直秉承和衷共濟、同舟共濟的團結奮斗的思想,十分重聯合、團結、利用一切可以聯合、團結、利用的力量,去奮斗、革命。他曾以“同舟共濟”“輔車相依”書贈日本朋友山田純三郎。孫中山從多次革命受挫的實踐中得出的教訓就是“欲求成功,必須團結”〔18〕,號召全國的國民要“合為一氣,一致進行”〔19〕。從實踐上看,他聯合其他革命組織創立的同盟會,實際上是一個反抗清政府的“統一戰線”的共濟組織。辛亥革命成功推翻帝制,也是同舟共濟的結果:推翻封建統治的力量,除了革命黨以外,還有改良派的力量、新軍的力量、會黨的力量,甚至也包含了北洋軍閥。孫中山正是很好地借助了這些力量,才形成了推翻清王朝、結束帝制強大的“合力”。
三、孫中山在革命生涯中對《孫子兵法》的戰術應用
孫中山在革命生涯中,親自指導指揮了幾十次戰斗,他“每每召集各軍將領指示機宜。于指示時,置地圖于桌上,按圖指示,如何進軍,如何攻守,均合用兵原則”〔20〕。也就是說,孫中山在直接指揮戰斗中也常常應用《孫子兵法》的智慧原理。概括起來有:
(一)出奇
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生涯是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進行的,這一形勢決定了孫中山開展軍事斗爭,不能走常規路線,必須出奇制勝。孫中山于1923年指揮的討伐陳炯明叛軍之役,是一次關鍵的重要戰役。在這次戰役中,孫中山出奇兵,斷敵后路,絕其糧道,取得勝利,為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形成奠定了軍事和政治基礎。李浴日評價此戰乃是出奇制勝典型戰例。他總結說:先生在戰術上還有兩個貢獻,一是游勇戰術,二是非常戰術。并認為這種游勇戰術即出自《孫子兵法》。他說:“游勇戰術即現今所謂游擊戰術。惟現今的游擊戰術則比較進步了。”游擊戰術的原則,早見于《孫子兵法》中的“避實擊虛”“出奇制勝”。〔21〕在革命成功前,實際運用出奇制勝的典型戰例是1908年的欽廉之役。起義之初,義軍從安南繞道,分三路突然襲擊,路遇清軍就假裝是清兵,巧妙迷惑敵人,從而擊敗敵軍三營,占據馬篤山,取得初步勝利。當時安南法蘭西曾評論此役說“可稱奇捷”〔22〕。
(二)先發
“先發制人”是孫子兵法的重要戰術思想。在辛亥革命前,孫中山采取的戰略戰術大多是先發制人式的進攻策略。這是因為辛亥革命前,孫中山進行的革命斗爭是秘密的,敵強我弱,必須采取先發制人式進攻戰略戰術。即使辛亥革命后,孫中山在繼續革命的斗爭中,仍然主張先發制人。宋教仁案發后,孫中山就曾力主主動出擊,給予袁世凱以打擊,但因黨內意見不一,未能實施。對此陳其美在給黃興的信中比較詳細地說明了這一點,并以此證明孫中山在革命斗爭中的策略是英明正確的。孫中山在 《軍人精神教育》中說,武昌起義的勝利,就是先發制人的典型案例。他高度評價說:“革命黨人率先行動,以兩盒子彈取得了武昌起義的成功。余以為打破武昌者,革命黨人之精神為之兵法云:‘先聲奪人。’所謂先聲即精神也。”〔23〕
(三)速戰
“兵貴勝,不貴久”是《孫子兵法》中一個極其重要的戰術思想,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兵貴神速。孫中山在革命斗爭中尤其是辛亥革命前,由于沒有可靠的根據地作為依托,也沒有雄厚的群眾基礎作為依靠,更沒有自己的軍隊作為支撐,起義基本上都是采取突然襲擊、速戰速決的策略。他在1912年《告全國同胞書》中就明確主張速戰速決,他說:“運籌宜決而密,用兵當神而速。”〔24〕陳其美在給黃興的信中也比較詳細地說明了宋教仁一案發生后,孫中山先生曾主張運用“速戰”〔25〕方式,對袁世凱進行反擊。之后雖然有了根據地,也建立了自己的軍隊,但孫中山仍然十分重視速戰速決。1924年在討伐陳炯明及北伐期間致蔣介石的信中,孫中山再次強調了速戰的重要性。由此可見,速戰速決可以說是孫中山的一貫主張。
(四)嚴紀
嚴格的紀律是勝利的基礎。歷來治軍都十分強調用嚴格的紀律約束部隊。《孫子兵法》十分重視紀律建設,在為將“五德”中專門就有“嚴”這一條。“令文齊武”中“齊武”也是嚴。孫子演練宮女斬殺二妃子更是嚴。孫中山在革命斗爭中,深知嚴格的紀律是保證革命行動的基石。尤其是在秘密狀態下起義暴動,容不得半點懈怠,這也決定了嚴字當頭是孫中山治軍的一大特色。李浴日說:“先生在同盟會時代,為推翻滿清,對革命軍所頒布的‘軍律’極為嚴肅”。〔26〕此“軍律”共22 條,其中判處死刑的就有13 條,抵罪罰者有9 種情況。在中華革命黨時代“所頒布的‘軍律’亦極嚴肅”。共計25 條,其中死刑有16 種情況,禁錮9 種情況。正是這些嚴格的紀律規定,保證了歷次起義的順利舉行,也保證了在革命黨的關鍵時刻基本行動一致。
(五)治氣
中國古代用兵作戰十分講究“氣”的作用,所謂“一鼓作氣”“氣勢如虹”。實際上,“氣”就是精氣神,我們常說“人活一口氣”,俗語也說“不蒸(爭)饅頭爭口氣”。孫子在為將“五德”里面的“勇”,也含有“氣”的意思,并且強調說:早上氣勢兇猛,到了白天就有所減弱,而到了晚上則就懶洋洋地沒有了沖勁。孫中山深受其影響,在論述軍隊的戰斗力時,特別強調“氣”的作用。他認為革命軍隊要憑著一股子“氣”,要以一當十當百當千當萬。他強調革命軍之所以是革命軍,就必須以教育養成,“革命軍就是用一個人打一百個人”〔27〕。他解釋說:“是要各位兵士先有奮斗的精神。有了奮斗精神才能夠犧牲,才不怕死。軍人到了不怕死,還怕不打勝仗嗎?”〔28〕由此可見,孫中山對治氣是多么重視。
(六)用間
在《孫子兵法》中,用間單獨作為一篇進行論述,其重要性可見一斑。孫中山作為圣智之人,仁義之人,用間也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我們知道,1895年10月孫中山倫敦受難,被清使館拐騙,羈押使館,等待解送回國,因此命懸一線,危在旦夕。但他正是憑借大智大勇,巧妙用間,才得以脫身。情況是這樣的:1895年10月11日,清使館官員鄧廷鏗在倫敦德文郡街巧遇孫中山,他認出了孫中山,于是主動與他搭訕,套近乎說與孫中山是同鄉,于是一起邊走邊聊。當走到波特蘭大街時,鄧邀請孫中山去他家“飲茶”,誘捕了孫中山,伺機押解回國。鐵窗內的孫中山與世隔絕,多次發出求救信息,都沒有奏效。但他不氣餒,想盡千方百計,如通過宗教以獲信任,通過革命道理以獲同情。經過深入細致的工作,他終于獲得了公使館英籍工人柯爾和女管家霍維夫人的同情。在他們的幫助下,孫中山先生向老師發出了求救信息,成功脫險。這正是用間的典型事例。從某種程度說,辛亥革命的成功,也可以說是“革命成功,新軍在清”。
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最成功的用間是他們成功打入清軍內部,做通了部分新軍工作,使革命發生了質的變化。由于同盟會領導的文學社、共進社兩個革命團體在湖北新軍中開展了艱苦細致的革命工作,發展會員,宣傳革命道理,傳播進步思想,最終爭取到了新軍對革命的同情支持,進而參與、造成武昌首義,并取得了辛亥革命的成功。對此,孫中山說:“以南皮(張之洞)造成楚材,顛覆滿祚,可謂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29〕
總之,孫中山在革命生涯中,學習、研究、運用了《孫子兵法》中的智慧,并創造性地進行了發揮應用,為辛亥取得革命的成功助了一臂之力。
【注釋】
〔1〕李浴日:《中山戰爭論》,世界兵學雜志社1942年版,第1頁。
〔2〕李浴日:《中山戰爭論》,世界兵學雜志社1942年版,第3頁。
〔3〕翟杰、柳生編著:《孫中山的青少年時代》,中國華僑出版社2006年版,第8頁。
〔4〕翟杰、柳生編著:《孫中山的青少年時代》,中國華僑出版社2006年版,第37頁。
〔5〕《孫中山選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頁。
〔6〕《盛世危言》卷六《兵政》。
〔7〕《孫中山全集》第6 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31頁。
〔8〕《孫中山選集》(下),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55頁。
〔9〕《南方都市報》 2016年08月16日。
〔10〕《孫中山全集》第一卷,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53~254頁。
〔11〕孫重貴編著:《共和之父孫中山》,香港名人出版社2011年版,第130頁。
〔12〕周溯源編著:《孫中山全書》(上),紅旗出版社2013年版,第210頁。
〔13〕《孫中山全集》第一卷,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388頁。
〔14〕《孫中山選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0頁。
〔15〕《孫中山全集》第七卷,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21頁。
〔16〕《孫中山選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8頁。
〔17〕馮自由:《革命逸史》(第2 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江門日報》2011年1月10日第A10 版。
〔18〕陳旭麓、郝盛朝主編:《孫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40頁。
〔19〕《團結報》2016年11月14日。
〔20〕李浴日:《中山戰爭論》,世界兵學雜志社1942年版,第7頁。
〔21〕李浴日:《中山戰爭論》,世界兵學雜志社1942年版,第162頁
〔22〕李浴日:《中山戰爭論》,世界兵學雜志社1942年版,第5頁。
〔23〕李浴日:《中山戰爭論》,世界兵學雜志社1942年版,第85頁。
〔24〕李浴日:《中山戰爭論》,世界兵學雜志社1942年版,第152頁。
〔25〕《孫中山選集》(上),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88頁。
〔26〕李浴日:《中山戰爭論》,世界兵學雜志社1942年版,第145-146頁。
〔27〕李浴日:《中山戰爭論》,世界兵學雜志社1942年版,第85頁。
〔28〕《孫中山選集》(下),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15頁。
〔29〕孫重貴編著:《共和之父孫中山》,香港名人出版社2011年版,第10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