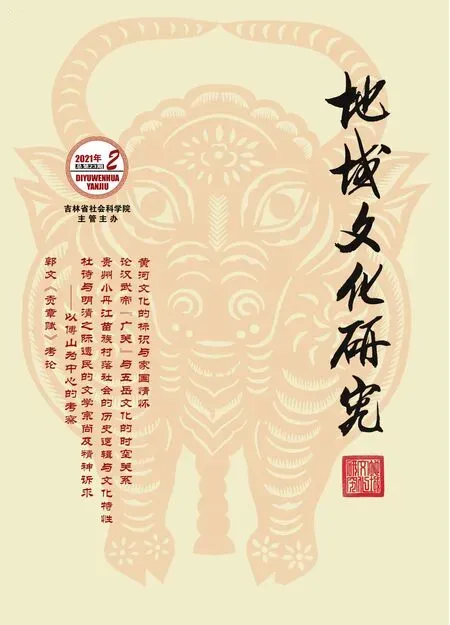“第三屆絲綢之路與敦煌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綜述
宿 星
2020年10月17—18日,“第三屆絲綢之路與敦煌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在甘肅省敦煌市召開。此次學術研討會由敦煌市人民政府、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西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主辦,敦煌市博物館承辦,來自國內20 多家高校和學術研究機構,近60名專家學者參加學術研討。與會學者圍繞敦煌歷史地理、民族關系、藝術宗教、絲綢之路中西交通方面與“推動敦煌文化研究服務共建‘一帶一路’,加強同沿線國家的文化交流,增進民心相通”等主題進行學術交流和研討,闡述分享對絲綢之路與敦煌歷史文化的研究成果,現將部分內容及觀點整理,簡要介紹如下。
一、敦煌與絲綢之路研究
與會學者們對于不同時期的絲綢之路歷史進行了廣泛探討。邯鄲學院的任乃宏等通過分析古籍《穆天子傳》,對周穆王的西行和東歸路線提出了新說,在目前被學界廣泛接受的“絲綢之路”含義的基礎上提出了“先秦絲綢之路”的概念。新鄉學院的王連旗更關注歷史給予我們的現實經驗。從先秦至南北朝時期國家為陸上絲綢之路的全面開通及保障陸上絲綢之路沿線地區的安全穩定做出的努力,總結成功經驗,建立起經濟上和文化上的血肉相連的命運共同體,增強廣大人民群眾對國家的向心力和認同感。西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陶興華等從先秦時期河西走廊獨具特色的文化發展,證明了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和互鑒,同時提出了先秦時期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發生區域并不在河西走廊一帶,其互動交融的交界區域和重要場所應該被確定在比河西走廊更加偏西和偏北的地帶,或許是在中亞綠洲和北亞草原地帶的觀點。西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的僧海霞則將重點放在了蒙元這一特定時期,解析當時中原人士與現實迥然有別的西域觀的形成是以話語主導者的政治需要為基礎,再現了中原士人域外地理認知所受的掣肘和遭遇的困境。河西學院的王紅成等則把目光聚焦于肅州,從明代肅州的軍事城防設置、朝貢使臣的東行路線和當時的貿易往來,說明肅州在明代綠洲絲綢之路上的重要作用。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的李若愚,以饒宗頤先生在中西交通史的研究為出發點,梳理其近年來相關研究,闡釋學界關于中國與波斯關系的觀點,對“黔首”“立石”“郡縣制”這些行為與波斯有關的觀點提出新解,認為中外文化之間存在交流與互動,但并不能簡單地認為這就是中西文化相互交流的產物,相似的習俗、觀念在不同的文化中分別發展是存在可能的,以期對早期的中西交通史有新的認識。
敦煌歷史研究,也是學者們討論的熱點問題。“敦煌”一名的含義,在歷史上一直都有著多種解釋。西北師范大學敦煌學研究所的李并成對多名學者的觀點進行分析后,認為探究“敦煌”一名的準確本義,還是應回到對其原始資料《史記》《漢書》等有關記載的準確解讀上。對于東漢應劭所言“敦,大也;煌,盛也”,這一解釋,認為所指并不限于敦煌本身,而更重要的是在于所指“廣開西域”。敦煌得名的原生性即在于西域的開拓及絲綢之路的開辟。西北大學的黎鏡明從東漢敦煌郡對西域事務介入的性質、動機和成效出發,分析了對西域的管控意愿和管控能力明顯弱化甚至缺失的東漢中晚期,敦煌郡在應對西域危局中發揮的巨大作用,以及東漢敦煌郡介入西域事務的條件和局限,否定了東漢敦煌郡介入西域事務的“代管說”和“大族自利說”,認為東漢敦煌郡對西域事務的介入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中央缺位情況下的地方補位。陜西省社會科學院的馬燕云,從唐宋時期敦煌民眾的飲食生活進行分類研究,得出了當時敦煌民眾飲食消費內容的多樣化,即主體可分為主食消費、副食消費和茶酒消費,以及飲食消費的社會性,即飲食消費的等級性和民族性的結論。
二、絲綢之路沿線出土文物與文化研究
在此次會議中,學者們對絲綢之路沿線出土的漢簡、斗瓶、梳篦畫像磚等進行了研究探討。在敦煌漢簡研究上,河西學院祁連學者李炳泉,綜合分析了敦煌漢簡、居延新簡及其他相關史料,認為“將卒長吏”主要是指受郡國委派護送所發戍田卒至服役地和從服役地迎回“罷卒”(即服役期滿的戍田卒)的縣、侯國之長相丞尉,或是指縣、侯國秩四百石(成帝陽朔二年前為五百石)至二百石的治民官;縣令作為秩六百石至千石的長吏,享有不承擔包括“將卒”在內所有“吏徭”的特權,不在“將卒長吏”之列。西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的楊芳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結合出土漢簡,對漢代河西歸義少數民族及其管理方面作進一步探討,認為漢朝對河西歸義民族實行靈活管理體制,并輔之優待政策,既適應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統治的需要,又與邊疆民族地區的實際相結合,對保障漢朝邊疆安全,維護河西社會穩定,促進絲綢之路繁榮發揮了重要作用。西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的李麗紅以敦煌馬圈灣漢簡武都郡籍戍卒省作簡冊入手,從戍卒籍貫、年齡、省作地點、代替人員及鉤校符上體現出漢代邊塞省作制度在運行過程中的有序性和組織嚴密性。
在絲路沿線出土文物考察上,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的史浩成對敦煌地區墓葬中出土的朱書或墨書等文字符號較為清晰的81 件斗瓶進行詳細的整理與分析,對其形制進行分類并總結從曹魏至唐代時期各自不同的特點,反映出當時中原文化與當地文化等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融合,以及敦煌地區在長期受絲綢之路的影響下,逐漸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并且體現在敦煌地區的喪葬習俗之中。西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的金玉考證了甘肅河西出土的魏晉十六國時期隨葬衣物疏中所記的8種名物,得出了《趙年衣物疏》所記“黃紿”是一種黃色的頭巾,《左長衣物疏》所記“單被”是一種上身衣物,《郭富貴衣物疏》所記“緋繡把”是一種陪葬墓中系有紅色刺繡過絲織物的手握,《姬瑜妻衣物疏》所記“緷襦”是一種緯向織制的絲織品制成的上身襦衣,《周女敬衣物疏》所記“青?”代指一種青色的上衣,《周女敬衣物疏》所記“金铓”是一種裝進“嚴具”的金飾品,《夏侯妙妙衣物疏》所記“黃遠蔾子”是一種黃綠色且可食用的植物,《桓眇親衣物疏》所記“鍼桐”是類似于今天針線包一類的縫紉工具包的結論。西北大學藝術學院的米雅楠則對新疆地區漢代的梳篦進行了分類整理,發現相較中原地區,新疆地區漢代的梳篦形制流行速度慢一些,梳篦主要的特色是樸素,且同一類型的梳篦之間沒有太大變化。
在絲綢之路沿線歷史文化研究方面,江蘇第二師范學院的楊賀站在音樂文化交流史的視角考察先唐西域音樂東傳所帶來的音樂文化的革新及其與文學演變的關系,認為中古時代西域音樂東漸對文學的影響則要歸結為“西樂東漸——同漢地音樂融合并接受其反撥——為漢地文學所用——接受漢地文學的改造”這樣一支四部曲,西樂東傳的過程也是其與漢地南北方音樂廣泛融合并同化為新“華樂”的過程。先唐西樂東漸豐富了中國音樂的藝術內涵,催生了新的音樂文化和文學,也為古樂和文學的唐宋因革奠定了藝術基礎。荊楚理工學院藝術學院龔伊林研究了山普拉墓地紡織品紋樣上的一些典型的藝術形象及其文化特征,并借用兩河文明、愛琴文明、草原文明等諸多藝術因素用以分析其紡織品圖案的復雜性。表明山普拉墓地紡織品紋樣受西亞早期文明、中亞貴霜及草原文化圈的影響較大,是絲綢之路東西文明交流的產物,是服飾文化高度發展的反映。西北師范大學敦煌學院的劉春山基于對石窟藝術的考察,將元青花大盤與敦煌唐代石窟圓光裝飾形式比較研究,認為元青花大盤復雜華麗的同心圓裝飾形式不僅受益于中亞金屬器,來自敦煌石窟的圓光也對它產生了影響。開封市建設委員會的宋喜信通過北宋東京天清寺繁塔“西域牽虎行腳僧”佛像磚,結合敦煌藏經中出土的東京天清寺《開玄鈔》,以及北宋有關“紙畫”“印施佛像”等文獻,論述了敦煌出土的“行腳僧”紙畫,應是源于宋初,且有出自北宋東京城之史跡。也依據“牽虎行腳僧”“伏虎羅漢”和“伴虎僧”等三種類型“僧虎同框”的圖像實例,闡明了“伏虎羅漢”有別于“伴虎僧”的問題。青海師范大學歷史學院的楊榮春則從沮渠牧犍在譯經造塔、抄經寫經、開窟造寺、塑像壁畫等方面取得的巨大的發展出發,論述了沮渠牧犍對北涼佛教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湘潭大學碧泉書院的劉嘯虎將關注點放在了唐代前期西北邊地軍人的日常飲食及進食方式上,從麥飯與馬盂中窺探與唐代前期經略西北的軍事態勢。
在對絲綢之路沿線近現代的歷史研究中,上海師范大學的康越良回顧了過去40年來有關民國時期甘肅開發史的研究狀況與主要成果,厘清現有研究的問題與不足,進一步明確今后研究的目標與方向,對不斷豐富和完善甘肅開發史研究具有現實意義。西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的侯培和則以甘肅省為例對西北抗戰大后方煙毒治理及績效進行了分析總結。美籍獨立學者任光宇在梳理學術界近年成果的基礎上,將清末涉及敦煌遺書流失和搶救的60多位相關人物,分為失職官員、無為學人和有功之人三大類,逐一排列并嘗試給予功過評議。
三、敦煌壁畫及文獻研究
敦煌壁畫一直吸引著學者們的目光,西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的秦丙坤和秦凱對敦煌莫高窟壁畫中出現的琵琶意象進行了分類分析,闡述了琵琶作為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質見證,在唐與西域、唐與日本文化交流中起到重要作用。西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的陳凱源在對莫高窟第23窟的造像意涵及功能分析后,認為該窟很有可能是一個以“法華”為主題,含攝不同禮懺滅罪法門于一體的禮懺場所。敦煌研究院的袁德領細致分析了莫高窟北魏第254窟《難陀出家因緣圖》,認為佛陀的左前方人物應為“密跡金剛”,右側人物應為“難陀”,左右兩前側應為《惜別圖》,《難陀出家因緣圖》的繪制,與當時流行的《密跡金剛會》有關。西北師范大學美術學院王成文對榆林窟現存的唐、五代、宋、西夏、元時期的23 個洞窟的普賢造像遺存,進行分類、分析和研究,從普賢圖像的基本組成元素包括普賢、六牙白象、圣眾隨從、背景圖像等在不同時代的變化入手,分析出榆林窟普賢圖像的藝術特征和美術史價值。寧夏海原縣文化旅游廣電局的李進興通過對各地遺址考古出土和發現的西夏釀酒、儲酒、飲酒等器具進行解析,從中篩選出幾個典型酒器與榆林窟第三窟的西夏《釀酒圖》壁畫中的器皿進行比對解讀,進一步確定了此幅壁畫的創作年代及壁畫中出現器皿的名稱,證實了西夏釀酒的盛行。西北師范大學敦煌學院的劉春山基于對敦煌石窟藝術的考察,將元青花大盤與敦煌唐代石窟圓光裝飾形式進行比較研究,認為元青花大盤復雜華麗的同心圓裝飾形式不僅受益于中亞金屬器,來自敦煌石窟的圓光也對它產生了影響。
在敦煌文獻研究方面,學者們關注的話題較為廣泛。敦煌研究院的楊富學和淮陰師范學院的蓋佳擇結合敦煌遺書和前人研究,剖析了歸義軍史上三起人倫悲劇疑云,窺探晚唐五代節度使家族的權力爭端,認為赤裸裸的利益成為悲劇得以一而再再而三發生的原因。首都師范大學的武思亞關注點則落在敦煌漢文書寫的變化上。從吐蕃時期敦煌與中原地區貿易的中斷入手,通過論證藏文在敦煌的普及,展現漢文書寫文化變革的社會因素;繼而分析硬筆寫本的內容類型,探究其書寫適用范圍的局限性;并對書手的民族、職業、階層進行揭示。西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王新春對瑞典國家檔案館藏斯文·赫定中國檔案的生成與移交、分類與內容、特色內容與學術價值做了總結。西北師范大學法學院的蔣晨光,以敦煌遺書宋里仁侍母案等為分析素材,解析了原生秩序下的情法資源優勢。攀枝花學院的曹利華更加注重微觀視角,從語言這一獨特視角出發,分析吐魯番出土文書中的商業類、生活類、軍事類、宗教類借詞“薩薄”“迭”“胡祿”“胡天”4詞,考證它們在漢語中的使用、流變及其所折射的民族關系與民族交往特點。在河西寶卷的研究上,西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的張之佐等從明清政府對民間信仰的態度、政策和明清時期河西地區民間信仰的特征入手,分析了明清時期民間宗教信仰與“河西寶卷”世俗化之間關系。河西學院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的崔云勝則將《仙姑寶卷》與黃天教《靈應泰山娘娘寶卷》進行比較,從靈應泰山娘娘處尋找和解釋了平天仙姑的來源和根基。
本次學術研討會內容豐富,討論充分,新人涌現,取得了圓滿成功。各位與會代表通過不同視角,對絲綢之路與敦煌歷史文化進行了深入的分析探討,既有新資料的發掘、新方法的運用、新領域的開拓,也有老課題的深化,必將對絲綢之路與敦煌歷史文化研究,起到很好的推動作用,并對弘揚敦煌文化及新時代“一帶一路”的建設提供積極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