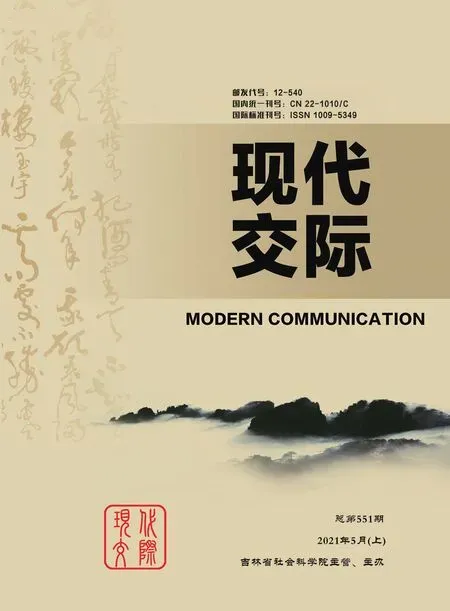從泰語漢源文化詞看漢語在泰國的傳播
楊 剛
(云南民族大學文學與傳媒學院 云南 昆明 650504)
作為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語言(尤其詞匯)反映社會文化,也受社會文化的制約。任何一種文化從其產生開始便與周圍的其他文化交流往來。國家間文化的交流,大都可通過歷史文獻、考古等進行復原、回溯,語言中的詞匯同樣具有這種功能。比如某種語言中的外來詞,尤其是其中異質特征明顯的文化詞,便是兩種不同文化交流的結晶。對上述詞語的語源和語義進行梳理,可以更好地反映文化交流演進的脈絡,為考古學、人類學等學科的結論提供語言學的有力佐證。
中國與泰國世代友好,學界對兩國文化交流研究成果豐富,唯漢語在泰國傳播的研究長期處于冷僻狀態。本文擬對《泰語詞典》收錄的漢源外來詞,特別是漢源文化詞進行定量定性分析,總結其基本特征,結合中泰文化交流史尤其移民史、宗教交流史的研究成果分析這些特征形成的深層原因,在此基礎上,初步勾勒漢語在泰國早期傳播的基本脈絡、主要路徑等,為中泰文化交流的研究提供新的角度。
一、泰語漢源文化詞的確定
(一)漢源文化詞的界定
本文所指“泰語漢源文化詞”為泰語詞匯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具體而言,為泰語詞匯中的一般詞,少數為基本詞;從其來源看,則屬于外來詞,具體而為泰語詞匯系統中源自漢語的詞語。與普通漢源外來詞不同,漢源文化詞主要反映中國特有或源自中國的事物。對泰語中的漢源文化詞進行考證,比如其出現的時間、語義流變的階段,不僅具有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價值,更能為泰國華人移民史的研究提供有力的詞匯學佐證。
(二)泰語漢源文化詞的特征分析
本文以廣州外國語學院編撰、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泰漢詞典》為分析樣本,以泰語詞類劃分標準,確定源自漢語的外來詞386個[1],在此基礎上挑選出反映中國特有事物或中國特征明顯的詞語,即本文所指的漢源文化詞,共計361個,以詞性觀之,名詞300個、動詞46個、形容詞15個。上述詞語總體上具有以下特征:
1.名詞高度集中
本文確定的361個漢源文化詞中,名詞300個,占比高達83.1%,從其語義所反映的事物來看,上述詞語皆屬于漢語詞匯中的基本詞,比如:(豆腐)、(醬油)、(綾綢)、(繭綢)、(功夫)、(清明)、(老子)、(孔子)、(風水)等。其反映的都是與漢民族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事物、人物,具有使用頻率高、范圍廣、語義穩定等特點。詞匯學的觀點認為,語言的學習往往從基本詞開始,本文對泰語漢源文化詞的梳理結果符合上述結論。可推知,漢語在泰國的傳播,首先應該是從你無我有的漢語基本詞開始的。
2.借用方式簡單
本文確定的漢源文化詞,就借用方式來看,有71.43%的詞語采用音譯的方式。在詞語借貸中,音譯為最簡便、最原始一種。泰語漢源文化詞中音譯數量最多,比例最大,可知泰語對漢語詞語的借用其實層次不高。可推知,漢語在泰國的傳播,其傳播者大部分應屬于社會中下層人士。
3.地域特征明顯
本文確定的漢源文化詞,就其語源來看,絕大部分來自中國潮汕方言,這是泰語漢源文化詞最顯著的一個特征。比如:
相較之下,泰語漢源文化詞中源自官話的非常少。這與泰國移民史研究的結論:泰國華人先祖主要來自廣東、福建,不謀而合。可推知,漢語在泰國的傳播,傳播者的主力應該是來自廣東的中國人。
4.時代特征明顯
本文確定的漢源文化詞,就其反映內容而言,大都集中于中國封建社會相關事物,從所處時代來看,大都在中國近代以前。比如:(三保公)、(通事)、(符)、(風水)、(五行)等。上述詞語標志的都是歷史上曾經存在的事物或現象,即詞匯學所謂的歷史詞。歷史詞在現代漢語一般交際中不會使用,只有在特定的語境、涉及這些歷史事物和概念時才會使用。相較之下,泰語漢源文化詞中源于現當代中國的幾乎沒有;究其原因,應與中泰兩國友好往來自1949年之后一度中斷有關。可推知,漢語在泰國的傳播,在20世紀40年代以后有相當一段時間的停滯。
二、從漢源外來詞看漢語在泰國的早期傳播
(一)漢語傳播概況
中國與今泰國地區在漢武帝時期已有貿易將往。《漢書·地理志》記載:“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諶離國。”[2]學界一般認為,邑廬沒國即泰國叻丕[3],都元國、邑廬沒國、堪離國分別為泰國的巴真府、素攀府、北碧府[4]。一般認為,早期的語言傳播往往由經貿往來推動,因此,盡管沒有直接的文字記載,仍可推知早在中國西漢時期,漢語有伴隨經貿活動進入今泰國境內的可能性。
與經貿往來相比,佛教交流對漢語傳播的推動則更加強勁。中國南北朝時期,高僧曼陀羅、僧伽婆羅、須菩提、真諦等先后前往中國傳播佛教。從中國文獻記載來看,四位高僧都具有較高的漢語水平,比如,僧伽婆羅能與梁武帝有過面對面的交流[5],真諦與鳩摩羅什、玄奘并稱中國佛教三大譯師。以上事實說明,當時包括今泰國在內的中南半島,產生了對漢語的現實需要,出現一批熟練掌握漢語的人。漢語在泰國的傳播以從被動輸入轉為主動吸收。當然,這種“主動”以佛教的傳播為前提,或者說是佛教傳播的副產品。佛教僧侶學習漢語的目的在于傳播宗教,對漢語的學習圍繞宗教展開,具有較強的功利性和針對性;一旦宗教傳播的任務達成,其對漢語的學習隨之暫停,更談不上對漢語進行推廣與傳播。
中國文化在古代泰國的傳播與兩國政治、宗教(佛教)和貿易往來相伴,當上述傳播活動上升到一定層次,學習彼此語言成為必需。漢語隨商人、僧侶、進入泰國,但并未真正傳播開來,原因在于:首先,進入泰國的中國人數量不大,他們達到各自(或外交或宗教或貿易)的目的后,大都回國,定居泰國的為極少數,無法形成一定數量的漢語傳播者;其次,兩國之間的各種往來可借助雙方都熟悉的第三種語言,沒有必要一定使用漢語。
對漢語傳播起到實質性推動作用的是中國的移民。最遲至1165年,已有中國人到今日泰國境內從事貿易并定居,成為最早的華僑。[6]到了元代,中國人不僅留居當地,還與當地人通婚。汪大淵在《島夷志略》中曾提到,在今泰國北大年地區,華人廣受尊敬。[7]114宋元兩朝,一定數量定居華人的出現,為早期的漢語傳播奠定了基礎。到了16、17世紀(中國明末清初),移居暹羅的中國人逐漸在今北大年、宋卡、暹羅首都大城等地定居,泰國華人社會得以初步形成。[7]123華人社區的形成,對漢語在泰國的傳播影響重大。一方面,華人社區存在文化、語言傳承的內在需要,這極大地推動了漢語在華人社區中的傳播與傳承;另一方面,華人社區與當地族群存在一定的交流與互動,相互接觸中也推動了漢語在當地社區中的傳播,可以說,華人社區是漢語在泰國傳播最早的橋頭堡。
中國明代,漢語在泰國的傳播產生了質的飛躍。首先,從1371年開始,暹羅向中國派遣留學生學習漢語。[8]1678一般認為,語言的教學與學習是語言傳播最為主要的方式,暹羅向中國派遣留學生的事實說明,暹羅國內對漢語產生了現實的需要。漢語在暹羅的傳播已上升為政府的主動行為,真正意義上的漢語的傳播也由此開始。華人逐漸進入暹羅官僚體系擔任翻譯、使臣等職務,這一史實說明,華人社團已實現與暹羅社會的有機融合。伴隨著這種融合,不僅更多的暹羅人對漢語產生認知,而且其傳播形式已實現從華人相互間的人際傳播上升為更高層次的群體傳播。其次,1579年,中國政府設立暹羅館,專司暹羅語言、文字的翻譯、教習。[8]1678從其基本職能看,暹羅館已初步具備漢語傳播機構的基本特征。除了培養語言傳播人才,暹羅館編輯了最早的泰漢雙語字典《暹羅館譯語》。該字典收常用字3550個,其中部分泰語詞語的發音與潮州方言、閩南方言發音接近。由此可知,最遲在明代,漢語方言已經進入當時的泰語系統。暹羅館及其編纂的《暹羅館譯語》在泰國漢語傳播的歷史進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說明此時漢語在暹羅的傳播已有了專門的機構和相對固定的專職傳播者,取得了較明顯的傳播結果。
(二)傳播路徑分析
如前所述,泰語漢源文化詞絕大部分來自中國潮汕方言而非官話,這與最早遷入泰國的中國移民有較大關系。據考證,早在素可泰時期,中國潮州人已開始舉家移居至泰國做生意,而最早一批進入泰國的中國移民,其祖籍地多為今廣東潮汕地區。[9]53潮州移民的遷入,必然帶動潮州方言在當地的傳播。最開始,潮州方言只在當地華人中流行,伴隨華人社區與當地人交流的日趨頻繁,潮州所有而本地所無的事物逐漸為當地人所了解,最終以音譯的方式進入泰語詞匯體系,這也合理解釋了前文所述泰語漢源文化詞潮汕特征明顯的原因。
泰國華人根據年齡可分為老、中、輕三代。老年華人大多數只會說中國本地的方言;中年華人大多數會說中國方言與泰語;青年華人相當于泰國本地人,只會泰語,中國方言幾乎都不會。這樣的現實,一方面導致華人社團的漢語繼承出現斷檔,無法吸收新鮮的語言成分;另一方面則起到強化作用,即老、中年華人方言詞使用較多,進一步強化了潮州方言詞在華人社團漢語詞匯體系中的地位,這種強化最終在泰語漢源文化詞中體現出來。
泰語漢源文化詞的另一典型特征,即反映中國封建社會事物、現象的歷史詞占比較高,這與兩國歷史上的交往有較大關聯。一般來說,語言詞匯系統的交流與社會的開放度成正比例關系,即社會越開放、交流互動越通暢,甲語言中的常用詞、新詞等越會及時在乙語言中反映出來;反之,則會出現遲滯甚至空白。據考證,中國移民大量進入泰國主要集中于曼谷王朝拉瑪三世至拉瑪五世時期[9]54,即1824年1910年期間,此時正是中國清朝,仍與泰國(暹羅)保持著朝貢體系。中國清朝官話中的常用詞匯隨中國移民進入泰語詞匯系統,最終形成漢源外來詞的主體。拉瑪四世王時期至1975 年,中泰兩國中斷往來,此間,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社會劇變導致的漢語詞匯更迭,兩國往來的中斷所形成的“真空”,并未在泰語詞匯系統中及時反映,最終形成漢源文化詞古語詞較多的事實。
三、結語
中泰交往早期,泰國本土對中國知之甚少,通過幾代泰國華人與泰國社會的交流、融和,中國特有物產、風俗習慣、思想觀念等逐漸為當地人所了解,泰語中吸收的漢語文化詞正是這種文化傳播的結果之一。漢源文化詞進入泰語,擴大了泰語詞匯系統,又傳播了中國傳統文化。
漢語在泰國傳播過程中形成的漢源文化詞,在泰語詞匯系統中具有重要地位。經過分析,我們發現,泰語中的漢語外來詞結構上以音譯為主,內容上標記中國特有事物,受閩粵方言影響深刻、歷史詞較多等特點。這些特征的形成與中國華人早期移民泰國的歷史密切相關。對泰語中的漢源文化詞進行系統研究,無論對詞匯學還是在傳播學甚至移民史研究都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