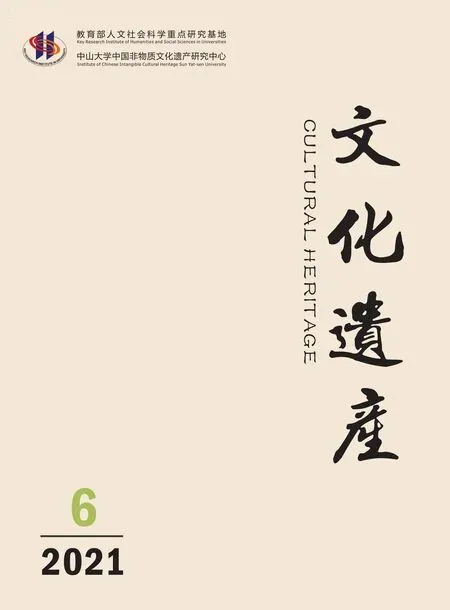20世紀初英國人類學家威廉·里奇韋的中國戲劇研究
譚 靜 程 蕓
1918年《新青年》第五卷第五號刊發了周作人的一篇著名文章《論中國舊戲之應廢》,其中一段這樣說到:
我們從世界戲曲發達上看來,不能不說中國戲是野蠻。但先要說明,這野蠻兩個字,并非罵人的話;不過是文化程序上的一個區別詞,毫不含著惡意。……中國戲多含原始的宗教的分子,是識者所共見的;我們只要翻開Ridgeway所著《非歐羅巴民族的演劇舞蹈》就能看出這些五光十色的臉,舞蹈般的動作,夸張的象征的科白:凡中國戲上的精華,在野蠻民族的戲中,無不全備。(1)周作人:《論中國舊戲之應廢》,《新青年》1918年第五卷第五號。后文中里奇韋著作中文譯名保留周氏的翻譯。
這篇文章,集中體現了20世紀初期中國知識界廢除“舊戲”(中國傳統戲劇)的激進主張,其中提到的《非歐羅巴民族的演劇舞蹈》即威廉·里奇韋(William Ridgeway,1853-1926)(2)William Ridgeway尚未有通行的中文譯名,本文參考《英語姓名譯名手冊》,譯作“威廉·里奇韋”。參見新華通訊社譯名室編《英語姓名譯名手冊》(第4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611、756頁。的著作TheDramasandDramaticDancesofNon-EuropeanRaces。里奇韋時任劍橋大學古典學、考古學教授,是英國人類學、民族學的創立者之一。該書出版于1915年,很快就進入周作人的閱讀視野,并被引以確證“中國戲”(可理解為中國傳統戲劇,即通常意義上的中國戲曲)在“世界戲曲”(可理解為一般意義上作為演劇形態的戲劇)發展史上不發達的位置。盡管周作人強調“野蠻”只用作發達程度的區分,并非價值優劣的評價,但在20世紀初“野蠻”“原始”其實即“落后”的時代話語的裹挾下,中國戲曲已被貼上“落后”的標簽。周氏這篇富有戰斗性和號召力的文章被中國學人們廣泛引用和討論,(3)參見周云龍《本真的幻象:中國論述與崛起的氛圍》,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4年,第109頁;張福海《中國近代戲劇改良運動研究(1902-191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10-413頁;高有鵬《中國民間文學發展史(第8卷)》,北京:線裝書局2015年,第2888頁;許昳婷《戲里戲外:中國現代話劇觀念的艱難抉擇》,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52-54頁。而受到周氏“廢除舊戲”主張先入為主的影響,里奇韋這部著作的問題視域、學術理路和文化觀念,也被后世學人有意無意地曲解和忽視。
事實上,通讀、細讀《非歐羅巴民族的演劇舞蹈》,我們發現,即便今日,該書的學術立場、戲劇史觀和所試圖傳達的文化觀念,仍然值得納入戲曲學術史、觀念史的維度進行再探討;其在歐洲學術史、中西學術交流史上的重要價值,尤其值得深入挖掘。
一、《非歐羅巴民族的演劇 舞蹈》的“問題意識”
威廉·里奇韋1853年出生于愛爾蘭,1926年去世。他曾先后就讀于都柏林圣三一學院和劍橋大學岡維爾與凱斯學院,1883年起任考克女王學院希臘文教授(Chair of Greek in Queen’s College Cork),1892年被聘為劍橋大學迪斯尼考古學教授(Disney Chair of Archaeology in Cambridge),1907年起同時擔任布里爾頓古典學準教授(Brereton Readership in Classics, Cambridge),1904年入選英國科學院院士,曾擔任皇家人類學學會主席(1908-1910),劍橋大學語言學、古文物學、古典學及人類學學會主席,英格蘭及威爾士古典學會主席(1914)等學術職務,被《泰晤士報》譽為“廣博型學者”(a scholar of wide range)。(4)“Obituary.Sir William Ridgeway: A Scholar of Wide Range,” Times Aug 13, 1926.里奇韋著述豐富,且多是相關領域的奠基性研究,許多著作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多次在歐洲和美國再版,對西方的人類學、社會學、民俗學和博物學等都有重要影響。
《非歐羅巴民族的演劇舞蹈》完成于里韋奇的學術成熟時期,可謂是他《悲劇的起源》(TheOriginofTragedy,1910)一書的“續編”,其寫作初衷是為進一步論證他此前提出的古希臘悲劇起源于“死亡崇拜”(worship of the dead)這一學說。(5)William Ridgeway, The Dramas and Dramatic Dances of Non-European Ra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5), Vii.
關于悲劇的起源,當時歐洲學界存在不同的學說,包括盛行已久的酒神崇拜說,19世紀中期以來興起的太陽崇拜說、樹神和谷神崇拜說、圖騰崇拜說,還有被東方學者普遍認定的“偶戲說”(puppet-play)。對這些學說略作了解便知,里奇韋的“死亡崇拜說”,正是在與同時代學者的論爭中形成的,這些學者包括東方學家、比較宗教學家馬克斯·繆勒(Max Müller, 1823-1900)、皮希爾(Richard Pischel,1849-1908),以及以人類學家弗雷澤(James Frazer,1854-1941)、哈里森(Jane Ellen Harrison,1850-1928)和康福德(Francis Macdonald Cornford,1874-1943)為代表的“劍橋儀式學派”(Cambridge ritual school)等。里奇韋認為,上述戲劇起源論,都是在“死亡崇拜”的基礎上衍生出的次級現象(secondary phenomena),都不具備“死亡崇拜”作為原初信仰(primary belief)的特性。(6)William Ridgeway, “Dramas and Dramatic Dances of Non-European Races: A Reply,” The Classical Review 30, no.7 (November, 1916): 207-208.而他則試圖“從人類學的立場來獲得這個問題真正的解答”。(7)William Ridgeway, The Origin of Trage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0), vii.
里奇韋“死亡崇拜說”的核心觀點,是戲劇起源于并依賴于人類對靈魂不朽的信仰(belief in the immortality of the soul)。因為人類相信逝者擁有不朽的靈魂,所以,戲劇化地(dramatization)表現逝者的功績或苦難,如同以舞蹈、頌歌、繪畫和雕像等形式一樣,既是對逝者靈魂的慰藉,又是向逝者靈魂、精神的祈禱,求其繼續庇佑、賜福人類。他指出,并非所有逝者都具有不朽的靈魂,那些受崇拜的不朽靈魂,只屬于原本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偉大戰士、英雄、部族首領、圣人等杰出人物。這一“戲劇化”的表現形式貫穿于被崇拜者生前、死后、被奉為英雄或圣人乃至最終被神化的各個階段。正是在與不朽靈魂的溝通中,戲劇的要素和形式獲得了完善和發展。(8)Ridgeway, Dramas and Dramatic Dances, 210; Ridgeway, Tragedy, 55.換言之, “死亡崇拜說”傳達出崇拜儀式與戲劇起源之間具有直接的關系。他還認為,儀式和戲劇的相似之處,在于都有一種“重現”(re-enact)的能力,并且“重現”的故事和思想,都借鑒了相似的神話或歷史的來源。
然而,儀式并不能等同于戲劇。對于先民而言,“死亡崇拜”信仰,及其在人類社會中的儀式化表現,是人類面對自然、死亡或災難等未知事物和現象時的一種處理方式。儀式神圣且嚴肅,構成了他們的生存狀態或生存方式本身。參與儀式的人,以身心同步在場的方式融入“重現”活動。相比之下,具有娛樂、游戲意味的戲劇,是有意識地對虛構進行表演;劇場之內的觀眾作為旁觀者,通常并不參與戲劇的表演(當然,現代的戲劇表演已打破這一慣例,此處主要討論早期戲劇)。然而,當追問崇拜儀式如何成為戲劇表演,以及戲劇表演如何成為向不朽靈魂敬獻崇拜的重要組成部分時,我們發現,在理論上,里奇韋也缺乏對人類儀式由“非戲劇”跨越到“戲劇”這一轉變的清晰論述。特別是,當他使用“戲劇”(drama)、“戲劇化”(dramatization)、“戲劇表演”(dramatic performances)(9)Ridgeway, Dramas and Dramatic Dances, 209.這些今人大約能明確其內涵和外延的詞匯,來描述早期乃至原始文化形態中的儀式性活動時,事實上,他所研究的人類活動就已經是“戲劇”了。“戲劇化”,實為去除了崇拜儀式中的嚴肅性和其作為生存方式的直接性,帶入了主觀的“表演—觀看”意識。里奇韋不可避免地受到后設的“戲劇”觀念的影響,并以此來研究“非戲劇”現象,而他本人對這個隱含的前提并沒有作充分的檢省。這既是前人的一種學術缺憾,也是值得后人警醒的一種思維慣習。
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洲學界有關中國戲劇起源的流行論斷,包括“偶戲說”和祖先崇拜說。“偶戲說”由德國東方學家皮希爾教授提出,他認為偶戲產生于印度,并且是印度戲劇與其他大多數東方戲劇的共同起源。偶戲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又與神靈崇拜和祖先崇拜關系十分密切。與里氏交往密切的新教傳教士和漢學家們,深受這些觀念的影響,并以實地考察和研究獲得的經驗,向歐洲讀者傳遞類似的觀念。1911年12月13日,倫敦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赴華傳教士麥嘉湖(John MacGowan,1835-1922,又譯麥高溫),在倫敦的“中國學會”(China Society)發表題為《中國戲劇的起源與影響》的演說,就宣稱“中國戲劇起源于偶戲(puppet-shows)”,(10)“The Chinese Drama, Its Origin and Influence,” Times Dec 14, 1911.他對中國鄉村演劇狀況的詳細描述,也被里奇韋多次引述。還有在中國傳教長達四十八年、后任牛津大學漢學教授的英國傳教士蘇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1935),在與里奇韋的通信中也確認偶像崇拜和中國戲劇的關系非常緊密,“供奉地方神靈(local gods)的各處廟宇都會演劇,演劇的目的不只是娛神,還要確保神靈保佑酬謝他的這一方土地和人民興旺發達。”(11)Ridgeway, Dramas and Dramatic Dances, 267.
里奇韋認為,中國的戲劇表演以酬神和祈求祖先神明的庇佑為目的,這種信念得以成立的前提,就是因為人們相信靈魂不朽,并且逝者的靈魂對后代的福祉具有強大的影響力。(12)Ibid., 268.通過交往密切的傳教士和漢學家的記述,同時,結合對不同國家和地域戲劇文化的考察,里奇韋提出了“地方神靈”產生的普遍機制:具有杰出個性的人在生前,就可能獲得崇拜;死后,受到更加頻繁的崇拜;埋葬其尸體的墳墓(tomb),逐漸成為祠堂(shrine),祠堂又成為神廟(temple),神廟又在年復一年的祭典上,成為民眾的朝圣之所(pilgrims resort)。(13)Ridgeway, “Dramas and Dramatic Dances of Non-European Races: A Reply,” 207-208; Ridgeway, Dramas and Dramatic Dances, 209.地方神靈就在墳墓、祠堂和神廟施行的祭祀和崇拜儀式中,同步產生。地方神靈在民間演劇中,既是觀眾,又是被演繹的角色。這兩個功能,呈現了戲劇與祭祀、崇拜、酬神等原始儀式在“死亡崇拜”這個維度上互為表里的關系。
時任劍橋大學漢學教授翟理思(H.A.Giles,1845-1935)認為,在中國文學和文化中,“地方神靈總是這片土地上的英雄兒女”;(14)Ridgeway, Dramas and Dramatic Dances, 267-268.翟理思之子,大英博物館東方部館員翟林奈(Lionel Giles,1875-1958)也以關公戲為例,來說明中國歷史劇主要表現的是英雄的生活、歷險及其最終被神化的主題。(15)Ibid., 268.翟理思父子的研究和總結,都被里奇韋視為對地方神靈生成機制的映證。經里奇韋人類學視角的重新整理,當時流行于歐洲的中國戲劇起源假說——“偶戲說”和“祖先崇拜說”,也成為包含在“死亡崇拜說”邏輯之內的次級現象。
關于中國傳統戲劇起源的探討,是戲曲史研究的重要內容,更是自王國維《宋元戲曲史》(1912-1913年成書)以來中國現代戲曲學一直爭議不斷的問題。它既關聯著史實、文獻層面的梳理和判定,還依賴著理論、方法和視域層面的切入和展開。曾永義先生曾對各種各樣的戲曲起源說,做了詳盡且清晰的梳理,并總結為五種類型。(16)曾永義:《戲曲源流新論》,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30-32頁。顯然,戲曲起源論和其它很多領域的發生學一樣,始終是一個敞開的問題域。
二、20世紀初歐洲的中國戲劇認知
《非歐羅巴民族的演劇舞蹈》“中國戲劇”一節包括“祖先崇拜”“中國戲劇”“劇作分類”“武戲演員與文戲演員”和“劇場”幾個部分。從學理脈絡和學術傳承來看,該書呈現的中國戲劇研究,濃縮了同時代歐洲學者的觀點,尤其深受翟理思父子的影響,并表現出人類學視野下比較戲劇研究的自覺。同時,里奇韋對中國戲劇舞臺表演形式和劇場的關注,與20世紀初歐洲和美國風行的“中國戲”(Chinese play)(17)所謂Chinese play,在世界文學語境含義豐富,可用以指中國戲劇,或指西方人創作的與中國題材或中國人物有關的戲劇,還可指歐洲上演的脫胎于中國戲劇的改編劇作。此處為最后一種含義。的演劇背景密切相關。上述層面,共同構成了里奇韋中國戲劇研究的時代語境。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漢學家,有意識地將中國戲曲作為一種演劇形態乃至社會文化現象來加以觀察,而不像同時代許多中國學人,還主要把戲曲視為一種文學形式去理解。翟理思同樣表露出歐洲新興文化人類學和民俗學的旨趣,而非只是以“純文學”(belles-lettres)視角來定位中國戲曲。他在《中國文學史》(AHistoryofChineseLiterature, 1901)中談到:
追溯到孔子以前或傳說時代(pre-Confucian or legendary days),我們發現從遠古時代開始,中國人就在嚴肅或節慶場合的祭祀和儀式上,伴隨音樂跳著固定形式的舞蹈(set dances)。……我們知道,歌、樂、舞很早就成為宗教儀式和各種慶典中常見的相伴形式(ordinary accompaniment),這種現象持續了許多世紀。(18)Herbert A.Giles,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01), 256-257.
歌、樂、舞相伴的形式,“自孔子以后1200年,沒有明顯的發展”,直到唐明皇建立“梨園”,“親自教習三百子弟表演歌唱(opera)”,(19)Opera在西方戲劇史上,最先是指一種用以復興古希臘悲劇的歌唱形式,后來才逐漸獨立成為一種戲劇體裁。結合唐代梨園教習的具體情況,此處將opera譯為“歌唱”。參見J.A.Cuddon, The Penguin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 and Literary Theory (Revised by C.E.Preston)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1999), 616.“并在唱段之間引入一絲故事的線索(the slender thread of a story)”,才產生了新的變化。翟理思將故事情節(盡管情節十分微弱)的加入,視作唐代在戲劇形式上貢獻。而“其后五百年,根據現有的證據,戲曲幾乎沒有走出宮廷,沒有成為民眾娛樂的組成部分”,直到13世紀中期宋朝滅亡、蒙古征服者建立大元帝國,“來自外部的推動力才喚醒了中國人的戲劇本能”。(20)Ridgeway, Dramas and Dramatic Dances, 270.歐洲漢學家們通常將周代、唐代和元代視為中國戲劇發展史上三個重要的時期。翟林奈亦將孔子時代宗廟祭祀慶典的嚴肅舞蹈(solemn dances)置于中國戲曲的起始位置,因其包含著中國戲曲的主要形式要素:歌、樂與舞。但他指出,嚴肅舞蹈并非中國戲劇的完成形式。如果對比稍后幾年問世的被視為中國現代戲曲學奠基之作的《宋元戲曲史》,就會發現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論斷:中英學者都把元雜劇作為中國戲劇的第一種完備形式。
翟理思《中國文學史》以朝代為序,共八卷,第六卷元代文學和第七卷明代文學述及戲曲的起源和發展、演劇形式、戲班和演員體制,以及戲曲在中國文學中的地位等諸多話題,頻頻被里奇韋引述。該書也深受西方讀者和學者的推崇。然而,在文學史書寫方面有著豐富經驗和巨大聲譽的中國學者鄭振鐸,卻對翟理思的書寫大為不滿。他評價到:“此書編次極不得當。斷代為‘卷’,本不得詳文學潮流的起訖。而各卷之中,所敘的時代亦多顛倒,事實亦多錯亂。其最甚的,如于元代‘戲劇’一章之中,不敘元曲之興衰,與關漢卿、馬致遠、王實甫、高則誠諸人之性格與其作品之影響,反支蔓旁及,犬牙錯出,遠敘中國戲曲之原,下及清代末葉劇場中瑣事……”(21)西諦:《評H.A.Giles的“中國文學史”》,《文學旬刊》第50期,1922年。鄭振鐸反復表達了一種擔憂,即翟理思的著作將導致西方讀者錯誤地認識中國文學。事實上,他的擔心盡管鞭長莫及,并不能改變西方讀者的認知,卻并非杞人憂天。僅從里奇韋對這本書的參考和引述,就足以說明“誤解”早已傳播開來。只是,與翟理思的初衷不同,里奇韋從人類學的視角出發,更多地將翟理思對中國戲曲敘述和研究,視作異域民俗,著重發揮其作為“民族志”的功能。
里奇韋對中國鄉村演劇的特點、功能、演劇場所、觀眾構成等方面尤為重視,不斷將中國鄉村演劇置于世界各民族戲劇表演和民俗研究的共時結構中展開比較研究。就演劇場所而言,中國鄉村戲臺以寺廟、神社和宗祠作為最原始的戲劇表演場所,與歐洲和亞洲許多民族和地域的風俗完全一致,在世界范圍內具有普遍性。(22)Ridgeway, Dramas and Dramatic Dances, 280.就鄉村演劇的觀眾而言,里奇韋提出神靈同時具備觀眾和戲劇角色的雙重身份。這個特點與里奇韋探討“地方神靈”的生成機制密切相關。他還依據內容題材,將中國戲劇分為戰爭題材(military)、民間題材(civil)和準宗教題材(quasi-religious)三種類型。(23)Ibid., 272.里奇韋尤其關注歷史和宗教題材,正是因為從英雄人物和當地神靈承擔的雙重角色出發,可以為“死亡崇拜說”的普遍有效性提供強有力的證據。由此,也不難理解里奇韋最后做出的如下結論:
如同西亞,古埃及,印度和緬甸一樣,中國的嚴肅戲劇也源于對死去的族長或祖先的崇拜。寺廟演劇大約是孔子時代宗廟中嚴肅的模仿式樂舞(solemn pantomimic dances)的直系后裔,……像在希臘,西亞,埃及,印度和緬甸,嚴肅戲劇(serious dramas)都是建立在歷史人物的功績,罪惡或苦難之上的。因此,對于證明希臘悲劇誕生自對著名首領的崇拜,比如對錫安的阿德拉斯托斯的崇拜,中國戲劇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24)Ridgeway,Dramas and Dramatic Dances, 280.
里奇韋在鄉村演劇的觀察與分析之外,還花費較多篇幅描述中國城市里“permanent theatres”(直譯為永久劇場,也就是戲園、戲樓這樣固定的專業性劇場)的設施、戲班組織、布景道具以及舞臺表演藝術等方面的狀況,甚至連戲臺場邊的人如何候場,如何搬動道具,如何給演員遞茶水這樣的細節也都一一記敘。
對1910年代里奇韋生活其中的倫敦所盛行的“中國戲”稍作考察,就會發現里奇韋關注上述層面的獨特緣由。1913年,倫敦上演了一部中國戲《黃馬褂》(The Yellow Jacket,又譯《黃衫記》),(25)劇本參見George C.Hazelton, Jr.and J.Harry Benrimo, The Yellow Jacket, A Chinese Play Done in a Chinese Manner(Indianapolis: The Bobbs-Merrill Company, 1913).劇名采用當代研究者的慣常譯法。汪仲賢(1888-1937)曾將此劇譯作《黃衫記》,當是此劇最早的中譯名,但并未通行。參見汪仲賢:《西洋的劇場軼聞(十五):西洋人演的中國舊戲》,《戲劇》1921年第一卷第四期。該劇1912年在紐約演出80場,1913年在倫敦演出154場,還在全美和眾多歐洲國家巡演,在西方世界廣受歡迎,搬演活動一直持續到1970年代。(26)Min Tian, The Poetics of Difference and Displacement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Western Intercultural Theatr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27;Ashley Thorpe, Performing China on the London Stage: Chinese Opera and Global Power, 1759-2008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73.1913年,翟林奈曾受邀為這部劇作撰寫了劇評《中國戲劇》(The Chinese Drama)。(27)翟林奈的劇評當時與《黃馬褂》節目單附在一起印發,遺憾未見全文,但里奇韋多有引用,并做了很高的評價。參見Ridgeway, Dramas and Dramatic Dances, 268.
這部“中國戲”最具特色之處在于其舞臺表演的呈現方式。首先,導演將舊金山唐人街粵劇戲班及其戲臺的設計原樣搬到了劇場上,構建了劇場中的劇場(theatre within theatre);其次,又將戲班中原本不在演員之列的后臺工作人員納入表演之中,這就是property man一角,在劇中“表演”著類似中國戲班中“檢場人”“管事人”“打砌末人”“管衣箱人”“打門簾人”或“管水鍋人”在舞臺以外的活動。本不屬于中國戲曲舞臺表演之列的人員,卻通過“戲中戲”(drama within drama)的表演結構,成為這部“中國戲”的重要角色。有趣的是,就連檢場人滿臉厭煩的“工作表情”,都被原樣地再現。
《黃馬褂》“劇場中的劇場”和“戲中戲”的結構,或可謂20世紀60年代以來風行的、由美國戲劇理論家阿貝爾(Lionel Abel,1910-2001)提出的“元戲劇”(metatheatre或metadrama)理論在20世紀初的一次精彩實踐。元戲劇理論涉及的層面很廣泛,與《黃馬褂》直接相關的,就是上述“戲中戲”的表演結構,表達了導演對戲劇表演和劇場中虛實時空界限的深刻反思。而“檢場人”這一角色,同時作為場上中國戲臺的觀眾和戲劇的表演者,是這部劇作設定“觀/演”關系虛實界限的關鍵一環。《黃馬褂》也因此被現代學者視作促進了20世紀初歐洲先鋒戲劇發展的經典劇作之一。(28)Tian, Poetics,27-28.所以,再次回顧里奇韋的評述,特別是《非歐羅巴民族的演劇舞蹈》對翟林奈劇評的引述,我們也得以從具體的時代語境出發,理解了他關注中國城市戲園及舞臺演劇的緣由,并由此看到中國傳統戲劇在西方傳播、接受的一個微小而有意義的切面。
《非歐羅巴民族的演劇舞蹈》一書對中國戲劇的評價和研究,既是里奇韋個人“問題視域”的一種確認,也集中反映了20世紀初期英國漢學研究領域中國戲劇研究的主要面貌。盡管概括粗疏,也難免存在以論代史的偏憾,甚至隔靴搔癢,但當我們回過頭,去理解那個時代的中西學術脈絡,特別是戲曲史研究對象化和學術化的內在理路與外在動力,翟理思和里奇韋的研究——可以稱得上西方學者書寫中國戲曲的具有代表性的早期嘗試——就和中國本土學者如王國維的努力相互輝映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翟理思的《中國文學史》寫作固然早于王國維《宋元戲曲史》(1912至1913年),里奇韋的寫作卻僅比《宋元戲曲史》晚出2-3年。我們尚不清楚這三種著述所代表的中英學術共同體,在中國戲曲研究這個特定的專門領域內,是否曾經有過相互的影響,更不清楚里奇韋是否對那個時代的中國學者和學術有所借鑒。可以確知的是,到了周作人的時代,《非歐羅巴民族的演劇舞蹈》已經進入了中國現代學者的視野之中,并進而成為新舊文化論爭的一個資源。這是在中國傳統戲劇研究史中值得重視的中西學術交流現象。
三、人類學范式與中國傳統戲劇研究的徑路
1915年,《非歐羅巴民族的演劇舞蹈》首次出版,即得到古希臘戲劇、印度戲劇和日本戲劇研究領域諸多學者的關注和批評,(29)R.R.Marett, “The Dramas and Dramatic Dances of Non-European Races by William Ridgeway,” The Classical Review 30, no.5/6 (August-September, 1916): 159-162; Roy C.Flickinger, “The Dramas and Dramatic Dances of Non-European Races in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Origin of Greek Tragedy, with an Appendix on the Origin of Greek Comedy by William Ridgeway,” The Classical Weekly 14, no.11 (January, 1918): 107-110.“死亡崇拜說”也不斷啟發著后世極為風行的“儀式—戲劇假說”(ritual-drama hypothesis)和世界各民族戲劇起源的探討,里奇韋本人也多次做出回應。(30)Ridgeway, “Dramas and Dramatic Dances of Non-European Races: A Reply,” 207-208; “EASTER TERM, 1920,” Proceedings of the Cambridge Philological Society no.117/115 (Lent, Easter and Michaelmas terms,1920): 7-10.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隨著文化人類學在美國的迅速發展,該書于1964年于紐約再版。再版編者認為,此書冠以“人類學家視野下的儀式、慶典和戲劇”(An Anthropologist Look at Ritual, Ceremony and Theatricals)之名會更為合適,并稱這部“巨著”(magnus opus)是“戲劇和人類學研究史上的里程碑之一”,(31)William Ridgeway, The Dramas and Dramatic Dances of Non-European Races (Reissued) (New York: Benjamin Blom, Inc., 1964), cover page.也有學者把這部著作列入進一步展開東亞、南亞和東南亞戲劇研究的重要參考文獻。(32)Joseph A.Withey,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the Theatre of Southeast Asia to 1971,” Educational Theatre Journal 26, no.2 (May, 1974): 209-220; Farley Richmond, “Asian Theatre Materials: A Selected Bibliography,” The Drama Review 15, no.2 (Spring, 1971): 312-323.
按照里奇韋的定義,“‘戲劇’是人類所有被戲劇化再現的情感、經驗、信仰和神話”(“theatre” becomes all of mankind's emotions, experiences, beliefs and myths, dramatically re-enacted)。(33)Ridgeway, Dramas and Dramatic Dances (Reissued), cover page.因此,他對世界各民族和文化的演劇形態的關注,都與他的學術出發點密切相關,即“在人類看似無關的戲劇活動之中尋找共同點(To find the common denominator between the seemingly unrelated theatrical activities of mankind)”,(34)Ibid.于是,“中國戲劇”成為里奇韋進行古希臘悲劇研究的有力參照,也成為他建構以普遍性為圭臬的人類戲劇起源學說的確證。
19世紀后期歐洲的文化人類學,盡管不同學者的研究取徑或有差異,但彌漫西方學界的歐洲中心主義觀念和進步史觀,在事實上塑造著這個時代學術研究的面貌。學者們自覺或不自覺地以“文明/野蠻”“進步/落后”等對立觀念為前提,將“歐洲”與“非歐洲”置于不同的價值維度,并認為歐洲文明將是落后的“非歐洲”社會及其文化演進的方向。在這樣的歷史語境下,里奇韋的亞洲戲劇研究,亦難免被現代學者批評是“最系統的歐洲中心論述”(the most systematic Eurocentric treatment)。(35)Tian, Poetics, 25.
20世紀初,隨著結構主義對西方學術范式的深刻影響,戲劇研究也同樣經歷著重要的轉向。此前的研究,受文化相對主義觀念的影響,認為宗教、儀式、戲劇的形成與特定的社會文化緊密相關,由此側重于對不同文化的差異和歷史發展做出描述與說明,而結構主義范式則將研究的側重點,引向對不同文化中的普遍現象和共性的關注。受這個轉向的影響,所謂“非歐洲”地區的儀式、戲劇和社會文化研究得以逐漸掙脫二元對立話語的束縛,獲得了與歐洲文化在價值維度上同等的地位。在這個意義上,里奇韋的中國傳統戲劇研究也表現出上述結構主義轉向的特點。他將“非歐羅巴民族”的演劇實踐,如他所引述的西亞、印度、中國、日本、緬甸等地區的戲劇,置于與古希臘悲劇同樣重要的位置,來探討世界戲劇的共同起源。這種研究方法,彰顯出里奇韋相對于同時代普遍存在的歐洲中心主義、歐洲種族優越論等觀念的“反叛”立場,即他基于實證研究和人類學轉向而促生的民族、種族平等觀念。由此不難理解,在時隔半個世紀后的1960年代,里奇韋的研究又被重申,他借鑒其他文化并以“他者”視角來反思歐洲文化,被視作最早拒絕于“真空”(in a vacuum)中進行古希臘研究的學者之一。(36)Ridgeway, Dramas and Dramatic Dances (Reissued) , cover page.
正如開篇提到的,里奇韋對中國戲劇的研究,卻被同時代受到西學東漸潮流裹挾的中國新式文人和啟蒙學者特別是部分舊戲改革派學者的“誤解”和“誤用”,與之在歐洲和美國的學術接受歷史截然不同。20世紀二、三十年代,諸如周作人、錢玄同、胡適、岑家梧等一批學者、文人關于廢除中國舊戲的討論,牽涉的不僅是“舊戲”的命運,更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前途。當時的中國知識精英,看到是中國的民族特殊性,而不是世界各民族的共性;關注的是新文化對舊文化的代替,而不是傳統文化的延續性。里奇韋對中國戲曲特征的客觀描述,因之成了為廢除舊戲而鼓呼的重要證據。周作人堅持廢除舊戲的重要理由之一在于“皇帝與鬼神的兩件……是根本的野蠻思想,也就是野蠻戲的根本精神”。(37)周作人:《論中國舊戲之應廢》,《新青年》1918第五卷第四號。反觀里奇韋的研究,他恰恰是要通過對鬼神的現世來源和人類鬼神信仰機制的追問,來論證世界戲劇起源的學說。由此看來,同時代的中國學者不但忽略了里奇韋在事實上對中國傳統戲劇地位與價值的抬升,也錯過了在世界戲劇文化的版圖中,客觀、冷靜地審視中國戲曲的契機。
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文化人類學、文學人類學的方法研究中國戲劇,成為中國學界的熱潮。其“遠因”,或可追溯至20世紀上半葉已經在中國開始的相關嘗試。(38)方克強:《新時期文學人類學批評述評》,載《跋涉與超越》,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7年,第17頁。中山大學的董每戡教授(1907-1980)被認為是中國最早采用人類學、民俗學的視角來研究古代戲曲的重要學者。(39)康保成:《宗教、民俗與戲劇形態研究》,《民族藝術》2004年第2期。董每戡先生發表于1948-1949年間的《說“傀儡”》與《〈說“傀儡”〉補說》兩篇文章,集中體現了他受到的歐洲人類學和考古學研究范式的影響。(40)陳壽楠、朱樹人、董苗編:《董每戡集》(第一卷),長沙:岳麓書社2011年,第167-201頁。《說“傀儡”》一文詳細梳理了“偶人”在中國的發展史,在論證偶人與祭祀儀式具有密切關系時,不僅采納馬克斯·繆勒對墨西哥廟宇祭神使用“人體犧牲”(Human Sacrifice)的民俗研究做論據,還在1976年整補該文時,引用了1971年《安陽后崗發掘簡報》以及刊登于1973年第2期《文物》上的考古學最新研究。董每戡提出“中國的傀儡戲源于印度”,(41)陳壽楠、朱樹人、董苗編:《董每戡集》(第一卷),第197頁。并在《〈說“傀儡”〉補說》一文中重點探討了傀儡戲的起源問題。就傀儡戲的發源地而言,他與皮希爾持論相同;就傀儡戲的起源與宗教儀式的關系而言,他認為“另外還有一面似乎更重要,那就是相信人在死后有生命繼續或靈魂存在的觀念”,“這觀念便成為傀儡之產生的哲學底根源”。(42)陳壽楠、朱樹人、董苗編:《董每戡集》(第一卷),第201、204頁。董每戡先生的觀點,正與里奇韋“死亡崇拜說”的核心前提——“人類對靈魂不朽的信仰”一致,但不同之處在于,里奇韋以之為人類戲劇的普遍起源,董每戡以之為傀儡戲的起源。
相比而言,同是以世界戲劇發展史為參照,里奇韋、皮希爾、繆勒等歐洲學者以歐洲戲劇研究的問題為出發點,附帶以中國傳統戲劇研究為其提供證據;而董每戡先生則是以中國傳統戲劇作為主體,參考中西方學者的研究,在學術共同體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并與之形成對話。值得注意的是,與前述1920-1930年代“舊戲改革”話語下的戲曲研究相比,董每戡先生此期(1940年代末)的戲曲研究,已然脫離了“新舊之爭”“野蠻/文明”“落后/進步”的話語體系,表現出客觀、包容的學術立場,進而彰顯了里奇韋等歐洲戲劇人類學研究范式的學術價值。此外,如齊如山,曾一再提倡發揮縣志、風土志在傳統戲曲研究中的重要價值,(43)齊如山:《齊如山回憶錄》,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98年,第97-98頁。也被認為是中國戲劇人類學的踐行者和奠基者之一。
這里,不能不提到荷蘭漢學家龍彼得(Piet Van Der Loon,1920-2002)和日本學者田仲一成(1932-)的相關研究。龍彼得任教于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他關于中國戲曲與儀式關系的研究,(44)參見龍彼得撰《中國戲劇源于宗敎儀典考》,王秋桂、蘇友貞譯,《中外文學》 1979年第12期。與自里奇韋時代就影響深遠的儀式—戲劇研究的傳統密不可分,至少,可以納入這一學術譜系中去觀察。田仲一成被視為二戰后日本以人類學、社會學方法研究中國戲曲最重要的學者。他對元雜劇題材和演劇關系曾有這樣一段論述:“元刊雜劇中一大半屬于歷史劇,有力地說明其脫胎于鎮魂儀式的事實。歷史劇基本上都是祭祀戲劇。雜劇中的故事從哪兒來?應當從孤魂祭祀中來。人們祭祀逝去的英雄或親人,緬懷他們的事跡,表演他們的故事,這就產生了戲劇。古希臘戲劇以悲劇為主,悲劇的誕生與戲劇的產生是同步的。我認為金元雜劇也是如此。”(45)康楽整理:《金元雜劇與祭祀儀式——田仲一成教授與康保成教授對談錄》,《文化遺產》2015年第3期。田仲一成的相關論斷,堪稱是里奇韋“死亡崇拜說”的回響。只是這一論斷并沒有得到中國本土戲曲史研究者的廣泛認同,或者說,受到了尖銳的質疑。(46)田仲一成:《獻疑于以民俗學為禁忌的作風——就中國戲劇的發生等問題答解玉峰先生》,《學術研究》2007年第3期;解玉峰:《民俗學對中國戲劇研究的意義與局限——兼答田仲一成先生》,《學術研究》2007年第9期;傅謹:《中國戲劇發源于鄉村祭祀儀禮說質疑——評田仲一成〈中國戲劇史〉》, 《文藝研究》2008 年第7 期。但不可否認,他的研究與龍彼得一起,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戲曲研究的視角、方法和觀念產生了顯著的影響。
里奇韋《非歐羅巴民族的演劇和舞蹈》已成為歐洲學術的典范性著述,對其研究范式、學術史價值的討論,促使我們再次審視20世紀以來歐洲和中國學者面對傳統文化和民族戲劇時不同的學術語境和歷史語境,以及人類學、民俗學研究在中國傳統戲劇研究領域的發展歷程。同時,里奇韋的研究也為當前中國戲曲展開跨學科、跨文化研究提供了借以反思的材料。其中一些在今天看來或許刺目的混亂和誤解,既延續了此前中西交流史上沉淀下來的偏見或誤會,又參與了之后西方學者和讀者對中國戲曲和近代文學觀念的進一步建構,其種種影響和接受歷史,則有待繼續深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