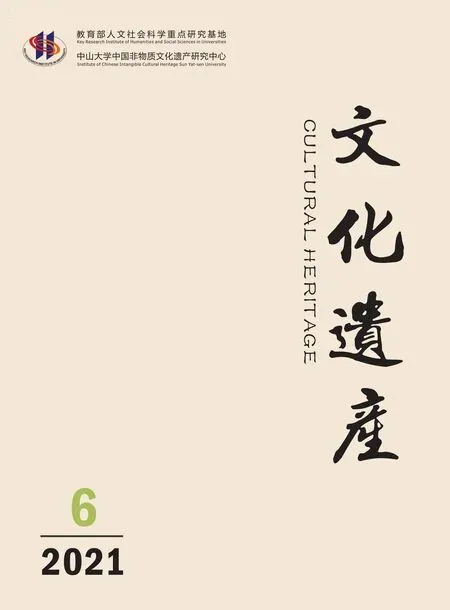黔東南苗族服飾文化的核心內涵及當代創新*
鄒 蓓
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位于貴州省東南部,2020年末常住人口375.86萬人,戶籍人口488.65萬人,少數民族人口占戶籍人口的比重為81.7%,其中苗族占43.4%。(1)“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州情概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門戶網,http://www.qdn.gov.cn/zjqdn/zqgk/,訪問日期:2021年11月10日。黔東南地區的苗族服飾款式多樣、造型奇美、色彩豐富、技藝精湛,保存良好,被稱為“苗族服飾博物館”。這些多姿多彩的服飾,銘刻著苗族歷經磨難的歷史歲月,是苗族歷史記憶的載體、集體審美追求的展現,具有深厚的文化內涵和極高的美學價值。本文將重點探討黔東南苗族服飾的文化記憶功能與審美價值,并從當代鄉村振興角度探討如何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其功能價值,發展服飾文化產業,促進鄉村文化建設與經濟發展。
一、 黔東南苗族服飾的文化記憶
馬克思指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2)馬克思:《路易·波拿馬的霧月十八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99頁。苗族原本有自己的文字,因歷史上在逃避戰難不斷遷徙的過程中失去了文字,其歷史主要靠口頭講唱和服飾圖案而傳承。黔東南苗族服飾將本民族先民的故事、民族的遷徙、民眾的生活等,一針一線繡進衣服上,一錘一鏨刻入銀飾中,因而苗族服飾被譽為“穿在身上的歷史”。
(一) 民族歷史的記憶
苗族是中國歷史悠久的古老民族之一。據中國古代典籍記載,苗族起源于遠古時代活躍于中原地區以蚩尤為首領的“九黎”部落聯盟,在涿鹿被黃帝部落戰敗后,退到長江中下游,逐漸形成“三苗”部落,從事農業稻作。由于戰爭的失敗,苗族在歷史上歷經了多次大規模向南向西的遷徙,大致路線是由黃河流域至湘(湖南)、黔(貴州)、滇(云南)。苗族人民用形象化的符號將本民族苦難的發展歷史記錄在服飾上,讓服飾圖案成為記錄苗族歷史文化的載體,其中包括對苗族創世、戰爭、遷移等重大歷史事件的描繪,比如關于苗族創世神話的“蝴蝶媽媽”“姜央射日月”“駿馬飛度”等圖案,這些都成為苗族傳世的“無字史書”。如黔東南有一幅分為三個層次圖案的苗族刺繡,形象地展現了《苗族古歌·蝴蝶歌》中啄木鳥、蛀蟲王幫助蝴蝶從楓木中生出來的過程。(3)索曉霞:《苗族傳統社會中婦女服飾的社會文化功能》,《貴州社會科學》1997年第2期。《苗族古歌》這樣唱道:“砍倒了楓樹/變成千萬物/蝴蝶孕育在楓樹里心頭。/是誰來把大門開;讓蝴蝶出來?/蛀蟲王來打開大門,讓蝴蝶出來。/門兒一打開,蝴蝶輕輕翻身把頭抬。/是誰從東方來?/啄木鳥從東方飛來。/喙殼粗象大腿,/啄開木頭吃蛀蟲。/要啄就啄根和梢,/莫啄中間那一節,/別碰傷蝴蝶手和腳;/有朝一日她壯了/有了力氣就出來。”(4)馬學良譯注:《苗族古歌》,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3年,第162-163頁。在這幅刺繡圖上,這一苗族創世過程被刺繡者分成三個層次直觀而形象地描繪出來了:第一層為楓樹、啄木鳥、蛀蟲王層;第二層為蝴蝶層;第三層為鹡宇鳥。第三層描繪的是《苗族古歌·十二個蛋》中妹榜妹留(即“蝴蝶媽媽”)生下十二個蛋后“鹡宇替她孵、鹡宇替她抱”的故事。為什么鹡宇鳥幫她孵蛋呢?因為她們都是楓香樹所生:“砍倒楓香樹,樹心生妹榜,樹梢變鹡宇,親從這里起。”(5)過竹:《苗族神話研究》,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64頁。苗族古歌認為,人、獸、神共有一個從楓木生出來的母親——蝴蝶媽媽,她生出苗族先祖姜央,姜央創造人類。因此,蝴蝶媽媽是苗家崇拜的神靈,是苗家人的先祖母,這些苗族創世神話故事在黔東南苗族服飾中都有描繪。“駿馬飛度”是苗族服飾和頭冠上常用的圖案,由馬和騎士組成,橫貫在象征黃河的飾帶上,這樣的圖案也被稱為“人騎馬”圖案,它描述苗族祖先遷徙時萬馬奔騰過江河的非凡氣勢,是苗族先民悲壯遷移的歷史見證。
(二) 圖騰崇拜的遺存
自遠古開始,人類作為地球上唯一的智慧生物,始終在探討著裝飾自身的各種方法,服飾藝術就是由古老而神秘的人體裝飾發展起來。這些古老的人體裝飾,既有實用功能,更有深層圖騰崇拜的文化因子。在苗族人的原始思維中,所有的事物都是可以相互滲透或者通過神靈來相互庇佑的,他們相信自己和動植物之間有著特殊的聯系,認為種族或支系的起源是來自于某種動植物,即動植物圖騰崇拜。關于苗族圖騰發生的準確年代,至今很難考查,但詳細考察苗族的神話傳說與遺留物品,可以發見若干圖騰的痕跡與遺風。苗族服飾中使用最多的圖案是蝴蝶,這是因為苗族古歌里有《蝴蝶歌》,蝴蝶媽媽從楓樹中誕生并長大后,與清水塘里的泡沫婚配,生下十二個蛋。鹡宇鳥孵了三年半,孵出了尕哈神、人類的始祖姜央、雷公、水龍、老虎和長蟲。這是苗族對人類和萬物始祖“蝴蝶媽媽”圖騰崇拜的體現,與苗族神話傳說有著千絲萬縷的內在聯系。貴州苗族有結發模仿狗耳的犬圖騰崇拜。《說蠻》云:“(黔苗)狗耳龍家,居深林。薦莽衣、尚白。束發不冠。善石工。婦人辮發螺髻,上若狗耳,故因以名。”(6)轉引自周絢隆《試論中國古代的冠禮》,《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3年第4期。苗族服飾上還繪有“龍狗和六男六女”圖案,反映的是苗王的龍狗殺了敵王娶了苗王之女,生下六男六女,繁衍人類,被苗族民眾尊為祖先的故事。丹寨苗族也自稱“嘎鬧”(苗語意譯為“源于鳥圖騰部落”),系遠古蚩尤部落中以鳥為圖騰的“羽族”后裔。鳥,也被作為祖先和繁衍子孫的象征。在鳥圖騰的基礎上,苗族人創造和發展了錦雞文化、百鳥衣文化、鳥籠文化等鳥圖騰文化。這些動物圖案是對苗族先民適應自然和征服自然頑強生命力的頌歌。一些植物圖案同樣記錄著當地的圖騰文化,表達了苗族民眾對生命的膜拜,對幸福生活追求的思想情感。例如,苗族創世紀神話中,《楓木歌》講到楓木可以生人,民間蓋房時,還以楓木作中柱,于是楓木便成為苗族祟拜的對象,而反映在苗族的服飾上,苗族婦女們將楓木圖案刺繡在盛裝或者便裝中,來寄托對生命的祝福。
(三) 民眾生活的再現
黔東南苗族服飾文化是該民族共同體生活的產物,是這個民族在特定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生活中形成的獨特文化,反映著當地苗人的社會生活、歷史發展、生存環境等方面的狀況,是這一民族與其他民族形象區別的重要依據。卡西爾《人論》認為,人與動物的區別就在于人具有符號系統,“人不再生活在一個單純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個符號宇宙之中。”(7)[德]恩斯特·卡西爾:《人論》,甘陽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第33頁。全部人類行為由符號的運用所組成,或依賴于符號的作用。苗族服飾是一個自成體系的苗族文化符號世界,蘊藏著苗族豐富的生產生活文化內涵。農耕和守獵是苗族的主要生產方式,這種關于農耕和狩獵的生活化場景在苗族服飾圖案中有著比較充分的體現。如在稻作農耕中水牛的作用十分重要,因此水牛成為苗族服飾中表現最多的圖案之一。苗族服飾中還大量使用植物圖案和幾何紋。常使用的植物圖案有牡丹花、石榴、菊、荷、楓葉等,除裝飾、美觀之外,部分圖案還帶有特殊寓意,表達著美好期望,如石榴籽多,將石榴紋于身上,寓意多子多福。幾何紋常使用的紋樣主要有鋸齒紋、水波紋、回紋及銅鼓紋、卷草紋等。幾何紋除美觀之外,還多有象征意義,如婦女披肩上繡著的兩條橫紋,代表著黃河和長江兩條大河,在橫紋中間還繡有樹木河流的圖紋,表達著苗族人民對于自然的敬畏與熱愛。
黔東南苗族服飾是苗族婦女綜合運用繁復多樣的手法創造出來的藝術杰作,它還承載著極為豐富的苗族文化信息,具有展現和傳遞苗族人的族群、性別和婚姻等信息的功能。黔東南苗族是崇尚銀的民族,苗族婦女更是鐘愛銀飾,銀飾成為她們節日盛裝最為昂貴的裝飾物。苗族銀飾圖案,多以苗族人民日常生活中的花鳥魚蟲、飛禽走獸為主,如蝴蝶、牛角、錦雞、花草、魚蟲等,非常貼近大自然,但又富有文化意蘊。苗族銀飾主要是用來裝飾未婚女性的,在黔東南的清水江流域及都柳江流域,銀飾盛裝對主人具有三種含義:一是表示穿戴者已進入青春期;二是表示穿戴者尚未婚配;三是表示穿戴者欲求偶。多數地域的蘆笙場,環佩叮當的銀飾盛裝代表一張通行的入場券,是向圍觀的青年小伙子們展示自己的資歷證書。(8)柳小成:《論貴州苗族銀飾的價值》,《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4期。苗族也是一個遷徙民族,素有“東方吉普賽人”之稱,在五千多年歷史發展進程中,由于數次大規模遷徙,迫使他們將自己創造的財富制作成代表自己族徽標志的、可以隨時帶走的銀首飾,銀飾既是快速變現的工具,又是家族身份、地位的象征,由此逐漸形成了苗族銀飾以大為美,以多為美,以重為美的特點。
二、黔東南苗族服飾的審美特征
黔東南地區由于雷公山和月亮山等山脈,以及清水江、舞陽河和都柳江等江河的自然阻隔,長期與外界聯系較少,加之這里苗族人口相對集中,民族的血緣親族凝聚力很強,因而,至今這里的苗族文化仍保持了相對完整、獨立的狀態。黔東南苗族服飾也保持了古代原始民族古樸、稚趣的審美情趣。
(一) 圖案奇——情趣盎然
苗族服飾圖案是隨著苗族服飾發展起來的服飾裝飾藝術,它們多彩多姿,寓意深刻,且具有濃郁的生活情趣。黔東南苗族服飾圖案色彩濃烈、色調飽滿、風格古樸,體現了獨特的美學理念。苗族服裝的鑲花部位的圖案造型,多半從動物植物中汲取題材。其圖案造型多以花鳥蟲魚寫實為主,給人一種熟悉的真實美。如雷山苗族女子盛裝是由雄衣和石衽上衣發展演變而成。上裝的衣袖、衣邊及背上均用挑、縐等繡法繡成龍、虎、羊和魚、蝶、蟲等動物圖案,顏色為紅、藍、綠、黃等色,沿托肩鑲長方形花草圖案。穿時,袖、肩綴滿各種圖案的銀花片。下著青色家機布長縐裙,外罩二十四條紅底繡有花、鳥、蟲、魚、蚌、蛙、龍、鳳圖案的花飄帶,頭戴銀角,頸系壓領、項圈,再飾以銀頭花、銀梳、銀泡、銀簪、銀手鐲、銀鎖、耳環、戒指等。腳穿繡花船形鞋。盛裝的各種圖案濃縮了苗族生活環境的景物,具有十分濃郁的生活氣息。苗族優秀的繡手具有大畫家的思維,在一些圖案創意上構圖講究嚴謹、對稱、協調,每幅繡圖均有主、副圖案;她們想象力豐富,取材廣泛,天空、大地、人、神、植物、動物……無奇不有,且遠古、近現代風格均有。其圖案有以自然崇拜中的“神物”為表現對象,諸如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冰清玉潔的玉蘭花、不畏嚴寒的臘梅花,以及仙風道骨的云中白鶴、輕盈敏捷的雨中飛燕等。此外,漢族傳統的吉祥圖案,也較多地出現在苗族服飾的裝飾上。如:“龍鳳呈祥”“長命百歲”“彩蝶雙飛”“二龍戲珠”“雙鳳朝陽”“雙喜”等組合圖案。特別引人注目的是雷山苗族服飾刺繡,其構圖、用色、繡技實為“三絕”。比如,在衣袖圖案上,往往以變形的蟬頭為中心,兩旁對稱的是歡快奔跑狀的抽象梅花小鹿,緊挨著的是對稱的抽象魚躍圖。(9)覃國寧:《淺談苗族服飾的民族文化特征》,《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92年第5期。這表現動物植物的圖案造型來自他們對日常生活的觀察與體驗,通過對這些物體的深刻感知,轉化成為藝術創造,使苗族服飾圖案既呈現出盎然的蓬勃生機,又具有令人遐想的深意,這體現了苗族繡女的聰明才智和藝術創造才能。
(二) 好五色——古樸簡約
苗族服飾主要由紅、黑、白、黃、藍五色構成,但由于苗族居住的地理環境不同,在“五色”的搭配上亦存在些差異。川黔滇型昭通楚雄式服飾以紅黑二色為基調的同時注重突出紅白黑三色的大塊色彩,其他藍、綠、黃諸色則處理成細小的星點,很不顯眼。黔東南型、湘西型服飾則多在紅黑二色的基礎上,重點施以青綠或墨綠色,視覺上是紅綠二色對比造成的艷麗明快的強烈塊面,又有對比色黃、白、藍加以調和,頗富節奏感,充滿生命活力,給人一種五光十色、閃爍不定的感覺,似乎色彩也是動的。(10)參見楊鵑國《服飾·風格·特征——再論苗族女性藝術文化》,《貴州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2年第1期。追溯苗族這種“好五色”的特殊心理的根源,其實是對苗族祖先—“其毛五彩的犬”—盤瓤的圖騰崇拜的體現。苗族的祖先部落群是盤瓠氏集團,《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傳》云:“高辛氏有犬戎之寇……時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盤瓠。下令之后,盤瓠遂銜人頭造闕下……帝不得已,乃以女配盤瓠。盤瓠得女,負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處險絕,人跡不至,于是女解去衣裳,為仆鑒之結,著獨立之衣……盤瓠死后,因自相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制裁皆有尾形。其母歸后,以狀白帝。于是使迎致諸子。衣裳班蘭,語言侏離,好入山壑,不樂平曠,帝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其后滋蔓,號曰蠻夷。”(11)范曄:《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傳》,《二十五史》(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局1986年,第1049頁。“五色衣”,一方面作為苗族人民對保護神和祖先的古老記憶,藉此祈求得到庇護,祛災免難;另一方面作為一種民族外在標識,通過對比強烈的五色起到增強民族凝聚力的積極作用。苗族服飾尤其喜歡用紅色,他們認為紅色是最美、最神圣、最具有生命力的顏色,如丹寨蠟染就用牛血等涂染紅色。這可能與蚩尤血染紅旗仍戰斗不息的故事有關。傳說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黃帝擒殺了蚩尤,將其尸首肢解,拋于異處。《史記》卷一《五帝本紀》引《皇覽·冢墓記》說“蚩尤冢在東平郡壽張縣闕鄉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氣出,如匹絳帛,民為蚩尤旗”。(12)司馬遷:《史記》,《二十五史》(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局1986年,第6頁。蚩尤旗影響著苗族偏愛紅色的心理,迎合了苗族崇拜蚩尤的思想意識。
(三) 多變幻——壯美奇幻
黔東南服飾極富神話、傳說、故事的神秘傳奇色彩,而又不失濃郁生活氣息的情節畫面,經過抽象化的處理,千變萬化,集壯、美、奇、幻于一身,令人嘆為觀止。首先,在苗族服飾圖案中,有許多與苗族人民日常生產生活相關的自然景物的描繪,花草樹木、鳥獸蟲魚成為最基本的要素,在這樣的背景下,繪制了人們生活在山野叢林,蜂蝶在花間飛舞,鳥獸在林間出沒,人與動物和諧同處,富于浪漫的想象。在苗族服飾充滿神性意識的圖案中,無論是人騎龍、人馭鳳、人馴獅象牛鹿,還是姜央變月、姜央造人、牛變龍、龍變花、魚變龍等等,其圖式的夸張怪誕,無不飄浮在苗族女性那特有的幻化藝術空間里。苗族服飾的這種特殊審美觀照方式,把看似平常的日常生活審美化和藝術化,并借以表達他們真善美的觀念。其次,在苗族服飾圖案中,許多圖案以起伏流暢的曲線傳達出活躍生動、富于變化動感。苗族女性在藝術構思時常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其造型總是力求化靜為動,雖靜猶動,蘊含著一種活潑、熱烈的生命力。例如,流行在臺江施洞地區的關于女英雄務茂西的刺繡紋飾上,中心是正在練武的務茂西。據說她是鴨子所變,能飛,十分勇敢而且力大無比。常見的是務茂西騎著馬或騾或獅或虎奔馳(亦有打赤腳行走的),左右上角是展翅飛翔的巨鳥,下面是呈奔跑狀的大象、鹿子或巨龍等其它動物,烘托出務茂西的偉大,從中心往外看,四周的動物似乎都在圍繞著她旋轉。(13)楊鵑國:《服飾·風格·特征——再論苗族女性藝術文化》。
三、黔東南苗族服飾的當代創新
2021年1月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意見》指出:“把鄉村建設擺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位置,全面推進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振興,充分發揮農業產品供給、生態屏障、文化傳承等功能,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深入挖掘、繼承創新優秀傳統鄉土文化,把保護傳承和開發利用結合起來,賦予中華農耕文明新的時代內涵。”(14)《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意見》(2021年1月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農村部網,http://www.moa.gov.cn/xw/zwdt/202102/t20210221_6361863.htm,訪問日期:2021年8月26日。綜上所述,黔東南苗族服飾不是簡單的實用品,也不是純粹的藝術品,而是具有獨特民族文化認同功能與審美價值的文化品,在當今中國農村現代化建設實踐中,要充分發揮黔東南地區苗族服飾“文”(文化記憶)、“藝”(審美藝術)、“技”(傳統技術)和“品”(民族品牌)等特殊功能和作用,根據現代服飾文化審美需求,創新性地發展服飾文化服飾文化產業,促進鄉村文化建設和經濟發展。
(一) 用苗族服飾之“文”增強民族文化認同
社會的現代化和文化的多樣性強力推動著當代人類社會的發展,當今世界各民族正以空前的速度和規模融入現代社會。在民族傳統文化和現代文明既沖撞又交融的大背景下,增強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認同感顯得尤為重要。德國學者揚·阿斯曼認為,集體記憶中具有“凝聚性結構”的是文化記憶,所謂文化記憶是指對共同的過去的記憶中所包含的共同的價值體系和行為準則,以及對重要事件的回憶所提供的解讀當下生活意義的重要維度。(15)[德]揚·阿斯曼:《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份》,金壽福、黃曉晨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46頁。黔東南苗族服飾以深厚的文化底蘊為依托,其圖案、色彩、造型、功能等,無不承載著這個民族的信仰觀念、風土人情、精神風貌、審美趣味等文化傳統,是一種能夠促進民族精神凝聚,提升民族文化認同的重要力量。如苗族服飾中所體現的“天人和諧”的生態觀、“積極進取”的生命觀、“團圓和美”的幸福觀等,這些在歷史中形成的共同生活規范和價值追求,曾經塑造了苗族人的精神品格,也應當成為繼續影響當下及未來苗族人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理念的文化力量。高小康認為,“一種文化活動能不能成為一種精神凝聚力量,形成一個區域或族群的人們的文化特征和傳統,關鍵在于能不能使這個區域和族群的人們找到一種共享的、族群特有的歸屬感,并由此而形成代代傳承的對這種身份歸屬的記憶、自豪和自尊。這就是特定族群的文化認同感。”(16)高小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是否只能臨終關懷》,《探索與爭鳴》2007年第7期。近些年來,外來文化的多樣性使得青少年對本民族的文化認知與傳承逐漸減少,民族文化要想得到傳承和保護,必須要有人一代代傳承下去,因此,必須增強年輕一代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強化他們對民族傳統文化傳承的責任意識。記錄苗族歷史與生活的苗族服飾文化,承載著本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情感、民族記憶,對喚醒民族文化認同和重構民族文化形象具有重要作用,要通過加強對苗族青年的民族服飾文化教育,增強他們的民族文化主體意識。有學者指出:在“非遺”的語境中,傳統服飾文化在得到人們重視與認可的同時也“正在成為一種人文資源,被用來建構和產生在全球一體化語境中的民族政治和民族文化的主體意識”。(17)方李莉:《論“非遺”傳承與當代社會的多樣性發展——以景德鎮傳統手工藝復興為例》,《民族藝術》2015年第1期。
(二) 用苗族服飾之“藝”發展民族文化產業
作為傳統手工藝的持有者具有追求更好生活的權利,貧窮與落后并不是傳統文化的必要附加屬性,文化亦是促進經濟飛躍的有力助推器。傳統手工藝在鄉村建設中呈現了與現代社會發展良好的價值契合關系,這也是手工藝能真正構建鄉村經濟文化和諧圖景的關鍵所在。(18)張娜、高小康:《后工業時代手工藝的價值重估》,《學習與實踐》2017年第1期。黔東南苗族在服飾藝術上有著超凡的領悟力和杰出的創造力,這與其獨特的精神價值、思維方式、藝術想像力和審美觀念緊密相關。苗族婦女通過抽象或具象的刺繡、蠟染圖案來表達自己的情感世界,這是她們對大自然的認知,對族群起源的思考和對祖先深厚的崇拜情結,以及對美好生活向往的真實寫照。無論是摹仿自然界中的花、鳥、魚、蟲,還是寓意深遠的歷史傳說故事,均有著較高的審美境界及鮮明的藝術特征。但隨著時代的變遷和社會的發展,苗族服飾文化既應保留其優秀傳統內核,也要重視在變化的環境中求得發展,發揚優良傳統、摒棄自身不足、融入現代元素,反映當代苗族的生存環境和生活狀態,形成符合當代苗族人審美需求的服飾文化產業,是苗族服飾文化發展的必然趨勢。黔東南苗族服飾從質料的加工、款式的設計、色彩的搭配,以及圖紋的描繪上,既具有原始的實用性,又具有裝飾的藝術性,無不顯示出苗族人民獨特的藝術智慧和別樣的審美情趣。在發展現代服飾文化產業中,在遵循民族藝術審美規律,符合現代人審美需要的原則下,可以大膽地把苗族服飾的優秀文化元素和設計理念,運用到現代服飾的設計創新中,在不改變圖案中原有的造型特點的前提下,對傳統圖案進行解構與重構的再創造,讓優秀的民族服飾文化元素時尚化,這既可以提高現代民族服飾中所具有的文化內涵與地域特征,也能提升服裝的審美情感與產品的附加值。這種以傳統苗族服飾之“藝”為“本”,推進現代服飾產業之“體”發展,所形成的富有本民族特色的現代服飾審美工藝文化體系和文化產品,既能讓大眾較為直觀地感受到服飾上所具有的苗族獨有的文化內涵、領悟到苗族女性質樸自然的審美文化取向,又能較好地滿足當代人對服飾文化的美好追求和服飾文化產品的消費,從而也達到了促進鄉村經濟發展的目的。
(三) 用苗族服飾之“技”拓展民族文化市場
要充分發揮苗族服飾傳統技藝在農村現代化建設中的作用,將振興傳統工藝與發展本地產業經濟結合起來。首先,作為傳統手工技藝產物的苗族服飾,從來都不是完全浪漫化的存在,不是為藝術的藝術,而是為生活為生產的藝術,他們的手工技藝常常與生計相關,是與老百姓日常生活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生存狀態和經濟形態。在大力發展鄉村產業經濟的背景下,文化傳承勢必要與產業經濟相結合。苗族傳統服飾文化技藝作為一種資本,只有在保護的基礎上進一步用于服飾文化產業開發,才能獲得更好的發展。黔東南苗族服飾中的刺繡、蠟染、挑織等制作工藝具有鮮明的民族風格和地域特色,其刺繡技法種類繁多,據統計大約有二十余種,以破線繡、皺繡、辮繡、絞繡、軸繡、剪貼繡、堆繡、錫繡、打籽繡、薄錦繡、挑花等最具代表性;蠟染技術是苗族古老的傳統印染工藝,至今黔東南丹寨等地仍保留和使用蠟染制作服飾的傳統,這些技藝是苗族傳統服飾的精華所在,最具民族服飾產業開發價值,有著廣闊的市場潛力。其次,在琳瑯滿目的服飾市場中,消費者所追求的不僅僅是實用需要,也追求服飾所具有的文化內涵,服飾中所具有的文化內涵越深、意義越大,其市場的競爭性就越強,產業的附加值就越高。在利用傳統技法發展現代民族服飾文化產業的過程中,既要關注現代人的審美趣味與需求,又要保留其所具有的獨特性技藝的精華,將傳統刺繡、蠟染、挑織技術與現代流行時尚風格緊密結合起來,借鑒苗族服飾文化圖案中的顏色配色方法,與當前生活中的流行顏色結合,讓苗族文化符號不斷地與現代審美相融合,設計和制作出具有高品位和民族特色的、現代消費者真正喜愛的服飾產品。其三,在黔東南苗寨,大多數婦女都是紡織、挑花、點蠟花的高手,刺繡、蠟染、挑織手工藝具有投資少,收益快的特點,將苗族服飾文化資源轉變為具有經濟價值的產業資源,具有非常好的基礎。但在大力發展鄉村文化產業的背景下,必須徹底轉變傳統苗族服飾的家庭作坊式和純手工式的生產模式,通過體制機制再造,建立集體化、公司化、集約化、規模化的產業生產組織形式,以及機械化、智能化、科學化的生產方式,促進苗族服飾產業的市場化和現代化發展。
(四) 用苗族服飾之“品”創新民族文化品牌
“黔東南苗族服飾”是貴州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項目,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項目,是我國民族服飾著名品牌。在經濟全球化和文化多元性的今天,苗族服飾文化必須堅持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發揮苗族服飾文化品牌效應,打造新的文化產業品牌,讓民族服飾文化之花盛開于中華文化百花園,讓中國服飾文化之風吹遍世界各地。其一,與國內產業接軌,對苗族服飾文化品牌進行創造性轉化,提高產品競爭力。在傳承和保護苗族服飾文化的基礎上,苗族鄉村服飾文化產業要積極尋求與國內文化產業接軌,使其蘊含的文化價值和美學價值得到最合理的轉化,傾力打造苗族服飾文化產品品牌,提高產品的質量和競爭力,塑造苗族鄉村新經濟形態,促進民族地區文化產業的高質量發展。比如,在當前國風盛行的服裝設計中,可以將苗族的文化符號與漢服相融合,利用苗族的文化中所具有的獨特圖案,以刺繡的方式繡到漢服上,讓兩個民族不同的文化相融合,創造出一個既表現出中國漢服所具有的獨特美感,又具有獨特民族韻味,又符合時代發展和現代人審美的服裝造型。再如,將苗族服飾進行產業化發展,鼓勵在苗族當地開辦苗族服飾加工廠,實現苗族服飾的規模化生產。另外,還可以通過現代媒體手段,加大對黔東南苗族服飾宣傳力度,提高其社會認知度;可以通過互聯網商務平臺,推廣苗族服飾產品,提高其市場知名度。其二,與國際市場接軌,對苗族服飾文化品牌進行創新性發展,增強國際影響力。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快速發展,“互聯網+”時代的到來,中國民族服飾文化走出去已成為一個發展趨勢。在黔東南苗族民族服飾文化與國際接軌的過程中,要堅持“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的發展觀,重視民族服飾賴以生存的文化根基。在日益激烈的國際文化市場競爭中,要傳承和發展黔東南苗族服飾文化,必須找準民族文化與國際時尚之間的碰撞點,在現代服裝文化中創新性加入民族傳統文化元素。黔東南苗族服飾文化的傳承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創新,其獨特地域色彩和民族風情,雖經過長期的變革但依然保持著獨立的特色和民族性。通過對苗族服飾的文化特點和藝術風格的參悟,以及對苗族優秀文化元素的提煉,從中汲取靈感,經過現代性再創造,打造民族文化產業品牌,創造出更多優秀的產品,增強國際影響力,使更多的人了解苗族服飾文化,促進黔東南苗族服飾文化更好的傳承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