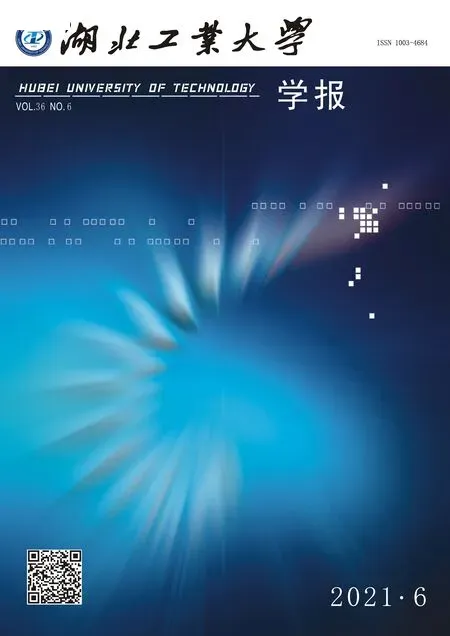從《畫像》看王爾德對莊子“逍遙”的誤讀
張靜宜, 彭家海
(湖北工業大學外國語學院, 湖北 武漢 430068)
逍遙,是一種無拘無束的精神境界,既指身體的不受羈絆束縛,又指心靈的自由放逸。在哲學方面,“逍遙”意味著不囿于外物而自為絕對自由的存在,一如《逍遙游》中的“無所待而游于無窮”。作為“逍遙”哲學的宗師,選擇隱居山林不入世俗,以一種率性自適,順其自然的方式為逍遙放歌。古往今來,解莊者無數。其中,英國作家王爾德于1890年發表了一篇名為《一位中國哲人》的書評,翟理斯將其翻譯為《莊子》。這表明王爾德已接觸了中國哲學。次年,王爾德最知名的作品《道林·格雷的畫像》出版,公眾嘩然。為考察王爾德作品是否吸收了中國哲學因素,本文將從其文學創作中主題、題材、人物、語言風格等特征入手,對《道林·格雷的畫像》(以下簡稱《畫像》)進行簡要的文本分析,探尋王爾德作品中莊子思想的痕跡。
1 與中國哲學的相遇
1.1 尋求自由的心靈殿堂
比較文學中的“影響”概念與一般意義上的“影響”概念是有區別的。通常所說的影響指一種事物對另一種事物發生作用,引起后者的反應和反響。比較文學的“影響”概念則更強調“外來性”。
這種“外來性”源自經濟迅速發展,物質文明快速進步的十九世紀末。這時期的英國社會表面輝煌,實則刻板而克制:婦女著裝不露出頸子和手腕;不得提及人體的某些器官;苛刻控制個人情欲……壓抑苦悶的氛圍以及對人性的極端壓制共同鑄就了知識分子“反叛”的溫床,他們對社會現狀極端不滿,開始尋找新的精神寄托,期待從新的思想源泉中汲取力量。而抱有同一期待的王爾德曾在《英國的文藝復興》(1882)一文中這樣描述道:“在這動蕩和紛亂的時代,在這紛爭和絕望的可怕時刻,只有美的無憂的殿堂,可以使人忘卻,使人歡樂”。就這樣,在這一訴求的召喚中,在哲學上擁有崇高地位的莊子,也就是那個思想處于絕對優越和領先位置的中國哲人,打破了僵凍著十九世紀末的冰水,引領者藝術家們將目光轉向中國,并傳遞給他們古老而深邃、自由又超脫的中國智慧。
1.2 對“逍遙”的追尋與效仿
1.2.1隨心自在與追求個性解放《莊子》一書,盡數表達了莊子的處世哲學、政治思想和道德覺悟。而“逍遙”一詞則可總括莊子的思想。莊子一生以大道為依歸,他所追求的,并非名利、權勢等世俗的東西,而是摒棄凡心,追求精神上的解脫。莊子繼承了老子的諸多觀點,認為天下萬物源于“道”,“道”就是自然之理,萬眾之師。因此人若要得解脫、得逍遙,就要順應自然。
處世方面,莊子提倡順著事物的自然盡心去做;道德規范方面,他認為只有認識到人與自然之間不可分割的整體性的人,才能說是有德之人;治世方面,他強調帝王之道應該順應自然,順應民心,慣行無為而治;養生方面,他提倡以自然養神,與自然合二為一。所以,莊子的“逍遙”實則是要認識到人與自然的一致性,一切行為皆應順應自然的道理去進行,不因外物錯亂本性,精神上超脫一切自然和社會的限制,這般才能忘記人生的束縛,隨心所欲遨游于天地間,達到真正的逍遙。
而在遙遠的西方國度,那位同樣追求自由的王爾德自然被莊子灑脫不拘泥的性格所吸引,對其一見傾心,遂引為同道。在處事方式和行文風格方面,王爾德無不表現出對莊子“逍遙”思想的追尋與模仿。出生在富裕優越的家庭,接受著高等教育,混跡于倫敦上流社會,生來就注定區別于蕓蕓眾生的王爾德,執著于近似于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和游離于無政府主義的社會追求,妄想得到凌駕于英國傳統社會之上的“自由”。在建構自己的藝術世界中,王爾德允許自己的主人公犯錯,就如《畫像》中的道林,他的肆意妄為或被掩蓋,就連生死危機也被化解,讓他得以繼續逍遙度日。而作家在塑造人物的過程中,往往會不自覺傾注作者本身的思想,一定程度上作家創造的人物反映的就是作家本人。因此,我們可以看出,王爾德所追求的“逍遙”理念,在于理想化社會背景中的完全的個性解放,而不是以積極客觀的態度去對待社會和生活,他過于追求現實社會中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的絕對自由和無限制的特權。
1.2.2修身養性與追求感官享受如要徹底理解莊子的“逍遙”,就不得不提及他所說的修身養性的方式。莊子看到人們在膨脹的物欲中丟失了心靈的安寧與和諧,造成各種人生煩惱和困惑。他主張通過“坐忘”“朝徹”“見獨”等方法來修持、養生。在《莊子》中,“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謂坐忘。”(《大宗師》)“坐忘”即要拋棄各種私心雜念,深入理解自然并感受自然本性[1]。莊子還曾借一得道之士女偊之口簡潔地敘述了“聞道乃一過程”的思想。女偊在談到自己的聞道過程時曾對人說:“三日后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徹;朝徹,而后能見獨。”(《大宗師》)女偊所說的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心境就能夠清明洞徹即為“朝徹”;心境清明洞徹,而后就能體悟到絕對無待的哲學本體即“道”了(即“見獨”)。莊子的這些思想其實是在向人們提供一種修身養性的方法,為人們排除外界干擾、獲得心靈寧靜提供途徑,從而使人能夠得到精神層面的逍遙。
在《畫像》中,王爾德借道林忘我地搜羅世界各地奇珍異寶的行為方式,來彰顯通過藝術帶來的感官刺激也可得到精神上的自由。這一理念成為了他自我放縱,尋求陌生愉悅感的道德支撐。從研究香水和制香秘訣到收集野蠻部落的樂器,再由購入超巨型綠松石到研究北歐國家寒冷的房間里充當壁畫的掛毯……這正是王爾德所描繪的,一個忘我的逍遙者:道林終日沉迷于充滿酒色聲情的“藝術”世界里,只求無盡地放大感官享受,沉迷于精神的虛假自由,從而代替現實生活中的不自由。事實上,道林為實現“逍遙”的方式明顯偏向了滿足“欲”的層面,于空洞藝術中尋找感官的刺激與滿足的行為無法實現真正的精神層面上的“逍遙”。
2 變味的唯美主義
2.1 “為藝術而生活”
在一篇題為《社會主義制度下人的靈魂》的文章里,王爾德引用莊子學說:“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宥》)這表明他認同莊子的主張,即政府應該秉承清靜無為,展示他反對權威和治理的觀念。和莊子抗議說教類似,王爾德對英國社會的市儈哲學和虛偽道德深惡痛絕。他需要一種獨立于現實之外的藝術哲學,而唯美主義就是這樣一種存在。
唯美主義的基本原則是“為藝術而藝術”,將藝術與道德、社會、政治等實用價值分開。這一思想吸引了一大批才華橫溢的作家、藝術家與批評家。作為唯美主義思潮的理論奠基人,佩特(Walter Pater)的美學見解對王爾德的思想與創作產生了較大影響。佩特不僅提出了藝術的目的在于培養人的美感,尋求美的享受,而不應受社會或道德觀念制約的觀點,還推崇與中國哲學一脈相承的“審美無為”的理念,即用看待藝術的態度看待生活,帶著強烈的感情去關注,卻不是去實際地參與到某種切實的行為,佩特將其稱為“熱情的冷漠”[2]。他認為人生的目的不在行動,而在于思考——是無為而非作為。這種以藝術的方式對待生活,即“為藝術而生活”。此外,佩特在其作《文藝復興史研究》的結論中指出:人生易逝,萬物皆變,能夠使生命燃燒出寶石般熾烈的火焰且盡可能保持在這種焦點狀態,乃是人生的成功。佩特對一個個凝聚著巔峰體驗的審美瞬間的看重不僅構成道林所謂的“新享樂主義”的內核,而且作為一種時間哲學滲透到王爾德的創作和美學中去,可以說,瞬間哲學成為了唯美主義者體驗時間的獨特方式[3]。因此,對絕對藝術自由的向往、對純粹美的真切追求以及對唯美思想的接納和吸收,促使王爾德堅定地成為了唯美主義創作的實踐者和倡導者。
2.2 《畫像》的華麗辭藻
王爾德的唯美藝術不關乎說教、道德、政治等方面,他認為藝術的使命在于為人類提供感官上的愉悅,而非傳遞某種道德或情感上的信息,它只能以藝術自身的標準來評判。而他在進行文學創作時,使用的語言也皆是絢爛唯美,游離現實,幽默生動,極具諷刺意味又不失哲理,建構了屬于自己的語言藝術。
王爾德擅長通過感官描述打造出一個超脫現實,如天堂般純凈,美好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感官的美好被無限放大,具象環境的描寫被無限縮小,這樣的藝術創作秉承了“藝術不反映現實”的理念,也滿足了讀者閱讀時在感官上對美的需求。在其作《畫像》中,開篇就描述了一幅直擊讀者感官的意象:“蜜蜂時而在許久未曾修剪過的長草之間翻飛,時而又不知疲憊地繞著滿是粉塵的金黃色忍冬花飛舞,沉悶的嗡嗡聲似乎讓此刻的沉寂顯得愈發壓抑。模糊的隆隆聲自倫敦傳來,宛若遠處的風琴湊出的低沉樂曲。”[4]華麗的辭藻,模糊的背景,絢麗的色彩伴隨著低沉的聲音交織出的和諧畫卷,充分調動起讀者的感官,使讀者仿佛置身于不知是臆想出的亦或是真實存在著的,唯“美”的無人之境。
同時,唯美的語言又近乎諷刺,王爾德利用悖論特殊的語言形式對當時的上流社會進行批判。美國批評家布魯克斯將悖論語言的特征總結為:反諷和驚異[5]。它將那些家喻戶曉的格言警句進行顛倒,或者是把人們視為違反常規的事情當成美德進行宣揚[6]。例如《畫像》中:“良知和怯懦本就是一碼事”、“忠誠的人只曉得愛情淺薄的一面,不忠的人才會體會到愛的悲傷”、“擺脫誘惑的唯一辦法就是屈服于它”[4]。這些悖論語言大多結構對稱、看似不合邏輯又荒誕可笑,實則卻蘊涵著對社會現象的尖銳諷刺。而道林也正是在這些悖論的蠱惑下,一次次與道德背道而馳,漸漸享受墮落與罪惡的快感,最終成為王爾德筆下欺世盜名、超脫現實的逍遙者。
2.3 背離傳統的人物形象
與莊子“性者,生之質也”(《桑庚楚》)中倡導自然之性不應人為的去改造,要順應人的自然性情,不用人為的道德去壓抑、束縛的觀點有所偏差,王爾德的唯美主義人物個性創作,具有享樂、功利的特征。具體來說,就是以奢華的穿著打扮和風流灑脫、紈绔子弟的形象示人。他在其后所作的喜劇中,常常將主人公作為英國傳統文化與維多利亞后期消費時尚融合后的產物而不加以束縛,更將其恣意、反叛的個性表達至極致,離經叛道、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形象成了王爾德唯美創作的特色:飲名酒、啖美食、抽雪茄是他們的愛好;赴宴會、逛舞場、談戀愛是他們的“事業”;他們出入于俱樂部,周旋于各種社交聚會[7]。除了《畫像》中的道林,著名的花花公子形象還有:《一個無足輕重的女人》中的伊林沃茲勛爵,《溫徳米爾夫人的扇子》中的達林頓勛爵。這些擁有足夠經濟保障和優越社會地位的花花公子們,以一種浮夸、享樂、閑散的生活方式不斷背離和沖擊著傳統觀念。正如文學評論家愛普斯坦1998年在其《紐約書評》中所說,“王爾德用他極端的唯美主義和花花公子面貌挑戰的不僅僅是維多利亞時代的虛偽,而且還在不斷挑戰著英國歷史上最頑固的禮法。”[6]
2.4 藝術與現實的脫鉤
對待藝術與現實的態度方面,王爾德與莊子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相通之處。王爾德認為藝術應與現實徹底分開來。唯美的藝術應該超脫現實,不與道德聯姻,不適應任何社會目的,只是“為藝術而藝術”,這樣的藝術才是逍遙又自由的。而莊子的美學思想同樣包含著深刻的悲劇意識,他渴望擺脫現實世界,走向純粹的審美自由和虛構的烏托邦世界[8]。他認為現實生活是混濁的,因而清高自許,思想放縱,采取“獨與天地精神往來,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的脫離現實的態度[9]。為超越生命中存在著的種種痛苦、絕望和無法克服的虛無感,求得詩意的生存和逍遙的人生需依賴于想象力和審美幻覺達到對現實世界的否定與超越。
在王爾德眾多作品中,最能體現出他對現實存在的否定,意在切斷藝術與現實聯系情節的,是《畫像》中名為西比爾的女演員之死。文中年輕瀟灑的道林愛上了戲劇演員西比爾。他愛上了扮演伊摩琴、扮演朱麗葉等完美藝術角色的她,而在現實與藝術交錯間,面對褪去角色濾鏡,有所缺陷的西比爾,道林感到十分失望,認為現實中的西比爾不僅扼殺了自己的愛情還背叛了自己的唯美藝術幻想。最終無法接受道林轉變的西比爾,選擇結束了自己年輕的生命。王爾德似乎試圖通過這個情節告訴讀者:藝術不應與現實捆綁,不應受道德制約,它只是為藝術自身,為抵抗現實之丑而存在。而這恰巧也是王爾德的悲觀和掩藏在其恣意張揚創作下的頹廢與絕望的隱晦體現:對藝術中存在的完美世界的執著以及對現實世界的存疑與否定都促使王爾德愈發求存于唯美主義創作。但若想逍遙避世,主觀地避開所有存于現實的世俗之物,沉溺于與現實脫鉤的想象和藝術中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要避世更要在世上,超脫于“物”,得精神自由,方能獨守一角青空。
3 結論
王爾德的行事作風、處事態度及唯美主義創作在許多人看來都是極端的,是帶有反抗意味的。這與他所受到的來自東西方思想的影響密不可分。而王爾德在嘗試解讀莊學思想的過程中,也存在著理解偏差。其中包括不自覺的誤讀與有意誤讀。
王爾德并非是直接閱讀莊子原作,在不具備漢學素養的情況下,研讀的完成是完全依靠譯者的。而不論是譯者翟理斯還是王爾德,他們都是從自身文化結構、思想的理路出發,來理解和闡釋莊子的思想。翟理斯于1889年出版譯著《莊子》(Chuang Tzu:Mystic,Moralist,and Social Reformer),他的翻譯總的說來比較自由,但譯文加入的個人成分太多,與《莊子》原意有較大出入。因此這個譯本歷來評價并不太高[10]。
除卻存在于不同語言文化間的屏障,個人意識的滲透也是誤讀的關鍵,王爾德從莊子這種顛覆性的思想中,介入自己的權力意識,以此獲得了精神反叛的參照動力,為自己抨擊維多利亞社會的生活方式、對唯美的“沉溺”尋得了理論依據。在王爾德看來,寫作中個性的張揚、主體完全自由的實現以及對藝術服從道德觀念的背離,開辟出一片遠離世俗的世外桃源。一些理解偏差助力了他批判當時奢華偽善的英國社會乃至整個西方文化存在的弊端。
結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王爾德想要在中國哲學中尋找理論根據為自己的創作和生活方式進行辯解時,無意或有意地曲解了莊子的思想。事實上,王爾德雖對莊子“逍遙”十分向往,但因其認識水平未達到,誤讀是必然的。而莊子對“逍遙”的獨特見解不僅深刻影響了王爾德,對后世也有無盡的啟發:逍遙如“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逍遙游》)并非是王爾德理解的處世行事獨立不拘,完全棄絕與人世相連的繩索,而是要擁有獨立超然的人格,心中不受任何時代環境所影響才能真正做到毀譽由人,得失不論,“至樂無樂,至譽無譽”(《至樂》)。再如列子御風而行,看似逍遙,“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逍遙游》)卻仍需借助風和空氣,依賴世俗之物才得以遨游于天地。然逍遙之游非形體之游,而是精神之游,憑借自身努力突破外物的束縛,達到無所牽掛,無所依賴,無所畏懼的境界,這時方可游刃有余,勝物而不被物所傷,擁有通透無礙的心境,悠然于世。也正如莊子所說: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莊子·人間世》)得失從緣,必無增減。萬物于世,必有不得已,然精神超脫,可得逍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