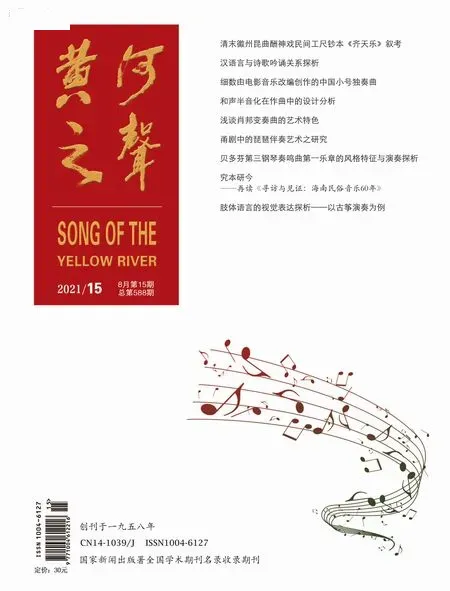從嶺南地區(qū)箏曲的演奏技法論客家箏派的形成
王 瑤
在中國的嶺南地區(qū),存在著兩個箏派共存的局面,這兩個箏派分別為“客家箏派”和“潮州箏派”。使筆者感興趣的是,既然客家箏派和潮州箏派地域相近,為什么會產(chǎn)生兩個截然不同的地域箏派?
本文以客家箏派的形成為研究對象,從《崖山哀》和《出水蓮》等客家箏曲探討客家箏派中獨具特色的演奏技法,從而得出客家箏派區(qū)別于潮州箏派在嶺南地區(qū)獨成一派形成的原因。
一、客家箏派的歷史及音樂特點
客家箏派作為中國九大箏派中的一門重要的流派,它在流傳發(fā)展過程中形成了特有的代表曲目、代表人物和記譜法等。本人認為客家箏派形成的時間距今并不久遠,根據(jù)筆者對資料的掌握,最早將客家箏樂進行傳播和發(fā)展的是民國時期的何育齋,其后經(jīng)過何育齋的弟子羅九香將客家箏樂中相關演奏技法、音樂風格加以規(guī)范化,使客家箏派自成體系,達到了一個嶄新的高度。下文從客家箏派的代表人物、代表曲目和記譜法三個方面對客家箏派的重要構成因素進行梳理。
(一)代表人物
關于客家箏派的發(fā)展軌跡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何育齋對客家箏曲進行分類、整理等等,使客家箏樂初見端倪;第二階段是羅九香在繼承何育齋對客家箏樂所做貢獻的基礎上,開拓創(chuàng)新最終促使客家箏派發(fā)展成型。
1、客家箏派先驅(qū)何育齋
何育齋(1886—1949)原名載生,廣東大埔莒村人,善彈箏,一生都在致力于對廣東漢樂和客家箏樂的發(fā)展。作為客家箏派的開拓者,何育齋最先對廣東漢樂樂曲進行了系統(tǒng)的整理,選編了作為客家箏譜中的《中州古調(diào)》(23首)和《漢皋舊譜》(37首),并將這些樂曲廣泛應用在“和弦索”演出活動中,在當時廣為流傳。
2、一代宗師——羅九香
羅九香(1902—1978)廣東省大埔人,從小受漢樂的熏陶,后來跟隨何育齋學箏。羅九香在客家箏樂方面有著很高的造詣,一方面他繼承了何育齋的遺志,另一方面又加以創(chuàng)新,吸收其他流派箏樂的優(yōu)點,可以說真正使客家箏派發(fā)展成體系化是在羅九香先生手里完成的。
如前所述,兩位客家代表人物可以說都對客家箏派的發(fā)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但客家箏派的形成不是僅憑這兩位演奏者所做的貢獻,而是離不開眾多在背后默默努力地客家箏派的演奏家們,才能使客家箏派在眾多藝術流派之林中熠熠生輝。
(二)代表曲目
客家箏曲是從廣東漢樂《中州古調(diào)》和《漢皋舊譜》中脫離出來的。根據(jù)何育齋先生對客家箏曲的整理,主要分為兩大類,一類具有中原音韻的樂曲編入《中州古調(diào)》計有:【出水蓮】、【崖山哀】、【雪雁南飛】等共二十首(均為六十八板),這類曲目根據(jù)板數(shù)的劃分屬于大調(diào)樂曲。(這些曲目也有【硬弦】、和【軟弦】之別)。另一類是將帶有戲曲過場音樂的曲牌編入《漢皋舊譜》計有:【春傳】、【蕉窗夜雨】、【翡翠登潭】等。這類曲目短小精干,板數(shù)不拘,結構富于變化,多為串調(diào)或小調(diào)。
眾多的傳統(tǒng)客家箏曲,不僅為后人提供了一份寶貴的文化遺產(chǎn),同時也成為客家箏派構成的重要因素。
(三)記譜法
在客家箏樂的發(fā)展過程中,形成了具有濃郁地方特色的記譜方式,即工尺諧字譜。這種記譜方式是何育齋先生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從傳統(tǒng)工尺譜中編創(chuàng)發(fā)展而來的,20世紀40年代后,客家箏曲中才逐漸開始用五線譜進行記譜。
工尺諧字譜與客家方言緊密結合,采用聲字并用的手法,對客家箏譜中《中州古調(diào)》和《漢皋舊譜》進行記譜,《中州古調(diào)》箏譜中讀音均為客家方言,這些客家語言中保留中古音,是以《中原音韻》為根據(jù)的工尺譜的變音讀法。
如工尺諧字譜中“上”,讀成“姓”;“凡”讀成“喚”、“番”等。這些變音讀法,受樂曲的約束,從而比較確切而真實的把古代民間音樂繼承、保存之,形成濃郁地方特色的記譜方式。另外,只記旋律骨干音,對樂譜其他裝飾音忽略不記,在一定程度上為演奏者提供了即興發(fā)揮的空間。
根據(jù)何育齋的《何育齋箏譜遺稿》中對工尺諧字譜的記述可以看出,客家方言對客家箏樂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由此產(chǎn)生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工尺諧字譜被廣泛應用在《中州古調(diào)》和《漢皋舊譜》箏譜中。工尺諧字譜只對旋律骨干音進行記譜的方式,為演奏者提供了充足的即興發(fā)揮空間,也給客家箏派的演奏技法的形成和發(fā)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二、客家箏派與潮州箏派風格比較
客家箏派與潮州箏派雖然在地域上相鄰,但在音樂特征方面兩個箏派之間存在許多的差異性。例如,在記譜法上,上文提到客家箏派采用工尺諧字譜進行記譜。與之不同的是,潮州箏派所采用的記譜法是“二四譜”,這種記譜法采用二、三、四、五、六來記錄音高,其按照順序所代表的音高為:sol、la、do、re、mi,由此,看出這種記譜方式基于五聲調(diào)式排列的。同時,“二四譜”也是采用潮州方言唱譜,獨具地方特色。但這兩種記譜法只記旋律骨干音,對其他細枝末節(jié)的音忽略不記,具有很強的即興性和靈活性。
筆者認為,客家箏派與潮州箏派在表現(xiàn)不同個性化的箏樂上,關鍵的原因在于它們對演奏風格方面的追求與演奏技法的運用。
風格是一個流派所具有的重要特質(zhì)之一,客家箏派與潮州箏派在長期發(fā)展的過程中各自形成了具有自身鮮明色彩的流派風格。兩個箏派之間由于地域相近,所以在音樂方面難免會產(chǎn)生交流和影響。從一定程度上來說,客家箏派與潮州箏派在表達音樂的內(nèi)容上會有一定的相似之處,但在板式布局和變奏手法的運用方面,兩個箏派則采取截然不同的處理手段。歸根到底,還是與兩者所追求的演奏風格有著密切關聯(lián)。下文以兩個箏派共有的箏曲《寒鴉戲水》為例,對客家箏派與潮州箏派之間的演奏風格進行比較。
《寒鴉戲水》是客家箏派與潮州箏派共有的一首異名同調(diào)的曲目。在潮州箏派這首樂曲叫《寒鴉戲水》,在客家箏派中則稱為《水上鷗盟》。在板式結構布局上兩者不同,《水上鷗盟》的板式結構由慢板和中板組成。在演奏時,中板部分反復演奏較多,可反復演奏三遍以上,只是在速度方面作對比,在反復時速度逐漸加快,最終達到高潮后速度才漸慢。
潮州箏曲《寒鴉戲水》的板式結構由頭板、二板、拷拍和三板構成,相較于《水上鷗盟》來說,《寒鴉戲水》的板式變化相對自由,這取決于演奏者的審美意趣,在拷拍和三板之間進行反復演奏,能夠展現(xiàn)出一種演奏者個人風格。在速度變化方面,與客家箏曲《水上鷗盟》相同。
從變奏手法的角度來說,客家箏曲對旋律的各種再生式的加工和變化,主要可以歸納為“加字”、“減字”。“加字”變奏常用的方法有“佛弦”、“中指起板”及固定音高配奏(“企六”)。“減字”變奏有“減字”和“么板”。
在《水上歐盟》慢板的1-12小節(jié),變奏方式相對單薄,主要采用“中指起板”和“企六”的加字變奏手法豐富旋律。而《水上鷗盟》的第1、7、9小節(jié)的第一拍采用“中指起板”變奏手法并結合左手滑音和顫音相關技法,既突出了中指厚重的音響效果,又通過左手滑音和顫音使音樂韻味更加細膩,恰到好處地反映出客家箏派中典雅、樸素的音樂風格。
潮州箏曲《寒鴉戲水》旋律相對復雜,主要利用密集的變奏加花手法來豐富旋律,以突出右手的演奏技巧,左手旋律方面比較簡單。潮州箏派在變奏手法上與客家箏派相比種類豐富,主要體現(xiàn)在對“催”的變奏方式上,這種“催”的變奏手法在潮州箏曲中不下于50種。《寒鴉戲水》正是反映了這一特點,該曲著重采用豐富多樣“催”的變奏手法對旋律進行擴充,其中包括“單催”、“雙催”及“企六催”等。這些華麗多彩“催”的變奏手法使音樂的流動性增強,同時也使潮州箏樂清麗、活潑的演奏風格得到彰顯。
客家箏曲《水上鷗盟》旋律相對簡約凝煉,節(jié)奏音型稀疏,但是在左手做韻方面相對復雜,出現(xiàn)大量滑音與顫音,極少使用花指,這恰恰能夠體現(xiàn)出客家音樂中古樸、典雅的風格。而從《水上鷗盟》的變奏手法分析可以看出,“中指起板”與“企六”的變奏手法與演奏風格之間相互影響,變奏手法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反映出客家箏曲中簡約、質(zhì)樸、淳厚的音樂風格。
綜上可知,在演奏風格上,客家箏派更多的是保留中原音樂的某些特征,同時融合了當?shù)匾魳返脑兀哂幸欢ǖ谋J匦裕瑥亩憩F(xiàn)出一種古樸典雅、簡約自然的風格。潮州箏派則通過右手復雜多變的加花變奏手法及自由的板式變化,形成了一種華麗活潑的音樂風格。總而言之,客家箏派與潮州箏派所表現(xiàn)的演奏風格是截然不同的,這也是客家箏派區(qū)別于潮州箏派而自成一派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客家箏曲演奏技法分析
客家箏樂除了在演奏風格上具有自身的特色之外,還體現(xiàn)在樂曲中演奏技法的處理手段上。本文通過對客家箏派中特有的演奏技法進行剖析,從而為進一步探究客家箏派中演奏技法特征方面進行深入的了解。
客家箏樂與其他流派一樣遵循著“右手撥弦,左手做韻”的演奏形式,該箏派演奏技法種類繁多,以佛弦、迴紋滑音和游移性按音為代表,從《出水蓮》等樂曲中可以看出這些客家箏派特有的演奏技法在不同的樂曲中有著異曲同工般的表現(xiàn)方式。
1、拂弦
“拂弦”又稱歷弦,花指,屬于右手演奏技法中的刮奏類,它是客家箏曲中一種具有特色的演奏技法。在一般的古箏曲中,刮奏是一種表現(xiàn)力極強的演奏技法,通常要刮的飽滿有力,以此來展示樂器特征與演奏者的水平。但是客家箏派中的“佛弦”一般是“短拂弦”,“短拂弦”在客家箏曲中的運用是有節(jié)制的,常用兩、三個音,最多不超過四個音。
拂弦技法在客家箏曲中運用的頻率較多,這在《出水蓮》這首樂曲中可以得到充分體現(xiàn)。《出水蓮》慢板中經(jīng)常采用短拂弦進行裝飾。這種“拂弦”短小而精致,不僅突出了旋律音,使聲音線條更加流暢、優(yōu)美,還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出客家箏曲中含蓄、凝重的音樂風格。
在客家箏樂中,非常重視左手演奏技法,正如客家箏派代表人羅九香所說:“古箏的藝術主要在左手”。右手簡潔的旋律為左手做韻提供了充足的空間,所以左手“吟揉顫按滑”做韻手法可以說是千變?nèi)f化,并且在用法方面非常講究。如“迴紋滑音”和“游移性按音”等。
2、迴紋滑音
“迴紋滑音”是“滑音”類的一種變體,同時也是客家箏樂中富有特色的演奏技法。長迴紋滑音演奏時較為復雜,因為這種按音在演奏時音準相對來說較難控制。在《蕉窗夜雨》第二段的慢板中出現(xiàn)了具有綿延悠長的長迴紋滑音,該技法在此處的運用一方面填補了音樂行進中的空白,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客家箏曲中淡雅、穩(wěn)重的特質(zhì)。
3、游移性按音
客家代表曲目有硬弦和軟弦之分,它們是客家箏曲中一種特有的調(diào)式,硬弦和軟弦具有不同的調(diào)式色彩,根據(jù)所表達不同的音樂內(nèi)容而定。客家箏曲中游移性按音主要體現(xiàn)4、7上,并且4、7兩個按音的音高不是以十二平均律為標準而設定的,而是隨著樂曲情緒而游移。4、7兩個音高和韻味對于把握客家箏曲的音樂風格相當重要。
關于4、7兩個音的音高在民間有兩種界定標準。一是7的音高在b7—7之間,4的音高在4—#4之間;二是7的音高在b7—7兩音之中,4的音高在4—#4之中。故此,兩個音具有游移性。筆者認為前者相對來說界定較為合適,因為“4”、“7”兩音在不同的樂曲中依據(jù)不同的樂曲內(nèi)容演奏者所按的力度不同,所以難念會造成音高上的細微的差別,不會完全處在b7—7,4—#4之中,故筆者不贊同后者的界定標準。另外,游移性按音很難用文字來表述清楚這兩種音高標準,在譜面上也較難記譜。游移性按音在硬弦和軟弦中所出現(xiàn)的做韻手法眾多,下文將以客家軟弦箏曲《崖山哀》作品為例,對游移性按音進行解釋說明。
《崖山哀》在慢板部分出現(xiàn)大量的游移性按音。其中,慢板的第一段45-46小節(jié)里,骨干音為“低音7、低音5、1、2,運用重顫和輕顫的技法,加重了音樂情緒的起伏,折射出宋代滅亡的沉痛之感,再次將客家箏曲中含蓄、委婉之風進一步展現(xiàn)。
簡而言之,這些種類繁多靈活的演奏技法與客家箏樂中所追求的音樂風格緊密相連,構成了客家箏派中重要的一環(huán),這也是該箏派魅力所在。
結 語
從《崖山哀》、《出水蓮》、《蕉窗夜雨》和《寒鴉戲水》這四首樂曲中的相關演奏技法可以看出,客家箏派在演奏技法上不以復雜、高超為主,只為表達音樂的心境,進而體現(xiàn)出高雅、古樸的音樂風格。值得一提的是,客家箏派作為嶺南地區(qū)的一支重要的流派是在客家歷史文化的大背景下產(chǎn)生的。另外,客家人在顛沛流離的過程中形成了感嘆國家興衰、懷念家鄉(xiāng)故土、及弘揚中原文化精神的內(nèi)容,所以說客家箏曲中很大一部分的樂曲內(nèi)容是含有客家文化精神的,例如《崖山哀》和《蕉窗夜雨》等。同時,這種客家文化精神也反映出客家音樂風格中所表現(xiàn)的沉穩(wěn)、含蓄的特點。所以,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客家箏派的形成絕非偶然,而是在客家歷史文化的沉淀下,結合演奏者對客家音樂的理解,而形成的一門獨具特色的藝術流派。
從宏觀的角度來說,客家箏派作為一門獨立的箏派能夠嶺南地區(qū)與潮州箏派相互共存,從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客家文化歷史的影響。本人在梳理客家文化史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羅九香提出客家文化觀念,即客家人文化的認同正是與客家箏派所形成的時間相吻合,都是出現(xiàn)在20世紀30年代。所以,筆者推斷何育齋在創(chuàng)立客家箏派時或多或少會受到羅香林先生所持客家文化觀點的影響,而這種影響在客家箏樂上以含蓄、古樸的音樂風格和演奏技法上得到了有力的印證。目前各學者對于客家文化歷史所持觀點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他們大多數(shù)人認為,客家文化主要來源于中原音樂、中原文化精神。而客家箏派的演奏風格和演奏技法更多是以這種中原文化精神為根基,將這種中原文化精神融入到客家箏樂藝術之中,從而形成獨一無二的藝術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