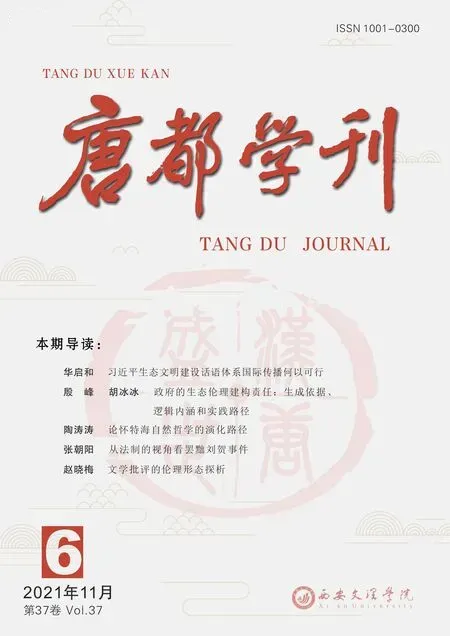論懷特海自然哲學的演化路徑
陶濤濤
(浙江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杭州 310058)
自20世紀初物理學革命以來,現代自然科學的迅猛發展對科學界和哲學界均產生了極大的震動。以牛頓經典物理學為支撐的傳統機械論哲學不斷喪失其解釋自然的合法性,新時代正迫切地呼喚著符合科學革命新范式的自然哲學。懷特海作為少數當代西方知識界同時精通科學和哲學的一流思想家,受此影響也開始逐漸從純粹的數理邏輯的研究轉向對自然科學的哲學思考。在近代西方哲學“認識論轉向”思潮的裹挾下,懷特海最初也主要是從認識論的視角重新審視和探討了自然科學知識的基本原理及其相關概念,卻又最終返本開新,構建了機體本體論的形而上學。懷特海的自然哲學上承早期數學和邏輯學的具體研究,下啟后期宇宙論形而上學的宏大敘事,因而在其哲學思想的發展歷程中占據著承上啟下的關鍵地位。本文試圖依據懷特海早期涉及哲學的相關科學哲學論文和著作,通過重點解讀《自然的概念》,進而透視其自然哲學思想的核心理念和基本特征,并同時考察其從科學走向哲學、從自然哲學走向形而上學的內在邏輯理路。
一
16世紀興起的西方近代自然科學發展至19世紀末,以牛頓經典物理學為支撐的近代自然科學的觀念體系因其取得的一系列令人驚羨的巨大成就而深入人心。然而,普朗克在1900年提出的量子論(1)普朗克在1900年提出量子假說后,量子論經由眾多物理學家共同的發展和完善,直到1925年左右才成為體系化的量子力學。雖然懷特海也曾關注并參與過量子理論的討論,但在他撰寫相關自然科學哲學的論文和著作時,主要還是針對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來構建自己的自然哲學。以及愛因斯坦分別在1905年和1916年提出的狹義相對論和廣義相對論徹底動搖了經典物理學的理論根基,顛覆了傳統的機械宇宙論和絕對時空觀。物理學上的科學革命無疑給懷特海的認知帶來了極大的震撼,以至于直到晚年,懷特海還一再強調:“到1900年,牛頓物理學被推翻了,摧毀了!……人們認為愛因斯坦做出了劃時代的發現。我對他尊敬且感興趣,但仍然有所懷疑。我們沒有理由認為牛頓的《原理》是終極真理,同樣,我們也無理由認為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是終極真理。”[1]由于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徹底改變了經典物理學對物質、時間和空間等基本概念范疇的理解,這一革命性的理論標志著作為近代科學基礎的牛頓物理學正在日益喪失其主導性的支配地位。懷特海對此明確地表示:“科學思想的舊基礎已經無法為人所理解。時間、空間、物質、質料、以太、電、機械、機體、形態、結構、模式、功用等等都需要重新加以解釋。”[2]22以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為兩大基本支柱的現代物理學迫切要求當時的科學共同體對此予以解釋和回應,第二次物理學的綜合已經勢在必行。與此同時,現代生物科學的發展特別是達爾文的進化論突破了舊自然哲學的禁錮,機體與環境、創造與突現的關系等成為所有以進化論為問題域的自然哲學必須要面對和解決的基本問題。由于近代西方哲學為適應自然科學發展的需要而發生了“認識論轉向”,因而認識論的問題成為近代西方哲學的中心議題。科學革命所引發的范式轉換迫使哲學家需要承擔起認識論上的變革:重組基本概念以適應現代科學革命的結構,以確立自然科學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在科學范式新舊交替的時代背景下,新自然哲學需要完成兩項緊迫的任務:“(一)拋棄經典科學與近代哲學中某些未經審查的基本假定和基本概念,重新構造或重新組合抽象概念,使之獲得正確的相對地位,從而與現代科學的新成果取得諧和。(二)用比抽象概念更具體的知覺來作對比,作參照,從而完成上述諧和,并為新科學提供概念差別,形成更完整的思想體系。”[3]34面對一系列強勁的科學革命引發的經典物理學危機和機械論哲學范式轉換的雙重挑戰,作為融貫科學與哲學兩大領域的思想家,懷特海適時轉變了自己學術研究的重心,從數理邏輯轉向了自然科學哲學。
懷特海最早涉及自然科學的哲學論文有三篇:《空間、時間和相對性》(1915年)、《思想的組織》(1916年)和《某些科學觀念的剖析》(1917年),這三篇初涉哲學的論文可以看成是懷特海開始建構新自然哲學的前奏。《空間、時間和相對性》探討了時間和空間,主張時空相對論,即時間廣延表現的是事件之間的延展關系,空間廣延表現的是對象之間的延展關系,并肯定我們是生活在時間的“綿延”(duration)之中,而不是時間的“瞬間”(instant)。《思想的組織》討論了科學結構的本質就是邏輯,科學已經發展到組織的時代,科學知識就是特定類型的思想的組織,又由于自然科學對外部世界的研究是以感官知覺為中介的,因而科學理論與感覺經驗密不可分。《某些科學觀念的剖析》則進一步剖析了事實、對象、時間和空間等基本概念,肯定了知覺和自然、經驗和思想同為具有內在關聯的整體,并闡明了科學哲學的主題包括知覺論和歸納邏輯。這些早期論文的共同特征是基于對經驗的探究來試圖構建思辨的認識論,進而將數學、邏輯學、物理學和心理學等知識融貫為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以達到對自然的明晰、簡潔和精確的認識。
這些從科學走向哲學的過渡時期的理論著作,展現了懷特海初涉哲壇時的理論基調和思想特色。在懷特海看來,科學哲學的基本問題就是要闡明現實的自然界與人的經驗感受之間的精確關系。為了清晰地闡明精確思維與經驗感受之間的關聯,懷特海圍繞五個核心理念嘗試建構出相應的解決方法。具體而言,一是繼承和接受了英國經驗論的傳統,事實上懷特海認為科學的任務就是要發現現實的自然界中已為人們所熟知的那些關系,而這些關系“存在于形成我們生活經驗的知覺、感覺和情緒的流動之中。通過視覺、聽覺、味覺、嗅覺和觸覺,以及比較早期的有感覺的感受而產生的全景,是唯一的活動領域”[4]63。二是致力于闡述和構建有關時間、空間及其相互關系的理論。他認為絕對時空觀的時間和空間中的“點”都是根據物質實體之間的外部關系,通過人的理智從經驗事實中抽象推理出來的,并不能作為具體的現實存在物。懷特海贊成愛因斯坦的時空相對論,即時間和空間是事物之間相對關系的表現形式。三是探討科學和形而上學之間矛盾的關系。懷特海在《思想的組織》中強調二者的獨立性,即“科學的基礎不依賴于任何一種形而上學結論的假定,而是科學和形而上學兩者都開始于相同的直接經驗給予的地基,并且在主要的進程中以相反的方向完成它們不同的任務”[4]65。但隨后又在《某些科學觀念的剖析》中肯定了科學和形而上學之間的聯系:“科學只不過使形而上學的需要變得更為迫切。”[4]105四是推進休謨原理的發展,探索人的思維推理結構的奧秘。懷特海運用奧卡姆剃刀原理,認為除了感覺對象和經驗活動能識別的各種關系外,其余都是思想建構的抽象產物。五是運用數理邏輯將科學概念轉變為知覺對象的類概念,“通過這種邏輯建構,我們終于得到一些概念:(1)它們在個體的經驗中具有確定的示例,(2)它們的邏輯關系具有一種特殊的平穩性。”[4]119由此可見,懷特海希望從自然科學的方法中組織思想,協調各種因素,進而提煉出科學的方法論和認識論原則,用以解釋自然界的因果規律。
懷特海早期的科學哲學論文在理論的概念化方面雖然比較簡要,但是很明顯已經具備了朝向系統化的自然哲學演進的雛形。他對自然科學的哲學問題的研究主要包含認識論和知覺論,并試圖以更加精確的理論模型來融貫科學和哲學的諸多觀念。“在這些早期哲學活動中,作為數學家出身的哲學家,懷特海曾經顯露出過對精確性的用心良苦的追求,曾經致力于對科學思想的基礎及日常語言進行形而上學式的純化和精化。”[3]59這種努力的企圖就是要將科學的最新成果作為構建新自然哲學的動力,以化解新興自然科學和自笛卡爾到休謨以來西方近代哲學的沖突。
二
隨著《自然知識原理研究》(1919年)、《自然的概念》(1920年)和《相對性原理》(1922年)這三部著作的出版,懷特海在自然哲學體系化的構想上取得了重大進展。其中,《自然知識原理研究》主要依靠從數學和物理學中得出的觀念研究自然,提出了“事件”(event)和“對象”(object)的理論,并介紹了“廣延抽象法”(the method of extensive abstraction)。《自然的概念》則避免數學概念的討論,更為精致密切地闡述了哲學原理,尤其對以牛頓物理學為預設前提的近代機械唯物主義及其導致的“自然的二分”(the bifurcation of nature)提出了尖銳批判。《相對性原理》除繼續探討事件概念外,依據相對性原理突出強調“自然的相關性”(the relatedness of nature),同時推翻了古典物理學的絕對時空觀,代之以“時空的連續統理論”(theory of space-time continuum)。這三部著作以《自然的概念》為核心,既相互獨立又互為補充,雖然每部著作各有側重,但在核心觀點上都是對同一主題的不同闡述。懷特海力圖通過這些著作奠定現代自然哲學的科學基礎,同時這也是重組思辨物理學的必要前提。具體來說,這些著作主要闡述了如下觀念:
第一,懷特海明確界定了“自然科學哲學的主要任務是,闡明對知識來說被認為是復雜事實的自然的概念,揭示基本的存在物和存在物之間的基本關系——所有自然律都要依據這些關系來陳述,確保這樣揭示的存在物和關系適合表述自然中存在的存在物之間的所有關系。”[5]38為了辨明自然的概念,懷特海首先反思和批判了牛頓物理學中表達的實體自然概念。這個概念的科學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哲學,即對物質實體的偏愛、對絕對時空觀的構想等是由樸素的日常感覺強加給科學思維的,而這些對思維方式來說必不可少的抽象存在物卻被不合法地轉變為理解自然的形而上學載體,它們揭示的只能是思維虛構中的自然,是概念化的抽象的自然。懷特海進而闡發了他對自然的理解:“自然是我們通過感官在感知中所觀察的東西。在這種感覺—知覺中,我們意識到某種非自然的并對思想來說是自我包含的東西。”[5]2人對自然客觀性的認識,并不是將自然視為外在于身體主觀感受的客體,人不是在自然之外去認識自然,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人的身體在感知自然的同時,也就是在積極地介入和參與自然的演化。人能同質性地思考自然,即透過身體直接感知到的自然才是真實具體的自然,而科學中所涉及的自然理論是從這種具體整體的自然抽象而成的概念系統。人與自然、人的身體感受、經驗活動和自然的諸多要素之間是密不可分的有機整體。
第二,為了進一步闡明自然的準確含義,懷特海認為必須要以新的觀念重塑思辨物理學,即用事件理論和對象理論重新理解自然,把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由物質實體轉向了被知覺的事件,將自然建構為綿延時段中由事件和對象構成的復合體。在懷特海看來,沒有瞬間的自然,只有作為過程的自然,“自然是作為事件而呈現的”[5]13。事件成為構成自然的終極事實,“事件的流逝就是生成中的廣延。‘過去’、‘現在’和‘未來’這些術語都在指稱事件。過去的不可挽回性就是事件的不可改變性。一個事件就是此在、此時和此地。”[6]62可見,自然在本質上是短暫易逝的,不存在能讓人直觀的靜止不動的自然。以流動的事件取代僵死的物質實體,自然也就從“死的自然”轉變為了“活的自然”。由于自然中的事件處于連續不斷的流動和變易狀態,懷特海進而提出了對象理論用以描述自然界中的恒定因素,“對象表現了在事件中被認知到的恒常性,相同事物可在不同情形下被認知;也就是說,相同的對象因與不同的事件有關聯而可以被認知。因此相同的對象在事件之流中保持其自身的存在。”[6]62-63懷特海又將對象細分為感覺對象(藍色、形狀等)、知覺對象(椅子、石頭等)和科學對象(電子、分子等),對象進入事件的方式成為該事件特征中的構成要素,事件因對象的進入而是其所是。事件是現實,對象是潛能或可能性。正因為事件的生成離不開對象,對象的顯現必須借助于事件,事件與對象須臾不可分離,所以懷特海才指出“自然是這樣的:沒有對象進入事件,就不可能有事件也不可能有對象”[5]119。
第三,懷特海批判了牛頓的絕對時空觀,建構了自然的相對時空觀。絕對時空觀假定時間與空間相互獨立、互不影響,它們是客觀獨立自存的實體。宇宙作為靜止的絕對時空的坐標系,無論有無事件的發生,時間均勻流逝,空間客觀存在。懷特海認為,這種機械論的“自然唯物主義”是由以下三位一體的東西構成的:“(1)無擴延瞬間的時間系列,(2)物質存在物的集合,(3)作為物質關系的結果的空間。”[5]59相對論修正了絕對時空觀,代之以相對時空觀,即空間和時間不是客觀自存的實體,空間是事件排列的一種秩序,時間是對事件先后發生的次序進行度量的結果。當我們談論自然的概念時,“必須避免抽象的空間和時間,必須訴諸自然的最終事實即事件”[5]148。自然是事件的結構,此時的事件其實已經具有了本體論的意味。自然的事件是在四維時—空系統中的創進和冒險。事件的流變和擴延產生了時間和空間,即事件的流變是指事件接續不斷地沿著過去—現在—未來的綿延時段生成和消逝,時間是由具體事件的流變所形成的先后秩序抽象化而來的概念;事件的擴延是指每一事件都能擴延至其他諸多事件之中,同時該事件又能吸納其他諸事件,事件之間的內在關系使其相互擴延成為有機關聯的連續統,空間是由事件之間內在關系而構成的連續統的抽象形式。沒有事件發生,也就沒有時間和空間。由此,時間和空間的概念都是在事件的流變和擴延的歷程中,經由人類知覺感知和理智抽象思考所抽離出來的抽象形式。自然是由此種具有內在關系的諸多事件相互融攝而形成的復合體,自然的流變就是事件在宇宙生生不息的創造性進展中的探險之旅。
第四,懷特海批駁了盛行已久的傳統機械論哲學對自然的錯誤認識,這種哲學信仰“自然是物質材料的集合,這種物質材料在某種意義上存在于無擴延時間瞬間的一維系列的任一連續部分上。而且,物質存在物在每一瞬間的相互關系把這些存在物制作成了無邊界空間中的空間形狀”[5]59。也就是古典物理學中三位一體的時空物質觀,即物質的質點存在于沒有廣延的瞬間的“點”之中,與其他時空區域沒有任何關聯。這種哲學用抽象的物質概念在解釋變動不居和多樣關聯的自然界時,在認識論上必然要陷入截然二分的思維模式,由此導致了被懷特海稱為“自然的二分”的理論困境,“它把自然二分為兩個部分,即在意識中理解的自然和作為意識的原因的自然。……兩種自然的匯合點是心靈,作為原因的自然是流入物,而顯現的自然是流出物。”[5]26這就在認識論上產生了被懷特海稱作“心理添加論”對初性與次性、實體與屬性等各種二元論的劃分,從而導致“原因的自然”成為真實的、客觀的自然,而“顯現的自然”成為可感覺的、主觀的自然,并使得真實的自然不可知,可知的自然又顯得不真實。懷特海認為,心靈對自然本身的直接把握并不需要額外增添心理的附加物,外在顯現的自然就是人能夠真實感知到的自然。心靈與自然是密不可分的有機整體,心靈能夠本能地、直接地與自然相遇相知。而自然科學并不需要考慮與認知心靈的關聯性,“我們僅僅關注自然,也就是說,只關心作為知覺知識的對象,而不關心知者與被知者的綜合。”[6]vii這就避免了私人的價值觀念介入科學實踐,從而保障了科學知識的真理性和客觀性。
第五,針對科學、自然哲學和形而上學之間復雜的關系問題,懷特海雖然多次明確地表示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并不涉及價值,也不需要形而上學的介入,但形而上學思想始終像幽靈一般揮之不去地纏繞著他。懷特海在《相對性原理》中為他的新自然哲學選擇的術語是“泛物理學”(pan-physics),即“它(科學哲學)和倫理學、神學或美學理論無關。它完全致力于確定最普遍的概念,這些概念只適用于我們感官所觀察到的事物。因此它并不是形而上學,應該被稱作是泛物理學”[7]。然而這一術語他只使用過這一次。一個合理的解釋就是懷特海的新自然哲學試圖將自然科學的不同主題統攝在一個概念之下,也就是他所認為的“科學的哲學——被設想為一種主題——就是要努力把所有的科學展示為一種科學,或者——在失敗的情況下——反證這種可能性”[5]2。這一設想最終在《自然知識原理研究》的再版序言中徹底明晰了:“自從本書第一版在1919年上市以后,我又在《自然的概念》和《相對性原理》中重新思考了該書的主題。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夠將這些著作的觀點,具體地呈現在一種更加完整的形而上學之中。”[6]二版xi由此可見,一直困擾著懷特海思想中的科學與形而上學之間復雜的糾葛,最終以形而上學的勝利而告終,今后的自然科學不僅不拒斥形而上學的介入,還將為未來形而上學的科學化提供理論支持。
懷特海在這三部自然哲學著作中不僅從認識論的視角闡述了哲學問題,還試圖挑戰和修正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在懷特海看來,“我與愛因斯坦的分歧主要產生于這樣的事實:我不接受他的非均勻空間理論或他關于光信號的根本特征的假設。”[5]序言2懷特海在《相對性原理》中提出了一個有可能代替愛因斯坦理論的引力理論,遺憾的是這一引力理論后來被美國物理學家威爾所證偽。就此而言,懷特海的這些著作并沒有在實質意義上改變當代物理學的走向,但他的著作卻給哲學界帶來了強烈的沖擊。憑借著這三部著作,懷特海在科學哲學的領域內聲名鵲起,同時這也為他進一步思考和完善新自然哲學并最終走向形而上學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和實在的可能。
三
晚年的懷特海從倫敦大學退休以后,受邀去哈佛大學主持哲學講座。根據羅威爾講座的內容集結出版的《科學與近代世界》(1925年)代表了懷特海哲學思想發展新舊交替的過渡階段。《科學與近代世界》有兩大主題:一是承接和延續先前自然科學哲學三部著作中的思想,系統地表述了新的自然哲學理念;二是隨著懷特海哲學興趣的不斷擴大,他的哲學研究的議題由原先的認識論擴展到了本體論和價值論,此前受到排斥的形而上學也得到了初步建構。因此,這部著作標志著懷特海的哲學思想已經開始由自然科學哲學逐步過渡到形而上學和宇宙論的階段,同時也預示著懷特海自然哲學的終結和有機哲學或過程哲學的興起。
在《科學與近代世界》中,懷特海回顧了近代自然科學的發展歷程,進一步思考和完善了先前自己對自然科學哲學各項主題的研究。自17世紀以來,由伽利略、開普勒、牛頓及其追隨者們發展成為近代科學基礎的機械論范式代表了人類抽象智能的一次偉大勝利。科學上的機械論與哲學上的唯物主義相結合,就產生了被懷特海稱之為“科學唯物論”(Scientific Materialism)的觀念,也就是人們通常所理解的機械唯物主義。在懷特海看來,近代哲學在科學唯物論的影響下陷入了進退失據的兩難境地,“它以極復雜的方式在三個極端之間搖擺。一種說法是二元論,認為物質與精神具有同等的地位。另外兩種都是一元論,其中一種把精神置于物質之內,另一種則把物質置于精神之內。”[2]64-45這種觀念帶來的結果就是科學守住了唯物的自然,哲學則占據了思維的心靈。近代哲學思想中的主體—客體、主詞—謂詞、實體—屬性和心物二分等各種二元論思想也無不與此相關。
正如恩格斯對19世紀自然科學的三大發現給予哲學的巨大變革所做的評價那樣,“隨著自然科學領域中每一個劃時代的發現,唯物主義也必然要改變自己的形式。”[8]20世紀初的相對論和量子力學對物理學帶來的根本性變革同樣也需要唯物主義做出相應的改變。懷特海早在《自然的概念》中就已經對此做了批評:“18世紀和19世紀接受的自然哲學是一批嚴格的、像中世紀的哲學那樣規定的觀念,而且這種接受幾乎是不帶任何批判性研究的。我把這種自然哲學叫作‘唯物主義’。不僅從事科學的人而且所有哲學流派的追隨者都是唯物主義者。”[5]58雖然懷特海在此前自然哲學的三部著作中懷著強烈的使命感探索了這一轉變的可能,但是真正成熟的思考結果誕生在了《科學與近代世界》。在這部著作中,懷特海將生物進化論思想納入其中,提出了代替科學唯物論的“機體機械論”(Organic Mechanism),即“機體論的自然哲學必須從唯物論哲學所要求的東西的反面出發。唯物論的出發點是獨立存在的實體——物質與精神。物質受著空間運動的外在關系的改變,而精神則受著思維對象的改變。在這種唯物主義的理論中,兩類獨立的實體都受著與各自相應的激情的改變。而機體論的出發點則是事物處在互相關聯的共域中的體現過程”[2]169。懷特海機體機械論的基礎概念是“機體”(organism),機體的本質就是模式或結構。這一概念此時與“事件”可以等同使用,它取代了科學唯物論的實體。機體不僅涵蓋了傳統的生命有機體,也包括像月球、椅子和電子等在內一切無生命的存在物。至此,懷特海最終完成了對自己的新自然哲學的構建,這種以機體為本體論的新自然哲學同時也就是機體形而上學。
此外,懷特海早期哲學思想研究的主題受近代哲學“認識論轉向”影響較深,以知覺認識論為主要的研究議題,但在《科學與近代世界》中,他的哲學研究的興趣從認識論轉向了本體論和價值論。其中,早期的事件本體論開始逐漸讓位于機體機械論中更具有生物學色彩的機體本體論,即自然界是由活動的有機體構成的。機體機械論則又進一步發展成為經驗形而上學和過程宇宙論。另一重大轉變就是將價值納入自然哲學的考量范圍。如果說懷特海此前的哲學著作對形而上學保持著若即若離的曖昧狀態,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他對價值問題是明確拒斥的。懷特海甚至將任何價值的介入都排除在自然科學哲學的研究之外,如在《自然的概念》中就表示:“把關于自然的思想的同質性看成是根本不涉及任何道德或美學價值的東西,盡管對道德或美學價值的理解在相應的自我意識活動中是強烈而生動的。自然的價值對存在的形而上學綜合來說也許是關鍵的東西。但是,我恰恰不想進行這種綜合。”[5]4懷特海的這一立場在機體機械論對自然的形而上學討論中徹底改變了。他在《科學與近代世界》中明確了自己對價值問題的態度:“一種自然哲學必須研討六種概念:變化、價值、永恒客體、持續、機體和混合”[2]100,“我把‘價值’這個字用來說明事件的內在實在性”[2]107。懷特海機體論的自然哲學對價值問題從否定到肯定的轉變,不僅標志著此刻機體論的自然哲學與自己以前的自然科學哲學的不同立場,同時也表明了對早期科學無涉“知者與被知者綜合”觀點的修正。機體機械論“把那些牢固地根植于審美經驗、倫理經驗和宗教經驗的觀念從一開始就納入宇宙論之中”[9]。由此,機體論的自然哲學通過融貫生物學、美學、倫理學和宗教等思想,逐漸轉變為機體宇宙論。
值得注意的是,懷特海在早期的科學哲學論文和著作中對形而上學問題的態度極為復雜。他在很多時候強調科學和形而上學的獨立性問題是為了說明不借助于參照本體論和價值論,也同樣可以取得自然科學研究的進步。但這并不是說科學就可以脫離形而上學,相反,懷特海認為科學家對自然的研究始終要受到他們所默認的形而上學框架的制約。正如柯林武德所言:“受過數學訓練的懷特海,則代表了一種唯理論傳統,這個傳統把被認識者與必然和永恒的真理相等同。這把懷特海引回柏拉圖,使他堅持永恒客體世界的實在性,并將之作為宇宙過程的先決條件。”[10]由于懷特海深受柏拉圖哲學的影響,因而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一直都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他,這也是從一開始涉足哲學以來,懷特海始終對形而上學問題糾纏不清的原因。這種對形而上學迷戀的情結終于在《科學與近代世界》中得到了釋放,新自然哲學從此不必再對形而上學遮遮掩掩。“懷特海的意義上的形而上學的任務,相對于描述世界怎樣存在的自然哲學,是追問探究具體的生成事實在其中成立的根據。”[11]這就要求形而上學不僅要為自然科學的研究提供預設的背景,更需要對人類社會生活的全部知識進行批判性的賞析。這部著作對形而上學問題的集中探討出現在“抽象”和“上帝”兩章。后期形而上學的巨著《過程與實在》中的許多核心概念如現實事態(actual occasion)、永恒客體(eternal object)、攝入(prehension)、上帝等也都被先行提出并得到了初步的探討。
綜上所述,懷特海前期自然科學哲學探討的許多主題都在《科學與近代世界》中得到了系統的梳理和闡發,“縱觀懷特海自然哲學有四項基本立場:整體經驗論、批判實在論、機體論以及過程論,這些論點成為其后機體哲學的特色。”[12]機體論的自然哲學一經形成就成為向機體形而上學進發的起點。因而要想完整準確地理解懷特海后期的有機哲學和過程宇宙論,通曉他前期的自然哲學就成為必由之路。由于當今物理學仍然處在懷特海所設想的第二次綜合階段,所以當代自然哲學的建構仍然處在過程之中。通過考察懷特海從自然科學哲學轉向形而上學的演化歷程,可知自然科學的變革為哲學提供了科學精神,思辨的形而上學又為科學提供了哲學智慧,未來的新型自然哲學同樣也將會是實證科學和思辨哲學的聯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