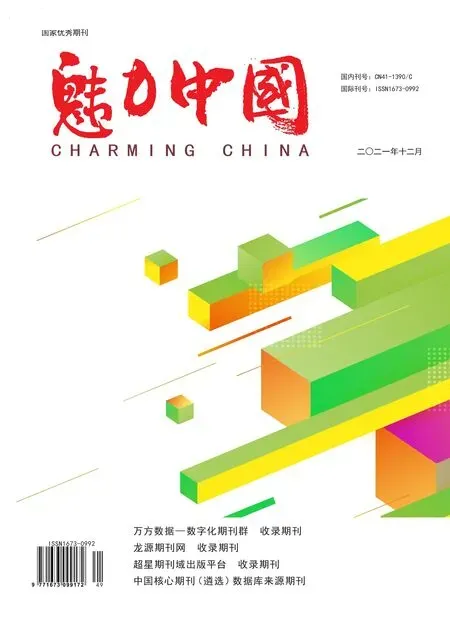創新發展歌唱藝術 提高娛樂文化藝術水準
孫美娜
(上海師范大學影視傳媒學院,上海 200235)
面對這種新情況和新特點,國內的音樂工作者必須轉變觀念、積極應對、參與競爭,除了不斷推出新人新歌外,還要用與時俱進、不斷改革創新的精神,在歌唱藝術和技巧上進行改革和創新,通過創新促進發展。而所謂的創新,就是要研究和追求變化。創新實際上就是變化的過程,也是變化的結果。而這種變化,必須是對僵化條框的突破,必須適應時代的需要,順應大眾的需求,這就既要繼承傳統、更要突破傳統,以時尚流行托舉和拓展傳統。而就目前來說,可大力推廣普及“民通”唱法,也就是推廣“藝術流行歌曲”用不斷提高歌唱藝術水平和發展普及多種歌唱藝術形式,使社會大眾特別是年青群體進一步達到歌中有教、又唱又樂,在娛樂的同時提高對藝術的認知、提升演唱藝術水平。這對于克服泛娛樂化現象、發展音樂藝術、加大推進先進文化傳播力度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和作用;同時也有利于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滿足人們對音樂的不同需求,提供精彩紛呈的精神食糧,使美麗的歌壇也得到更多的文化滋養。
一、在娛樂中提高對藝術的認知
音樂,決不能只被當作是一種娛樂,更要看到它提高人的素質的功能。但正如一些主流媒體所指出的,當前特別是對知識階層,對文化素質較高的成年人,缺少適合于他們需要的好聽又好唱的歌.通俗歌曲,容易上口,而且不少帶有表演形態的勁歌狂舞,確實受到特別是青少年的喜愛。但如果不伴隨勁歌狂舞和艷裝或者選秀搞笑,受眾會感到有不少流行歌手演唱的歌曲好比是一杯白開水,令人大倒胃口。所以,對成年人特別是文化素質較高的成年人來說,會感到索然無味而難以接受,而即使青少年也會出現兩種情況:一是使許多青少年的歌藝水平長期得不到提高,停留于泛娛樂化。不少青少年“跟風”唱口水歌,給人以“愚笨呆傻”之感;有的不知不覺地患了“偶像中毒癥”還在自得其樂!而即使選秀造出的星,很多因為藝術功底受限而曇花一現。另一方面隨著年齡的增長、文化素質的提高,對低水平演唱的通俗歌曲的興趣也會逐步減弱,不可能永遠勁歌狂舞。而美聲、民族唱法的歌曲,雖然高雅好聽,但專業性很強,要學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影響了歌唱藝術的普及。從這一分析可見,對部分的成年人,特別是知識階層、有一定年齡的企業家及白領們來說,社會對他們的音樂文化需求未能滿足;同時對相當一部分要求欣賞和學習藝術歌曲的青少年來說,他們難以從娛樂中提高對藝術的認知,他們的需求不但未能得到滿足,有的還須從泛娛樂化的“跟風”泥沼中解放出來。總之,他們都需要“有抒情韻味、旋律優美、格調健康、寓意深刻”,而又好聽好學好唱的歌。這就向廣大音樂工作者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就是如何使好唱的通俗、流行歌曲與民族、美聲歌唱藝術相融合,達到新的藝術化;如何使高雅好聽而難唱的美聲、民族歌曲與流行歌曲歌唱藝術相融合,達到通俗化、流行化,用時尚元素和流行手段托舉傳統的民族、美聲歌唱藝術,讓青少年感受傳統藝術的獨特魅力,用全新方式,讓傳統回歸大眾土壤,并通過創新推動發展,推向新的藝術高峰。概括而言,就是如何突破傳統、改革和創新演唱方法,為他們演繹和提供好聽又好學好唱的藝術流行歌曲,以此發揮主旋律的作用,推進“兩個文明”建設和先進文化傳播,豐富人民音樂文化生活,占領音樂文化市場。而這一新唱法也就是人們常說的跨界音樂藝術。而跨界音樂藝術也是當前的國際時尚。上海要建設國際化大都市文化,也應像建設上海特色的城市基礎設施那樣,有“上海牌”“中華牌”的跨界音樂,而跨界音樂的推廣,也可起到托舉和拓展美聲、民族傳統音樂藝術的效果。
二、音樂文化在不斷創新中得到發展
改革和創新是一切事物發展的生命力。就從現在國內流行的美聲、民族、通俗三種唱法來說,它也是逐步發展形成的,最多也只有二、三百年的歷史。以后是否永遠如此?筆者認為,不可能幾百年后永遠是這三種唱法。就看由流行歌曲基礎上形成的藝術歌曲發展史,無論是中國還是外國,它也是一個從無到有的發展變化過程,是我們的前人不斷研究探討、不斷實踐發展的結果。在歷史的不同時期,藝術歌曲都以不同的演繹形式,對時代的進步和音樂文化的發展產生過積極的意義。藝術歌曲本源于18 世紀后期和19 世紀早期浪漫主義音樂時期的德國,經過莫扎特、貝多芬始創,到使藝術歌曲創作走向繁榮的舒伯特,逐漸形成歐洲藝術歌曲的主流。舒伯特一生創作了600 多首歌曲,他的“小夜曲”“野玫瑰”“鱒魚”“圣母頌”“魔王”“流浪者”“紡車旁的瑪格麗特”等,廣為流傳。在蘇聯衛國戰爭時期,根據伊薩科夫斯基詩歌編曲的“燈光”“喀秋莎”(布朗介爾作曲),根據民歌改編、波杰柯夫作詞、伊凡諾夫作曲的“小路”,丘爾庚作詞、索羅維約夫.謝多伊作曲的“海港之夜”,丘爾庚作詞、諾索夫作曲的“遙遠的地方”等大量優秀的藝術歌曲的產生,對于鼓舞蘇聯人民奮起反抗德國法西斯的侵略,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我國的藝術歌曲,在“五四運動”以前主要是用外國的曲譜填詞的“學堂樂歌”,如李叔同的《送別》《祖國歌》等等。“五四運動”以后,我國音樂界前輩也都致力于藝術歌曲的創作,并留下了大量優美的作品,如蕭友梅的“問”、趙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他”、“賣布謠”,黃自的“玫瑰三愿”“賦登樓”“思鄉”,應尚能的“漁夫”,劉雪庵的《紅豆詞》《長城謠》等等,至今都不能令我們忘懷。抗戰時期的藝術歌曲對于全國人民奮起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如聶耳的“鐵蹄下的歌女”、冼星海的《黃河頌》、賀綠汀的“嘉陵江上”、夏之秋的“思想曲”等等。再如,陸華柏作曲、張帆作詞的《故鄉》、陸華柏作曲、胡然、映芬作詞的《勇士骨》等,充分發揮了藝術歌曲的寫作技法,反映了中華民族不屈于外強的英勇精神。張寒暉創作的流亡歌曲《松花江上》唱出了東北同胞的心聲,唱出了全國人民的抗日呼聲,悲劇性的音調化成了巨大的愛國力量,激發起民眾團結起來,投身于反擊日本侵略者的戰斗中。建國前后也出現了不少杰出的作曲家、詞作家、翻譯家和優秀的藝術歌曲,有不少作品也達到了很高的藝術成就。
以上論述說明,創新和發展歌唱藝術,不但在歷史上推動了社會的前進,而且也推動了音樂文化的自身發展。正如當下有的業內人士指出的那樣,將來的音樂市場會更加細分化,每種類型的音樂和歌手都會有其相對市場。超越傳統、創新唱法,已經具備了更為有利的條件和極為廣闊的空間。學習前人經驗,結合今天的實際,經過不懈的努力,完全可以通過創新歌唱技巧來達到歌唱藝術的多樣化、多流派,以此提高娛樂文化的藝術水準,適應瞬息萬變的大眾口味,并使上海和我國的音樂文化更加豐富多彩。
三、推廣“民通”唱法,促使寓教于樂
多年來,我國許多音樂工作者,不顧種種爭議,堅持以新唱法、新風格來創作和演繹藝術流行歌曲,并且已經取得了不少驕人的成績。如國內歌壇的李娜、于文華、譚晶等,以及港臺的李泰祥等著名歌手和創作人,都邁開了跨界音樂、藝術歌曲的步伐,影響甚廣。而我國西部地區的原生態歌曲,許多地方的田山歌、民謠和少數民族歌曲也都以各種不同的歌唱藝術為豐富祖國的音樂文化做出了新的貢獻。就筆者而言,這方面也有不少體會和收獲,特別在2002 年,在筆者獲得了開羅國際歌唱大賽“特別演唱獎”和在中國輕音樂學會“首屆學會獎”大賽上,榮獲“全國最佳民通女歌手新人獎”后,有媒體褒揚筆者創造了特有的“孫派唱法”,甚至夸獎我是“民通演唱領域的領跑人”,使筆者既受鼓舞、又感內疚。因為成績不多,但大眾給了筆者很高的評價。筆者從實踐中發現,通俗和藝術相結合的“民通”唱法,因為既有易學、易唱、易傳的特點,又有動聽的藝術享受,既避免了美聲、民族唱法的難度,又避免了通俗唱法一般缺少藝術性的弊端。這種優化組合的歌唱藝術,沖破了歌壇的沉悶死板條框和氣氛,給歌壇帶來了新鮮感,也給大眾帶來了興趣并受到普遍的青睞。特別是受到中年人以上人群,包括知識階層和企業家的歡迎,同時許多追求藝術風格的青年人也十分喜歡,并成為他們在欣賞和學習音樂藝術上不斷成熟的途徑。不但中國人喜歡,外國朋友也喜歡,這在筆者2000 年參加訪美演出和在埃及開羅的比賽中獲得的熱烈掌聲中,深深地給了筆者這種感受和體會。所以,推廣“民通”唱法也是提高娛樂文化水準的一條有效途徑。
當然,要推廣“民通”演唱方法,首先必須要抓好創作,這就要廣大詞曲作家的支持和努力,但這要有個過程。近幾年來,筆者也嘗試創作了一些作品,不過尚屬努力摸索之中,為了盡快推進發展和變化,我想也可以把一些比較優秀的通俗歌曲加以適當的改編,用“民通”的格調進行演唱,這方面筆者也在不斷地嘗試。其次,要在歌唱方面實現二度創作,這就是要提高演唱技巧和藝術。而從演唱技巧來說,筆者感到首先歌曲的先天條件很重要,同時還要看這首歌的歌詞適宜哪些受眾對象。只要歌曲本身條件好,就要根據適宜受眾的特點,用最佳的演唱技巧和情感,盡量把它發揮得淋漓盡致。比如我演唱并在中國輕音樂“學會獎”比賽中獲獎的“真情永久”,其本身的風格就適宜用“民通”唱法來演繹,在用氣、聲腔、音色上努力把民族唱法的藝術性和通俗唱法的流行性有機的融合起來,對其中藝術難度較高而難唱的盡量處理得通俗些,對過于通俗而缺少藝術性的加以藝術化,使男女老少都感覺好學又優美動聽。再如獲“全國十大金曲獎”的“秋天的女人”以及自己譜曲演唱并被《談婚論嫁》等電視連續劇選為主題曲的“問你一聲好”等,都有這樣的發揮。平時我演繹“民通”唱法較多,但也不是對每首歌都是一種唱法,有時候也會運用“通、民、美”三種合唱法,總之,要視歌、視人、視情來區別對待和靈活運用,以最佳的歌唱技巧和情感來達到最美的效果。
筆者認為,“民通”相對而言更“通民”,它更能貼近生活、貼近大眾,就如當下盛行的國風音樂一樣,會受到越來越多人的喜歡。當然,要使一種新的唱法普及,我們還要做許多的努力,包括權威部門和媒體的進一步支持和認同。在這方面,中國輕音樂學會很有開拓精神,他們首先開設了“民通”獎項,對“民通”歌曲給予了極大的支持,令歌壇面目一新。就當前來說,特別需要媒體突破傳統,在啟用新人、講究時尚、形象和娛樂的同時,更要打破框框,支持、宣傳歌壇創新、支持百花齊放、百花爭艷,推介新唱法、新風格,滿足大多數人需求的好聽又要好學好唱的藝術品位和藝術享受,從娛樂中提升對藝術的認知。這也應該是音樂文化發展要貫徹“以人為本”,為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服務的一個重要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