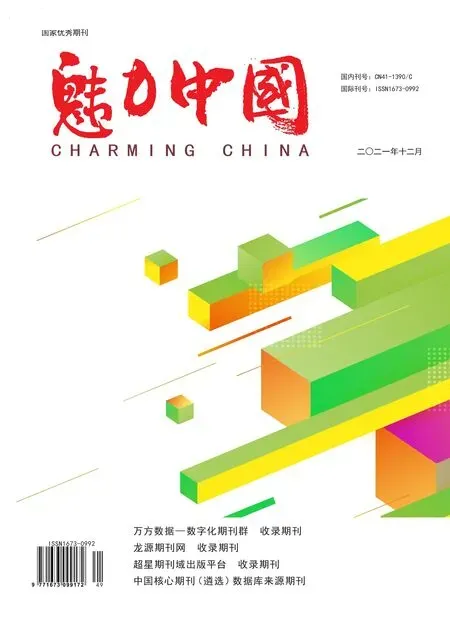父母處分未成年子女不動產的效力研究
郎博爾
(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北京 100875)
近年來,未成年人“名下有房”的現象遍地開花,其形成緣由可謂五花八門——也許是從長輩手中繼承或自身勞動所得;也許是購房者試圖以此規避限購政策和可能開征的遺產稅;抑或是未成年子女的父母想要暗度陳倉,以房屋過戶的手段轉移資產、逃避債務……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第23 條的規定,“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的監護人是其法定代理人”。換言之,一般情況下,父母既是未成年子女的監護人,也是其法定代理人,保護未成年人財產的主體和處分未成年人財產的主體身份混同。因此,當未成年子女的利益與父母自身利益發生牽連乃至相互沖突,保護未成年人的權益并不能僅僅依靠于骨肉親情。然而,令人抱憾的是,《民法典》對此僅概括性規定了“監護人除為維護被監護人利益外,不得處分被監護人的財產”,肇致在司法實務中,其一,處分行為是否維護了被監護人利益的判定標準不統一,同案不同判;其二,非為維護被監護人利益所做出的處分行為效力不明晰,威脅了第三人的交易安全,特別是在標的數額巨大、涉及法律關系相對復雜的不動產案件中。有鑒于此,筆者將在本文中嘗試從我國現行實體法及相關司法實踐出發,對父母處分未成年子女不動產的效力問題加以剖析。
一、判定是否維護未成年子女利益的標準
(一)司法現狀(見表1)
(二)檢討分析
根據《民法典》第35 條的規定,維護被監護人的利益是處分被監護人財產的前提條件,然而,判定監護人的處分行為是否維護了被監護人利益的統一標準尚未成形。筆者擇取了上訴四個司法實務中的典型案例,嘗試對較為普遍的爭議點做出剖析回應,并提出私以為合情合理的判斷標尺。
1.根據主觀表述還是客觀用途進行判斷
不難看出,案件1 和案件2 中的法官主要根據父母的主觀表述確定其處分目的,從而決斷其是否維護了被監護人之利益;而反觀案件3、案件4,法官更加重視憑客觀證據確定父母處分財產的用途,進而分析該處分行為是否是為了未成年子女的利益而發生。
雖然人們常言“虎毒尚且不食子”,父母對孩童的慈愛似乎與生俱來、理當如此。但另一方面,也恰是因為這樣的固化印象,父母對子女財產性利益的侵害才具有極強的內部性和隱蔽性。在現實世界中,也不乏父母以為子女治病或出國留學亟需資金為由,將子女房產出賣或設置抵押權后,取得資金卻用于個人投資或其他用途的情況。內在精神領域畢竟模糊且多變,甚至會存在當事人自身理不清自己心緒的情況,就更不可能以外部物理方法精準探究。因此,以父母處分財產的客觀用途判斷其是否維護了未成年子女的利益為宜,除非存在案件2中父母以公證書予以聲明保證的情況。
2.家庭利益與子女利益的關系
案件3 中的法官主張,父親抵押兒子房產,所獲貸款用于墊付其承接工程的資金,在某種意義上是為了改善家庭條件,給兒子創造更好的生活及受教育的機會,因此維護了未成年子女利益;而反觀案件4 中法官的說理,其認為父母抵押女兒房產的直接目的系自身取得借款,無證據證明維護了未成年子女的利益。
《民法典》第35 條規定,“監護人除為維護被監護人利益外,不得處分被監護人的財產”。拙見以為,首先需要明確的是,綜合考量未成年子女健康發展所需的種種要素,此處的“利益”不僅僅指被監護人的財產性利益,即財產的損益、負擔、風險等;還理應囊括被監護人的人身性利益,即保護未成年子女的生命健康、使其獲得悉心照料、接受優良教育等。后者其實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家庭經濟的正常運行和家庭氛圍的幸福和諧。因此,完全割裂子女利益和家庭利益殆不可能。但另一方面,同樣不能過于寬泛地將所有對父母有益之事統統納入維護未成年子女利益的范圍內,筆者將于下文闡述私以為公平合理的判斷標準。
3.具體判斷標準
若論及判斷監護人處分行為是否維護了被監護人利益的具體標準,首先應當指明的是,既不應以結果獲益反向推定處分行為有利于未成年子女,也不應以結果不利反向認定處分行為不利于未成年子女,而應以處分行為發生的時間為節點,考察父母處分該財產的客觀用途是否有益于維護未成年子女的利益。這是因為社會生活錯綜復雜、經濟情勢瞬息萬狀,若僅以結果為準繩進行判斷,沒有一對父母能確保自己的處分行為萬無一失,一定達成維護未成年子女利益的目的。換言之,以結果為標準將肇致監護人為規避承擔法律責任,一概拒絕處分被監護人之財產,《民法典》第35 條將喪失其存在意義。
其次,《現代漢語詞典》對“維護”的注解為“維持保護,使免于遭受破壞”。有鑒于此,筆者認為宜采用“父母為子女利益,有處分子女特有財產之必要時,始得處分”的標準。該“有處分之必要”又可被細分為兩種情形——其一,被監護人的利益已然受損或存在受損的現實危險,監護人為填平該損害或預防損害的將來發生,處分未成年子女之財產。如為支付未成年子女醫藥費而出賣其房產,或在未成年子女的不動產上設定抵押權擔保其本人之債務,抑或在家庭經濟狀況已然無法維系未成年人正常生活、接受教育的情況下出賣其房產。其二,處分行為對被監護人的利益有所增益,例如不動產賤買貴賣,抑或在未成年人需要出國深造前變賣其名下房產。但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該收益的獲得不得以被監護人的財產處于高風險中為代價,如將未成年子女的房產用于其父母或第三人的經營融資,即便未成年人可能從中受益,但大額虧損亦如影隨形。
二、非為維護被監護人利益所做出的處分行為的效力
《民法典》第35 條規定,“監護人除為維護被監護人利益外,不得處分被監護人的財產。”由此觀之,監護人為了維護被監護人的利益而做出的處分行為當然有效。然而,就監護人非為維護被監護人利益所做出的處分行為的效力,法律既未明確肯定亦未直接否定,仍屬立法空白。
(一)認定處分行為無效的裁判理由
1.《民法典》第35 條系禁止性規定
部分法院主張,《民法典》第35 條屬于禁止性規定,職此之由,父母非為維護被監護人利益處分其財產,與第三人簽訂的合同無效。禁止性規定,一般指《民法典》第153 條所寫明的“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但進一步深究,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的《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14條,只有“效力性強制規定”方才必然導致合同無效。根據《民商事合同案件指導意見》第16 條的劃定,效力性強制規定規制的是合同行為本身,且該合同行為一旦發生,將絕對地損害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
事實上,《民法典》第35 條雖然有“不得”之表述,但其本質為“管理性強制規定”——規制目的在于給監護人提供一個指引、標準和告誡,涉及的主要是被監護人之利益,而非國家利益或社會公共利益。因此,以《民法典》第35 條系禁止性規定為由,否認父母非為維護未成年子女利益而訂立的合同的效力,殊難贊同。
2.無權處分
司法實務中的部分判決認為,《民法典》第35 條本質上是對監護人的處分權作出了范圍限制,是以,父母非為維護未成年子女利益處置其財產屬于無權處分。首先,細究無權處分的構成要件,行為人必須以自己的名義實施處分行為,因無權處分而訂立的合同的當事人系行為人和相對人,而非真正的權利人。
其次,反觀具體實踐情形,監護人往往以被監護人的代理人的名義實施處分行為。另一方面,即使監護人以自己的名義訂立了合同,鑒于物權的公示公信原則,第三人仍知道或應當知道該不動產的真正所有人系被監護人。在此情況下,即便被監護人并未在合同上簽字,第三人卻實際知曉并認可了父母的處分系代理行為。由此,探知雙方當事人的內心真意,也應當判定屬于監護人代理被監護人處分其房產的情形。簡言之,父母以自己的名義處分未成年子女房產缺乏現實可能性,以無權處分為由,否認父母非為維護未成年子女利益而訂立的合同的效力,難謂妥當。
3.無權代理
也有部分法官主張,若父母非為維護未成年子女利益而與第三人簽訂合同,其行為構成無權代理,因被監護人成年后未予追認而無效。根據《民法典》第171 條的規定,狹義的無權代理囊括自始無權代理、超越代理權、代理權終止三種情形。父母直接基于法律規定而取得代理權,那么,其違反《民法典》第35 條的行為可謂突破了代理權之限制,屬于較為典型的超越代理權的情況。該觀點源自法條、邏輯自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且很好庇護了未成年子女的利益。
(二)認定處分行為有效的裁判理由
1.父母無償贈與的房產系家庭共有財產,其有權處分
長久以來,針對父母無償贈與的財產屬于家庭共有財產還是未成年子女的特有財產,司法界和理論界可謂聚訟紛紜。主張前者如賀珠明與姚明春、王雲軒民間借貸糾紛一案,簡言之,法院主要理由如下:(一)父母出資。一般情況下,不動產權屬證書的登記權利人推定為實際權利人,但有證據證明購房款實際出資人不是登記權利人時,需要根據實際出資情況確定房屋歸屬;(二)父母控制經營。房屋一直由王永權、姚明春夫妻用于經營,明顯超出王雲軒的基本生活需要。
針對上述觀點,筆者認為父母無償贈與的房產系未成年子女的特有財產,緣由如下:首先,若承認他人贈與未成年人的房產是個人所有,而父母贈與未成年人的房產卻隸屬家庭共有,將肇致贈與的法律后果因贈與人的不同而改變,著實缺乏法律依據。其次,《民法典》第34 條寫明,“監護人的職責是……保護被監護人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以及其他合法權益等。”由此觀之,維持未成年子女財產的使用價值和價值本就是父母負有的法定義務,不能因其履行了管理職責就判定父母是贈與財產的實際所有人。再次,法院傾向于將無償贈與的房產歸于家庭財產,其背后的核心意圖在于防止假借贈與房屋之名,行逃避債務之實。債務人是否是為轉移資產而將房屋登記在未成年子女名下或進行過戶,一般可以通過借款時間和購房時間或辦理過戶手續時間的先后進行判斷。如果贈與行為發生于債權之后,或有證據證明因“債權發生的可能性非常高,為了逃避將來會發生的債務的履行”,父母事先將房屋贈與未成年子女的,宜通過《民法典》第539 條規定的債權人撤銷權制度進行救濟,而非一概為了保護債權人利益,粗暴地將父母無償贈與未成年子女的房產定性為家庭財產。
2.不違反法律的禁止性規定
該觀點近年來為各大法院所廣泛采納,主張既然《民法典》第35 條并非禁止性規定,那么,父母非為維護被監護人利益處分其財產,與第三人簽訂的合同仍然有效。至于案涉房屋買賣合同損害了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則可另案主張監護人承擔侵權損害賠償責任,但并不影響原合同的效力。不難看出,此見解的中心思想系首要保護第三人的交易安全,重視市場交易秩序的維穩。
(三)筆者愚見
盡管在法理層面,“無權代理說”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采用該觀點的實際法律后果卻不甚樂觀。家庭具有封閉性、隱秘性,交易第三人作為外人,很難也沒有義務去判斷父母的處分行為是否維護了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因此,若適用“無權代理說”,其一旦與父母簽訂處分未成年人財產的合同,就需要面臨以下風險:首先,極可能需要等到子女成年后方可追認合同效力。該時間跨度長達幾年甚至十幾年,法律關系長期處于不確定、不穩定的狀態,容易衍化新的復雜矛盾。其次,即便第三人及時行使了撤銷權,但事實上,他已經付出了時間成本、機會成本乃至訴訟成本,卻沒有達到交易目的。長此以往,整個社會將極度不信任未成年子女名下的房產交易,在未成年人確因罹患重病、出國學習等亟需資金時,其名下的不動產難以發揮應有的融資功能。
事實上,探究父母處分未成年子女不動產效力的本質,是意圖在捍衛未成人利益和保護第三人交易安全中找尋一個不偏不倚的平衡點。從這個角度出發,王澤鑒先生的觀點比較折中——根據處分行為的性質,確定父母非為子女利益的財產處分行為的效力:如屬無償行為,應為無效;反之如屬有償性行為,應為有效。依此原則,當父母非為未成年子女利益無償處分其財產時,相對人取得極大利益卻并未支付對價,即使該處分行為無效,相對人亦無太大虧損。在此情況下,法律應側重保護未成年人的利益,判定父母的處分行為無效。相反,當父母非為未成年子女利益而有償處分其財產時,鑒于相對人支付相應對價后方才取得利益,若仍認為處分行為無效,對相對人顯失公平。因此,此時法律應偏重維護交易安全,認定處分行為有效。
三、小結
綜上所述,針對父母處分未成年子女不動產的效力問題,筆者以為,首先需要判斷處分行為是否維護了未成年人的利益,具體標準系“父母為子女利益,有處分子女特有財產之必要時,始得處分”。父母為維護未成年子女利益而做出的處分行為當然有效,而論及非為維護未成年人利益所做出的處分行為的效力,則需要具體考察處分行為的性質,若屬無償行為,處分無效,如是有償行為,處分有效。
就筆者個人感受而言,父母處分未成年子女不動產的效力確是一個龐雜、難解的論題。正如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朱廣新所言,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民法總則》第35 條第1 款第二句實質上是將具有監護監督屬性的法院決定權 (即批準權)后置并轉換成了一種司法裁判權。對當事人而言,它實際上是把非訟事件變成了一種訴訟事件。這種立法體例對問題的處理明顯有些極端與僵化,不利于對被監護人和交易相對人的保護。”理固宜然,筆者在此不揣淺陋,提議參酌中國臺灣地區民法第1101 條第2、3 款的規定,對監護人處分被監護人某些重要財產尤其是不動產的行為,作出非經法院許可不生效力的特別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