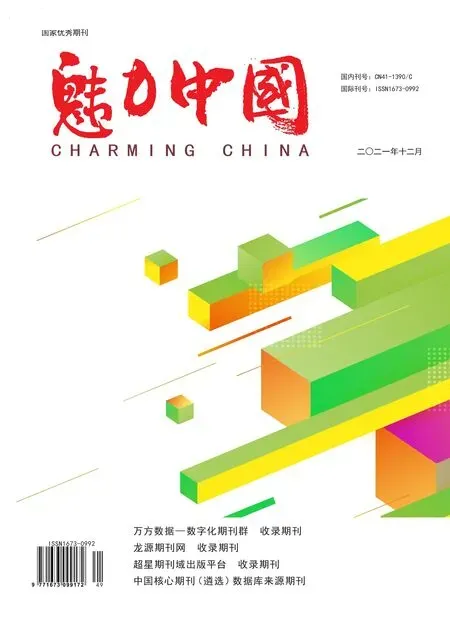美聲唱法歌唱技巧與巴彥淖爾草原歌曲演唱方法的融合
王璐
(河套學院藝術系,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0)
一、美聲唱法氣息與巴彥淖爾草原歌曲氣息的融合
美聲唱法對于演唱者的要求比較高,尤其是對表演者氣息的要求程度更高,因此,在日常的發聲訓練中要加強演唱者對于歌唱氣息的控制。有了氣息,唱歌就有了支撐力。美聲演唱中的呼吸和生活中的呼吸是很相近的,但又有著巨大的差別。美聲唱法的歌唱氣息比正常說話更低沉、更靈活。我們唱歌中所運用的氣息是要依據一首曲目所包含內容的需求從而變化的使用,最重要的是有技術性的呼吸方式。唱歌有了呼吸的幫助,便能擴大歌曲的影響力。美聲唱法演唱者只有具備了科學的呼吸方式便能輕松自如的進行呼吸活動。
內蒙古巴彥淖爾地域蘊藏著富饒的民族特色與草原藝術特色的歌曲,繼承并弘揚了蒙古族一直以來都有的草原游牧文化,它是一種巨大的財富。婉轉而不失深沉情境的音調在巴彥淖爾這片土地上流傳,大家以它來歌唱祖國、祝福家鄉、歌頌大自然,從而表明人民內心深處的豐富情感,這種獨一無二的藝術感染力也成為了蒙古族音樂文化研習的關鍵內容,更是巴彥淖爾音樂藝術文化魅力所在。
在歌唱草原歌曲中,呼吸方式非常類似,筆者在采風中親眼所見、親耳聽到巴彥淖爾地區草原歌者所演唱的草原歌曲,表情豐富夸張,對于不同主題的歌曲,歌唱者感情深切,情感油然而生,高亢有勁的高音區,深沉雄厚的中低音區,特別有魅力。由此看來,高低起伏,婉轉動聽的草原歌曲不但具有北方游牧民族特殊的藝術感染力,更為關鍵的是采用了技術性的腹式呼吸方法,從而可以讓人在展示唱歌時得到一種莫大的支持力,蒼茫大草原,聲音不僅可以向遠方傳去,還可以發出悅耳動聽的美妙歌聲。
在美聲唱法歌唱實踐當中,肺部吸氣飽滿而深沉,橫膈膜下降,呼吸通道得以充分的打開。歌唱的聲音與之流動起來,而美聲唱法中,最不可或缺的就是歌唱者有氣息的支持力。不同風格類型的作品中,還要求歌唱者自身氣息運動的協作能力,保證歌者演唱技巧與藝術表現力,以達到凸顯不同風格特征的目的。
草原歌曲演唱當中比較重視氣息與情感的結合,強調咬字吐字的的作用,其中氣息要吸到腰腹四周,保持肋間肌的擴張。演唱過程中氣息與字的密切配合至關重要。不能過分強調字的作用否則會導致氣息的絕對下沉,損失其自由靈活性,呼吸器官也很難達到協調配合。草原歌曲與美聲唱法的呼吸方法的融合可以使歌唱呼吸器官增強其全面的能動作用。兩者結合之后,不但訓練出來的聲音可以增強草原歌曲的生命力,而且減少演唱者對于聲帶的損傷,使巴彥淖爾歌者的歌唱演繹道路變得更加寬闊。
二、美聲唱法發聲原理與巴彥淖爾草原歌曲發聲原理的融合
歌唱的發聲原理是美聲唱法中又一重要因素。聲帶是發聲器官的主要組成部分,位于喉腔中部,由聲帶肌、聲帶韌帶和粘膜三部分組成,左右對稱。氣息通過閉合的聲帶引起聲帶振動,氣息沖擊聲帶的速度和力度都會對聲帶產生不同的作用力,使之發出的聲音大小、高低、音色都會大不相同。
美聲唱法在真假聲的轉換中有很高的要求,真聲帶動全部聲帶振動,進而引起共鳴,其發音的音色與歌者平時說話的音色基本相同。假聲是指演唱時通過有意識的控制而只使部分聲帶發生振動所發出來的聲音。在美聲唱法中,我們強調的是真聲和假聲的結合,在高音區和中低音區中,在真假聲混合上統一化。真假聲的混合可以擴展歌手的發聲音域,不僅讓歌手發出圓潤通暢的聲音,嗓子也不會感到不適。美聲唱法的真假聲結合的聲樂藝術處理方法,不僅提高了歌手的聲音表現能力,而且可以使音域更寬廣、聲音更加飽滿而富有感染力。而對于喉嚨狀態方面,在美聲唱法中有著嚴格的要求,喉嚨要保持張開,像剛要“打哈欠”一樣,這樣喉頭才能保持穩定。美聲唱法歌唱家的聲音具有很強的穿透力,這與歌唱家各個發聲器官的協調運用是密切相關的。演唱時打開喉嚨并且利用“貼著咽壁吸著唱”的感覺,不僅可以使歌手的喉頭穩定,還可以輕松自如的打開喉嚨。
巴彥淖爾地區草原歌曲中烏拉特民歌的發聲狀態比較注重喉嚨的打開,在演唱過程中,聲音集中到眉心,喉頭隨著不同聲區則穩定放松,使很多歌者可以自如運用真假聲的轉換。演唱烏拉特民歌的演員有的雖已年過七旬,但是婉轉舒展的音色依然能夠維持至今,大多數歌者沒有受過非常專業的聲樂訓練,她們的學習方式多為口口相傳,在世世代代傳承中不斷完善,最終形成自己獨有的藝術特色。草原歌曲沒有科學完善的發聲系統,傳承方式多是“口傳心授”,她們雖然平時日常生活中經常唱歌,但是對于科學的發聲方法和原理很少運用到演唱中。雖然烏拉特民歌中加入的裝飾音、起音、倚音的演唱技巧能使歌曲的民族韻味濃厚,但是演唱者的喉部使用頻率過多,對于聲帶的長期保護有著阻礙的作用。
倘若在草原歌曲演唱方法的發聲方式上,咽喉器官能夠放松,在真聲中混入一部分假聲,演唱者能歌唱的更加輕松,也使得發聲器官得到更好的保護,美聲唱法更細致于發聲的技巧和位置。但在演唱過程中相較于草原歌曲對情感的理解略有遜色,所以美聲唱法可以在保持原有優點之外,可以吸取草原歌曲的情感表達方式,讓美聲歌唱變得更富有感染力。所以,美聲唱法和草原歌曲的演唱方法,在聲樂藝術領域各有千秋,彼此之間取長補短能促進提高民族聲樂的長久發展,草原歌曲可參照美聲唱法體系完整的發聲方式,巧妙的使用在本身的歌唱表現中,逐步可以使草原歌曲的發聲模式更加健全,相較于美聲歌曲而言,偏向純真聲歌唱,這會使演唱者的發聲器官變得勞累甚至老化速度加快。如果參考美聲唱法的發聲模式,在氣息和腔體等方面同時作用下依據實際情況的使用假聲,不但能保護演唱者的發聲器官,還能提高演唱者對自身演唱能力的控制。
三、美聲唱法共鳴腔體與草原歌曲共鳴腔體實踐運用的融合
人體有口腔、鼻竇、頭部和胸部的共振即口咽腔共鳴、鼻腔共鳴、頭腔共鳴、胸腔共鳴,而音高不同所產生的共振聲音也有所不同,整體音色和局部音色也是有差距的,說話的人通常是沒有共鳴的,一旦使用了共鳴,音色就會與之前大不相同。
在唱歌過程中,單獨使用一個器官會導致音色不統一化。如果唱歌的人單獨使用口咽腔共鳴,則發出的聲音都是真實的聲音,聲音聽上去是實實在在的過于平直,時間稍長便會感覺嗓子累。若單獨使用鼻腔共鳴,聲音不流暢,音調聽起來不悅耳,發出的聲音會不清晰,鼻音過于重會有礙唱歌的發揮。若單獨使用頭腔共鳴,發出的聲音全是假聲會感到虛假,而長期使用假聲唱歌,會嗓子擠卡并導致聲帶受傷。若單獨使用胸腔共鳴,聲波的震動會落到咽喉里去,產生的效果會聲音很低沉,不流暢。而美聲唱法是將口腔共鳴、鼻腔共鳴、頭腔共鳴、胸腔共鳴集于一體。并根據聲音高度的變化,適當的調整不同共鳴腔的比例。在演唱草原歌曲時,一定要具備一定的音量,而音量的大小取決于共鳴腔的應用。古人稱贊傳統的草原歌曲“其聲音洪大,隔七嶺尤聞之”,用極其夸張的語言來描繪草原歌曲的超強穿透力,這也表明草原歌手有著非常不錯的聲音共鳴。
共鳴腔體的特殊運用是傳統草原歌曲聲樂藝術重要的表現手段,優質的音色,音量的把控,極其強烈的穿透力無一不突顯著傳統草原音樂藝術歌曲那特殊的共鳴腔體,這與美聲唱法的呼吸運用有著截然不同之處。草原歌曲演唱高音時口型稍扁,聲音在氣息的支持下直接通過口腔前面硬口蓋穿過鼻腔進入頭腔產生共鳴。美聲唱法的共鳴是整體共鳴,口型是立著的,口腔內部打開,聲音在氣息的支持下通過后咽壁的軟口蓋上去后呈投射狀打出來。兩者各有特點,取其精華使其融合可以使我們的傳統草原歌曲煥發出新的光芒,美聲唱法是科學系統的,其整體共鳴理論使得美聲唱法的歌唱音色更加豐滿并且解決了換聲區的問題。
假若傳統草原歌曲可以取其精華并且根據自身特點添加運用美聲唱法的整體共鳴,以口咽腔共鳴為主,腔體不需要開的太大,喉頭的位置不可以太低,發聲共鳴集中于頭腔,胸腔共鳴起到輔助作用。這樣吸收到美聲的科學唱法,在演唱時可以更加圓潤、立體、通暢還能保持自身的特點,使演唱者在演唱草原歌曲時更能突現出自身的嗓音音色,使其更加具有藝術魅力,從而得到更長遠的發展 。
結論
總而言之,美聲唱法雖然有科學的呼吸方法、發聲理念、腔體共振原理以及豎式化的歌唱語言等一套科學歌唱發聲系統,但也需要演唱者擁有自身對歌唱的理解,才能更好的去完成作品,不去深層次理解歌曲內涵的演唱者是不會有長遠發展的。巴彥淖爾地區的本土草原歌曲給人感覺溫暖、柔和、還飽含著熱烈的情感,但是演唱者在轉換腔體的使用時不夠流暢,是本土音樂無法走出地區的主要因素之一。此外,演唱者對自身發聲器官的保護相比美聲唱法也稍有遜色,這也給演唱者對聲樂的研習和表演帶來更大的困擾。而美聲唱法與巴彥淖爾草原歌曲演唱技巧的結合,能以兩者的優點填補雙方的空缺,是聲樂中極為巧妙的交融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兩者的磨合將會是艱難而漫長的,它是歷史的必然產物,也會是被大眾所認可的,能被世人所接受的更優秀的歌唱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