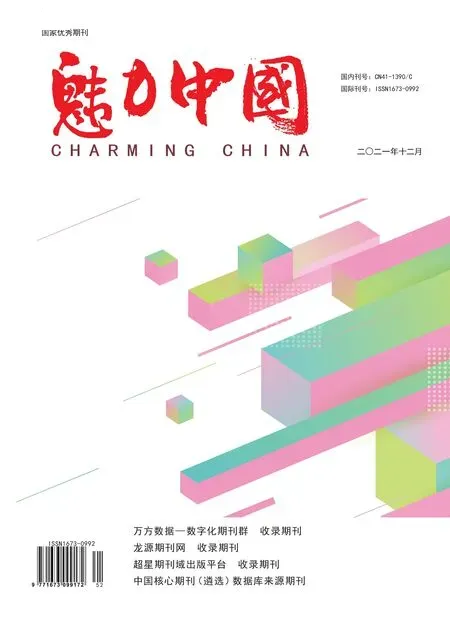海德格爾與杜威技術哲學思想比較
賈思宇
(黑龍江大學,黑龍江 哈爾濱 150000)
引言
作為實用主義者的杜威和存在主義者的海德格爾,雖然處在不同的領域,但是他們都關注技術,并且使技術成為構成其哲學的重要要素。在海德格爾哲學早期的基礎存在論中,雖然沒有提到技術,但是技術在此在對存在者的解蔽,在此在的時間性的展現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到了晚期海德格爾更是提出一系列的專業術語來解釋技術發生的問題。而杜威從早期就對技術有著濃厚的興趣,他的技術思想體現在其實用主義工具論的各個方面,只是很晚才被人們關注。
一、海德格爾與杜威對技術關注的原因
(一)時代影響
一直以來,人們對哲學家都有著這樣的誤解,認為他們只關注一些遠離世俗的,普遍的,中立性的術語,但是哲學家所處的時代必定對其思想產生影響。杜威所處的時代,被描述為機器時代,這一時代產生了許多技術人工物,這使杜威對這些技術人工物產生思考,研究它們如何對我們的經驗和認知發生影響。雖然海德格爾對技術的闡釋是脫離現世的,追溯古希臘,還受到了中國傳統老莊“道”的影響,但是他的這套學說也是在社會環境的影響下產生的。
(二)哲學發展的影響
兩者對技術的關注不僅受到社會的影響,還來源于他們對哲學發展路徑的探索,形而上學在黑格爾哲學體系中發展到極致,現代哲學家對形而上學繼續發展的可能性進行反思,并通過對傳統哲學的批判,提出新的學說[1-2]。
二、海德格爾與杜威技術哲學思想的共同思想路徑
(一)對傳統哲學的批判
兩者對于傳統哲學的批判角度相同:兩者都對傳統哲學的同一方面進行了批判,但是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闡述。
兩者都對古代哲學中沉思與活動的二分進行批判。杜威認為古代人們追求沉思生活是為了在思想中把握確定性來逃避現實生活中的危險,他是從自然環境的因果論的角度闡述的。而海德格爾認為古代哲學崇尚存在是因為他們只是關注無變化的、確定的存在,而忽視動態的存在過程。而這是由命運決定的,與人對自然的交互作用無關。
兩者都對笛卡爾式的主體的形而上學進行批判。在《存在與時間》中,海德格爾在解構存在論歷史任務中對其進行批判,批判傳統存在論將存在限制在認識論的維度,忽略了存在的時間性,在《經驗與自然》中,杜威也反對這種主體性的形而上學導致我們只把對象局限于認識的對象。
(二)對歷史性和情境的重視
兩者對傳統哲學相似的批判角度,導致它們在構建自己學說的過程中,運用到了相同的要素。傳統哲學局限于認識論中,而技術成了我們打破傳統哲學的壁壘,并使兩者的哲學都關注到了歷史性和情境。這是對傳統時空觀的改造。傳統的時空觀都局限于形而上學的意義,都是從對象的角度進行把握,被當作是不言而喻的,海德格爾和杜威都認識到歷史性和背景視域的重要性。海德格爾的基礎存在論中,時間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此存在的狀態不是從一個絕對的命題中推出的,在此時間中展現出自己的狀態。“我們必須把時間擺明為對存在的一切領會及解釋的視野。”而歷史性就是此在本身的時間性的存在方式。“歷史性就意指這樣一種此在的演歷的存在的構建。”所以此在存在總是由過去的一些因素在起作用,并且指引著此在將來存在的方向。此在就是在這種歷史的過程中領會著他的可能性并展現著他的可能性。
杜威也十分強調歷史的因素。比如其對習慣的闡釋,每個人都有習慣,人們的活動都受到了之前活動的影響。習慣不只是僵化地包含著過去的動作,它還含有對于未來可能的變化的預測。此外習慣不是固定不變的,人類能形成習慣,他就會與周圍世界不斷發生聯系,在相互作用中,人類會發生很多變化,就會在舊的習慣中產生新的因素,并且這是一個不斷前進發展的過程,因為人類學習的越多,與環境交互作用越多,“即指在一個歷史過程中前面各項在目前的階段上愈多地被保持下來和統一起來—為了使它本身繼續下去就愈需要學習,否則,它就會死亡和毀滅。”對于意義的活動方面,過去活動的意義對現在活動的意義具有影響。
(三)對意義價值的闡述
同時在對意義的闡述上,兩者也具有相似性。在古代哲學中,意義是與靜觀相連的,事物的意義完全是從認識論中獲得的。但是海德格爾和杜威都認為事物的意義是在活動中展現的。并且都認為存在一個包含一切意義的整體。杜威將心靈概念進行改造,認為“心靈系指那些體現在有機生活的功能中的意義整個體系而言。”作為包含一切意義的體系心靈是隱秘不顯現的。它是關聯一切的,可以作為恒常的背景;而與心靈相對的概念是意識,意識是存在于一個特定時間中的,是局部的,非連續的。杜威舉了讀書的例子來闡述心靈與意識的關系。當我們讀一本書時,會意識到許多意義,這些意義都是來源于一個在有機活動中形成的完整的意義體系即心靈,只是我們沒有認識到。這與海德格爾所說的,此在的一切存在的可能性都是作為一個整體在先存在的,通過此在與存在物打交道顯現出一部分存在狀態有異曲同工之妙[3-4]。
三、海德格爾與杜威技術哲學思想不同的意義
雖然海德格爾和杜威在學說中有相似之處,都想通過對之前哲學的批判,提出一些新的東西。并且他們各自的新學說中也有相似的角度,但是不可否認兩者對技術問題的分析中還是有很大差異的。海德格爾的技術哲學思想明顯具有一種悲劇色彩,而在他在晚年形成的神秘主義,不是偶然,而是受到了希臘-德國浪漫主義以及末世神話論的影響。而美國哲學家杜威,由于沒有過于受到德國浪漫主義的影響,廣泛關注公共事務,被稱為負責任的哲學家。
(一)羅蒂對兩者的比較
理查德·羅蒂最初在《實用主義哲學》中最先對海德格爾和杜威進行了比較。
羅蒂認為海德格爾和杜威都認為傳統哲學耗盡了自己的一切可能性,并在此基礎上發展自己的哲學。杜威認為傳統哲學耗盡一切可能性后,只剩下對具體的存在者的思考。海德格爾認為形而上學思考毀滅后,是為存在留下位置,海德格爾仍試圖在思、詩中尋找答案。
羅蒂認為杜威在對傳統哲學的改造過程中,完全拋棄了傳統哲學,通過哲學向科學轉向來模糊一切學科的界限,他采取了一種工具論的態度,在日常世界的交互作用中發展自己的學說。海德格爾認為,我們可以在與傳統存在論相對立的思想中繼續發展哲學,他脫離了現實的問題而轉向思,他對“思”的留存體現了他對傳統哲學的依戀。
如果從杜威的角度看海德格爾,會認為海德格爾逃避了現實的責任,但如果從海德格爾的角度看杜威,也會出現一些問題。海德格爾把技術問題看作“世界圖像”中的一環,而杜威對實存的自然物的改造,只是一種現實主義態度。而杜威的人道主義只是時代的產物,他完全沒有從現代環境中抽離出來。
(二)約瑟夫·馬戈利斯對羅蒂的批判
在約瑟夫·馬戈利斯的杜威與歐陸哲學對話一文中,對羅蒂的文章進行了批判,認為其解釋全然不對。羅蒂對兩者的闡述,是為了給他自己的哲學提供合法性。在羅蒂的闡述中,杜威被歸為一種世界觀的哲學,而海德格爾是從脫離世界觀的角度進行闡述。
在馬戈利斯看來,兩者都認識到哲學是世界觀的哲學,只是對哲學的世界觀的把握不同,海德格爾認為世界觀雖然伴隨著此存在而產生,總是在特定的場合內并且與人的實際活動相關,但是哲學的世界觀是與這種普遍的世界觀不同的。“哲學的世界觀必須是這樣的世界觀,它必須由哲學明白地、清晰地、或者無論如何突出地得出來或顯示出來,也就是說,通過理論化的思索,排除對世界和此在藝術和信仰的解釋。”杜威與歐陸哲學的對話,由此可見,杜威受到生物學,進化論的影響,批判傳統哲學中空洞的世界概念,而指向一種普遍的,人類活動的世界觀,而海德格爾仍是在德國古典哲學的影響下,指向與科學信仰相區分的,哲學的世界觀。這是導致兩者立場不同的原因。
羅蒂在比較的文章中更傾向于杜威,認為杜威徹底拜托了傳統哲學并直接轉向日常世界,但是事實上,兩者都沒有徹底擺脫傳統哲學。他們肯定哲學繼續發展的可能性,因為他們都重申了真理、善等問題。但是羅蒂堅持認為重申這些問題是沒有意義的,認為日常世界就意味著哲學已經窮盡其一切可能性。
四、兩者的相似性和不同性的根源
我們之所以人為杜威與海德格爾的技術哲學思想具有相似性,是因為兩者的學說中都蘊含著一種不確定的情境,這種不確定情境的產生方式不同,導致兩者學說的差異。
在杜威的技術哲學中,我們能很明顯地看到一不穩定不確定的情境,杜威的探究邏輯就是在這種不確定的情境的需要下建立起來的。所以雖然杜威受到了黑格爾的歷史哲學的影響,但是杜威明確地反對黑格爾,他是從進化論的角度,將黑格爾的學說生物學化了。這種問題情境導致了杜威對二元論的批判,以有機體的交互作用活動為中心,并處于不斷變化的探索的技術哲學思想的產生[5-6]。
在海德格爾的技術哲學中,去蔽的活動體現了一種不確定的情境。而這種不確定的情境是在對傳統真理符合論的批判下形成的。海德格爾通過去蔽來反對真理符合論。去蔽使海德格爾保留了現象學方法的優先權,破除了現象學的推理角色,通過其存在論的方式來重新定義真理。為了使去蔽活動可能實現,海德格爾不得不設置一個產生去蔽活動的“此在”,但是如果這個此在仍是具有實體性的將毫無意義的。為了破除“此在”的實體性,海德格爾不得不使此在的去蔽活動在一個情境中產生。“人們現在將會預見到,海德格爾將不得不通過提供它們‘在先的’,‘存在論’的同形物‘復制’‘在自然中所識別的一切’”由此,才能使此在對存在的去蔽關系在擺脫形而上學的意義上得到實現。所以整體來看,海德格爾的存在論,包括其對技術哲學的闡釋,都是在傳統哲學的基礎上建立的。
因此,海德格爾和杜威的技術哲學思想都巧妙地運用了不確定情境,對不確定情境的闡述方式不同,導致兩者學說內容的不同。
五、結論
綜上,對海德格爾和杜威的技術哲學思想的分析,不僅為現代技術問題的認識和解決提供了參照,兩者的比較使我們加深了對現象學和實用主義哲學的認識。不確定情境是分析兩者學說的切入點,杜威受到生物進化論的影響,從危險的、不確定環境出發,來構建具有生產性的,探究性的實用主義哲學。海德格爾受到古希臘哲學的影響發掘技術的去蔽含義,去蔽,連接著此在與存在物,為了消解此在的實體性,不得不將去蔽活動設置在情境中。兩者對情境的共同關注和不同闡述使我們更好地把握現代西方哲學中,存在主義哲學和實用主義哲學的發展路徑[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