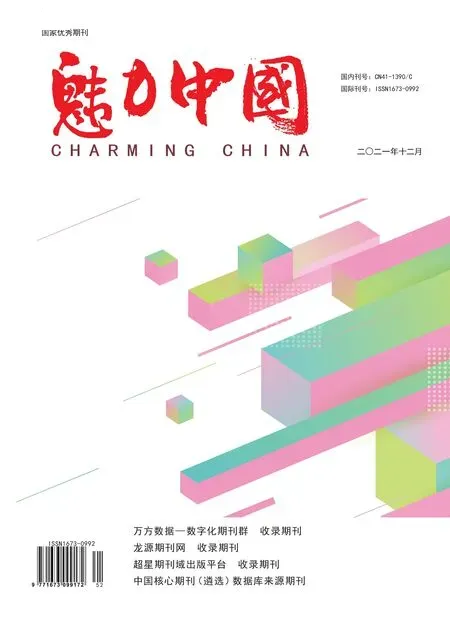關于網絡環境中版權制度的發展研究
孟靚
(中國政法大學,北京 100000)
網絡信息技術的發展在給人們提供互聯網帶來便利的同時,也衍生出了較多的負面問題,目前版權的問題是網絡環境下比較突出的法律問題。這是因為網絡環境中的“共享”概念和版權的“專有”概念碰撞之后極易引發網絡環境中的版權侵權和版權保護問題。網絡環境強調了“知識經濟”,也展現了“信息爆炸”,但是卻給現行法律和管理秩序帶來了不小的挑戰。尤其是網絡環境中不斷更迭的網絡技術對于有著作權的作品能夠實現完美復制、快速傳播、低廉使用,強烈沖擊了版權保護體系。因此,探索網絡環境中版權制度的發展,成為保護版權人正當權益和版權制度完善的重要途徑。
一、網絡環境中版權制度的發展機遇
網絡環境實質上是推動了版權制度的順勢而為,也引領了各行各業版權意識的提升,并在現有版權制度的大體框架之下根據網絡環境以及各行各業的市場規律明確了相應的規范性行為、平衡了各方的利益。這樣,網絡環境中的版權制度發展就融合了高新技術產業、文化娛樂產業、制作業等各行各業的具體內容,逐步朝著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方向和維護版權人利益的目的發展。
版權制度的法律內涵和目的是讓獲取版權保護的作品具有“原創性”和“獨創性”,促進各行各業的創新性發展。而且,從法律角度和文化發展角度來看,文化作品的發展其實離不開“前人栽樹后人乘涼”這一趨勢。所以,法律層面也允許文學作品創作過程中可以進行適當借鑒和應用,且需要標注出引用來源,并在適當引用或者借鑒限度內。網絡環境中,信息產業、文化產業、媒體產業以及制造產業都是在相互交融和相互促進的過程中發展的。所以,網絡環境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版權制度對于相關產業發展推進,并促進了優秀作品的傳播。而且,各行業的相互交融和發展以及網絡環境的構建過程,也為版權制度提供了發展的思路。
二、網絡環境中版權制度發展遭遇的挑戰
(一)網絡侵權影響嚴重化
網絡環境之下,數字技術、傳播技術和信息技術持續發展,但是隨之而來的是利用高新數字技術、新型傳播技術以及高新信息技術等實施的版權侵權行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戰。這是因為網絡環境之中,信息的傳播過程不再如同傳統信息傳遞過程需要依托物質作為載體進行,網絡用戶只需要在互聯網中通過搜索引擎進行相關作品或者信息的搜索即可“按需”進行獲取,這就造成侵權作品的傳播速度和傳播范圍大大提高,侵權影響日益嚴重化。比如,某些音樂作品、攝影作品、電影作品或者電視劇作品一經上市,網絡用戶通過一些不法網站就可以找到相應的資源進行下載。
(二)版權侵犯情況普遍化
相較之而言,傳統侵權行為的實現在作品復制和傳播過程中技術條件不成熟,人力成本和物力成本極高。例如,盜版書籍或者盜版音像制品的復制過程中,最開始是通過刻錄、翻拍、翻錄、印刷、復印的形式進行,需要專業的機器設備、大量媒介物質材料、固定的生產場地等;盜版書籍或者盜版音像制品的傳播更為復雜,不僅需要銷售場所、銷售渠道,還需要解決相應的物流運輸和倉儲等問題。所以,在網絡環境成熟以前,物質條件、技術條件使得版權侵犯的情況相對較少,損害版權人的行為大多出現在一些具備經濟實力和固定經營場所的人群中,且他們都是比較職業化和專業化的。
網絡環境成熟,數字技術和傳播通信技術的發展徹底將這一局面打破。作品被賦予“數字化”屬性之后,幾乎任何一個能夠操作計算機和使用網絡的人都可以簡單粗暴的進行數字化作品的“復制粘貼”,且這種“復制粘貼”的侵權行為不僅質量高,且成本幾乎為零。而且,在完成“復制粘貼”侵權行為之后,網絡用戶又可以零成本將數字化作品上傳共享到網站中或者傳播給其他網絡用戶。這樣,原作者的作品復制件在網絡之中就泛濫起來。所以,盜版者或者侵權者從傳統的“職業化”走向了“普遍化”,版權侵犯情況也就普遍化起來,侵權行為和侵權作品的數量急速攀升,造成的不良影響和后果日益嚴重,傳統版權制度挑戰日益加大。
(三)侵權執法難度擴大化
傳統環境下的侵權行為因為有著固定的場所、設備和侵權物品銷售環節等,所以在侵權者相關侵權責任追究和侵權經濟賠償的處理上相對比較容易。但是,隨著侵權影響趨于嚴重化和侵權行為轉向普遍化,網絡環境中的侵權執法難度逐漸擴大化。尤其是網絡環境實際上屬于一個虛擬環境,所以通過網絡技術或者信息技術實施侵權行為的人群往往不具備經濟賠償能力、侵權行為沒有盈利目的、侵權人年齡小,侵權發生地域較為分散。在網絡環境中逐一找尋侵權人并對其進行法律責任追究,不僅需要網絡安全部門、法律部門、工商管理部門、文化執法部門的協同,還需要網絡技術專家和信息技術專家的配合。所以,侵權執法不僅費時費力,且在版權人侵權經濟補償的追回上很難實現。
(四)“自媒體”時代創作業余化,版權制度覆蓋難
在網絡環境尚未成形以前,作品創作或者技術創作都是呈現“專業化”發展態勢,即通過專業創作者完成作品創作,并將作品交由專業的出版機構或者出版單位。無論是專業創作者還是版權出版機構、出版單位等都具有較強的版權意識,在進行版權制度落實和版權維護過程往往比較容易實現。尤其是依托于出版機構或者出版單位,公眾以及其他社會組織在合理利用版權作品的過程中可以聯系到對應版權人,在相應的版權使用規范條例或者合同之下,侵權行為不易發生。但是網絡環境中數字化技術和信息化技術發展使得“自媒體”時代應運而生,人人都是“媒體”的概念讓作品創作泛濫起來。
三、網絡環境中版權制度的國內外發展趨勢
(一)網絡環境中版權制度的國外發展趨勢
自上世紀末網絡環境加速發展和逐漸趨于成型以來,國外發達國家就針對網絡環境中的版權制度就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并通過版權保護機制完善、版權立法修改、市場交易機制創新等推動了版權制度的發展,也促進了版權相關產業的發展。例如,美國通過立法將“盈利為目的的網絡作品傳播行為”定義為了刑事犯罪,并將“發行權”“展示權”以及“表演權”納入了版權制度體系之中;澳大利亞把“向公眾網絡在線提供作品權”納入版權制度。與此同時,對于通過網絡環境實施侵權行為造成的影響嚴重化、執法難度擴大化、侵權情況普遍化、版權保護覆蓋范圍低等情況,也在逐步實施版權制度保護機制的改善。
其次,國外在網絡環境中版權制度最大的發展就是實現了對網絡服務提供商或者網絡服務提供人員等非直接實施版權侵害的侵權人實施了“間接責任制度”。這樣,通過對提供網絡服務的第三方進行約束和“間接侵權者”判定,有效約束了在版權侵害主體責任人實施侵權過程中為侵權行為提供工具、器材、技術、設備的主體,保障了版權人侵權之后的經濟賠償能夠基本實現。同時,通過對“間接侵權者”的相關機制明確和法律界定,列出“間接侵權”不承擔責任的具體情況,在促進網絡信息發展的同時也有效保護了版權人的權益。
另一方面,國外積極通過“技術立法”“商業模式轉換”“版權合理使用”“版權法定許可”“復制補償金”等對版權制度進行了多樣化和深層次的優化。從2000 到2015 年,國外各國的版權制度通過創新、完善、優化、修訂逐步適應了網絡環境。
(二)網絡環境中版權制度的國內發展趨勢
與國外相比,我國網絡信息技術發展較晚,但是從2005 年至今,我國網絡信息技術卻又展現出了迅猛發展的勢頭。且從2014 年開始,我國的網絡信息技術甚至趕超了部分國外發達國家。所以,網絡環境下我國版權制度同樣在不斷發展和完善。從20 世紀末到現在,我國先后出臺了《計算機信息網絡國際互聯網管理暫行規定》《關于制作數字化制品的著作權規定》《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令》《著作權法》《侵權責任法》等,并隨著網絡信息技術的發展進行了多次修訂、優化和完善。對于網絡侵權類型、形式、內容、特征都作出了詳細解釋,對網絡版權的保護和法律補救制度、網絡內容提供者承擔的相應侵權責任等也作出了補充。
網絡環境中我國的版權制度是在符合我國國情并在與國際接軌下進行發展的,實現了網絡環境中版權制度的落實,且做到了版權保護和版權侵害追責的有法可循和有法可依。但是,與國外相比,網絡環境中我國版權制度的發展還不能做到完全適應相關產業發展的需求,且我國網絡技術近幾年發展較快,還應當積極進行改革和完善。具體來說,在立法完善方面,我國應當積極優化間接侵權責任、合理使用范圍、法律許可范圍等方面的內容,加強“技術措施”的規則引入,并適當將一些侵權行為與《刑法》有機結合,起到遏制侵權行為的效果;在版權制度覆蓋方面,不斷擴大權益保護的范圍和力度;逐步優化和創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構建新型商業行為;鼓勵高新科技發展,推動版權相關產業發展,積極運用數字化技術的升級換代加強版權保護。所以,我國的版權制度在網絡環境之下還有漫長的路要走,還需要全方位多層次進行優化和補充,在借鑒國外成功經驗的基礎上,推動科學化和合理化的版權制度發展。
結束語
隨著5G 時代的深化以及6G 時代即將到來,互聯網構建的網絡環境還會發生深刻的變化。其中,版權作品作為網絡環境中的一種信息,其目的在于進行傳播,而版權保護的目的也是在于合理合法合規進行傳播。所以,版權保護和版權限制是統一且對立的有機結合。現階段,需要積極研究和加強版權作品的合理使用和保護,構建一個科學合理的版權制度,才能在保護版權人利益的前提下,實現版權作品的廣泛傳播和合理使用。同樣,也只有構建符合網絡環境的版權制度,才能推動網絡環境的綠色和諧,實現知識和科學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