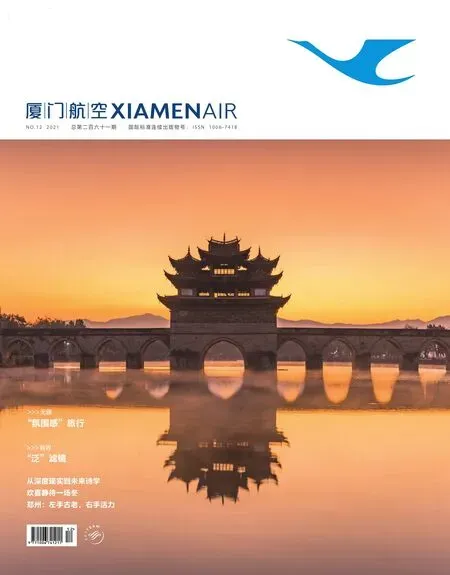藝術(shù)的真相:不必追求“真像”
撰文_馮安興
“蛇精臉,燈泡眼,一看就覺得很危險”,人們對于濾鏡的詬病,往往聚焦于使用濾鏡后“不像本人”“不夠真實”的問題上。不過,同樣是“不像”,一些與現(xiàn)實有出入藝術(shù)作品的命運就比人像照片的命運好得多,它們同樣在“濾鏡之下”經(jīng)歷了夸張變形,卻帶給人不同的審美體驗。
就拿史上第一個活著看見自己的畫作入駐盧浮宮的畢加索來說,粗獷的線條、扭曲的人體、變形的五官充斥在畢加索的作品中,但這些“變形濾鏡”下的作品卻不斷被挖掘和贊賞。還有以敘述“甲殼蟲被嫌棄的一生”而蜚聲文壇的卡夫卡,直接用“異化濾鏡”讓人變成蟲子,不用思考我們也知道人不可能變蟲子,但《變形記》就是成了20世紀最有名的小說之一。
同樣都是“不像”“不真實”,人像照片和藝術(shù)作品或許都給人“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的初體驗,不過側(cè)重點到底不同。夸張的人像照片更多地給人“看不懂”的迷惑感,而成功的藝術(shù)作品則更多帶來“震撼”后的恍然大悟。
藝術(shù)作品表面上的“不像”,實際正是為了突出藝術(shù)的真相。正如畢加索自己所說:“我把鼻子畫歪了,歸根到底,我是想迫使人們?nèi)プ⒁獗亲印!彼囆g(shù)創(chuàng)作用一些濾鏡式的變形去令內(nèi)核變得朦朧的同時,也給了人們?nèi)ヌ綄ぷ髌穬?nèi)核的動力——因為它變得如此不同,我們才會去拼命追尋背后某種形而上的哲思。并且,愛加濾鏡的創(chuàng)作者并不孤獨,因為很多時候,連觀眾自己也會主動戴上某種濾鏡去觀照藝術(shù)。
《格爾尼卡》:覺得我過于破碎?那就對了
牛頭、馬頭、人面,斷劍、斷臂、殘肢,《格爾尼卡》是一幅被畢加索加了“破碎濾鏡”的畫作。在形象的組織及構(gòu)圖的安排上,《格爾尼卡》顯得十分隨意,我們甚至會覺得它有些雜亂,但在“破碎濾鏡”之下,《格爾尼卡》卻有著精心組織的構(gòu)圖和完整的內(nèi)核。畢加索自己曾解釋此畫的象征含義,稱公牛象征強暴,受傷的馬象征受難的西班牙,閃亮的燈火象征光明與希望。如此說來,《格爾尼卡》畫面的緊張與恐怖氣氛和略顯破碎的質(zhì)感,或許正是戰(zhàn)爭帶給人類創(chuàng)痛的隱喻——當然,這只是一種解讀的可能性,戴上你自己的濾鏡,你也可以有別的思考。
蒙娜麗莎:我其實并沒有凝視你
作為最廣為人知的世界名畫《蒙娜麗莎》,許多觀賞者在看完這幅畫之后都“心有余悸”,他們覺得無論從哪種角度看向這幅畫,蒙娜麗莎似乎都在與自己對視。不過,這種所謂“蒙娜麗莎效應”其實并不存在,研究發(fā)現(xiàn),蒙娜麗莎的視線總體來說偏右,許多角度之下,蒙娜麗莎都不會回應觀畫者的目光。但是,即便已被“科學辟謠”,人們?nèi)栽敢庀嘈胚@種效應的存在——這本身就是解讀者對于藝術(shù)作品所加的濾鏡,觀眾更愿意相信有一束神秘的目光穿越時空而來,這種目光是否真的存在,實際并不重要。
李白:整個大唐,我是最會用濾鏡的詩人
詩歌語言與敘事語言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的變形程度是極大的,因此我們可以說,詩歌語言是存在于濾鏡之下的語言。縱觀整個大唐,在寫詩“加濾鏡”這方面,李白是“拿捏得死死的”。狂放是李白的態(tài)度,這種態(tài)度很難不令他的詩歌在濾鏡之下大放異彩。現(xiàn)在很多為人熟知的濾鏡特效,都可以在李白的詩歌中找到痕跡:“白發(fā)三千丈,緣愁似個長”里,就給抒情主人公用上了所謂“染發(fā)濾鏡”;“天臺四萬八千丈,對此欲倒東南傾”里,就給天臺山用了“增高濾鏡”;而“日照香爐生紫煙,遙看瀑布掛前川”里,顯然給煙也加了一層調(diào)色濾鏡……
蝙蝠:吉祥的濾鏡一加,我就是瓷器上的主角
按照蝙蝠的習性和長相,人類對于它的感情應該是恐懼大于喜愛的;但是,熱愛“諧音梗”的中國人因為蝙蝠的“蝠”與福氣的“福”同音,就給蝙蝠加上了一層“吉祥濾鏡”。從此,蝙蝠搖身一變成了一只象征福氣的小獸,蝙蝠花紋也在古代瓷器制作中得到追捧。在故宮博物院現(xiàn)存的瓷器文物之中,可以看見諸如“青花飛蝠紋筆筒”“黃地粉彩紅蝠紋碗”“青花桃蝠紋橄欖式瓶”等諸多含“蝠”量極高的瓷器,蝙蝠能從山林進入書房和廳堂,僅僅隔了一層“吉祥濾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