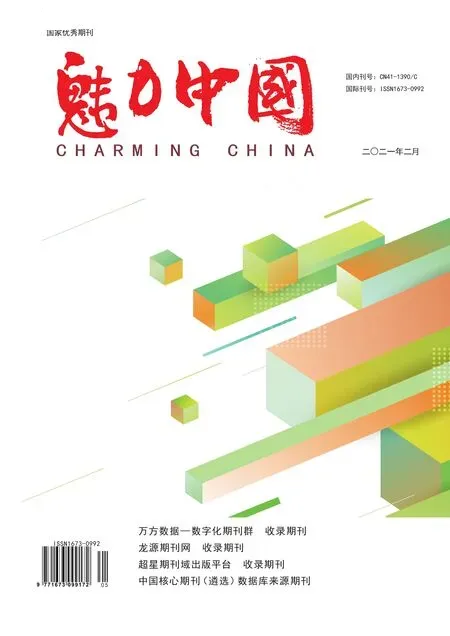淺析醫方緊急救治權與患者家屬知情權沖突
司雨晗
(內蒙古大學,內蒙古自治區 呼和浩特 010000)
一、概述
(一)醫方緊急救治權的概念
緊急救治權是指在緊急情況下,因得不到患方知情同意,為保障患者的利益,醫方可采取緊急醫療救治的權利,即醫生在采取相應的緊急救治措施時,應先取得患者本身或其家屬的同意,才可以行使醫療救治的權利。但當醫療機構遇到需要急需采取醫療措施進行救治的患者,并且患者又陷入昏迷,無法取得患者本人的同意或者無法與患者家屬取得有效聯系的兩難境地時,醫方為保障患者的生命健康利益,醫療決定權則有條件地讓渡到醫療機構手中,醫療機構在履行相關程序后即可實施緊急救治的權利。此時的醫療緊急救治權就是權利重新分配的結果。
(二)患者的知情同意權的概念與法律性質
從理論來講,患方的知情權包括患者的知情權與患者家屬的知情權。對于患者的知情權,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病情的了解權。病情的了解權分為患者的病情了解權和患者家屬的病情了解權。患者的病情了解權是指患者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并對自己身體狀況有基本預判的權利。我國《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第11 條規定,醫務人員可以根據具體情況,權衡患者的身體狀況。在實際醫療活動中,醫生為促使患者形成堅實的心理基礎,為患者營造良好的修養環境,醫生可能會對患者灌輸“善意的謊言”,本著“治療先治心”的原則,從而使患者配合治療,減輕他們的心理負擔。雖然該種做法在實踐中飽受爭議,但確實產生過積極作用。對于患者家屬而言,無論患者的病情如何,患者家屬都必須了解患者的實際情況,醫生要將患者的身體狀況以及風險預判等情況,如實告知其家屬,確保其親屬最基本的知情權,從而形成正確的認知。
第二,治療措施的知悉權。治療措施的知悉權是指患者應有權了解醫方所提供的治療方案與治療措施,基于對治療方案的風險以及相應并發癥的了解,做出是否接受治療的決定。醫方通過現有的病患資料有義務向患者提供合理有效的治療方案,并向患者詳述治療方案與風險,使患者對于即將采取的治療措施有一個基本的預期。
第三,醫療費用的知情權。患者及其家屬對所采取醫療措施的費用以及費用明細有權知曉。醫方應在自己職權范圍內,妥善使用治療費用。
對于患者家屬的知情權,尚存理論爭議。一部分學者認為,患者家屬知情權不能認定為民事的代理行為,認為知情權屬于人身權。而我國法律規定,對于人身方面的權利是不能代理的。但當前的理論通說認為,患者家屬知情權應認定為民事代理行為。患者家屬在法定或約定范圍內以患者名義實施醫療互動,其后果應由患者本人承擔的民事法律行為。
二、我國醫療緊急救治權實施現狀
(一)醫療緊急救治權行使條件
我國《侵權責任法》第五十六條對醫療緊急救治權進行了規定,成為醫療機構行使緊急救治權的主要依據,醫療緊急救治權行使主要有以下條件:
1.患者存在緊急情況
緊急狀況是一種抽象的狀態,在醫療領域主要體現以下四點:
一是患者不具有知情同意能力。患者的控制能力與辨認能力無法獨立行使,不具備明辨是非、權衡利弊的能力。二是時間的緊迫性。如若不采取及時有效的醫療措施,將會給患者的生命健康權造成極大的傷害,形成不可挽回的損失。三是病情的重大危險性。病情的重大危險性不僅要求具有緊迫性,同時還具有高度危險性。四是不救的不利性。如若醫方不給予患者進行及時的治療則會給患者乃至社會、國家帶來不利影響。
2.未能取得患方的同意
“未能取得患方的同意”作為醫方行使緊急救治權的前提條件。根據相關法律規定,醫方只有在取得患者或近親屬的同意之后,才能行使該項權利。如未能取與患者或其親屬的同意,醫方擅自行使緊急救治權利,則會造成對患方知情權的侵犯,同時,一旦發生醫療糾紛,醫療機構則會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3.經負責人批準
在緊急情況下,醫方無法與患者取得有效溝通,或者患者陷入緊急狀態,如不采取緊急救治,輕則影響患者康復,重則影響患者生命,此時,患者是否接受醫療的自主決定權發生轉移,在滿足合理條件下,醫方才可行使緊急救治權。我國在法律中對醫方緊急救治權進行了明確的界定,但是并未明確指出“負責人”的具體范圍,該項權利的行使是由住院總醫師還是由科室主任行使,只是一個模棱兩可的規定,在實踐中困難重重。
(二)醫療緊急救治權實施現狀——以內蒙古自治區為例
實踐表明,對于醫方緊急救治權規定的不盡完善,內容籠統模糊,往往會妨礙緊急救治權的行使;同時,無論對于醫療機構還是患方而言,日后一旦陷入醫療糾紛,造成維權障礙。
通過醫療大數據分析,內蒙古自治區自2013 年以來,全區各級法院共審理260 件醫療糾紛案件,其中涉及因緊急救治所引起的醫療糾紛為1 件,為內蒙古自治區人民醫院與張某香、郭某等醫療損害責任一案。對于該案,本文只選取與緊急救治有關的內容,以便發現緊急救治權與患方知情權在現實中的沖突。
在內蒙古自治區人民醫院與張某香、郭某等醫療損害責任一案中,本案的爭議焦點為,醫方在緊急救治的情況下,能否以身份證件的年齡認定為患者的實際年齡。即,內蒙古醫院是否存在私自篡改患者的真實年齡和在明知患者的實際年齡為81 歲的情況下仍進行溶栓的問題。對此,一審法院認為,身份證作為公民年齡的證明證件,醫院在緊急救治病人情況下采用其作為患者年齡無過錯。因此患者家屬提出由溶栓前篩查表顯示將患者的從81 歲涂改為78 歲的理由不能成立,故醫療事故鑒定結論中上述關于醫院明知患者的實際年齡81 歲的情況下仍進行溶栓的認定該院不予采信。
三、沖突原因分析
醫方緊急救治權與患者家屬知情權是對立統一的整體,二者經常出現沖突的原因集中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法律層面沖突之體現
1.患者家屬代行知情權之現行法律的缺陷
首先,對于“患者家屬”的界定不明確。在《醫療機構管理條例》和《執業醫師法》中,患者的知情權的代行主體為“家屬”,而在《病歷書寫基本規范》與《侵權責任法》中規定為“近親屬”。在實際操作中,我們能否將“家屬”等同于“近親屬”,他們之間一旦發生沖突,是否有順位要求,對于“家屬”主張采取醫療措施,而“近親屬”對采取醫療措施持反對意見等情況都未在我國相關法律中予以明確規定。同時,在《侵權責任法》中規定的患者的“緊急狀況”以及“患者家屬拒絕同意”等條件無法在實踐中具體界定,故存在一定爭議。
其次,患者家屬代行知情權的權利界定不明確。我國法律雖然對患者家屬行使知情權進行了規定,但是并未就該項權利的具體邊界以及在患者無法做出是否采取治療措施決定時,患者家屬能否決定患者的生死等問題進行規定。醫方在實際醫療活動中,針對患者家屬做出接受治療的決定或者放棄醫療救治的決定,是否還要考慮患者家屬實施權利的動機等一系列問題,都使得患者家屬的知情權模糊不定。
2.醫方緊急救治權之現行法律的缺陷
前文已經列舉了我國法律關于醫療緊急救治權的內容,各個法律法規中所涉及的緊急救治權的內容卻不盡相同。一旦面臨醫療糾紛時,患方和醫療機構選取何種法律法規作為支撐依據和維權手段,這些都需要法律法規具有統一性。
其次,對于醫療緊急救治定型問題,學術界尚存爭議。最高人民法院雖于2017 年發布醫療損害糾紛司法解釋中規定,鼓勵醫療機構積極搶救生命垂危的患者以及緊急救治經批準的醫院不承擔賠償責任,但是其到底是權利還是義務,并無定論。
(二)社會層面沖突之體現
醫患關系沖突的根本原因就是醫生和患者對于醫療技術與疾病的認知限制。
眾所周知,人體奧妙猶如浩瀚宇宙,當前的科學技術以及疾病研究只是窺探其中的僅十萬分之一,人類對自身的探索遠遠沒有結束。但現實中,很多人都片面認為“醫學就是神學”,認為去醫院就好比逛商場,花了錢,就一定能“買到”康復。但殊不知,人類對自身疾病的了解遠遠不夠,且永無止境。正是這種醫患雙方的認知差異,不斷給予本就脆弱的醫患關系致命一擊。
由于醫患關系中信任基礎的不斷瓦解,醫療資源配置的不均衡等因素的堆積,導致醫患關系一直處于“爆燃”狀態,一旦發生醫療糾紛,醫生也隨之從救死扶傷的“救世主”轉變為十惡不赦的“殺人犯”。這不僅使得醫療機構陷入曠日持久的醫療糾紛中,醫療機構的聲譽也受到相應影響,同時對于涉事醫生的身心造成巨大傷害。因此,在現實中,導致很多醫療機構審慎行使自己的醫療緊急救治權,謹小慎微,以免深陷訴訟的泥潭。
四、緩和醫患雙方權利沖突建議
(一)完善我國相關的法律制度
緩解醫患雙方的沖突,要立法先行。明確患者家屬代為行使知情權的范圍解決患者家屬之間是否有順位的問題。與此同時,通過立法明確醫方緊急救治權的事實標準,賦予醫方更多的自主權。明確界定“不能取得患者或者患者近親屬意見”的情形,解決立法籠統、模糊和的問題。我國還應借鑒國外關于醫方緊急救治的成熟經驗,吸收國外相關制度的優點,做到博采眾長,全面發展。
(二)建設完善的醫療保障體系
在實踐中,一旦發生醫療糾紛,患方多以醫方侵犯其知情權、醫療機構有過錯以及醫療機構未盡到合理的救助義務等為由要求醫方承擔賠償責任,使醫方陷入不必要的訴訟。對此,應不斷完善我國的醫療保障體系,給醫院“減負”,給醫生“松綁”。
此外,也可將糾紛責任的承擔不斷分解,轉移得到國家、政府或第三方機構上,減少醫方或患方單獨承擔責任的負擔,這樣既保證了醫療機構的合理運行,同時也為患方的生命健康提供了保障。
(三)積極運用5G 等科技技術
2019 年是5G 技術商用的開啟之年,在醫藥領域也掀起了5G 技術應用的高潮。從遠程手術零的突破再到醫療大數據的不斷完善,5G 網絡、大數據報告、遠程醫療、云視訊等先進技術,不僅提升了醫療衛生行業的綜合監督效能,同時提高了疾病的診斷率以及治愈率。對于解決醫療資源分配不均,減輕醫護人員高負荷工作,緩和醫患關系具有重要意義。
(四)設立獨立的第三方機構
《侵權責任法》第五十六條規定了“院長簽字制度”與“院長代理值班制度”,但這兩種制度在實際生活中并未發揮其應有之用。對此,我們可以設立獨立的第三方機構——醫療緊急救治委員會。該會的建立,應獨立行使自己的職權,確保不受任何一方的干預,保障醫方能順利行使緊急救治權。另一方面對于解決醫療糾紛,要充分發揮第三方中立調節作用,達到解決醫療糾紛的目的。
結語
在現實醫療活動中,醫療機構會遇到很多緊急狀況,因患者知情權的限制,使醫方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醫方擅自采取緊急救治,一方面會侵犯患者知情權,另一方面,如果沒有造成患者死亡等嚴重后果,醫患雙方會相安無事,如若發生醫療事故,不僅讓醫院陷入紛繁復雜的醫療糾紛,而且也會讓涉事醫療機構和醫生遭受無窮無盡的輿論懲罰。故,在面對緊急狀況時,在保障患方知情權的同時,如何最大程度地賦予醫方更多的緊急救治的權利,是我們亟需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