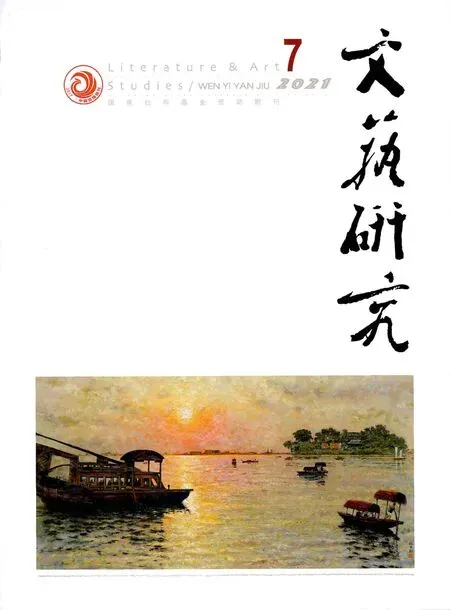新詩入樂與詩樂關系的現代重構
金婷婷
近代文藝變革大勢有二:其一是取法西方以實現本國文藝形式的革新;其二是順應傳統階級的瓦解推動文藝下移,即把文藝創作和接受的主體從少數精英士人轉換為更廣泛的民眾。在此過程中,溯源至《詩經》的歌詩傳統被重新激活,歷史上通行于民間的樂府、聲詩、詞曲等音樂文學也為從晚清改良派到新文化運動的革新者提供了豐富的歷史資源,“詩樂相和”儼然被視為文藝生命力和影響力的必要保證。從此意義上說,近代出現的“新詩入樂”主張與實踐,就不能單純理解作“為藝術而藝術”的活動,而應著重關注其所指向的重構現代詩樂關系的終極目標。本文將對此進行考察,以期增進對近代文藝思想乃至中國文學、音樂發展趨向的認識。
一、從文藝下移到民間中心:新詩入樂的思想史背景
文學與音樂同源而出,又隨著文明進步而各自獨立。兩者之分合本是文藝發展的自然規律,但自晚清以來,“可歌之詩”與“不可歌之詩”分別被打上了平民大眾階層與士人精英階層的烙印。這一分類的形成與所謂“文藝下移”思潮有關。梁啟超《變法通議·學校總論》言:“世界之運,由亂而進于平,勝敗之原,由力而趨于智,故言自強于今日,以開民智為第一義。”①在他看來,由戰爭決定的勝負只能得意于一時,從長遠看,各國勢力的競爭消長,實由全民之智即全民的文明素質決定。因此,清季改良派以“覺天下”(《湖南時務學堂學約》)②為己任,致力打破“知識”成為某種階層特權的現狀。他們認為,文明的創造和享有者不應只是作為社會精英的士人階層,還應包括天下萬民,如此才能實現開啟民智、提升國力的政治理想。譬如黃遵憲提倡變更文體,使文言合一,正欲使“天下之農工商賈、婦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③。
除了語言文字改革,晚清聲勢浩大的國樂改良運動也是推動文藝下移的一種策略。改良派認為樂歌對民眾有很大影響,如曾志忞言,“下等社會最優于感動音樂”(《樂典教科書自序》)④,應以“最淺之文字,存以深意”(《教育唱歌集序》)⑤。即便是深奧的文辭,也可“依節緩諷”,使人“久乃見其言之中情”(童斐《音樂教材之商榷》)⑥。樂歌教育的核心是藉由音樂滌蕩人心之力,使普羅大眾跨越知識修養有限的障礙,感受到詩歌的情意。若以西學比類中學,樂歌教育正與中國“以風化下”的歌詩傳統相通。《詩經·國風》篇什,多在民間傳唱;《詩大序》言歌詩風行,能“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⑦,雖然是從統治者的角度立言,但也確實說明了詩樂相和的社會功能。又孔穎達正義言:“詩是樂之心,樂為詩之聲,故詩、樂同其功也。”⑧就是說,在建立人倫規范、實施道德教化、移風易俗的過程中,詩、樂互為表里,共同作用。改良派希望建立新社會,也借用了歷史資源,如梁啟超將詩歌、音樂視為國民精神教育的兩大要件⑨,并將詩樂相和作為文藝下移的重要津逮。
然而我國至近代,詩樂已然分途。在梁啟超看來,這意味著文藝與民眾的疏遠。1904年,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論國樂改良,將造成詩樂分途的責任歸咎于專作案頭之詩的士大夫。他指出,我國的詩樂傳統自《詩三百》始,“如楚辭之《招魂》《九歌》,漢之《大風》《柏梁》,皆應弦赴節,不徒樂府之名如其實而已。下至唐代絕句……宋之詞,元之曲,又其顯而易見者也”⑩。梁氏所言之“詩”是廣義的詩,涵括歷代韻文文體。在他看來,從先秦到宋元這一漫長歷史時段內,韻文作品基本能夠在民間傳播,起到以風化下之效;但自明代以來,詩、詞、曲漸不入樂,成為士大夫私享的文學形式:
蓋自明以前,文學家多通音律,而無論雅樂、劇曲,大率皆由士大夫主持之,雖或衰靡,而俚俗猶不至太甚。本朝以來,則音律之學,士大夫無復過問,而先王樂教,乃全委諸教坊優伎之手矣……若中國之詞章家,則于國民豈有絲毫之影響耶?推原其故,不得不謂詩與樂分之致也。?
要言之,正是因為文人士子不關心音律之學而僅研求修辭義理,才導致俗靡之樂盛行。詩歌對國民無絲毫影響,詩、詞、曲淪為“陳設之古玩”,詞章家也成了“社會之蠹”?。
不難發現,在梁啟超的言說中,隱含著士大夫文學與民間文藝之間的對立,就詩歌而言,是否入樂是區分二者的標志。由此也能推衍出梁啟超衡量文體價值的標準:可歌之詩是由國民共享的文藝類屬,能夠影響民眾的思想情感;不可歌之詩只是士大夫階層獨享的如古玩般的文學形式。基于文藝下移、開啟民智的訴求,可歌之詩的價值,自然要高于不可歌之詩。
梁啟超的詩樂觀代表了改良派共識,不識樂理的士大夫成為改良派攻詰對象。如匪石言,“《詩》亡以降,大雅不作”,士大夫忽視音樂的情感教育,僅靠“仁義道德之說鼓動社會而終不行”(《中國音樂改良說》)?。又盛俊言,“音樂者,感情教育而振醒國魂、淘刷末俗之要素也”,但“說詩者不以音,而以義,作詩者亦不以聲,而以文”,振醒民眾的音樂“闃然無聞”,終致“種以弱,而國以衰”?。陳仲子以中西歌詞對比:“夫歐西之歌辭,大抵成諸素嫻文學者或著名詩人之手。而我國歌詞,乃由俗伶賤優之以訛傳訛,或任稍識之無者操刀以從事,安能望其轉移風化、發揚民氣哉?”(《近代中西音樂之比較觀》)?西方歌曲歌詞多為文學精英所作,而我國歌詞卻由不通文學的伶工所作,兩者差距一目了然。可見推行國樂改良,取法西樂只是手段,更重要的是倡導習文學者兼重樂理,使本國詩樂通過現代重構再次合一,如此才能實現轉移風化、發揚民氣的社會理想。
改良派詩樂觀主要從社會改良的角度著眼,未免存在抹殺不可入樂之文學的獨立價值的問題,但在近代中國急求開啟民智、實現民族復興的背景下,也有其合理性。然而,開啟民智不是一蹴而就的。即使在疾風驟雨般的辛亥革命之后,雖然舊有的政治體制與階層劃分被顛覆,但學術、文化、文藝的階層壁壘并沒有被完全打破,而且“下移”這一概念本身所附加的階級性也有問題。胡適就直接批評道,文化不應是“我們”向“他們”的施舍?,新文化運動應依靠“最大多數的人”?,亦即由民眾來創造、傳播文化。其思路已然從由上化下轉換為以民間為中心。兩相對照,晚清改良派教化民眾的姿態無疑顯得陳舊而保守,但其率先發掘的歌詩傳統,因其古老而純正的民間性,仍舊強烈地吸引著新文化運動序幕開啟之后更徹底的革新者。
胡適以“平民文學”與“貴族文學”的對立為軸線建構中國文學史,“詩樂離合”也是其考察兩階層文學關系的一個維度。在1928年出版的《白話文學史》中,胡適書寫由漢至唐的樂府史時,即確認了樂府的平民文學屬性。他說,樂府是平民文學的“征集所,保存館”?。蓋貴族文人遵循樂府采詩的制度將民間歌曲寫定,在此過程中,文人為了配合音樂的諧美,對民間歌辭有所修飾潤色。其后,文人更模仿民間歌曲來制作“樂歌”。至魏晉之時,曹操、曹丕、曹植、阮瑀、王粲諸詩人制作樂府,已不再從“仿作古賦頌里得著文學的訓練”,而是“從仿作樂府歌辭里得著文學的訓練”?,故能宕開建安文學的新風。盛唐是詩的黃金時代,其“發展的關鍵”也在“樂府歌辭”?,即使白居易、元稹等所作的不可入樂的新樂府,也蘊含著“古樂府民歌的精神”?。要言之,自漢至唐的幾百年間,樂府的興盛是因為“平民的歌曲層出不窮地供給了無數新花樣、新形式、新體裁;引起了當代文人的新興趣,使他們不能不愛玩、不能不佩服、不能不模仿”?。正是由于樂府這一可歌之詩的體裁,我國韻文文學才“能保存得一點生氣、一點新生命”?。
胡適的樂府史框架展現了自漢至唐文人創作可歌之詩的成就,而他在《詞選》自序中對唐宋詞史的勾勒,則呈現了詞體與音樂脫離后由盛轉衰的脈絡。胡適將唐宋詞史分為歌者的詞、詩人的詞與詞匠的詞三段,認為只有第一階段的詞可合樂而歌,是“歌者的詞,教坊樂工與娼家妓女歌唱的詞”,“不曾脫離平民文學的形式”?。后兩個階段的詞逐步蛻化為案頭文體,屬貴族文學。前后的分嶺在11世紀晚期,“蘇東坡一班人以絕頂的天才,采用這新起的詞體,來作他們的新詩”,而不再是給“十五六歲的女郎在紅氍毹上裊裊婷婷地歌唱”?。此后詞體逐漸脫離音樂,不再是“歌者的詞”,而變成屬于貴族文學的“詩人的詞”。這一變化的最終結果是詞體“命運的完結”:“因為文人把這種新體裁學到手之后,劣等的文人便來模仿,模仿的結果,往往學得了形式上的技術,而丟掉了創作的精神……于是這種文學方式的命運便完結了。”?與此同時,民間又出現了新的音樂文學形式:“民間的娼女歌伶仍舊繼續變化他們的歌曲,他們新翻的花樣就是‘曲子’。他們先有‘小令’,次有‘雙調’,次有‘套數’。套數一變就成了‘雜劇’;‘雜劇’又變為明代的劇曲。”?
按胡適演繹的歷史邏輯,中國文學進化的推動者實為生活在街坊里巷、山村鄉野的廣大民眾。他們以音樂為媒介影響貴族文人的創作,從而成就了樂府、詞體等韻文文體的繁榮。而當貴族文人不注重詩樂相和、專作案頭之詩時,詩歌則逐漸遠離平民,淪為因襲模仿的沒有生氣的案頭文學,南宋后的詞體就是例證。在“平民-歌詩”與“貴族-徒詩”的對應關系之上,又衍生出一種基于音樂的文學進化觀,如朱謙之所言:“中國三千年的文學史,應該就是一部音樂的文學史。”?在他看來,音樂文學由村夫農婦、癡男怨女信口唱出,表現真摯情感,是純粹的文學,而不合音樂的文學大多是貴族階層所作的佶曲聱牙的教令或者表現文采的散文,不能視作純文學。朱氏進一步斷言:“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平民文學,即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音樂文學,所以文學史和音樂史是同時合一并進的,如一個時代的音樂進化了,便文學也跟著進化。”?
綜上,晚清至民國初期,可歌之詩與不可歌之詩的階層烙印被不斷放大,最終凝定成只有詩樂相和才能立足民間,推動文藝、文明進步的歷史認識。這給予擁抱新文化的文學家、音樂家不小的啟迪和震動,使他們激發出續寫歷史、創造新歌詩的自覺意識。正如朱謙之所言:“今后的希望,是文人能夠謳歌,并且要平民都能從心坎里唱出最好聽最微妙的‘音樂文學’來。那時‘白話文學’才算完全建立了,那時‘白話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才算有一個最進化最光榮的地位。”?
二、“出身”與沖突:新詩入樂的“合法性”之爭
在近代文藝下移的語境中,繼承詩樂傳統意味著獲得占據文藝主流、主導文藝進步的話語權。趨新者主張用新音樂歌唱白話體新詩,也是自然而然的。新詩入樂思路的成形在20世紀20年代末,此時的新詩度過了“最興旺的日子”?,正處于“氣象頗是黯淡”?的時期。1928年,趙元任出版《新詩歌集》(商務印書館),為14首新詩譜曲。朱自清在聽過趙元任“自彈自唱”后,撰文專論唱新詩與新詩前途,新詩入樂首次得到理論層面的肯定。
胡適也是新詩入樂的潛在推動者。事實上,他在作新詩之初,并沒有將入樂作為“試驗”計劃的一部分。在1919年所作的《談新詩》一文中,胡適還認為音樂是文體解放的束縛,因為“詞曲無論如何解放,終究有一個根本的大拘束;詞曲的發生是和音樂合并的,后來雖有可歌的詞,不必歌的曲,但是始終不能脫離調子而獨立,始終不能完全打破詞調曲譜的限制”。換言之,由于要遷就音樂,詞和南北曲的文體形制雖較五七言詩自由,但仍不能完全解放;而新詩則“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詩體,并且推翻詞調曲譜的種種束縛”?。但在1928年出版《白話文學史》之時,胡適觀點已然發生轉變,特意表彰了詩樂相和的種種進步意義。此外,胡適為趙元任《新詩歌集》提供了《上山》《也是微云》兩首新詩,亦可見其觀點的轉變。造成這種轉變的最主要原因,是胡適迫切希望改變新詩漸被冷落的狀況,因為這大大削弱了文學革命的聲勢,與他再造新國民文學的愿景相違。胡適急于找到使新詩走向民眾,成為實質意義上的主流和進步文學的方法,故對唱新詩積極支持。
但趨新者對詩樂傳統的認知和想象,與實際的詩樂關系存在巨大反差。從《詩經》到樂府、聲詩、詞曲,中國歷代的詩樂結合都是自然發生且由本土孕育的,而如同“說話”“作文”?的新詩,與音樂缺乏天然聯系。此外,國樂改良后逐漸普及的新音樂是西方的舶來品,與本土樂調存在差異。因此,新歌詩能否銜接本國之歌詩傳統,便會受到質疑。更為棘手的是,詩樂相和雖然被賦予了極其崇高的意義,但就文學、音樂發展的趨勢而言,詩與樂的各自獨立勢不可當。如此說來,鼓吹唱新詩者在大舉推進創作實踐之前,更需要對其合法性加以闡釋。
新詩入樂合法性的第一個爭議點,即新歌詩的“出身”問題。歌詩起源于民間,由擅長音樂的伶工、歌女甚至一般勞動民眾所創造;當一種歌詩體裁因貴族文人的喜愛與模仿而走向案頭化后,民間又會出現新的歌詩體裁。從《詩經》、樂府、聲詩再到詞曲的嬗變,不外乎此,這也是近代學界的集體共識。但若按此邏輯推演,新體的白話詩也應有其民間血統,甚至體裁也應直接脫胎于近時流行的皮黃、鼓子詞、民歌小調等。但是,新詩實際上由文人用歐化、散文化的白話文作成,本身并不蘊含音樂性。更何況當時一般民眾對白話新詩完全陌生,自然不會有用民間格調來演唱的自發興趣。趙元任譜制《新詩歌集》時,也未沿用民間曲調,而是采用新興的西洋音樂技法。新詩與新音樂結合而成的新歌詩,既非本土文藝自然演化的產物,那么以新歌詩銜接本國詩樂傳統,似乎也過于牽強。趨新者在試圖重構現代詩樂關系的同時,無疑也把自己置于理論困境中。
朱自清尋得理論脫困的方法,即以“突變”來解釋詩樂關系嬗變的“非常態”。他首先承認“新詩徹頭徹尾受著外國的影響,與皮黃和歌謠同樣是風馬牛不相及”,但這并不影響新詩成立,因為“文學史的演進,到這一期,或者是呈著突變的狀態”?。所謂“到這一期”,即指晚清以來在社會全面而極速的變革浪潮中,詩的突變也變得合理;皮黃、歌謠不免簡單幼稚,不足以反映現代生活,并不能成為新詩的模范或者源頭,反倒是知識精英依照歐化句法摸索出的新詩,足以“表現舊來詩、詞、曲所不能表現的復雜的現代生活;我們更希望用它們去創造我們的新生活”。新詩體裁若能統合于文學史演進之中,則新歌詩的創作也屬順理成章,因為新詩的誕生“大部分是西洋的影響,西洋音樂化,于它是很自然的”?。
歷史進程中的“非常態”說,實乃近時趨新者的集體共識,絕非朱自清一家之論。正如胡適所言:“歷史進化有兩種:一種是完全自然的演化;一種是順著自然的趨勢,加上人力的督促。前者可叫做演進,后者可叫做革命……革命不過是人力在那自然演進的緩步徐行的歷程上,有意的加上了一鞭。”?可見,突變并非以人力強行改變歷史,只是通過“人工的促進”加速歷史的進程而已。那么,新詩與新音樂結合而成的新歌詩雖是突變的產物,但它的誕生并沒有違背歷史規律,仍然緊密維系著本國過去詩樂的關系。朱自清說:“從歷史上說,從本質上說,詩與音樂的關系,實在太密切了。”?新歌詩也自然不會被排除在這種詩樂相和的傳統之外。朱氏甚至報以十分樂觀的期待,認為新歌詩日后“必能普及”,且不僅限于“新生社會和知識階級”,更能深入一般民眾。新歌詩如若在實質上獲得民間屬性,那么,新詩作為文學主流、正體的地位也就難以撼動。
新詩入樂合法性的第二個爭議點,即在重構現代性詩樂關系的過程中,如何處理詩樂互涉和各自獨立之間的沖突。無論后人關于詩樂相和風行民間、陶冶萬民的歷史想象多么美好,詩與樂的分途的確是文藝流變的實情。古典時代也有批評詩樂分離的聲音,如李東陽言“樂始于詩,終于律,人聲和則樂聲和”,一旦“詩與樂判而為二”,則詩不過是排偶之文,業已背離“古之教”的原義?。鄭樵可謂最激進的批判者。他以“聲”為詩的本質,認為“詩者,樂章也,或形之歌詠,或散之律呂”。所謂“形之歌詠”者,即徒歌,有行、曲;所謂“散之律呂”者,指需絲竹配合演唱的詩體,如引、操、吟、弄等。鄭樵還認為“詩在于聲,不在于義”,可歌之詩足以令人感發,但時人對古、近體詩只窮究辭義,而不將其付諸管弦。這不僅埋沒了古人浩歌長嘯的深趣,更從根本上抹殺了詩的屬性,故“二體之作,失其詩矣”?。
鄭樵雖發掘出漸被埋沒的詩體內蘊的音樂性,但其思想中復古一面也顯而易見。因此,類似批評聲音在歷史上應者寥寥。面對詩樂分途的大勢,儒家學者多試圖重新解釋詩樂關系。朱熹認為“詩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所存”,即便詩無法再協之音律、被之弦歌,后人仍可按“以意逆志”之法“得其言,求其志,涵養其心”。他更提出“志者,詩之本,而樂者,其末也”?。也就是說,詩為教化之本,樂只是教化的手段。王夫之主張“詩樂之理一”,認為詩教可以代替樂教:“古之教士也以樂,今之教士也以文。文有詠嘆淫泆以宣道蘊而動物者,樂之類也。”?詠嘆誦讀詩歌也能感蕩人心,效果近似于樂聲之動人。朱熹、王夫之解決了詩樂分途與儒家教育思想之間的矛盾,這其實也說明,至遲在宋明時期,詩、樂各自的獨立性已經得到了大部分學者的承認。
近代以來,關于詩樂傳統失落的焦慮雖被重新點燃,但是學者對詩、樂客觀上各自獨立的屬性認識并沒有改變,且隨著西學視野的開啟,他們對詩樂發展規律的觀察也更為深刻。朱光潛比較中西詩學后,將“各國詩歌音義離合的進化公例”?分為四個階段:一是有音無義時期,原始民歌大半如此;二是音重于義時期,詩歌作者描寫人事物態,附于樂調的詞有了更豐富的意義,較進化的民俗歌謠屬此類;三是音義分化時期,這一時期民間詩轉為藝術詩,特殊階級的文人專講詩的寫作,詩樂分化以此為節點;四是音義合一時期,音義合一不是指詩樂的再次結合,而是指文人在文字上作音樂的工夫,“使語言的節奏音調之中仍含有若干形式化的音樂的節奏音調”。歐洲“在文字本身求音樂”的技巧成熟于19世紀,例證是象征派的“純詩運動”。而在中國,“聲律運動”在齊梁時代已然盛行,文人詩的發展已達“最后的階段”,即“詩有詞而無調,外在的音樂消失,文字本身的音樂起來代替它”?。
按朱光潛的文藝史觀,詩樂分途是各國詩歌進化所共經的軌跡,而中國詩體完成這一進化的時間相對要早。若從本國內部觀察,詩樂傳統的失落確為憾事,但若縱觀世界文學史發展脈絡,齊梁以降文人詩的繁榮及歷代文學家對文字本身音樂性即聲律的反復研討,也是中國文藝發達、領先于他國的重要象征。
因此,在一些學者看來,放棄一直牽制著本國文藝思想的詩樂傳統,順應藝術分門別類的現實趨勢,未嘗不是一種選擇。陳鐘凡為朱謙之《中國音樂文學史》作序時,就沒有顧忌后者的立場而直接表明看法:“過去的文學雖與音樂有密切關系,其歷史如是長久,今后的文學必脫離音樂而謀獨立。”?他認為“音樂文學”這一范疇屬于歷史而非當下,回溯音樂文學的歷史并不意味著一定要建立新的音樂文學。當然,文學與音樂仍可發生聯系,“如果系不朽之作,自有音樂家為你制譜,絕不致任它淹沒”,但這必須建立在音樂家的自發意愿之上,而文學界則沒有主動建立詩樂聯系的必要:“我們談文學史的人只談過去的事實,不必預測將來。談文學的人也只好專談文學,不必兼顧音樂。”?
唱新詩的鼓吹者自然也會留意到這一進化的悖論。朱謙之撰寫《中國音樂文學史》,即采取了跳出歷史邏輯的策略,他從美學層面來闡釋詩樂關系建構的必要性。他提出“真情之流”?的范疇,認為“一切現實都可以被理性鎖著了”,只有激發感性,人類才能感受到生命的流動和精神的自由舒展。所謂“真情之流”,即指感性的充分釋放:個體自然涌出富有生氣的情感,并且通過藝術來表現這種內在的、流動著的真情,最終與生命本真的韻律節奏發生共振。“一切藝術都是情感的表現”,所以“真情之流”就是“藝術的源泉”。由此,朱謙之建構出藝術的層級體系:訴諸視覺的雕刻、繪畫、建筑等不屬于時間藝術,不具備情感的流動性,只能間接表情;訴諸聽覺的藝術形式如音樂、詩歌等則能夠直接表情,“令人極強地感到情感的節奏和想像的自由”。因此,音樂、詩歌之泉流才是“真情之流”的最高潮。在音樂與詩歌之間,音樂的意義又高于詩歌,因為“音樂的狀態是本源的諧和或節奏”,也就是“真情之流”的源頭。他甚至說,“真情之流”就是“音樂之活動體”,音樂的人生才是“第一義的美的人生”?。
如果把音樂作為藝術和美的最高層級,詩人如果想進入“第一義的美的人生”,唯一的途徑就是賦予詩歌音樂性,“當我們傾聽詩人生命與熱情震蕩出來的韻律,即無異發現‘真情之流’,發現超自然的永恒的歡欣的‘美’”?。當然,在讀與聽的過程中,“真情之流”也能夠傳遞出來,但如朱氏所言:“白話詩雖能直接觸動感情,假使不能夠歌唱,還不能算是表情最自然最美的聲音。”?詩歌如果與音樂直接結合,則“把詩歌、音樂、人生,都打成一片,毫無區別,而成為混然的狀態了”。所謂“混然的狀態”,即充溢著“真情之流”的最純粹的審美境界。由是,唱新詩的藝術活動被賦予了生命美學的意義,這種超自然的、永恒的美,自然是凌駕于進化史觀之上的。
綜上,對詩樂相和報以強烈期待的近代學者強調歷史的突變特征,力圖把新歌詩納入詩樂傳統的統序中,甚至最終超越歷史邏輯,建立詩樂相和與人類生命本體的美學連接。而回到歷史邏輯內部,詩樂相和既然作用于人類精神的共同部分,自然能夠跨越階層而普適于民眾,從而具備從整體上推動文藝與文明進步的永恒內驅力,新詩入樂的合法性得到相對自洽的解釋。盡管如此,新詩入樂的創作實踐效果仍不如預期的那樣理想,更沒有在實質意義上占據文藝主流。而實踐的不理想,自然牽涉到詩樂傳統的解構危機。
三、歌唱與朗誦:詩樂傳統的重構與解構
在20世紀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這一時段,新詩入樂的創作實踐相當豐富,新歌詩在一般民眾中也引起了較大反響。趙元任是最具標志意義的人物,他不僅在1928年出版了音樂史上首部新詩歌譜,還致力于新歌詩的公開演出。據朱自清記述,趙元任曾在一個近千人的會場彈唱劉半農《教我如何不想她》及徐志摩《海韻》。朱自清回憶了演奏會的場景:“唱第一首里‘如何教我不想他’那疊句,他用了各不相同的調子;這樣,每一疊句便能與其上各句的情韻密合無間了。唱第二首里寫海濤的句子,他便用洶洶涌涌的聲音,使人悚然動念;到了寫黃昏的句子,他的聲音卻又平靜下去,我們只覺悄悄的,如晚風吹在臉上。這兩首詩,因了趙先生的一唱,在我們心里增加了某種價值,是無疑的。散會后,有人和我說,‘趙先生這回唱,增進新詩的價值不少’,這是不錯的。”〔51〕
趙元任通過音調的洶涌或平靜來表現新詩的情韻,使得聽眾獲得諸如“悚然動念”“晚風吹在臉上”等審美體驗,如此可增進一般民眾對新詩的理解。事實上,他在譜曲和演奏過程中就注意到新詩入歌所增加的價值。他認為,雖然“詩唱成歌就得犧牲掉它的一部分的本味”,因聽者不能體味詩的語辭與意義,故歌詩“于達意上總是有點損失,于表情上也有一種的損失”,但新詩“唱的時候又加上了好些音樂的興趣,因而使聽者所得的總共的美感可以增加”〔52〕。這種疊加的“總共的美感”,就是朱謙之所言對生命韻律“真情之流”的感受。
趙元任的《新詩歌集》并非孤例,20年代末期還出現了以發展新歌詩為宗旨的藝術社團。1927年初,錢君匋、沈秉廉、陳嘯空、邱望湘、繆天瑞等在杭州組織春蜂樂會,成員兼擅作詩與譜歌,互相配合完成數十首新歌詩創作。春蜂樂會的創作實踐持續近三年時間,已形成穩定的創作模式和作品范式。如《你是離我而去了》《我倆猶是昨日之我倆》《摘花》《金夢》,都有詩之抒情節奏與歌之旋律相襯相和的特點。
進入30年代,尤其是上海國立音樂院(后稱“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設立后,新歌詩的創作中心便轉移到音樂專業院校。該校《樂藝》《音》等雜志頻繁刊登新詩歌譜,音專師生青主、陳天鶴、廖輔叔等積極為新詩譜曲。青主更是建構了以朗讀為中心的新歌詩創作論:“最新派的樂歌作曲法,是以符合詩意的朗誦為主……就是要把音樂供文字的役使,樂音的高低強弱,不許和辭句的朗誦稍有沖突,它是要用音樂發揮那首詩的意義。”他進一步說:“你不懂得朗誦,你便不能夠成為一個新派的樂歌作曲家,因為新派的樂歌作曲家,離開了朗誦,尤其是正確的論理的辭句的輕重,便完全沒有創作唱音的可能。”簡言之,作曲家欲為新詩譜曲,必須先學會朗誦,因為唱音的高低強弱是根據朗誦的字句輕重而決定的。但綜合來看,青主對于唱音創作技術的解析其實并不多,其著重點反而是在介紹朗誦技法,即“論理的辭句的輕重”,如“千鈞為輕,蟬翼為重”八字,“無論知覺上、情感上,都好像蟬翼確實是重、千鈞確實是輕”〔53〕。音專學生廖輔叔推演了青主的朗誦論,總結出朗誦藝術的四要素,即發音的正確,重音的位置,停頓的關節,音色、音強等。在他看來,朗誦既是實用性的方法論,更有著挽救詩的死亡、促成音樂現代新生的重要意義:“要補救中國詩學的偏枯,并使中國的樂歌走上正軌,我不怕啰嗦再說一遍:只有提倡朗誦!”〔54〕
要言之,30年代所通行的新歌詩創作法,是根據朗讀的情感起伏和聲字輕重而譜曲的,這與當時日漸興盛的朗誦活動形成呼應。但綜合來看,這些作曲家對作曲技術的解析其實并不多,著重點反而放在朗誦技法的討論上,一旦落實到作曲活動本身,似乎仍舊要依靠個人的創作天賦,并無程式化的方法可供模仿學習。因此,由作曲家搭建的歌唱與朗誦間的橋梁也導向另一種可能,即讀詩對唱詩的取代。尤其是30年代后期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象牙塔中的音樂活動被迫中止,新詩入樂的實踐與宣傳更趨于停滯,曾是新歌詩創作前奏環節的詩朗誦,最終獲得了主體性和獨立性,成為推廣傳播新詩的最主要手段載體和最流行的聲音藝術。
誠然,唱新詩遙相承接了以民間為中心的詩樂傳統,但從普及于民眾的實踐層面來說,歌唱需要一定的專業訓練,如若動員一般民眾參與集體性唱新詩活動,按當時的音樂美育普及狀況,則太過理想化。所以朱自清說“唱詩是以詩去湊合音樂,且非人人所能”〔55〕,反倒是新詩的朗讀活動更易組織:“民國二十年以后,朗讀會也常有了,朗讀廣播也有了。抗戰以來,朗讀成為文藝宣傳的重要方法,自然更見流行了。”〔56〕基于對30年代之后文藝現狀的冷靜觀察,即使是在20年代高調提倡詩樂相和理想的學者,也不得不重新審視詩樂傳統的現代重構。
朱自清言:“詩原是樂語,古代詩和樂是分不開的,那時詩的生命在唱。不過詩究竟是語言,它不僅存在在唱里,還存在在讀里。”〔57〕此時他仍然強調聲音表情的意義,但對聲音的性質做了調整,即未必是樂聲,也可以是讀的聲音。強調“詩究竟是語言”,意味著把朗讀與詩的親緣關系排在歌唱之前:“新詩的可唱,由趙元任的《新詩歌集》證明。但那不能證明新詩具有充分音樂性;我們寧可說,趙先生的譜所給的音樂性也許比原詩所具有的多。”〔58〕新歌詩的音樂性是由外附加的,朗讀則能表現文字的聲音,即新詩內蘊的音樂性。由此觀之,似乎朗讀新詩,才是更為自然的藝術活動。
朱自清對誦讀的價值判斷,也逐漸高于他對詩樂的價值判斷。他舉出五言詩的例子,證明“詩到了朗讀階段才能有獨立的自由的進展”,因為“五言詩脫離音樂獨立以后,句子的組織越來越凝練,詞語的表現也越來越細密,原因固然很多,朗讀是主要的一個”〔59〕。脫離音樂之后,詩人不再借助音樂表情,只依靠文字本體的聲音表情,故而對詩的詞語推敲、句子組織等有更多關注,這必然促成詩歌創作的精致化。古人的朗讀,也即吟誦,和“照外國詩的讀法順著辭氣讀過去”〔60〕的現代朗讀之間存在本質差異,但朱氏把現代的朗讀與“讀”的古義相聯系:“讀原是抽繹義蘊的意思。只有朗讀才能玩索每一詞每一語每一句的義蘊,同時吟味它們的節奏。”〔61〕由是,現代意義上的朗讀便等同于有聲的“玩索”“吟味”,比起古人按一定腔調所進行的程式化的吟誦,反而是一種更為高級的、深層的審美活動。要言之,朱自清把曾經唱新詩的主張,悄然轉換成對朗讀的期待。而朗讀與詩結合的另一面,則是音樂與詩的分離。這便再次引起我們對詩樂關系的思考:是否詩與樂的各自獨立才是文藝發展的正途,而重構詩樂傳統只是一種徒勞無益的復古情懷?
筆者以為,詩與樂各自的獨立以及朗讀與詩的直接結合,并不能截斷詩樂之間的天然聯系。誠如朱謙之所言,藝術人生的最理想形態,即詩歌與音樂充分交融的“一種美麗的渴望的人生”〔62〕,情動于中,和詩以歌,始終是人類的生命本能。確實,在20世紀前期戰亂頻仍的環境之中,新詩的朗讀要比新詩的歌唱更容易付諸實踐,傳播面也更加廣泛。然而,當代藝術文化語境越來越開放、多元,民眾作為文藝創作和傳播的主體,審美接受力和包容力已非昔日可比,那么,詩樂關系的現代重構也必然能夠獲得充分、開闊的空間。重新審視近代學術史和文藝發展史,不難發現,近代學者在新詩入樂上已經做了相當多的努力,他們對新詩的擁抱與對詩樂關系的重構,并不是出于一種強行調和新舊的執拗情結,這反倒能啟發我們走出在新舊之間左顧右盼的迷思,回到中國藝術傳統的源頭,直面生命深處最純粹的情感需要。再者,不得不承認的是,新詩在當下的境遇很難用“蓬勃向上”來形容,“詩歌已死”的論斷仍舊不絕于耳。如果想讓新詩再次煥發活力,譜制新歌詩的實踐嘗試應該是不可或缺的。
①②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1冊,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14頁,第27頁。
③ 黃遵憲:《日本國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11頁。
④⑤⑥?? 張靜蔚編:《中國近現代音樂文論選編》,上海音樂出版社2005年版,第48頁,第19頁,第84頁,第37—38頁,第79頁。
⑦⑧ 阮元校刻:《阮刻毛詩注疏》卷一,浙江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67頁,第68頁。
⑨⑩?? 梁啟超:《飲冰室詩話》,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第58頁,第59頁,第59頁,第59頁。
? 盛俊:《中國普通歷史大家鄭樵傳》,《新民叢報》第42—43號合刊,1903年10月14日。
?? 胡適:《中國新文學運動小史》,《胡適文集》第1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頁,第111頁。
??????? 胡適:《白話文學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頁,第38頁,第158頁,第158頁,第23頁,第23頁,第4頁。
???? 胡適:《〈詞選〉自序》,《胡適文集》第4卷,第549頁,第550頁,第550頁,第548頁。
???????〔62〕 朱謙之:《中國音樂文學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頁,第49頁,第51頁,第18頁,第20—25頁,第25頁,第51頁,第25頁。
? 朱自清:《新詩》,《朱自清全集》第4卷,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1369頁。
????〔51〕 朱自清:《唱新詩等等》,《朱自清全集》第4卷,第1380頁,第1381頁,第1382頁,第1382頁,第1383頁。
? 胡適:《談新詩》,《胡適文集》第2卷,第138頁。
? 胡適:《逼上梁山》,《胡適文集》第1卷,第144—145頁。
? 李東陽著,李慶立校釋:《懷麓堂詩話校釋》,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頁。
? 鄭樵:《通志略·樂略》,世界書局1936年版,第346頁。
? 朱熹:《答陳體仁》,《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七,朱熹撰,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第2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653頁。
? 王夫之:《讀通鑒論》卷一九,《船山全書》第10冊,岳麓書社2010年版,第707頁。
?? 朱光潛:《詩論》,《朱光潛全集》,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208頁,第212頁。
?? 陳鐘凡:《序》,朱謙之:《中國音樂文學史》,第16頁,第16頁。
〔52〕 趙元任:《新詩歌集》,商務印書館1928年版,第6頁。
〔53〕 青主:《作曲和填曲》,《樂藝》1930年第1期。
〔54〕 廖輔叔:《朗誦的理論與實習》,《音樂教育》1935年第3期。
〔55〕〔58〕 朱自清:《論中國詩的出路》,《朱自清全集》第4卷,第1449頁,第1446頁。
〔56〕〔60〕 朱自清:《論朗讀》,《朱自清全集》第2卷,第435頁,第443頁。
〔57〕〔59〕〔61〕 朱自清:《朗讀與詩》,《朱自清全集》第2卷,第754頁,第755頁,第75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