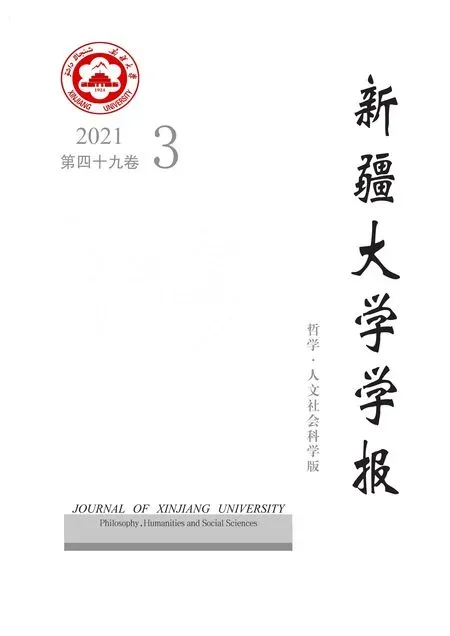口供印證的模式分析與具體運用
——基于中外口供證據規則的對比研究*
王宇坤
(北京大學 法學院,北京 100871)
一、問題的提出
作為法定證據制度的遺留,口供印證規則①印證是指利用不同證據內含信息的同一性來證明待證事實,印證要求不同證據之間的證據事實、證據信息能夠相互得到驗證。補強則是指補強證據對待補強證據的信息驗證,從而擔保待補強證據的真實性,增強待補強證據的證明力。因此,印證和補強具有方法上的一致性。其中,兩大法系國家、日本、我國臺灣地區多是采用“補強”一詞,我國法律及其司法解釋則是使用“印證”一詞進行替代適用。可以說,口供印證規則和口供補強規則其實是在同一理論平臺進行對話。本身帶有鮮明的法定證據主義色彩,這種證據規則要求裁判人員不能僅僅依據口供進行定案,口供必須獲得一定范圍和程度的印證才能成為定案依據。但是,兩大法系國家對口供印證的立法模式呈現為兩種樣態,大陸法系國家更多是從消極層面進行規制,要求審判人員不能僅僅依據口供認定案件事實,至于口供需要獲得印證的范圍和程度則是交由審判人員依據具體案件情況而定。英美法系國家以及受其影響的日本、我國臺灣地區則是從積極層面進行規制,要求口供必須獲得一定范圍和程度的印證才能作為審判人員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目前而言,我國(這里指向中國大陸,以下不再贅述)對待口供印證的立法態度發生了轉變,逐漸從消極的法律規制轉向積極的法律規制,通過積極法定化的口供印證規則保障口供的真實性,進而指導、規范公安司法機關運用口供辦理刑事案件。
1979年《刑事訴訟法》第35條規定,刑事案件只有被追訴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印證,審判人員不得認定被追訴人有罪。《刑事訴訟法》1996 年修改、2012 年修改、2018 年修改均保留了這一條款,這一規定被認為是消極的口供印證規則。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以下簡稱《刑事訴訟法解釋》)第106條規定了口供印證規則的具體實施辦法,這一規定使我國口供印證規則從消極的法律規制轉向了積極的法律規制。2021年《刑事訴訟法解釋》保留了這一條款,只是條文序號變為第141條。根據該項規定,如果偵查人員能夠根據口供提取到隱蔽性很強的物證、書證,其他證據能夠與口供相互印證,并且排除串供、逼供、誘供等可能性的,審判人員可以據此認定被告人有罪。易言之,如果審判人員想要依據口供進行定案,那么刑事案件中的證據必須達到以下三項要求:第一,口供的證據事實具有可信性,偵查人員能夠根據口供找到隱蔽性很強的實物證據;第二,口供必須能夠得到本案其他證據的印證;第三,綜合全案證據,審判人員對口供真實性的疑問能夠得到解釋或者排除。①值得注意的是,口供印證規則屬于證據的證明力規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屬于證據的證據能力規則。但是,《刑事訴訟法解釋》第141條要求審判人員依據口供認定案件事實,必須排除串供、逼供、誘供的可能。筆者認為,這種規定并非是混淆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和口供印證規則的界限,而是要求審判人員應當注意到口供的合法性可能會影響口供的真實性,審判人員依據口供認定案件事實,必須排除對口供真實性的所有疑問。
我國口供印證規則的立法轉變對審判人員識別虛假供述、制約偵查行為起到了一定積極作用。經驗事實證明,消極的口供印證規則不能起到預防冤假錯案的作用,相反“虛假印證”“制造印證”才是導致審判人員認定案件事實錯誤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見,我國消極的口供印證規則并不成功,這種狀況主要基于以下三種原因。第一,偵查中心主義的訴訟構造導致大量偵查案卷材料進入審判階段,審判人員認定案件事實的自由裁量權過小,只能按照偵查案卷材料所勾勒的“藍本”認定案件事實。與其這樣,審判人員不如通過積極法定化的口供印證規則規范、引導偵查人員印證口供,防止偵查權力出現恣意化的傾向。第二,我國刑事審級制度要求二審法院對一審法院的裁判進行全面審查,這種全面審查制度要求口供的印證必須通過一種具有可重復操作性的法定形式體現出來,積極法定化的口供印證規則恰好能夠滿足這一要求。第三,我國口供證據能力規則的內在困境導致了口供證明力規則的興起。有學者認為:“口供虛假與否,本是證明力問題,以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來化解,難度當然較大。如果轉換思路,從證明力的角度來防止虛假口供,效果可能更好。”[1]因此,相比于通過證據能力規則直接排除不合法的口供,審判人員更希望通過證明力規則將不真實的口供排除于定案依據之外,因為后者更容易得到追訴機關的認可,審判人員作出排除決定的阻力更小。
但是,相比消極的口供印證規則而言,積極法定化的口供印證規則可能過度限制審判人員的自由裁量權,導致機械審判,這對我國刑事司法證明實現印證證明模式的轉型沒有任何益處。因此,探討我國這種通過積極法定化形式確立口供印證規則的理論意義重大。下文,筆者通過揭示口供印證的域外模式,進而對比、評價我國的口供印證模式,并且闡釋我國口供印證模式的具體運用,最后指出我國口供印證模式的發展趨勢。
二、口供印證模式的域外考察
雖然兩大法系國家均規定了口供印證規則,但是兩大法系國家的口供印證規則卻呈現了不同的樣態。大陸法系國家實行消極的口供印證規則,這種證據規則形式可以歸納成為消極印證模式。英美法系國家以及受其影響的日本、我國臺灣地區則是實行積極的口供印證規則,這種證據規則形式可以歸納成為積極印證模式。
(一)消極印證模式
消極的口供印證規則主要作為限制內心自由心證原則而存在。大陸法系國家要求審判人員不能僅僅依據口供進行定案,至于口供具體需要獲得印證的范圍和程度則是交由審判人員依據刑事案件具體情況而定。德國《刑事訴訟法》沒有明文規定口供印證規則,但是依據德國刑事訴訟程序的制度和構造,審判法官必須依職權盡可能地查清案件事實真相。約阿希姆·赫爾曼教授指出:“對德國法官來講,查明實體法事實真相的刑事訴訟法原則,是標準性的指導原則。所以,只要無其他的證據可供審查供認的真偽性,德國法官對供認的處理,在結果上與中國法官一樣,不會因此而判決有罪。”[2]而且,根據德國《刑事訴訟法》第244條之規定,審判人員基于查清事實真相的需要,可以依職權將證據調查涵蓋至所有對裁判具有異議的事實和證據材料。這是因為只有履行了真實查明義務,審判人員才能充分地進行內心自由心證,才能適用“存疑有利于被追訴人”原則作出選擇。根據這項規則的要求,審判人員可以向控方和辯方提出查證申請,并且進行詢問。“對于法官的職權查明義務范圍,德國聯邦最高法院的一貫判例認為,是一種全面的案情查明,這種查明應當涵蓋法院獲知的或應當獲知的、須運用一定證據加以證明的情況。即便法院認為基于迄今為止的證據已經對案情獲得確信,即便現有證據收集形成的案情被改變的可能性非常小,法院也不能對可以運用的其他證據不加以運用。”[3]
但是,隨著德國控辯協商制度的適用和發展,德國學術界對口供印證的研究開始出現分化趨勢。“‘協商式的刑事訴訟制度’的支持者們認為,甚至是刑事訴訟法第244 條第2 款也不要求在被告人做出全面的可信的供述后,法庭還要收集另外的證據。雖然在對被告人陳述的準確性和完整性不存在疑問的案件中,這種說法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只要被告人的供述缺乏細節而且僅僅是為了使法庭作出經協商的判決而承認最低限度的事實,就不屬于這種情況。”[4]
(二)積極印證模式
英美法系國家實行二元制的審判結構,如果被追訴人作出認罪答辯,審判法官可以不經證據調查程序,直接判定被追訴人有罪。對于適用陪審團審判的刑事案件而言,積極的口供印證規則主要作為傳聞證據規則的例外而存在,平衡傳聞證據規則過嚴限制所帶來的放縱犯罪風險。在特定情形之下,如果能夠獲得一定范圍和程度的印證,那么被追訴人的庭外事實陳述可以不受傳聞證據規則的規制,具有可采性。根據美國《聯邦證據規則》第804 條第(b)款第(3)項之規定,被追訴人在法庭外作出不利于己的事實陳述,如果這種事實陳述能夠得到其他證據的印證,那么該證據屬于傳聞證據規則的例外,不受排除。①See Fed.R.Evid.,Rule 804.(b)The Exceptions.The following are not excluded by the rule against hearsay if the declarant is unavailable as a witness:(3)Statement Against Interest.A statement that:(A)a reasonable person in the declarant’s position would have made only if the person believed it to be true because,when made,it was so contrary to the declarant’s proprietary or pecuniary interest or had so great a tendency to invalidate the declarant’s claim against someone else or to expose the declarant to civil or criminal liability;and(B)is supported by corroborating circumstances that clearly indicate its trustworthiness,if it is offered in a criminal case as one that tends to expose the declarant to criminal liability.英國法律對傳聞證據規則的限制則是更加嚴格。根據1984年英國《警察與刑事證據法》(PCEA 1984)第76條第1款之規定,在任何訴訟程序中,除非被追訴人的自白屬于法律明確禁止的情形,否則均可成為對其不利的指控證據,不受傳聞證據規則的規制。隨后,英國《刑事司法法》(CJA 2003)第118條第5款也確認了這一條款。在英國,庭外自白是否具有法庭準入資格,取決于它是否能夠獲得印證,審判法官需要通過Voir Dire這一特別程序進行審查判斷。②See Gregory Durston,Evidence:Text&Material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p.296-297.
審判法官主要通過審查口供獲得印證的范圍和程度,從而決定口供是否具有可采性。對此,英美法系國家以及受其影響的日本、我國臺灣地區發展出了多種判例和學說。對于口供需要獲得印證的范圍而言,日本主要存在“罪體說”和“實質說”兩種學說的對立。“罪體說”主張只有犯罪事實的罪體部分需要印證,并不需要實現全部犯罪構成要件事實的印證。“實質說”主張印證的范圍只要能夠保證自白事實的真實性即可,不必像“罪體說”那樣進行形式上的范圍限制,而是主張推認事實能夠達到合理程度即可。③參見田口守一《刑事訴訟法》,張凌、于秀峰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303頁。美國的州法院主要通行“主要犯罪事實證明說”的理論觀點④參見梁玉霞、郭明文《自白補強規則比較研究》,《當代法學》,2006年第2期,第137頁。,這種學說類似日本的“罪體說”。美國聯邦法院和少數州法院采用“可信性說”⑤參見向燕《論口供補強規則的展開及適用》,《比較法學研究》,2016年第6期,第38頁。,這種學說類似日本的“實質說”。對于口供需要獲得印證的程度而言,日本主要包括“絕對說”和“相對說”兩種觀點。前者主張口供之外的其他證據結合起來應當能夠充分證成待證事實,后者則是主張口供和其他證據結合起來能夠證成待證事實即可。⑥參見黨建軍、楊立新《死刑案件適用補強證據規則若干理論問題研究》,《政法論壇》,2011年第5期,第141頁。美國個別州曾經采取“絕對說”的觀點,但是后來普遍采取“相對說”的觀點,這是因為前者否定了口供應有的證明力,使口供印證規則難以發揮應有作用。⑦參見梁玉霞、郭明文《自白補強規則比較研究》,《當代法學》,2006年第2期,第139頁。
值得注意的是,英美法系國家積極的口供印證規則僅僅用以解決口供的法庭準入資格問題,并不直接產生案件事實認定的法律效果。被追訴人是否有罪這一問題仍然需要交由陪審團成員根據自己的內心良知作出裁決,排除內心合理懷疑。但是,“審判法官需要對陪審團成員進行適當警告,充分說明依據未經印證的證據進行定罪的錯案風險,否則視為審判程序違法”[5]。
三、我國口供印證模式的評價
我國適用積極法定化的口供印證規則,它十分強調口供的積極定案功能,明確規定口供需要獲得印證的范圍和程度,明確限制運用口供進行定案的整體證據要求。總的來說,我國的口供印證模式是把口供印證中的經驗法則予以法定化,進而將其作為判處被追訴人有罪的法定條件。因此,我國積極法定化的口供印證規則可以歸納成為法定印證模式。
(一)法定印證模式的特點
1.指引性
法定印證模式的口供印證規則能夠成為刑事追訴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的指引準則,只要刑事追訴機關辦理的刑事案件達到了法定證據條件,審判機關必須作出有罪判決。因此,法定印證模式的口供印證規則之下,偵查人員將會積極引導被追訴人作出有罪供述,明確告知被追訴人選擇認罪或者認罪認罰的從輕量刑后果,并且按照法定證據條件尋找印證證據,完成口供印證的證據鏈條。
2.可信性
法定印證模式的口供印證規則是把口供印證中的經驗法則予以法定化,防止偵查人員運用口供進行“虛假印證”“制造印證”,增加運用口供進行定案的可信程度和可靠程度。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解釋》第141 條之規定,偵查人員必須根據口供找到隱蔽性很強的物證、書證,審判人員才能根據口供認定案件事實。這項規定的目的就是為了防止偵查人員根據現有證據進行“指供”,要求偵查人員按照供證關系的正常規律審查判斷口供。不僅如此,還有學者認為,《刑事訴訟法解釋》應當吸納更多能夠保障口供真實性的開放式規定,譬如口供需要包含對特殊犯罪細節或者大量犯罪細節的準備描述。①參見向燕《論口供補強規則的展開及適用》,《比較法學研究》,2016年第6期,第41頁。
3.整體性
法定印證模式的口供印證規則并不僅僅關注犯罪行為和犯罪結果的印證,亦不僅僅注重口供和印證證據之間的信息驗證,同樣要求全案證據都要能夠擔保口供的真實性,全案證據與口供之間不能出現無法排除、解釋的矛盾或者疑點。
4.定罪性
法定印證模式的口供印證規則是一項判處被追訴人有罪的法定條件。這種證據規則并不僅僅只是擔保口供的真實性,同時還承擔著定罪功能,這是兩大法系國家口供印證規則所不具備的功能。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及其司法解釋的規定,如果審判人員綜合全案證據審查,發現依據口供進行定案能夠達到法定的證據要求,審判人員可以作出有罪判決。
(二)法定印證模式與其他印證模式的比較
筆者通過對比研究發現,盡管積極印證模式和法定印證模式都帶有積極性的特點,但是刑事司法制度上的差異導致我國口供印證規則的適用效果與英美法系國家完全不同。盡管英美法系國家實行積極的口供印證規則,但是英美法系國家獨特的二元制審判結構能夠有效阻斷積極印證模式所帶來的弊端,陪審團成員認定被追訴人有罪仍要排除內心合理懷疑,并非體現為一種機械化的審判活動。對于受到英美法系國家影響的日本、我國臺灣地區而言,雖然它們沒有實行二元制的審判結構,但是積極的口供印證規則更多是以判例和學說的形式體現出來,判例和學說不能對審判人員認定個案事實產生直接的約束力。而且,日本、我國臺灣地區的刑事訴訟法典僅僅規定了消極的口供印證規則,這種立法設置與大陸法系國家的做法一致。②日本《刑事訴訟法》第319條第2款規定:“不論被告人的自白是否在審判庭上作出,該自白是不利于自己的唯一證據時,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見田口守一《刑事訴訟法》,張凌、于秀峰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301頁。“‘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惟一依據……’(§156Ⅱ前),換言之,法官不能單憑被告或共犯之自白,就依自由心證‘確信’其犯罪事實而判處被告有罪。此時,法官‘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見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356-357頁。因此,無論英美法系國家還是受其影響的日本、我國臺灣地區,審判人員認定案件事實的自由裁量權并未受到過度限制。相比之下,我國則是通過司法解釋的形式把積極的口供印證規則予以法定化,口供印證規則直接成為了一種定罪標準。在這種情況下,積極口供印證規則的弊端無法消除,審判人員認定案件事實的自由裁量權將會受到極大限縮,審判機關對追訴機關的權力制約無法達到均衡狀態。
總結而言,無論英美法系國家的積極口供印證規則,還是大陸法系國家的消極口供印證規則,它們都是屬于刑事證據的排除規則,它們對案件事實認定的否定效力大于肯定效力。其中,大陸法系國家體現為一項限制證據證明力的證明力規則,英美法系國家則是體現為一項擔保證據真實性的可采性規則。但是,我國的口供印證規則則是屬于一項判處被追訴人有罪的證據規則,這種積極法定化的證據規則帶有了證明標準屬性,它對案件事實認定的肯定效力大于否定效力,從而成為刑事追訴機關查明、指控被追訴人犯罪事實的指引準則。其實,無論審判人員依據口供進行定案,還是僅僅依據間接證據進行定案,《刑事訴訟法解釋》都詳細規定了審判人員審查判斷證據的法定要求。可以說,法定印證模式的口供印證規則實則屬于我國證明力規則盛行下的一種必然產物。
四、我國口供印證模式的具體運用
我國口供的法定印證模式遵循這樣一種證明理念:如果口供能夠成為直接證據,那么口供便可直接獨立地證明犯罪事實發生的過程和細節,只要口供的真實性能夠得到其他證據的驗證,那么審判人員即可依據口供認定案件事實,判處被追訴人有罪。因此,口供法定印證模式的具體運用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理解,即是口供適格的審查判斷和口供印證的審查判斷。
(一)口供適格的審查判斷
我國偵查機關制作的偵查案卷材料可以暢通無阻地進入審判階段,因此多份口供可能并存在法庭審理環節,而且部分或者全部庭前供述可能會與被追訴人的當庭供述相互矛盾。目前而言,不論被追訴人的庭前供述,還是被追訴人的當庭供述,這些事實陳述均能成為口供,同樣都能成為口供印證規則運用中的待印證證據,具體則是要看哪些口供能夠獲得其他證據的印證。口供的法定印證模式之下,一旦部分或者全部口供能夠獲得其他證據的印證,即使不同口供的證據事實出現矛盾,或者部分口供不能獲得其他證據的印證,那么審判人員亦可通過獲得印證的口供進行定案。①《刑事訴訟法解釋》第96條規定:“被告人庭審中翻供,但不能合理說明翻供原因或者其辯解與全案證據矛盾,而其庭前供述與其他證據相互印證的,可以采信其庭前供述。被告人庭前供述和辯解存在反復,但庭審中供認,且與其他證據相互印證的,可以采信其庭審供述;被告人庭前供述和辯解存在反復,庭審中不供認,且無其他證據與庭前供述印證的,不得采信其庭前供述。”
當然,并非口供的所有內容都需要獲得其他證據的印證。一般而言,口供同時包括犯罪事實、非犯罪事實和認罪態度表現三個方面內容,只要口供中的犯罪事實能夠獲得其他證據的印證即可。口供中的犯罪事實指向被追訴人陳述的犯罪構成要件事實,其整體內容必須具有邏輯上、信息上的一致性、同一性,不得自相矛盾、出現反復。在林森浩故意殺人案中,雖然被追訴人林森浩能夠承認自己實施了投毒行為,但是其又辯稱投毒行為僅僅只是愚人節的玩笑,其本人并沒有殺害黃洋的主觀故意。②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13)滬二中刑初字第110號刑事判決書,訪問日期2019年10月21日,網址:http://www.pkulaw.cn/Case/。這種認罪陳述直接證成了犯罪構成要件事實的客觀方面,但是同時也直接否定了犯罪構成要件事實的主觀方面,從而使口供無法直接獨立地證成完整的犯罪構成要件事實,導致犯罪事實陳述的無效。當然,對于特殊類型的刑事案件而言,即使口供只能體現犯罪構成要件事實的客觀方面,如果指控人員能夠根據客觀方面推導得出犯罪構成要件事實的主觀方面,此時口供也被認為具有完整的犯罪事實陳述。
口供中的非犯罪事實指向被追訴人陳述的非犯罪構成要件事實,譬如量刑事實、抗辯事由、日常行為表現等。口供中的認罪態度表現指向被追訴人表現出的認罪伏法態度,被追訴人是否明知自己的加害行為已經觸犯刑事法律規范,屬于刑法所規制的犯罪行為。對于口供印證規則而言,只要口供中的犯罪事實能夠獲得印證即可,非犯罪事實和認罪態度表現都不是這一證據規則的必要組成要素,僅僅只是犯罪事實陳述的非必要延伸。值得注意的是,美國辯訴交易當中也存在著這樣一種特別的認罪答辯——阿爾弗德答辯。“這種答辯被告人放棄審判權利,但繼續維護他們的無辜。”[6]對于這種情況,如果刑事案件存在強有力的證據證明犯罪,審判法官亦可接受這種認罪答辯。
(二)口供印證的審查判斷
口供的法定印證模式之下,印證證據必須具備法律要求的數量和質量,口供必須得到法律規定范圍或者程度的印證,從而擔保口供的真實性。一方面,沒有一定數量的證據印證口供,口供的真實性自始無法得到驗證。另一方面,如果口供的證據事實沒有得到充分的印證,那么犯罪構成要件事實就無法得到充分證成,口供的真實性不能得到有效驗證。
1.印證的方式
口供的印證方式比較單一,即是以口供這一直接證據為中心,逐一通過其他證據印證口供的證據事實。具體而言,其他證據對口供的印證屬于印證的一種具體表現方式,主要表現為一種由證到供的印證方式,這種印證方式要求其他證據和口供的證據事實具有同一性,其他證據能夠證成口供的真實性。但是,《刑事訴訟法解釋》第141條規定,偵查人員必須根據口供發現隱蔽性很強的物證、書證,審判人員才能依據口供認定案件事實,判處被追訴人有罪。因此,《刑事訴訟法解釋》的規定其實又為口供增加了由供到證的印證方式。由供到證的印證方式要求偵查人員根據口供找到了其他證據,并且其他證據的證據事實和口供的證據事實具有同一性,其他證據又反向證成了口供的真實性。一般而言,由供到證印證方式的證明力大于由證到供印證方式的證明力,可靠程度和可信程度更大。這是因為,由證到供的印證方式僅僅只有其他證據對口供的單向印證,可能存在“虛假印證”“制造印證”之嫌,可靠程度、可信程度較小。但是,在由供到證的印證方式中,一些隱蔽性很強的物證、書證來源于口供,同時又對口供形成了反向印證,實現了雙向印證,可靠程度、可信程度較大。總結而言,口供印證規則呈現的是口供與其他證據之間的線型印證關系,只是這種證據規則可以表現出由證到供的印證方式和由供到證的印證方式兩種形式而已。
目前而言,司法實踐當中口供印證規則的具體運用并未嚴格按照《刑事訴訟法解釋》的有關規定執行,并不一味強調偵查人員必須根據口供找到隱蔽性很強的物證、書證,而是要求其他證據能夠擔保口供的真實性,尤其強調通過客觀性較強的實物證據擔保口供的真實性。這種做法其實是把口供的雙向印證變成了單向印證,降低了口供的印證難度。這種做法的形成原因主要基于以下兩點。第一,并非在所有刑事案件當中,偵查人員都能根據口供找到隱蔽性很強的實物證據,因此并非所有刑事案件的審判人員都能按照《刑事訴訟法解釋》第141條的規定達到法定證明要求。第二,《刑事訴訟法解釋》第141條沒有明確解釋“隱蔽性較強”的具體含義,控辯審三方對“隱蔽性較強”可能有著不同的理解,從而導致審判人員審查判斷口供是否獲得雙向印證的可操作性不強。
2.印證的范圍
我國《刑事訴訟法解釋》第141 條對口供需要獲得印證的范圍規定比較模糊,僅僅指出辦案人員必須根據口供找到隱蔽性很強的物證、書證,并且刑事案件的其他證據能夠與口供相互印證。物證、書證屬于客觀性較強的實物證據,它們承載案件事實或者信息的穩定性較強,不容易被篡改,《刑事訴訟法解釋》增加這一規定的目的就是為了防止偵查人員“制造印證”“虛假印證”。目前而言,我國刑事審判實踐已經確立了“實物證據定案標準”,這是口供印證范圍的最低限度。“實物證據定案標準”要求口供必須得到實物證據的印證,犯罪構成要件事實的客觀方面得到充分證明。①參見李曉杰、陳靜《論言詞證據補強規則的建立——以客觀性證據為補強基礎》,《人民司法(應用)》,2016年第13期,第68頁。這種做法非常接近日本“罪體說”或者美國“主要犯罪事實證明說”的理論觀點。
目前而言,最高法院基于口供沒有獲得實物證據的印證,已經撤銷原判、發回重審多起案件。在李萬華故意殺人、盜竊案中,李萬華對檢方指控的殺人、盜竊事實沒有異議,辯護律師作出故意傷害致死的罪輕辯護。但是,最高法院基于“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裁定撤銷原判、發回重審。究其原因,就是因為刑事案件中的口供只能得到言詞證據的印證,沒有實物證據對其進行印證,犯罪現場沒有提取到衣物、相關指印、腳印等與李萬華相關的物證,又未在被害人的雙手甲床內檢驗出異物,也無證人證實李萬華進入過現場。因此,本案無法排除第三人作案的可能性,犯罪構成要件事實的客觀方面無法得到證成,刑事案件處于“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無法排除合理懷疑”的狀態。②參見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辦)《刑事審判參考(總第100集)》,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年,第38-42頁。
值得注意的是,基于部分刑事案件類型的特殊性,刑事案件確實沒有實物證據存在,審判人員此時嚴格執行“實物證據定案標準”可能會放縱犯罪行為。此時,“實物證據定案標準”會有相應松動。譬如,強奸案件、貪污受賄案件可能只有言詞證據能夠印證口供,那么審判人員只能通過積累言詞證據的數量達到口供充分印證的效果。
3.印證的程度
通過對比我國《刑事訴訟法解釋》第140 條和第141條的規定,可以看出我國對口供的印證要求采用“相對說”的理論觀點,只要口供和其他證據結合起來能夠達到法定證明要求即可。但是,部分實務部門人員認為,“對于重罪案件,如殺人、搶劫等重大案件和可能處以死刑、無期徒刑等刑罰的案件,應當嚴格限制被告人口供的證明作用,要求能證明案件事實,并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程度”[7]。根據《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5條之規定,死刑案件的口供必須得到全方位的印證,這種規定說明了死刑案件的口供印證程度高于一般刑事案件的口供印證程度,需要達到“絕對說”理論觀點的印證程度。①《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5條規定:“辦理死刑案件,對于以下事實的證明必須達到證據確實、充分:(一)被指控的犯罪事實的發生;(二)被告人實施了犯罪行為與被告人實施犯罪行為的時間、地點、手段、后果以及其他情節;(三)影響被告人定罪的身份情況;(四)被告人有刑事責任能力;(五)被告人的罪過;(六)是否共同犯罪及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七)對被告人從重處罰的事實。”
4.印證的效力
按照印證證據是否能夠對待印證證據形成印證關系,印證的效力可以劃分成為肯定效力和否定效力。其中,肯定效力是指口供獲得其他證據的印證之后,審判人員可以據此判定被追訴人有罪的積極效果。否定效力是指口供得不到其他證據的印證,審判人員必須作出無罪判決的消極效果。一般而言,口供的法定印證模式十分強調口供印證的肯定效力,只有特殊情況下口供印證的否定效力才會發揮作用。具體而言,如果被追訴人的認罪態度比較穩定,不同口供的證據事實之間沒有較大出入,那么只要單個口供能夠獲得其他證據的印證,審判人員即可認定案件事實,作出有罪判決。易言之,在被追訴人認罪態度比較穩定的情況下,口供印證的肯定效力發揮主要作用,審判人員可以直接作出有罪判決。
但是,如果被追訴人的認罪態度出現反復,不同口供的證據事實之間出現矛盾,那么即使單個口供能夠獲得其他證據的印證,審判人員也不能夠認定案件事實,不能作出有罪判決,審判人員還必須綜合全案證據進行反向疑點排除。這是因為刑事案件當中能夠獲得印證的口供可能并非被追訴人對犯罪事實的唯一陳述,刑事案件可能存在多份口供,其他沒有獲得印證的口供可能直接指向被追訴人沒有實施犯罪行為。因此,審判人員必須同時運用其他證據對被追訴人的翻供理由或者無罪辯解進行反向證偽,否則審判人員只能作出“存疑有利于被追訴人”的無罪判決。易言之,在被追訴人認罪態度出現反復的情況下,口供印證的否定效力大于口供印證的肯定效力,如果審判人員無法成功消除口供與其他證據之間的疑點或者矛盾,那么只能作出無罪判決。
五、代結語:我國口供印證模式的發展趨勢
總的來說,我國《刑事訴訟法》及其司法解釋關于口供的證據規則可以劃分成為兩類,一是通過口供的證據能力規則解決口供的合法性問題,二是通過口供的證明力規則解決口供的真實性問題。其實,兩類證據規則的規范效果屬于一種“此消彼長”關系,口供的證據能力規則越發達,那么適用口供證明力規則進行規范的必要性也就越小,這也是法定證據主義轉向自由心證主義的邏輯基礎。但是,如果口供的證據能力規則不發達,或者不能有效發揮其應有的規范作用,那么通過口供證明力規則保障口供真實性的必要性也就越大。目前而言,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實施的乏力直接造就了法定印證模式的口供印證規則。未來,我國規范口供的證據規則將會呈現出一種兩級分化傾向。一方面,隨著立法者和司法者深入地推進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立法和實施,口供的證據能力規則可能成為規范口供的主導證據規則,我國口供印證規則將從法定印證模式回歸到消極印證模式。另一方面,如果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仍然不能有效規范口供的合法性問題,那么法定印證模式的口供印證規則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持續存在,并且發揮作用。這種情況下,為了能夠使口供印證的審查判斷更加科學化,更多審判人員審查判斷口供印證的經驗法則將會逐漸上升成為證據規則,口供的法定印證標準將從“罪體標準”逐漸走向“可信性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