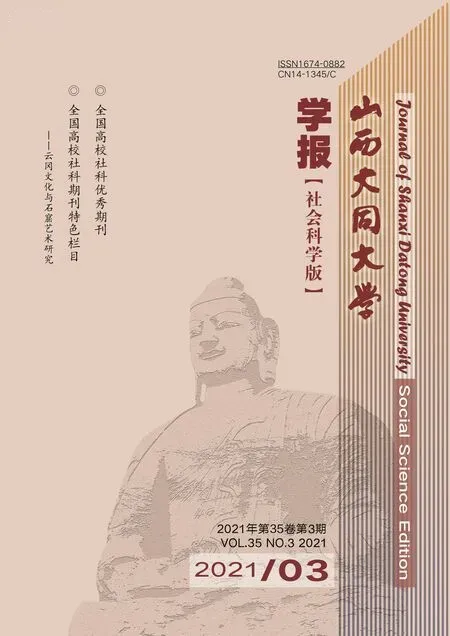疫情視角下的公安機關家庭暴力干預
——以浙江省S地區為例
沈可心,曾范敬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涉外警務學院,北京 100038)
家庭暴力,又稱親密伙伴暴力,是指在親密關系中,關系一方對另一方的生理、心理和性傷害行為。家庭暴力存在于各個群體中,而女性成為最可能的受害者。但是,男性受害者也不應受到忽視,男性受害者數量的減少源于男性舉報暴力的可能性降低。社會經濟地位、教育水平也是影響家庭暴力的因素。社會經濟地位和教育水平較低的家庭往往更容易發生家庭暴力。然而,在當今生活和工作壓力倍增的情況下,社會經濟地位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也可能造成家庭暴力的發生,特別是在男性主導的文化中,擁有高等教育水平的女性被認為挑戰了男性權威而面臨家庭暴力的風險。失業也會增加家庭暴力的發生率。每次全球大衰退時期,高失業率成為家庭暴力的“觸發點”,無力供養家庭產生的受挫感常導致暴力行為的發生。[1]同時,童年經歷或目睹過家庭暴力的人在長大后更可能遭遇或實施家庭暴力。學者Gerino將之歸因于認知因素,認為有類似經歷的人會將家庭關系中的暴力行為合法化。[2]學者陳月提出,施暴者因早期的經歷和已經形成的扭曲性格而產生心理健康問題,進而導致成年后以暴力解決問題的思維定式。[3]
家庭暴力在自然災害、人為災害等災難時會有所上升。以2005年卡特里娜颶風發生時期為例,密西西比地區基于性別的暴力提升了四倍;[4]2011年新西蘭基督城地震期間,家庭暴力上升53%。[5]家庭暴力發生率不僅在災難期間有所上升,其后幾年的環境恢復期仍保持上升趨勢。可以說,家庭暴力不僅隨著環境的改變而展現出突發性,也具有持續性特征。
一、新冠疫情對家庭暴力產生的影響
新冠疫情成為影響家庭關系的因素之一。疫情發生突然,成為近百年來人類遭遇的影響范圍最廣的全球性大流行病。為了避免病毒傳播,保持社交距離、居家隔離等公共安全措施在全國至全球范圍內擴散實施。然而,為了保護公共健康進行的隔離措施導致高危人群易受風險的概率上升。在可能面臨家庭暴力危險的個體中,居家隔離政策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據湖北省荊州市監利縣藍天下婦女兒童維權會數據顯示,疫情期間家庭暴力舉報數翻倍,且90%的家庭暴力與新冠疫情有關。英國衛報報道稱,巴西家庭暴力事件上升40-50%;西班牙一地區政府報告在隔離前期求助熱線上升20%;英國家庭暴力求助熱線上升25%。[6]美國福布斯雜志報道稱,阿根廷、澳大利亞、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南非、美國等家庭暴力報道均有上升,部分歐盟國家在封鎖期間家庭暴力數上升三分之一。[7]家庭暴力上升的原因主要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因疫情帶來的恐懼和焦慮加倍。此次疫情具有突發性、高風險和蔓延快的特點,其防控難度已遠超此前歷次公共衛生事件。疫情爆發初期,病理尚未明確,各類傳言此消彼長,死亡人數也急劇上升,造成人們極度的不安全感和危機感。一方面,施暴者將實施暴力作為發泄渠道,以緩解內心的焦慮和煩躁;另一方面,施暴者借機利用新冠疫情向受害者灌輸恐懼與服從以達到強制性控制的目的。第二,家庭面臨的經濟和社交限制。居家隔離帶來的最直接的影響是人們外出活動和經濟活動的減少。疫情期間,大部分企業停產停業,致使個人和家庭的經濟收入減少。經濟收入的減少帶來經濟安全感的缺失,導致一方對伴侶施加更多的控制。[9]同時,疫情改變了家庭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包括重構家庭生活、與家庭成員相處時間的延長以及與其他人接觸減少,這些都會增加家庭成員的壓力,特別是那些原本就充滿矛盾的緊張的家庭關系。調解機制的缺失以及原既定生活的紊亂助長了暴力行為的升級甚至犯罪。居家隔離政策使得受害者被迫與施暴者全天候24小時共同隔離在家中,為施暴者進一步實施控制提供了可能。施暴者以易被傳染為由阻止受害者尋求外界幫助,或者進行信息封鎖,通過傳播錯誤信息進一步控制受害者的行為和思想。[10]第三,受害者支持系統的弱化。家庭之所以容易發生暴力行為,是因為其內部權力的扭曲和破壞而缺乏外部群體的監督。疫情期間,家庭暴力的隱蔽性得到進一步加強。在施暴者全天候的監視下,受害者既不能在最短時間內尋求有效的幫助,潛在舉報者也因缺少了解渠道而難以及時阻止家庭暴力的發生。
二、浙江省S地區家庭暴力調研及分析
新冠疫情對社會的各個方面產生了深刻影響,也改變了潛在的犯罪。以家庭暴力案件為例,由于受害者與施暴者共同生活的時間延長,為防止因警察介入而可能遭受到更嚴重的傷害,家庭暴力的報警率可能會降低。同時,居家隔離也可能使施暴者施暴能力下降,而受害者報警率上升;或者,居家隔離使得施暴者變本加厲,受害者的報警率上升。文章選取浙江省S地區為實證研究對象,分析疫情期間家庭暴力報警率的變化。
S地區現有人口數為84.3萬人,其中流動人口數為43.4萬人,戶籍人口數為40.9萬人。下轄9個鎮(街道)。新冠疫情期間,S地區于2020年1月底至2月底實施嚴格的居家隔離政策,小區封閉,非必要、非重要崗位者不出門。由于疫情防控有力,于3月開始逐步恢復正常生產生活秩序。在數據搜集過程中,以2020年2月至8月的報警電話為基礎,參考2019年數據進行同期對比。
2020年2月至8月,S地區家庭暴力報警數為789件,同比上升16.4%。2-3月份是居家隔離政策實施最嚴格的時期,家庭暴力發生率在各時段均有上升。居家隔離帶來的最直接的影響是人們外出活動和經濟活動的減少,導致施暴者和受暴者共同生活時間延長。對于那些本就籠罩在暴力陰影下的受害者來說,居家隔離使得施暴者有了更多的可乘之機;而在那些本不存在暴力行為的親密關系中,隨著疫情在全國至全球范圍內的迅速擴散,人們承受著被感染的風險,加之工作壓力和面臨失業的恐懼,可能使得家庭成員之間長期積累的矛盾加深直至爆發而產生暴力行為。此外,壓力上漲會促使人們酒精攝入量的增加。酒精攝入,特別是達到有害攝入時是發生家庭暴力的主要原因。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0年2月,全國食品煙酒類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達到1至8月的最高值。酒精攝入不僅使家庭暴力發生率上升,其嚴重程度也會加劇。從施暴者角度出發,酒精攝入會直接導致認知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的下降,使得個體無法通過談判等非暴力方式解決沖突;從受害者角度出發,在受到暴力傷害后,酒精成為個體緩解傷痛的自我治療手段。
隨著居家隔離政策的逐步放寬和生產生活秩序的恢復,人們外出時間增加。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0年4月客運量超過2月的3倍,約為3月的1.5倍;4月餐飲收入約為2月的2倍和3月的1.4倍。[13]外出時間的增加使得個體情緒宣泄渠道增加,施暴者和受害者共同生活時間減少,家庭暴力發生率在4月明顯下降。6月初北京新發地出現確診病例,并小范圍擴散。該時期S地區家庭暴力發生率在夜晚至凌晨時段顯著上升。可以推測是因在保持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下,北京疫情的出現導致人們夜晚外出活動減少,家庭成員夜晚居家時間延長而導致家庭暴力發生率上升。
從數量上看,2020年2-8月,男性實施的家庭暴力報警數占報警總數的90.4%,其中丈夫對妻子實施的家庭暴力報警數占比71.9%,父親對孩子實施的占比9.9%,兒子對父母實施的占比4.9%。相比2019年同期,男性實施的家庭暴力報警數上漲6%,女性上漲25%。從反復程度上看,在報警內容中涉及“一直”、“經常”、“又”等詞語的施暴者多為男性。從嚴重程度上看,由男性實施的家庭暴力中有87.8%屬于肢體暴力,7.8%攜帶工具實施,其中丈夫對妻子實施的以刀、棍、酒瓶為主,父親對孩子實施的以衣架、木條為主。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女性實施的家庭暴力總數較低,但其中有15.4%的女性使用了工具,且使用菜刀的占據較多數。
從報警人身份來看,受害者是最主要的報警主體,占比90%;非當事人的報警數占比9.9%,同比上升1.9%。在非當事人報警的案件中,由小孩報警的父母之間實施家庭暴力的比例為49.3%,與2019年同期相比上升10.9%;鄰居報警的比例為40.3%,同比上升34.5%;路人報警的比例5.9%,同比下降29.1%;保安是今年出現的新的報警主體,其報警的比例為4.5%。從以上數據可以發現,居家時間的延長改變了非當事人,特別是鄰居的報警動機。在居住緊密的樓房,鄰居更有機會聽到或看到暴力事件的發生而導致報警數上升;而隨著疫情防控期間保安巡邏的加強,保安成為家庭暴力的舉報者和第一干預者。
通過上述數據的整理與分析可以發現,疫情與家庭暴力發生率有著密切的聯系。居家隔離措施帶來的家庭暴力受害者“暴露時間”的延長、疫情帶來的家庭經濟壓力的上升、家庭成員心理壓力的加劇、情緒宣泄渠道的減少、家庭矛盾的積累……種種因素加劇著個體自控能力的下降而導致暴力行為發生。家庭暴力發生后,施暴者、受害者、證人等相關人員成為行為干預的第一步。然而,由于婚姻、血緣、贍養、撫養等特殊關系的存在,為了維護彼此間的關系和“家丑不可外揚”的心理,受害者選擇“能忍則忍”;而證人也本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態度進行調解,其結局往往是家庭暴力行為的升級和擴散。在施暴者全天候的密切監視下,受害者只能尋找時機利用電話、網絡等方式尋求救助。居家隔離措施導致潛在舉報者的干預作用難以發揮實效,尋求公安機關進行干預成為受害者和潛在舉報者的現實選擇。公安機關如何利用公權力進行家庭暴力的有效干預,采取何種措施避免家庭暴力升級而一招制勝,成為公安機關解決家庭暴力案件的重要考量。
三、對公安機關干預家庭暴力的討論
公安機關干預家庭暴力是指公安機關及人民警察依法對已發生或可能發生的家庭暴力采取的預防、制止和處置的行政和刑事執法行為。[12]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的頒布和實施,公安機關在工作實踐中有了總體的指導和規范。在接處警過程中,也更加關注家庭暴力事件的發生以及行使權力的規范化。但是,家庭內部本身的排外性和封閉性以及受傳統觀念的影響,仍有一部分公安民警不愿介入家庭矛盾,對干預家庭暴力存在畏難情緒。同時,出于維護和諧家庭生活的目的,公安民警在處置家庭暴力案件過程中往往采取息事寧人、相安無事的態度,不僅難以取得應有的干預效果,對施暴者也缺少震懾力而可能縱容家庭暴力,繼續發生,受害者也從此喪失對公安機關的信心而可能采取極端的“自救”措施,引起社會矛盾的擴大。此外,家庭暴力并不是簡單的糾紛、暴力事件,而是一系列復雜矛盾構成的社會問題,單靠公安機關一個部門是絕不能完成的。
作為干預家庭暴力的重要參與者之一,公安機關起著防范和阻止家庭暴力行為發生和升級的關鍵作用。疫情期間,家庭暴力的隱蔽性進一步加強。在家庭成員外出和社交活動減少、施暴者全天候的密切監視下,受害者只能通過電話、網絡等方式尋求救助。同時,居家隔離政策使得潛在舉報者“愛莫能助”,公安機關成為受害者尋求救濟的主要渠道。因此,在處置家庭暴力案件中,公安機關不僅要更新執法理念,提高對家庭暴力事件的重視度,也要注意自身角色的轉換,從消極的調解者身份轉變成積極的行政執法者。[13]同時,也要帶動社區、婦聯、社會組織等主體的參與,發揮其調解作用。具體來說,第一,未雨綢繆,及時取證。疫情期間施暴者與受害者接觸親密且持續,受害者尋求救濟的機會稀缺,且往往等到暴力行為不斷升級而再也無法忍受后選擇報警。公安機關在接到相關警情后需要提高重視,注意報警人話語的隱蔽性,提取關鍵信息并及時處警。在處警過程中,受害人往往因夾雜著感情因素而選擇調解,在辦案民警取證時也不愿意配合做筆錄、驗傷,導致取證難度增加。因此,處警民警需提高取證意識,防止一時貪懶造成今后補正難、調解難、處罰難的現象出現。第二,善用“告誡”,震懾家暴。公安部門的介入是制止家庭暴力的最有效、最成功的手段。[14]家庭暴力相對隱蔽,又具有反復的可能,在面對家庭暴力案件時如處置不當可能難以發揮應有的干預效果,不能有效應對受害者的求助,反而導致故意傷害的繼續,甚至民轉刑惡性案件的發生。2020年以來,S地區共接家庭暴力類案件789起,開具《家庭暴力案件告誡書》172份。相對于調解處理這一對施暴者毫無震懾力的處置方式,告誡手段有效阻隔了家庭暴力的隱蔽性和反復性。第三,重點走訪,聯動關注。社會隔離不等于社會孤立,公安機關作為疫情防控的主要力量之一,不應以防控為由推諉、拖延家庭暴力事件的處置。在做好個人防護的前提下,配合村居、社區和計生等部門,加強對發生過和易發生家庭暴力及經常因家庭瑣事發生糾紛的家庭開展走訪,做到定期動態掌控。同時,在走訪過程中開展有針對性的談話,幫助強勢方端正態度,學會克制;幫助弱勢方找到防范或者避免家庭暴力的方法,鼓勵受害方在必要時拿起法律武器捍衛合法權益。第四,拓寬渠道,事后保障。公安機關可以加設線上線下家庭暴力求助渠道,開通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的報警功能,安撫并提醒報警人對現場狀況、受害者傷勢情況等相關證據的收集和保留。
四、結論
家庭暴力的發生是一系列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包括性別、年齡、童年經歷、社會經濟地位、教育水平、失業率等內部因素,也包括他人實施暴力行為的潛在影響、社會性別的不平等、社會資源和機會的短缺、自然或人為災害等外部因素。新冠肺炎疫情成為影響家庭暴力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疫情不僅帶來了家庭暴力事件的上漲,也改變著公安機關的工作方式。公安機關在更新執法理念的同時要注意自身角色的轉換,做到事前預防、事中制止,事后保障,切實發揮家庭暴力的干預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