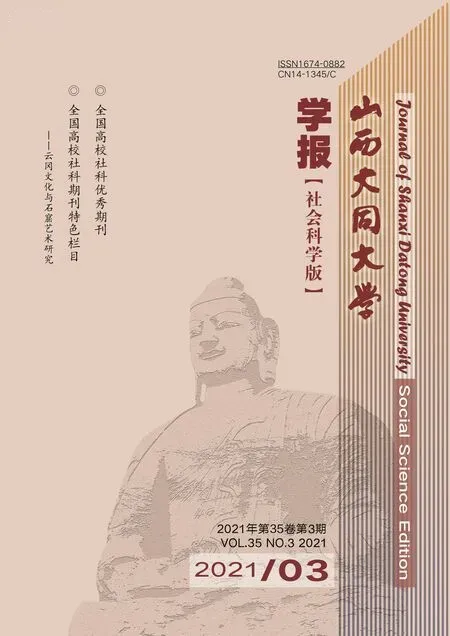八十年代文學坐標系上的曹乃謙
——重讀《到黑夜想你沒辦法——溫家窯風景》
李丹宇
(忻州師范學院中文系,山西 忻州 034000)
山西作家曹乃謙的創作經歷頗為曲折,38歲才開始寫小說,1988年,因汪曾祺力推在《北京文學》上發表短篇小說正式走上文壇,其后,他用十年時間寫的《到黑夜想你沒辦法》,起初不被國內出版社看好,直到2005年才在中國臺灣出版,2006年馬悅然翻譯的瑞典譯本出版,然后才有簡體中文版。之后,由于瑞典漢學家、諾貝爾文學獎評委馬悅然的盛贊與舉薦,曹乃謙又一度成為備受文壇矚目的作家,但巨大的爭議隨之而來。針對馬悅然“曹乃謙是中國最一流的作家之一”的說法,評論界比較一致的看法是“獨具特色,卻難稱一流,”[1]“曹乃謙與一流作家還是有差距的”。[2]不可否認,曹乃謙作品中原汁原味的鄉土語言、粗鄙凡俗的“溫家窯風景”、土頭土腦的雁北風情,成為普通讀者難以跨越的接受鴻溝,所以當時主流學界對“曹乃謙熱”的反應是失語或拒絕,此后便逐漸趨于沉寂。“曹乃謙效應”曇花一現不免令人深思。從2007年興起“曹乃謙熱”,至今又過了十多個年頭,重讀曹乃謙的《到黑夜想你沒辦法》,可以發現,曹乃謙長久被中國的文壇主流所忽視,主因是其游離于潮流脈搏的躍動,而我們往往習慣于在潮流之中看作家。可以說,曹乃謙在八十年代文學坐標系中,既非一流,也非主流,卻因其小說與八十年代文學潮流的離合關系而別具韻味。
一
《到黑夜想你沒辦法》主要描寫山西雁北地區曾經極度貧困的生活。曹乃謙把小說所描寫的背景放置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之交的“文革”時期,作者自己說:“《到黑夜想你沒辦法》一書的時代背景是在一九七三年以前。”[3]從其描寫的內容看應該屬于反思文學,但細細品讀,又覺得他站在反思文學坐標系之外。這主要體現在他對歷史的拷問和人性的思考方面,較之潮流中的反思文學作品,明顯呈現出非主流的超越性。
“反思文學”一般是用來指稱八十年代初期繼“傷痕文學”之后的一種文學思潮。反思文學雖不再滿足于僅僅對荒謬政治進行揭露和控訴,而是開始思索造成歷史創傷的深層原因。反思文學與傷痕文學一致的是幾乎所有的文本都將反思對象指向了政治和時代,“對于當代歷史的曲折,又大多主要從革命政治權力在當代的命運的角度,來處理現象,提出問題。”[4](P260)在反思文學作品中,對反思角度有著先入之見的創作者們將其視角鎖定在政治和時代層面,卻忽視了對歷史背景下人性復雜性的深度思考,從而導致反思小說忽略了許多更應該反思的隱匿性內容,諸如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凝滯保守的落后文化、扭曲異化的復雜人性等方面,特別是缺乏對人性的具體表現和深刻剖析,凸顯其對“左傾”思想及其根源的淺層次批判。
曹乃謙小說中的“文革”開會場景,以及獨斷專行的人物形象,都使我們意會到這里所指“曾經的時代”是七十年代。由此看來,作者有反思“文革”時代的創作意圖,并非個別論者所言:曹乃謙“將人物從其所屬的社會歷史環境中孤立出來單純受困于本能欲望。”[5]但曹乃謙關心的是人類的生存狀態,“我想告訴現今的人們和將來一百年乃至一千年以后的人們,你們的有些同胞、你們的有些祖先曾經是這樣活著的。”[6](P101)其與眾不同之處正在于擺脫傳統的政治反思角度,將視角轉向了人,因此,其筆下的人物不再是王蒙、高曉聲、張賢亮、古華等作家筆下飽受極左政治戕害或者民粹主義道德想象下的“人民”,而是在生存線上掙扎的“國民”,正如曹乃謙所說,“我這本書不是寫政治的,我是寫生活在最基層的人們的生活。”[6](P162)
曹乃謙直面苦難與愚妄,表現出對人本身存在狀態的思考。他毫無隱諱地寫出在貧窮中熬煎的“溫家窯”。溫家窯人窮到有時連衣服都是一家人伙同換著穿,土炕上裱幾層從礦上撿回來的洋灰紙,“窮得總有好些男人一輩子娶不起老婆的”(《黑女》)。《愣二瘋了》里的愣二想吃一頓不和山藥蛋的莜面窩窩的愿望始終無法實現,最后因娶不起媳婦發瘋。《賊》中的板女總在感嘆:“唉——窮死了”,她為給奶哥哥弄點吃的做了賊,先到地里偷,摘點黑豆莢、玉茭棒,刨幾窩山藥蛋,最后又偷了公家的白面烙餅吃了個飽,卻為此被法院判了兩年,還被五成兒貨丈夫打斷了腿。反思小說中也有關于饑餓的經典描寫,如《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和《綠化樹》,但這些作品并沒有觸及到生存的本能世界,因此有些不夠原生原狀。《犯人李銅鐘的故事》甚至還帶有一定的理想主義色彩。曹乃謙小說之所以不同于許多反思文學中描寫饑餓的小說,就是因為他不僅描寫了貧窮帶來種種基本生存需要的匱乏,而且刻畫了一個個被生存本能拖向非理性世界的形象。
在曹乃謙的筆下,性欲貫穿了小說文本的始末,成為作者另一突出描寫的內容。其小說中引人注目的光棍群體,如愣二、福牛、羊娃、狗子、玉茭、下等兵等等,經受著非正常生活狀態下性的悲劇,以及這種情境下人性所受到的折磨和蛻變。《到黑夜想你沒辦法》中多篇涉及亂倫情節,母子亂倫(《愣二瘋了》《玉茭》)、父女亂倫(《天日》)、嬸侄亂倫(《看田》)、兄妹亂倫(《狗子、狗子》)、兄弟朋鍋(《男人》),這些本性渾金璞玉的村民,被生理欲望降服,逐漸變得心理扭曲、人格變態,不僅摧毀了自己,也使他人深受傷害,最終讓生命瀕臨錯亂,甚至走向終結。比如,玉茭家窮到沒法兒給兒子娶妻以致出了有違倫理的丑事,最后玉茭領罪被餓死。按照農村習俗家里給死去的玉茭娶鬼妻,村民們同情地安慰玉茭媽,這下玉茭終于有了個女人,你該笑才對。玉茭媽“想裝笑可笑不出,差點兒又要放開聲哭”(《玉茭》)。在作者平淡描寫的背后是極其嚴酷的日常生活,極度困窘的生存狀況及生命本能欲望的驅動力量,蠶食侵吞著溫家窯人道德上的愧意,情感的錯位昭示了溫家窯人生存的卑微、荒謬和心靈的無所皈依。
談到寫性,也許有人會立即想到文革后寫性的第一人——張賢亮,其《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被認為是反思文學的代表作。的確,對于剛剛從“文革”中走出來的中國人來說,還處于談性色變的蒙昧狀態,張賢亮大膽挑戰這個被長時間遮蔽的文學命題,可謂顛覆性之舉。然而今天看來他的作品也只是把人們的視線和注意力集中在性書寫上,而未集中在對其中性的獨特思考和咀嚼上。也就是說,張賢亮將“性”引入敘事,是以原始的生命形式見證那個荒謬的年代,目的仍然在于發掘政治內涵,如同劉心武提出的“救救孩子”一樣,張賢亮更多地聚焦主人公命運沉浮所預示的知識分子問題,因此,其關于“政治與性”的書寫不能不受到問題結構的牽制而失去人性的光澤。
曹乃謙則借“性”入手,在中國傳統親情倫理的大背景上剖析人的非常態心理。他所反思的是特殊時期人性本身的復雜性。這樣的思考已經超越了七十年代時空所限,面對人類生存困境的永恒難題,曹乃謙從存在意義上揭示了受難歷史背后人性的向度,這也正是反思文學所缺憾的,而“文本的魅力和生命力是同基于它對人性審美把握的深度和廣度而表現出來的超前性成正比的”。[7](P92)
因此說,曹乃謙并沒有徹底放棄講述歷史的沖動,他以對意識形態的疏離為其文學追求的起點。如果說“文革”后八十年代反思文學作家以人民代言人的角色自居,那么曹乃謙則是自覺的國民精神啟蒙者與批判者。從文學精神上說,他對國民文化心理痼疾的揭示體現的正是回歸“五四”傳統的新啟蒙意識。無疑,曹乃謙的“溫家窯風景”與魯迅的“未莊社會”在精神啟蒙上一脈相承。透過曹乃謙的文本,也可發現一顆滴血的心在吶喊,其中對人性的冷靜諦視和魯迅的無情解剖一樣達到使人戰栗的程度。玉茭向人們炫耀自己在城里“加入了殺人放火團,還敢鬧女人的事”,在莊稼地攔截女人后,看到群專來了著實有點怕,但四五天后沒見什么動靜便完全不放在心上了。讀到這里我們無一不會想到阿Q做小偷和向吳媽求愛的悲劇。《親家》中的黑旦與親家關于彩禮的約定,每少給親家一千塊彩禮需要付出的代價是自己的女人每年要到他那里住一個月。黑旦送女人到親家那里時,“送過一道一道的梁,又送過一道一道的溝”,從中不難窺見其內心無法抑制的煎熬和屈辱,但黑旦以阿Q式隱忍獲得自我慰藉:“球。去吧去吧。人家少要一千塊,就頂是把個女兒白給了咱兒。”再看小說里那個“臉上的皺紋像耕過沒耙過的山坡地兒、下巴的胡子像羊啃過沒啃凈的墳頭草的人”,可以宣判玉茭的死刑,還鼓動溫孩懲治女人,簡直就是溫家窯的“古久先生”。魯迅鄉土小說中的每個人物無不是從歷史深處走來,帶著我們這個民族的苦難記憶,帶著我們這個民族的精神衰變和文化沉落的累累印痕。由此而言,曹乃謙接續了魯迅小說對人性深度透視的傳統,超越單純的鄉村立場,筆鋒真正觸及到鄉民的內在靈魂。
二
《到黑夜想你沒辦法》從敘述方式看很接近于新寫實小說,即把溫家窯原生態的生活內容和農民近乎凝滯的生存方式,還原式地展示給讀者,作者一般不參與其中,也不妄下評論。同時,從發表時間來看,1988年也應該置于新寫實小說潮流的潮頭。
新寫實小說中關于貧困的敘寫同樣觸目驚心,如《狗日的糧食》中癭袋女人曹杏花從騾子糞里淘洗出玉米粒煮給全家人吃,《風景》中一家十一口擠住在十三平方米的“河南棚子”里艱難地生活著;但新寫實小說極寫這種貧困狀態下人的惡俗,卻很少拷問造成貧困的原因以及貧困狀態下人性的異化。新寫實作家也執著于寫人的基本欲望,寫人的非理性,比如劉恒的《伏羲伏羲》;但是其更多地呈現出“情欲、情愛”傾向,是在人性中挖掘潛藏的自然主義因素,而不是狀寫貧困生活逼迫下的一種無奈和痛楚。而且,在劉恒、方方、劉震云等新寫實作家作品中,隱去了“文革”歷史場景,只是以總體氛圍和隱喻性書寫暗示出時代背景。這樣,新寫實小說“基本上不是一種有意識地反思和批判,而只是一種無言的呈示”。[8](P519)“零度情感寫作”的美學追求遮蔽了作家的態度,因此新寫實小說沒有對人物的庸俗低劣的人生追求表示不滿或憤懣,消失了針砭社會的熱情,拋棄了現實主義文學的精髓——“理性的深度,即理性批判精神”。[9](P163)總之,相對于傳統現實主義而言,新寫實小說作家的身份由啟蒙者、吶喊者轉變為原生態生活的觀察者、體驗者與記錄者。正如有的學者所言:“新寫實派過于注重形而下的真實性,形而上的缺失使靈魂搏斗的必要性與激烈度大大降低,人性所需的本質沖突呈扁平趨勢。”[10](P343)
然而,曹乃謙小說看似不帶感情,但透過其原生態描寫,我們會明顯地感受到作者心中強烈的同情、愛憎以及兩難態度。
一方面,曾經的山西雁北地區苦寒閉塞落后,卻保留了原始質樸的民風世相,雁北黃土地上的民眾土氣、敦厚、善良、樸實,曹乃謙筆下的溫家窯人同樣有著當地人求真求善的傳統和樸素的道德觀。《老銀銀》中的老銀銀要尋短見首先想到跳井,但一思謀臟了井水村民咋喝便作罷;要去尋死還想著節約燈油,返回窯里把原先打算為其魂靈照路的“長明燈”吹滅。《三寡婦》中的三寡婦被爹賣到窯子里受盡凌辱,但她還是選擇寬宥和忘卻,她知道爹是沒法子的。《親家》中黑旦的女人為了自己兒子能娶上媳婦要被親家接走住一個月,送行時黑旦瞭見自己女人吊在驢肚下一悠一悠的兩只腳,心里頭也在打悠悠,但他堅定地認為“中國人說話得算話”。《狗子》中的狗子勇敢地頂著雞蛋大的冷蛋去苫公家的土坯,卻沒據此邀功請賞,被采訪時表現出憨直的本性。
另一方面,由于雁北地區的封閉和凝滯,長期居于一隅的鄉民,因襲著沉重的傳統習慣,形成較為穩固的惰性。曹乃謙小說里不僅再現了黃土地上古老的民風民俗,并且深入挖掘,揭出與之相應的集體無意識,同時基于文化視域將其提升到存在的高度上進行審視,表現出濃濃的悲憫情懷。在相對偏僻原始古樸的溫家窯,宿命思想是束縛人們的無形枷鎖。《莜麥秸窩里》中丑哥對自己心愛的姑娘被迫嫁給“窯黑子”一事無能為力,甚至認為自己應該安之若命,是自己命運多舛。而被籠罩在男權倫理社會和封建舊勢力陰影下的女人們,則背負著傳統宿命觀的厚重包袱,她們被迫屈從于世俗的規矩甚而影響到下一代。《女人》里溫孩總算用兩千塊錢娶了女人,女人過門后卻不順從丈夫,白天不出地也不做飯,于是,在溫孩媽和村人的唆使下,溫孩“揳得女人臉上盡黑青”,終于女人被打服帖了。更可悲的是慫恿兒子打女人的溫孩媽當年就是這樣被溫孩爹整治過來的,但她還是認為“樹得括打括打才直溜,女人就是個這”。不僅如此,令人憂心的還有溫孩媽背后那個龐大的群體,地里那些以看客心理欣賞溫孩女人臉上黑青的女人們,她們“撇嘴兒,眨眼兒,搖頭兒”,表現出幸災樂禍的痛快,這個群體便是魯迅所說的“做穩了奴隸的人們”。女性命運的悲哀讓人辛酸,女性的蒙昧和被奴化更讓人痛心;而男人的自私自足自輕自賤則不免使人震驚。小說《蛋娃》中的蛋娃算計著怎么樣讓老柱柱叫其“脖工”,從而吃上自己心心念念的油炸糕;但眼看吃糕無望,他便折磨死蒼蠅,還罵罵咧咧地鋤斷老柱柱家的玉茭苗報復,暴露出狹隘自私的根性。《狗子、狗子》里的狗子奴性十足,會計叫他做啥他就做啥,甚至明知道喝會計家的剩飯要鬧肚子也不敢不喝,還裝出很香的樣子。會計要霸占他心愛的松木棺材,他也不敢不答應,最后竟采取了一種最無奈的辦法,把自己活活餓死在棺材里,以生命的代價保住了他的“大洋箱”。溫家窯人就這樣按照他們固有的價值體系生活著,不僅感知不到自己生存的卑微;反而自我滿足自得其樂,就如《老銀銀》中兩個瞎子喝酒時說的:“他有眼的哇,不也就是個羊頭就燒酒?”
當然,曹乃謙小說的情感傾向不是絕對地趨于愛或趨于恨,而是更多地將人本性中的自然性與社會性扭結在一起,在靈與肉的糾纏中對復雜人性進行縱深開掘。《黑女和她的二尾》中的黑女看到村里男人打光棍,心理思謀著“雞子還要匝匝蛋,狗子還要連連蛋。咱一個當女人的,總不能眼看著他們連個雞子狗子都不如。”于是以身相許。她以悖逆貞節觀念挑戰傳統倫理鄉俗,無疑是對社會道德的違背,卻又是一種不顧一切的無私獻身。《男人》中的老柱柱讓妻子與自己的弟弟“做那個啥”,老柱柱由不得支楞起耳朵聽著西房的動靜,心一會兒一驚一喜,一會兒一抖一顫,似真似幻的聲音傳來,震得他頭暈。那一起一落的心理變化,那左右為難的矛盾心態,兄弟相濡以沫謀求生存的溫情被畸形的婚戀事實沖淡了,弟弟交給哥哥給孩子捏三孔窯的紅布包更凸顯了等價交換的冷漠。作者冷靜地敘寫著溫家窯人的欲望狀態,敘述背后卻隱藏著一聲聲沉重的嘆息。
汪曾祺就認為,曹乃謙小說的敘述看起來不動聲色,但那是經過痛苦思索的。他說:“我們從曹乃謙對這樣的荒謬的生活做平平常常的敘述時,聽到一聲沉悶的喊叫:不行!不能這樣生活!作者對這樣的生活既未作為奇風異俗來著意渲染,沒有作輕浮的調侃;也沒有粉飾,只是恰如其分地作如實的敘述,而如實地敘述中抑制著悲痛。這種悲痛來自對這樣生活、這里的人的嚴重的關切。”[11]馬悅然也說:“曹乃謙冷靜狀態之下藏著對那山村居民的真正的愛,對他們的艱苦命運的猛烈的憎恨。”[12](P3)
三
批評家雷達先生曾憂慮思潮與文體的矛盾,慨嘆:“潮流循環不息,作家的追逐也不息,難得平靜下來修煉文體。”進一步坦言道:“在我看來,歷史上的好作品,大都是既在潮流之中,又與潮流保持著一定的審美距離。”[13](P4)
曹乃謙在潮流涌動的八十年代走上文壇,盡管其作品還不能說就是雷達先生企望的“好作品”,但他未隨波逐流,仍然堅守著自己的一片園地耕耘,尤其顯得難能可貴。
八十年代初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基本上可以定性為傳統現實主義文學,即使有些作品借用了現代派手法,但骨子里還是傳統的。就反思文學作品而言,其主要藝術特征就是“突現故事的政治背景和故事情節……由于要在每一篇作品中濃縮幾十年的故事,使‘反思’小說大多傾向于篇幅的拉長”。[14](P207)
八十年代末出現的新寫實小說則明顯有反撥傳統寫實的意味,還原式客觀敘事,近乎冷漠的敘述態度,消解典型意義,在很大程度上借鑒了自然主義、現代主義的藝術手法。
曹乃謙的小說突破了傳統小說的模式,一方面,他不刻意追求情節的曲折性,也不刻意追求人物的典型化,只是運用簡潔的對話、寫真式的細節以及自言自語式的心理活動來描述特定環境中人物的命運;另一方面,其小說風格又與同樣注重敘事的新寫實小說有異,更像是一種小品文體。
小品文本來是一種融敘事與抒情為一體的、短小精悍、言之有物的散文樣式。筆者以為小品文的文體特征首先在于其“小”,即“篇幅短小”。夏丐尊先生說:“從長短上說,二三百字乃至千字以內的短文稱為小品文。”[15](P2)其次則是“品”,有品評之意和品格之意,即小品文美在含蓄獨特、內蘊豐厚和情韻無限,即古人所謂的“金熔玉琢,節短音長”。[16](P1)好的小品文必然具有形式上惜墨如金而內容上意味深遠的特征。
曹乃謙小說的獨特之處正在于文筆的簡約和雋永。《到黑夜想你沒辦法——溫家窯風景》這部長篇小說實際是由30篇小說構成,獨立成章,應該為系列短篇,只是人物有交叉而已。看似平常的寥寥數語,在曹乃謙的語言組織下就成了一個故事,短句,短段,短章,語言短促,大多故事在五百字到兩千字左右,可謂惜字如金,而言外之意卻躍然紙上。例如,《親家》中只有34句話,其中寫對話就有19句;《莜麥秸窩里》只有55句,其中48句是對話。曹乃謙創作的其他作品也大多簡潔如此。以《莜麥秸窩里》為例,這篇小小說描述性的話語只有7句,其余都是對話,而且對話的語句特別簡單明了:
“丑哥保險可恨我。”
“不恨,窯黑子比我有錢。”
“有錢我也不花。悄悄兒攢上給丑哥娶女人。”
“我不要。”
“我要攢。”
“我不要。”
“你要要。”
……
“丑哥。”
……
“丑哥。”
“嗯?”
“要不,要不今兒我就先跟你做那個啥哇。”
“甭!甭!月婆在外前,這樣做是不可以的。咱溫家窯的姑娘是不可以這樣的。”
“嗯。那就等以后。我跟礦上回來。”
……
“丑哥。”
“嗯?”
“這是命。”
……
……
“咱倆命不好。”
“我不好。你好。”
“不好。”
“你好。”
“不好。”
“好。”
“就不好,就,不……”
幾句簡短的對話而且中間還插入對話間的沉默,卻把一對情人的真摯情感表露無遺,同時丑哥不忍心破壞姑娘的貞操,姑娘違心嫁人后又悄悄攢錢要給丑哥娶女人,這其中隱含的人物品性、買賣婚姻、歷史話語等等,足以讓讀者想象出一個曲折凄婉的愛情故事,可謂是文體省凈但是意韻深長。
可能有人會認為曹乃謙的小說充斥著丑和臟。其實,那些在自然主義、現代主義視域下津津樂道的欲望場景,在曹乃謙的筆端卻處理得節制而巧妙。同樣涉及亂倫描寫,新寫實作家劉恒在《伏羲伏羲》中不厭其煩地對亂倫的嬸侄倆之間不堪入目的細節作自然主義式摹寫,甚至還煞有介事地寫了楊天青死后赤裸的丑態;而曹乃謙在書寫亂倫時則多用敘事空缺方式,如《愣二瘋了》中愣二爹一走,愣二就瘋了,幾天后又莫名其妙的不瘋了,從愣二媽回避村人的詢問和“總比殺了人好”的自言自語中,讀者才會猜出個中原因。《親家》里黑蛋與親家的交易也需讀者慢慢品味。這種含蓄的表達符合中國人傳統的感情倫理表達方式,也符合山西雁北人獨特的地域文化心理,同時又有古典美學中留白表意的傳統特點。類似這樣的敘述在曹乃謙的小說中特別多。這種敘述風格很像短篇小說作家汪曾祺。“汪曾祺的小說耐讀、耐品、耐人尋味。”[17](P265)汪老也曾自評:“我永遠只是一個小品作家。我寫的一切,都是小品。”[18](P2)
除此之外,小品文內容上多寫普通人的日常瑣事,“真”成為小品文的靈魂。曹乃謙將生活中的真實人物直接作為小說中人物形象的寫作方法也近似于小品文的方法。在傳統小說中,塑造人物形象時虛構成分較多;而曹乃謙的小說大多數是按原型去狀寫,如愣二的原型就是一個要飯調唱得最好的叫二明的后生,溫寶的原型是小學校的王老師,丑幫的原型是北溫窯的幫幫。[6](P184)他不止一次地強調,他寫的都是真事兒。有記者提問他:“您的作品得到馬悅然這么高的評價,或者說國外如此認可您的作品,您自己覺得是您作品中的什么東西打動了他們?”曹乃謙毫不猶豫地回答:“真實。只有真實才能打動人。真實的情節,真實的細節。另外還得再加上真實的情感,這很重要。”[19](P194)而選取小人物的生活內容,著意表現天然的日常性和真情實感正是小品文的特色之一。
結語
曹乃謙用原汁原味的鄉土語言描摹著粗鄙凡俗的“溫家窯風景”,用苦心經營的敘事展示著土頭土腦的雁北風情,可以說,他整合了魯迅的沉郁和沈從文、汪曾祺的沖淡,游刃于五四以來鄉土文學的兩支流脈之中,再加上其提供現實生活純態事實的自然主義書寫,如同彈奏出一曲民族、通俗、原生態組合的旋律。曹乃謙這種執著于個體心靈的文學表述雖然在當時的文學潮流之外,卻揭示了文學的豐富性,從而凸現出作家及其作品的獨特價值。“真正的文學不是追趕新潮,并非一定非得與現代或后現代話語機制接軌,而是應該去表現人類真正的生存處境。”[20](P52)曹乃謙小說可能面臨傳播的困境,但其對新時期文學的意義不應被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