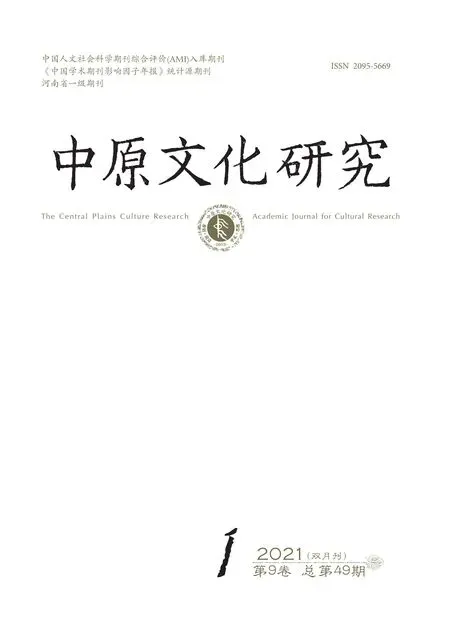晉豫風后神話傳說的歷史嬗變與文化記憶*
段友文 王子仙
20世紀80年代,德國埃及學家揚·阿斯曼將“集體記憶”的概念分解為“交往記憶”和“文化記憶”,首次提出:“文化記憶是關于一個社會的全部知識的總概念,在特定的互動框架之內,這些知識駕馭著人們的行為和體驗,并需要人們一代一代反復了解和熟練掌握它們。”[1]13此外,揚·阿斯曼在“傳統的形成”“對過去的指涉”“政治認同或想象”這些要點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了文化記憶的概念:
文化記憶是每個社會和每個時代所特有的重新使用的全部文字材料、圖片和禮儀儀式……的總合。通過對它們的“呵護”,每個社會和每個時代鞏固和傳達著自己的自我形象。它是一種集體使用的,主要(但不僅僅)涉及過去的知識,一個群體的認同性和獨特性的意識就依靠這種知識。[1]14-15
以上的論述將回憶、認同和文化的延續三者聯系在一起,并將其視為文化記憶理論的核心概念。“記憶是那種能夠使人類形成身份認同的能力”[2],每個個體以自身已有的記憶為出發點,同時不斷累積經驗,這些對過去的思考、感知都成為實現自我認同的基礎。
黃帝被視為中華民族的人文初祖,學界往往以其為核心,從古典文獻、歷史考古等角度對世系、古帝、祭祀三個系統中的黃帝形象進行考證,然而對其周圍的“群臣”較少關注。風后作為上古時期黃帝的臣屬,位列三公,助其戰敗蚩尤,統一華夏。以往學者曾依托“風后八陣圖”對中國陣法作溯源式的研究,從零星的史料中尋找“證據”,試圖構建出中華兵法的歷史發展軌跡[3]。但對于創制者風后而言,其歷史并不只是存在于典籍文獻中,更重要的是他作為群體的文化記憶保留在民眾的日常生活中。本文將從文化記憶的角度闡釋晉豫風后神話傳說,解讀其生成場域和衍生過程,構建其當代傳承保護體系,從而進一步探討文化記憶如何建構和塑造歷史以及如何影響地域群體的身份認同。
一、空間與記憶:風后神話傳說的生成場域
(一)風后神話傳說的地理生態解讀
在進入文明社會之前,原始人類以神秘性的思維方式認識世界,萬物被視為一種神秘的存在。這里的“神秘”并不意味著宗教性,而是“含有對力量、影響和行動這些為感覺所不能分辨和察覺的但仍然是實在的東西的信仰”[4]28。因此對這一時期神話傳說的研究不能用現代人的思維和視角來度量,而是要從其所處的地理環境出發,運用原始思維探尋其合理性。
風后神話傳說產生于新石器時代的中原地區,因海平面漲落和黃河、淮河、海河泥沙堆積等因素,上古中原的自然地理環境與今相比有很大的不同。據中科院青藏高原綜合科學考察隊的第四紀地質專題研究報告《西藏第四紀地質》中的《西藏全新世古環境和氣候變化圖式》可知,距今四千五百年(至遲約三千年)始,地球重新轉入冷干期,中原一帶逐漸變得不適宜人類長久居住,狂風、嚴寒成為主要的自然現象。此時,中國社會進入炎黃、顓頊時代,發生了中國歷史上三次“爭帝大戰”的重大事件,戰爭中雙方大量將風雨雷電等作為斗爭工具,以期望擁有自然的巨大威力來獲取勝利。在自然和社會雙重環境影響下,風后神話得以形成并流傳。上古時期空氣流動之自然風變為神性的風,并把這種強大的力量附著于神話人物身上,使其在部族社會發展的關鍵時期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早期人類在面對自然界的強大力量時,因生產力的低下和自身力量的弱小,往往將這些事物視為一種神秘的存在。然而,這種神秘思維也在一定程度上轉變為集體記憶沉淀于人的思想體系中,成為人認識世界的重要渠道。
(二)風后神話傳說的地方分布
“地方”不僅僅是古人“天圓地方”的宇宙觀,也是一個承載著文化空間和社會秩序的表述單位。古時地方未被劃分為現今的行政區域,地域分隔概念還不清晰,晉南、豫西毗鄰,文化上互通有無,交流和對話頻繁,兩地以風后為中心,依托豐富的物質實體資源,形成了既有聯系又有分異的“風后文化圈”。通過地方遺跡與文獻資料的相互佐證,風后的出生地、活動地和埋葬地分別為山西運城解州、河南具茨山和山西運城風陵渡,并以賢臣將相和地方神等多種形象保存在民眾的記憶里。
1.山西運城風后神話傳說
在現實的空間格局中,運城風后神話傳說的遺跡主要為因民眾信仰而建成廟宇、墓葬等人文景觀。據考證,風后的出生地為現今運城解州鎮社東村,早年間有一所占地二十多畝的風神廟,被毀于抗戰時期,但當地至今都流傳著有關風后神異出生以及名字由來的傳說。相傳,社東村有一對夫妻,到了晚年卻依然膝下無子。在他們準備放棄之時,一個兒子意外地降生在這個家庭,且唇紅齒白、聰明伶俐,生下來就會說話。兩位老人經受不住喜悅,竟相繼而亡。當鄰居們埋葬了兩位老人后,忽然一陣狂風將嬰兒吹向天空。嬰兒被大風裹挾著降落到芮城境內的九峰山上,被一位修行的仙師撿到,并教給他許多法術和特異功能。因孩子是大風帶來的,仙師認定他是女媧仙祖給自己選的孩子,便讓他姓“風”名“伯”。后人因尊敬風伯,將其稱為風后。在仙師去世后,他便離開九峰山外出仙游,途中結識了黃帝,開始了自己的政治、軍事和發明生涯[5]3-4。與典籍文獻中的有關記載不同,這一民間傳說描述的風后事跡更具有地方性,與女媧建立了聯系,顯示了民眾對風后濃厚的懷戀之情。此外,當地還產生了一系列的信仰活動,如每年農歷二月十五前后舉行的風圣廟會。廟會的歷史,其實就是民間信仰的歷史。這一民俗節慶強化了風后在村民心中神圣的地位,擴大了風后在民眾生活中的影響,它是風后信仰的產物,又進一步鞏固了風后信仰。
墓葬則是寄托民眾情感的另一文化空間。傳說在風后去世后,黃帝特意將這位大功臣葬回他戰斗過的地方——河東黃河大拐彎處臨河高原之上,現今風陵渡鎮西王村與趙村的交界處仍保留有風后冢。據《陜西省潼關縣地名志》記載:“風陵渡位于山西省的最南端,是晉、秦、豫三省的交界處,有‘雞叫一聲聽三省’之稱。因地處咽喉要沖,向為兵家必爭之地,是我省西南重要門戶。風陵渡鎮(趙村)東南約一里處,有‘風陵’,相傳是黃帝賢相風后之陵墓,風陵渡由此得名。”[6]133民眾通過墓葬這種記憶實體,追思先賢,傳承其英勇無畏精神。
2.河南具茨山風后神話傳說
以河南新鄭與新密交界的具茨山為軸心的文化圈,保留了大量的黃帝文化,是探研上古文明必須關注的地區。具茨山風后神話傳說與黃帝征戰的神話傳說內容緊密勾連,既有典籍的書面記載,又有實體的景觀呈現。與運城風后神話傳說以人文景觀為主的文化空間不同,具茨山風后神話傳說的遺跡主要呈現為因附會神話傳說而注入人文意蘊的自然景觀,如風后頂、講武山等。相傳黃帝在東海邊上訪得風后,把他請到具茨山,擔任宰相,代替自己發號施令。群山最高頂為風后居住處,即為風后頂。新密是黃帝建都之地,也是黃帝涿鹿之戰前屯兵備戰的大本營。《密縣志·山水志》載:“講武山在縣東南三十五里。黃帝常與風后講武于此,因名。”[7]237這些被賦予記憶與情感的自然景觀成為記錄神話傳說的物化載體,為風后文化記憶的延續發展提供了條件。
地方既具有儲存和喚起群體記憶的重要功能,也承擔著記憶的刻寫與重構。晉豫兩地以物質的形態將風后神話傳說凝固為在現實層面上可觸、可感的邊界和對象,以廟宇、墓葬、自然景觀等方式延續風后文化的內容和價值內涵。
二、象征與記憶:風后神話傳說的多樣延續
尤里·洛特曼將“能在自身凝結有關自己過去語境的記憶并加以保存與復原的所有符號稱為象征”,并指出它是“人類本體和文化記憶的保存者”[8]。原始社會生產力低下,人們對自己無法駕馭的物質產生崇拜、敬畏,日月星辰、風雨雷電、山川河流等自然現象和物象逐漸被形象化、人格化,成為展現原始先民最初精神世界的象征因子。正如丁山所說:“‘自然崇拜’,是宗教的發軔,任何原始民族都有此共同的俗尚。按照宗教發展過程說,崇拜自然界的動植物是比較原始的,由‘地母’崇拜到‘天父’,到祖先的鬼魂也成為神靈時,宗教的思想便告完全結束。”[9]3同樣,中國史前神話中的神靈也經歷了由自然神到社會神的繁難過渡。風后神話傳說的形成以萬物有靈的風神崇拜為信仰基礎,以儒家崇尚德行的思想主張為衍生動力,在后世的文化語境中不斷被賦予了新的象征內涵,使風后具備了神性與人性的雙重意蘊。
(一)風神崇拜:風后神話形成的信仰基礎
風神崇拜至少在商代就已經出現,根據出土的甲骨文獻資料可以看出,商人的信仰對象除了上帝、祖先神之外,還包括由風、雨、云、雪等現象構成的自然神①。眾多自然現象之所以被商人祭祀,究其根源,就在于在生產力極不發達的社會背景下,外在力量成為影響民眾生產生活的主導因素,使得商代的宗教信仰形成了“萬物有靈”的特征。在眾多自然現象中,與農業相關度最高的是雨,然而通過考察已出土的甲骨文,商人重視祭風神甚于祭雨神。首先,商代形成了系統的風神譜系,“東方曰析,風曰劦(協);南方曰因,風曰(凱);西方曰豐,風曰彝(夷);(北方曰)勹,風曰伇(冽)”[10]2046。在這里,四方之神與四風相配合,成為一個嚴密的復雜組織。其次,風作為“帝”的臣屬而存在,如“于帝史風二犬”[10]2040。最后,商代存在祭風來求雨或止雨的現象。如“其寧風(鳳)伊”“亡雨,(其)寧風(鳳)伊奭一小牢”[11]561。這條卜辭主要包含了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商人求風于伊尹、伊奭,來達到止雨的目的;二是商代“風”意假借“鳳”字來傳達,將風這種本身形象難以捉摸的現象具化為其他事物。《史記·殷本紀》載:“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12]91可見鳳或者說鳥在商人的信仰體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甚至于鳳鳥可能就是商人的圖騰。而商人因為對鳳鳥的崇拜,又提高了風的地位,這也從側面解釋了商人重視祭祀風的原因。
如果將商代末期的風神崇拜,概括為具有圖騰信仰特征的自然崇拜,那么周代風神的“人神化”特征開始顯現,但自然性因素仍占主導地位。屈原《離騷》:“前望舒使先驅兮,后飛廉使奔屬。”王逸注:“飛廉,風伯也。”[13]28飛廉的形象為一種神禽或神獸,并以現實存在之物出現在史書中。《漢書·武帝紀》載:“飛廉,神禽能致風氣者也。明帝永平五年,至長安迎取飛廉并銅馬。”[14]193該記載顯示東漢學者曾見過神禽飛廉,但出于現實考量,將此現象解釋為文人學者希望通過附加神物的方式,來達到強化帝王權威與王權統治的目的,則更具有可信度。
隨著民眾的思維方式和思想觀念的發展轉變,萬物所蘊含的原始色彩逐漸隱退、減少,人性因素超越神性因素,產生出一系列人格化的神靈形象,形成中國史前神話的人生意象集群②。在這些人生意象中,有一部分由自然意象轉化而來,具有人神相兼的身份,風后便為其中之一。如丁山先生所言:“若以《書·盤庚》‘我先神后’言,后亦先神之名,則風后即風神,猶《楚辭》之言風伯矣。”[15]335而與典籍文獻中記載的大量風神崇拜不同,風后的風神職能最早在漢、晉之后才被廣泛流傳,這一現象的出現與黃帝、伏羲地位日漸提高有密不可分的關系。顧頡剛先生在對上古史材料按其發生的次序進行排比性研究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了一個理性假設:“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發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統恰是一個反背。”[16]52該理論的核心要義在于“時代愈后,傳說的古史期愈長,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隨著秦漢大一統王朝的建立、統治者的政策引領以及民眾內心呼聲的提高,黃帝成為華夏統一精神的代表,相應的與其相關聯的風后事跡也不斷被創造、豐富和傳承,《事物紀原》“將相”條引《軒轅本紀》曰:“帝舉風后為相、力牧為將,此蓋將相之始也。”[17]212此外,因“太昊庖犧氏,風姓也”[18]3,風后與伏羲之間逐漸建立了聯系。將自然崇拜之物“風”擬人化,賦予了風后其人以神奇的本領,使其形象和施展神通的方式逐漸具象化,形成了在理性思維發展下特有的風后神話傳說。由此可見,風后的出現正是在一定的文化思想環境下,以潛在的方式接續殷商以來風神崇拜的結果,也是宗教倫理觀念對原始神話意象進行改造的結果。
任何文化都具有目的性,風神崇拜的實質在于風與人類生活關系的密切關系。萬物的生命和人類的生產,是風神崇拜的本質所在。從商周到漢、晉,風神形象經歷了從風—鳳—飛廉—風后的變化過程,這是華夏民族從萬物有靈觀念中走出的過程,亦是華夏先民宗教信仰建構的過程。
(二)尚德傳統:風后神話傳說的衍生動力
從神話的演變中不僅可以看出民族文化價值取向的變化軌跡,而且能清晰地折射出民族精神形成與定型的過程。逆向來看,中華民族精神的形成過程也是中國古代神話傳說被全面改造的過程,其中尚德思想的形成,使遠古時代的神話英雄逐漸披上了賢良的“外衣”,成為受人頂禮膜拜的對象。漢代以來,儒家學說作為正統思想一直占據著統治地位,推崇以仁義為核心的道德規范,眾多學者從哲學的角度對道德論進行規范和理論升華,并通過重新塑造神話傳說中的形象和行為的方式來體現這一思想。在這樣的文化語境中,風后成為助黃帝平定四海、統一華夏的大功臣,人性色彩逐漸濃厚。《史記》僅言黃帝舉風后,在之后的記載中其事跡愈加豐富。其中,關于風后的得名,《帝王世紀》言:“黃帝夢,……帝寤而嘆曰:‘風為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于是依二占而求之,得風后于海隅,登以為相。”[18]21風后以“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而得名,該傳說也成為后世創作“風后因風之神力以助黃帝作戰”傳說的基礎。通過對典籍文獻和活態資料的雙重對讀,可以看出,風后在成為黃帝陣營中的一員后,主要呈現為軍事始祖型和治國良相型兩種形象。
1.軍事始祖型
風后在黃帝戰蚩尤傳說中,其卓越的軍事成就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在涿鹿之戰中制指南車破蚩尤的功績。《事物紀原》“指南”條:“《志林》曰:‘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彌三日,人皆惑,帝令風后法斗機作指南車,以別四方。”[17]107除典籍文獻記載以外,民間口頭傳說也對風后在戰爭中表現出的謀略做了補充敘述:
交戰時雙方兵將混戰在一起不易分辨,足智多謀的風后便想出一則妙計,黃帝兵將出戰時,身上均佩戴一枚槐樹葉作為記號,如此便能分清敵我,黃帝部族因此打了勝仗。戰敗的蚩尤發覺了黃帝兵將身上佩戴有槐葉以作記號,便在再次出戰時,命令兵將也佩戴上槐葉,迷惑對方,以求亂中取勝。此舉讓風后知曉,交戰時,他便讓黃帝兵將佩戴上皂角樹葉,而蚩尤一方渾然不覺,仍然佩戴槐樹葉。雙方交戰之時正值炎熱的夏天,烈日當頭,蚩尤部族佩戴的槐樹葉經不住太陽暴曬很快就蔫了。而黃帝的兵將佩戴的皂角樹葉,卻耐得了太陽曬,依舊青綠。如此是敵是友一目了然,黃帝一方很快將蚩尤的士兵們斬殺,黃帝又取得了勝利。③
這些傳說同樣在新鄭、新密廣泛流傳,其故事情節大致相同,展現了風后卓越的軍事才能。
二是創作了《握奇經》《風后八陣圖》等兵書。因風后為黃帝的軍師,后世多有托名于風后的兵書,如《漢書·藝文志·兵書略》中的《風后》十三篇圖二卷[19]193,《文獻通考·經籍四十八》有《風后握奇經》一卷[20]1790。還有依據戰爭經驗所做的《風后八陣圖》,由唐代獨孤及所作的《重建風后八陣圖記碑》記載道:
黃帝受之,始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而命將。于是乎征不服、討不庭,其誰佐命?曰:“元老風后。”蓋戎行之不修,則師律用爽;陰謀之不作,則兇器何恃?故天命圣者,以廣戰術,俾懸衡于未然,察變于倚數,握機制勝,作為陣圖。夫八宮之位正,則數不僭,神不忒,故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衡抗于外,軸布于內,風云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以致用也。④
該碑文記述了八陣圖乃風后所作,并精練地敘述了風后八陣圖在實戰中所發揮的巨大作用,也使后人領略到上古時期兵法的精妙。《禹貢釋文》引《周公職錄圖》曰:“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21]39又言風后之圖乃天授之,以助黃帝統領九州,增加了風后制圖的神話色彩。
此外,還有關于風后造福于地方民眾的事跡。《路史》載:“風后為之(黃帝)相,因八卦設九宮,以安營壘,次定萬民之毳。黃帝滅蚩尤,徽猷多本于后尤,北復以其輕,其余于輞谷。人賴其利,遂世祀之,是為金山之神。”[22]62風后在助黃帝戰敗蚩尤后,又率輕兵在輞谷剿殺其余孽,百姓們因此受益,祭祀他為“金山之神”。有傳說道,風后本是天上的金山星。黃帝來到人間后,王母娘娘擔心他只身孤單,便派金山星下來做他的助手。以上關于風后的記載雖出現較晚,但所述之風后形象更加立體鮮明,反映了民眾對他的敬仰崇信之情。
2.治國良相型
風后被稱為“第一宰相”,不僅能上馬治軍,也能下馬治國。清《解州全志》的《建風神廟記》載:“軒轅黃帝氏相,姓風名后,解其故里也。廟建于城東南五里,其來遠矣。……予惟風后者,隆古之神圣。其生也,中條山、鹺海之英;其出也,應黃帝夢寐之感。配上臺之尊,為軒轅之師。上繼羲、農之治,后天以成務;下啟堯、舜之傳,先天以開人。民未宮室,相以制之;民未器用,相以作之;制度文為之未備,相以創立之。凡仰觀天道,俯察地宜,神化宜民,由于黃帝之裁,成者悉有以輔相之。史稱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23]271風后作為黃帝之師,上繼伏羲、神農,下啟堯、舜,教百姓建造房屋、使用工具、創造文字、制定法律,集多種成就于一身,在黃帝統一華夏進程中起到不可磨滅的作用。此外,還有關于風后為醫藥之神、善推演甲子的記載:“嘉靖二十一年,又修景惠殿,于太醫院祭祀三皇,配以句芒、祝融、風后、力牧等歷代醫師共二十八人配祀儀。”[24]59不可否認,善醫藥、制屋舍這些內容固然可能是后人附會,但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人們重務實、重民生的價值取向和思想觀念。將這些功績都歸功于風后,其根本原因也在于風后具有風之神力可助民眾開展農業生產,這一活動是人類生存的基礎性活動,也是華夏民族進入文明時代的佐證。
按照顧頡剛先生所指出的,“各時代的時勢”是了解各時代傳說古史的基礎。風后傳說的豐富,一定程度上也是漢儒學者不斷爭鳴、論證主張的結果。提倡“尚德”“仁義”等思想觀點是最終目的,豐富人物的事跡則是手段以及間接的結果。在向風后等人身上累積、追加事跡的過程中,除了滲透進各派的思想,還以一定的“素材”為依據。這些“素材”,就是所處時期的歷史事實。《史記·五帝本紀》是對黃帝神話傳說的一次系統整理。其中記載的黃帝“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是體現黃帝任用賢臣的主要事跡,也是風后之名首次出現的可考文獻。這一時期與之相對應的史實案例不勝枚舉,如齊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高傒修齊國政,……齊人皆說”[12]1487。還有秦穆公任用蹇叔、百里奚;秦始皇任用王翦、李斯;漢高祖任用蕭何、張良、韓信等。可以說“春秋之后,中國文化是在理性的時代復制和發展著上古神話中所表達的基本文化精神和心理范型的”[25]106。而上古神話傳說的內容則在一定程度上敘說著正在發展著的歷史。在天、地、神、人所組成的思維結構中,人占據了核心的地位,乃至于成為神以及自然的主人。而也正因時代思想發展的需要,風后神話傳說才能以豐富的內容和深厚的意蘊存在于民眾的歷史記憶中,歷久彌新。
三、融合與傳承:風后神話傳說的當代演述
“歷史事件的‘文本化’和‘去文本化’是形成和創作文化記憶的過程”[26]。文本化指在神話傳說的演變中,文化記錄者從他的立場出發選取“有意義的事件”,“寫成”該符號系統的記憶文本。文化記憶的釋放則需要經歷一個逆向的過程——“去文本化”。文化接受者在面對前人編寫好的符號程序時,通過自我探尋和重建解碼,從事件的敘述中還原事件,從記錄中賦予記憶不同的意義。風后神話傳說以典籍文獻之類的舊文本為依據,歷經時代的變遷,融入了民眾運用不同解碼進行闡釋的所有記憶,生成了無數具有特定歷史文化內涵的新代碼。基于晉豫兩地不同的依托載體,風后神話傳說產生的新代碼主要呈現為河南境內的文化景觀再造和山西古河東地區的廟會祭祀活動等。其中河南具茨山文化圈主要以自然景觀為載體,以黃帝文化為核心,風后文化色彩并不明顯。而以風后信仰為核心的山西運城社東村的廟會祭祀及演藝活動,是風后神話傳說在流傳的過程中與當地民眾的生產生活相融合而產生的典型新代碼,其目的在于以祭祀之形式,行崇拜之實踐,從而達到歷史真實與神化虛構的統一。
“廟會的實質在于民間信仰,其核心在于神靈的供奉,它可以是一種很大規模的群體性的信仰活動,也可以是一個村莊,一個家族的信仰活動;所有的娛樂都應該是圍繞某種信仰活動的具體展開而進行的”[27]3。風后崇拜盛行于以運城鹽湖區社東村為核心的地區,這一現象的形成既是上層統治者利用人們對賢臣良相的愛戴、崇敬與祭典的社會心理,有意引導和設計成為個人崇拜的一大創制,也是地方民眾將自己祈求風調雨順、生活美滿等愿望寄寓在神話傳說中的精神產物。
每年農歷二月十五,運城鹽湖區社東村會隆重舉行一次為期三天的古廟會,民眾稱其為“風圣廟會”。而風后與社東村的聯系,則主要體現為兩個方面:一是風后作為地方衛士守護一方民眾。傳說風后二月十五誕生于社東村,在建立功勛后,重新回到家鄉,教人們生產生活的各種技能,深受愛戴。后人為紀念風后,特建造過一座“風圣廟”,而且村東村西的出入口,曾立有名為“風后故里”的石碣石碑。從這則傳說可以看出,在社東村這一文化空間里,風后雖保留有黃帝屬臣這一身份,但更被濃墨重彩描繪的是其建設故里社東村的種種事跡,地方性特征明顯。二是社東村村民以風后后代自居。風圣廟是風圣廟會的核心信仰空間,也被稱為祖神廟。據村里年長者講述:“每年二月十五廟會期間都要請運城的蒲劇團唱三天的大戲,小時候自己在祖神廟里唱戲,現在在新建的社東舞臺上唱。”③人們將風后稱為始祖,既是出于家鄉情結崇拜地方圣人的直接體現,也是同根同脈的文化心理的民族共性使然,極大地增強了地方民眾的身份認同感。
風圣廟會最興盛時期曾吸引了來自河南、陜西、安徽、寧夏、甘肅、內蒙古等省區多達五六萬人參會,足可見人們對風后根深蒂固的敬仰、崇拜之情。但在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風圣廟被完全毀壞,石碑“風后故里”也被敲碎③,社東村風后的實體符號逐漸脫離了現實生活,只保留于民眾的歷史記憶中。但在高揚民族精神、強調文化自信的今天,實現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是各區域社會發展的重中之重。我們認為,在新時代的社會背景下重塑晉豫風后文化,主要包括以下兩方面:
一是構建黃帝譜系,實現風后文化與黃帝文化的整體性保護。黃帝譜系的建構,不僅要考察黃帝世系的形成,還要關注圍繞在他身邊的群臣。以往,運城、新鄭、新密市政府在塑造地域文化形象時,建造了以黃河文化和黃帝文化為底蘊的印象風陵渡景區與具茨山風景區,卻鮮少關注周邊的風后嶺等自然人文景觀,或只將其視為黃帝的依附產物,對背后的文化意蘊缺乏了解,這顯然不利于呈現文化的全貌。建構風后文化的保護體系,就要在整體的文化關聯中觀照其演化過程,實現風后文化與黃帝文化的整體性保護,即“將自然地理環境、人文社會景觀、神話傳說文本、文化傳承主體視為一個相互依存、彼此關切、良性互動的文化生態系統,促進它們和諧共生、協調發展”[28]。具體而言,要重構晉豫風后文化空間,依托神話傳說資源,把運城風陵渡、新鄭風后嶺等自然景觀與風后陵、風后廟等人文景觀納入到統一的傳承體系中,形成文化修復與重建的合力。民眾既是傳承的主體,也是文化記憶的所有者,要增強其文化自覺意識,喚醒其文化記憶,進而完成傳承地方文化的歷史使命。只有多重力量共同促進,才能激活文化遺產的潛在能量,創造出文化繁榮與經濟效益的雙贏局面。
二是弘揚賢臣德政,探尋華夏君臣文化之源。《商君書·畫策》言:“神農既沒,……故黃帝作為君臣上下之義、義子兄弟之禮、夫婦妃匹之合,內行刀鋸,外用甲兵。”[29]106商君以此來表明黃帝時期為適應社會現狀的需要建立了君臣秩序。《云笈七簽·卷二》亦言:“黃帝以來,始有君臣父子,尊卑以別,貴賤有殊。”[30]9兩者都表明“君臣上下之義”始于黃帝時期。其中,作為群臣之一的風后,為黃帝三公之首,輔佐黃帝治國安邦,以德治民,以德興邦,受到萬民敬仰。后代官吏崇拜風后之德澤,不少曾給其冢培植封土,有的還為其修繕祠廟。《蒲州府志》載:“明萬歷三十八年,蒲州知府張羽翔擴充廟墓,重建祠宇。蓋享堂三間,門樓一間,東西房六間,易民間地五畝零,南北長四十九步,界石立表,堂宇輝煌,風后之德澤恍然如新也。”[31]79民國12年(1923年),當地人士欲賣風后廟古柏集資重建享殿,河東道尹崔廷獻聞訊,遂倡議捐款修復,由尚琦章彩繪山海經故事,一邊是黃帝請風后為相,一邊是風后輔佐黃帝破蚩尤。2000年清明節,臺灣省易經姓名學會在風后陵祭祀以后,曾立了一通石碑以表追思之情。長期以來,風陵渡鎮一帶都有民眾前來祭祀,“香火年年盛,英靈世世昌”,表達了后人的敬仰和懷念。
綜上,建立晉豫風后文化的傳承保護體系,既要對記憶場域進行聯動式的整合和重塑,構造晉豫風后文化圈;又要增強記憶主體的傳承意識,提高其文化自覺;還要深入挖掘文化記憶功能,為構建德政清明的政治生態提供文化模式。只有從多角度探尋民眾文化記憶的形成機制,才能從根源處找到實現風后文化“兩創”發展的內源性動力。
結語
“在文化記憶中,基于事實的歷史被轉化為回憶的歷史,從而變成了神話。”[32]46本文從文化記憶的角度出發考證神話傳說的文本書寫和空間場域,實際上即是對神話的歷時流變和共時播布情況進行的研究梳理。風后神話傳說是萬物有靈的原始思維和黃帝、蚩尤部落沖突相互作用的產物,在后世崇尚德行的文化語境中不斷被賦予了“人性”因素,風后形象因而完成了由自然神到社會神的繁難過渡。河南具茨山地區和山西運城是風后神話傳說的主要承載地,兩地不同的文化環境塑造出了文化景觀再造和廟會祭祀活動兩種迥異的當代展演形式。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風后文化的物化實體不斷減少,民眾對風后的記憶也存在逐漸模糊的傾向。因而,新時代整合風后文化資源,促進晉豫兩地跨區域聯動式保護機制的形成,實現由文化資源向文化資本的良性轉化,應成為政、校、企等多方開展多維度深入合作的重要方向。
注釋
①根據出土的甲骨文獻,近世學者將商人的神靈譜系分為上帝、自然神、祖先神三個系統。其中“帝”是權能最高的至上神。參見晁福林《論殷代神權》,《中國社會科學》1990年第1 期。②此處借用王懷義在討論“史前神話意象的基本類型”時的相關概念,即按照史前神話中神靈的形象,將神話意象分為自然意象和人生意象,自然意象來自于原始先民對自然現象和自然物象的崇拜,人生意象由神奇、多樣的動植物合體的形象逐漸轉變為完全人性之后形成的神靈形象。參見王懷義《中國史前神話意象》,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版,第138 頁。③訪談材料。講述人:段堪新,男,1933年生,運城市解州社東村人。調查人:段友文、樂晶、苗賢君。調查時間:2016年7月23日。調查地點:運城市解州社東村。④碑刻資料。《重建風后八陣圖記碑》,時至元二十七年歲次庚寅中秋日重建。碑刻規格:高213cm,寬92cm,厚26cm,黃帝宮山門內的軒轅門、講武祖洞前。調查人:段友文、閆咚婉、劉國臣、冀薈竹、王子仙。調查時間:2018年7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