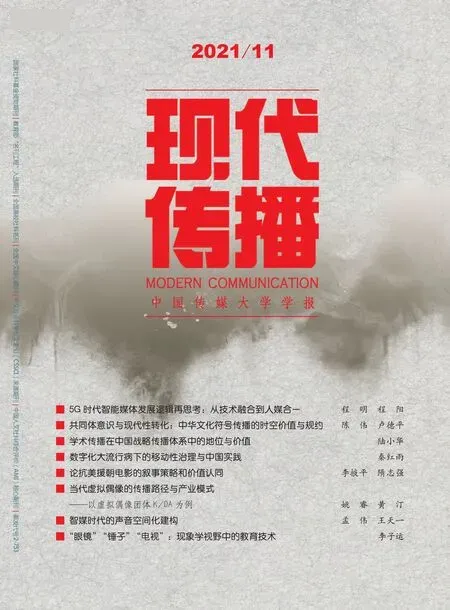數字化大流行病下的移動性治理與中國實踐*
■ 秦紅雨
肆虐世界的新冠疫情,被社會學家吉登斯稱為“數字化大流行病(digi-demic)”,因為“它深深地卷入了一個數字化的世界”,連“應對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數字化的”①。疫情不僅讓全球同此涼熱,強烈感受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真切含義,更讓人類對全球化、網絡化下現實地理和虛擬地理的“移動”充滿了憂慮和擔心,“讓這個流動性日益加強的世界(正如我們過去所熟知)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②同時,面對美國病毒溯源“政治化”的操弄,乃至意識形態方面的對抗,不得不進一步思考“在當今人類圈、生物圈和地球圈相互作用的全球危機中,如何確定西方世界所能提供的潛在信息”③,這對于向世界總結、傳播和分享中國的抗疫經驗,亦十分關鍵。新冠疫情,不僅讓人們看到“世界是平的”背后的“暗流涌動”,更讓人們思考“數字化大流行病”下“移動性”治理的優劣,畢竟“地球上多元文明之間的相互理解不僅是象牙塔學者的詩意夢想,而且是我們當下迫切需要完成的社會使命”④,這將“涉及到社會學、地理學、人口學、交通、傳播媒介化和政治權威的形式等跨學科視角”⑤,也為人們認識當今“移動性社會”的本質和趨勢提供了難得的觀察視角。正是基于此,借助新冠病毒傳播對“移動性”社會治理構成的挑戰,思考中國社會“移動性”治理經驗,有助于總結數字化社會“移動性”治理的得與失,反思“移動性”治理的未來發展空間和改進策略。
一、“移動性”社會已成為“地球村”的現實
隨著各種交流技術、現代交通方式的飛速發展,人與人之間的時空距離驟然縮短,國際交往日益頻繁便利,整個世界變成了地球村,貿易流動帶來了空間的擴張和觀念的跨國交流⑥,印刷帶動了物質、技術和勞力的流動,讓行動者網絡迅速就從本地擴展到國與國之間⑦,“移動”成為世界的常態,“流動性”成為現代性的典型特征⑧,“這些流動由資本、勞動力、商品、信息和形象構成”⑨。社會學、地理學、文化學、歷史學、經濟學、媒介學等不同學科領域的學者也對社會“移動性”治理給予了不同的學科觀照,為分析“移動性”社會提供了多樣的學理支撐和豐富的觀察視角。
從空間維度看,“移動性”重構社會治理的邊界。“離開流動我們將無法認識空間,無論是哪一種流動——光、聲、人、疾病、商品、訊息,等等。沒有流動空間根本無法存在,……空間中的生活經驗需要人的身體在不同位置的移動才能感覺得到。”⑩列斐伏爾從空間生產(the production of space)的角度,提出了“空間流動”的判斷,認為空間是具體化的、時間性的、歷史性的,空間的流動形塑著社會構型,也重組著都市中的社會關系,“真正是一種充斥著各種意識形態的產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空間流動”在不同階段也產生了不同的空間及其生產形式。哈特和奈格里在《帝國》中,認為帝國主義為了滿足跨國公司資本流動的本能,只好重新塑造新的地理空間,經濟“被控制在由高度分化、高度流動的結構(highly differentiated and mobile structures)構成的全球權力網絡之中”;大衛·哈維則揭示了新自由主義在地理上的不平衡發展的現實,強調新自由主義資本自由流動帶來的危害和維護資本主義壟斷階級利益的實質,“全世界的空間被非領土化,被剝奪了它們先前的各種意義,然后再按照殖民地和帝國行政管理的便利來非領土化”,同時他告訴人們以資本自由流動為主的“新自由主義的引入不是某個霸權勢力,例如美國,強制推行一些正統模式的結果,而是多樣化、創新和競爭(經常是一種壟斷型競爭)的結果,這些競爭包括民族間、區域間、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是大城市間治理方式和經濟發展模式的競爭。”卡斯特則從網絡社會的角度,強調“網絡社會流動”的價值,讓人們重思“流動空間”的價值與作用。
從媒介角度看,“移動性”挑戰和重構社會網絡。交通和交往技術的改進使人類社會交往互動的范圍不斷擴大,構建了一個天上、地上、地下相配合,線上與線下相結合的立體化交往網絡。歷史學家麥克尼爾認為人類發展的歷史是各種相互交往的網絡的發展歷史,從“弓與箭”這種古老技術在世界大部分地區的傳播,到地域性網絡的形成,到各種都市網絡的緊密聯系,再到海路大通之后的世界性網絡形成,以及電報技術下世界性網絡的“電子化”,人類始終都處在各種相互交往的互動當中,“人類彼此交換信息,并且使得這些信息來指導他們下一步的行動。他們也彼此交換或傳輸各種有益的技術、物品、農作物、觀念等等。更進一步,人們還可能在無意間交換著各種疾病、無用的廢物,以及那些看似無用但是卻關系到他們生存(或死亡)的種種事物。”從媒介學的角度,有學者提出“流動性已崛起為一種主導型隱喻——不僅在建筑學和城市主義中是如此,而且可用來描述當代社會生活的狀況。”各種媒體技術的改進不僅建構了“移動中的城市”,還生產了“電子游牧者”:“這個城市的居民常將它體驗為一種令人迷失方向的‘垃圾空間’,但在不受限制的市場的庇護下,它卻又是一個受到密切監視的區域。”隨著都市建設的不斷推進,各種媒介在建筑、交通、商業、文化等領域日益頻繁的使用,構成了一道移動的城市風景,“物理上的移動性和虛擬的移動性相生相伴”。而凱文·林奇關于城市景觀“流動”與認知的判斷,斯科特·拉什對“流動的客體和主體”的分析,厄里關于游客流動和游客凝視辯證關系的梳理,則為人們認識當今社會的“移動性”現實提供了生動的景觀、旅游等案例。
從社會的角度說,移動性重構和更新社會治理的理念。正如馬克思所說:“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已經消逝,現在代之而起的已經是各個民族各方面互相往來和各方面互相依賴了。”移動不僅帶來空間的巨變,也帶來風險的加劇。自然、人文、意識形態等方面的沖突對抗不斷出現,都考驗著各國政府的社會治理能力。麥克尼爾在《全球史》中提出了“生物—地理—化學流動”的“人類之網”“我們已經開創了一個嶄新的地球時代——人類紀(the anthropocene)——在這一時代里,人類的行為已經成為影響生物演化和地球這個行星‘生物—地理—化學流動’以及地理演進過程的最為重要的因素”,在日益流動的城市里,不僅物體、空間、技術、商品等的改變在加速,城市的歷史、形象、制度、文化也在迅速地消費化,也“提出了有關城市的公共文化的基本問題”。過去,全球化語境中“世界是平的”判斷成為全球熱詞,“9·11”恐怖襲擊事件和世界金融危機,更讓人們感覺到世界互聯互通、榮辱與共。客體(物品、資本、貨幣、通訊、商品)以及主體(勞動力、移民、旅游者)不斷擴大的加速流動,“描述的情形令人振奮,可是其意蘊令人不安。因為這種加速既‘壓縮’了時間和空間,又使社會關系‘疏遠’,正導致主、客體的掏空。加速的流動使得客體變得可任意處理,一次性使用,其重要性下降,而社會關系則掏空了意義。”而此次到現在還看不到頭的新冠疫情,不僅讓我們看到了病毒快速流過“地球村”的恐怖,也讓我們看到“病毒”移動背后的地域“鴻溝”,更讓我們見識了病毒傳播的“文明沖突”和文化差異。“移動性有意義的和意識形態的編碼可以反映一定背景面的社會態度和社會實踐。”在擔心、憂慮、痛心但同時又扼腕、驚訝、憤怒的過程中,人們看到了“病毒”移動應對和效果的巨大反差。
二、新冠疫情下“移動性”風險分析
今天的移動性社會,在大衛·哈維、吉登斯、卡斯特等人的研究和判斷中,分別稱為“液態社會”“流動性社會”“網絡社會”,并將移動性和網絡技術發展、現代性、空間重組乃至技術進步緊密聯系在一起。彼得·阿迪將前人的研究進行綜合,從移動性空間、移動性政治、移動性文化三個層面探究了現代社會“移動性”特性。在筆者看來,新冠病毒的快速移動與傳播,考驗著一個社會對移動性空間、移動性政治、移動性文化風險的化解。
(一)在空間上,病毒傳播帶來空間風險
移動性空間分為物理空間和精神空間,病毒傳播首先沖擊的是物理空間,病毒在每一個地方的傳播,都考驗著空間的反應能力、阻斷能力、動員能力和制度性規制。“空間是統治和管理手段最重要的一環,是一種有效用的治理技術,空間被應用到政治中來,而且產生巨大的實際性的政治效果。”而精神空間的知、情、意,則和人的社會聯系密切相連,正如馬克思所說,“人在積極地實現自己本質的過程中創造、生產人的社會聯系、社會本質”。而在今天的數字化社會,信息技術和信息流動對于當代人的精神空間重塑發揮著重要作用,“媒介就是我們的境況、我們的命運,以及我們面臨的挑戰。”正因為如此,伴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的是“信息疫情”(info-demic),情緒傳染、恐慌蔓延、虛假難辨、謠言滿天飛,成為“后真相時代”的典型表征。正如卡斯特所說,“網絡化邏輯會導致較高層級的社會決定作用甚至經由網絡表現出來的特殊社會利益:流動的權力優先于權力的流動”。全媒體時代信息的影響力、“信息疫情”的破壞力和公眾精神空間重塑相互共振,為人們提供了一個審視網絡社會治理的一次機會,也為思考今天的網絡化生存提供了空間。
(二)在政治上,病毒的信息傳播激化意識形態沖突
近年來,逆全球化、貿易爭端、難民、移民、隔離墻修建、國家開放程度等的討論,背后都涉及國家移動性治理等問題,能否處理好這一難題也成為考驗各國政府的政治難題。移動背后帶來的移動治理難題,也成為考驗各國政府的重要維度。基于自由主義的移動性治理,著重強調個體價值和自由權利,讓政府管理的混亂、無序和無力暴露在世人面前。西方社會在這次病毒的傳播下,遭受了很大的沖擊和損害,其民眾的抗議、封城的反復、疫苗的謊言、對中國的指責的背后掩蓋著政府移動性治理的失效。“這場阻擊戰已經將我們生存環境中一種病毒的存在帶入了整個國家甚至世界的政治生活中。……病毒也是政治的一種本體。”因此,移動性的治理,不僅成為健康社會的良好體現,更考驗著政府治理的現代化和治理能力的水平。“移動提供了政治的空間,能通過塑造一個人的競爭、對抗和反對的能力來讓我們更加政治化。”世界貿易聯系的日益緊密、信息傳播的全球化和環境危機的日益加劇,也造成了病毒傳播的快速與便捷。無論是病毒的溯源,還是對病毒傳播的認識,以及對病毒的有效控制,都成為一個嚴肅的科學問題和社會問題。“移動既對傳播做出反應,又促進著傳播,傳播既是移動的動因也是它的結果。”但是,在新冠疫情當中,病毒被政治化,或者說病毒的“移動性”被肆意政治化,甚至變成一種意識形態攻擊“工具”,這不僅讓“病毒移動”成為政治化抹黑的替罪羊,更與美國試圖發動的新冷戰相輔相成,威脅著更加健康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
(三)在文化上,病毒的文化認知影響共同體重塑
在這次新冠疫情防控中,關于戴口罩、必要封城、有限流動、對病毒的大數據追蹤等,都成為中西抗疫手段比較及民間熱議的大事件。因此,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將文化差異作為中西抗疫效果殊異的歸納,確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將中國乃至東亞的抗疫成功經驗歸結為“專制文化”的影響,也看出其思想依然是西方中心論的脈絡。自近代以來,中國對于工業革命驅動的全球“流動”有著深刻的體悟和歷史教訓,也引發了國人對“流動性”不一樣的體察和認知。在工業革命的驅動下,西方帝國借助船堅炮利,迫使中國被動進入全球現代化進程,也促使中國人反思閉關自守帶來的落后與屈辱:從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引進,到新中國舊貌換新顏的努力;從重開國門的改革開放,到社會各要素有序流動釋放的活力;從對世界貿易、全球化的恐懼和疑慮,到積極肯定和認同,逐漸形成了中國獨特的移動性空間和移動性文化。同時,過快的社會流動所帶來的城鄉撕裂、自然環境危機、社會空間改造難題,乃至SARS病毒突現帶來的警示,讓我國也始終警惕和反思“移動性文化”所釋放的負面因子。因此,基于近代以來的歷史經驗與教訓、現實挑戰與困境,我國對傳染性病毒采取了更加積極果敢的認識和行動,才有對“移動性文化”更加科學的認知和反思,這才是中國抗疫成功的基石。而反觀歐美工業革命以來形成的“移動性”文化,整體上是以自由主義思想為指導,以個體自由的最大化為根基,以政府鼓勵資本要素為主的全球移動為動力,形成了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以全球為對象的殖民掠奪、以全球貿易為目標的世界體系、以優勢技術為依托的霸權文化,構筑了300多年來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強勢地位。其根深蒂固的力量在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后都沒有根本扭轉,日益增多的難民、種族仇恨和恐怖主義沒能讓他們根本反思,惡化的氣候變化、生態災難更沒有改變他們的霸權心態。面對這樣一個劇烈的“移動性”時代,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關于“移動性”的文化仍然停留在帝國的光輝和霸權暢想中,新冠病毒的肆虐和抗疫失敗無疑再一次給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深深地上了一課。
三、新冠病毒“移動性”治理的中國實踐分析
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家治理現代化是中國現代化的重要維度。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我國第一次提出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命題,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又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治理能力現代化日益受到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來全球發生的最嚴重的傳染病大流行,其全球“移動”無疑是抗疫的重點和難點。因此對于病毒“移動”的控制、治理乃至思考不僅影響著我們今天對世界的認識,也能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古老的魔法世界和現代科技領域的融合和延續”。而中國以人民生命健康作為考慮的首要目標,在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下取得了非凡的抗疫“戰果”,不僅守護了中國和許多發展中國家人民的生命安全,為全球戰“疫”做出了突出貢獻,而且貫穿著偉大抗疫精神的“移動性”治理,是中國積極運用第四次工業革命成果,加強數字化社會“移動性”治理的有益嘗試,為國際社會“移動性”治理現代化提供了中國經驗。
(一)正視中國移動性現實,加強移動空間治理
在移動性社會中,風險增多、關系重構、身份模糊,往往引發對共同體和共同體文化的重新認知和認同。在不同的社會和文化語境中,“區域的穩定是相對的,而流動性是絕對的,兩者有著辯證的關系。……區域的穩定性必然以移動性為前提,而流動性又是區域形成的動力。”對于移動性的認知和理解,以及對移動文化的接受和把握,一方面是深扎于各個國家或地區自身的文化傳統,另一方面也對各個國家或地區的現代社會治理提出了更高的挑戰。在中國文化中,無論是對閉關鎖國、恪守祖制的反思,對安土重遷傳統、背井離鄉鄉愁的強調,還是對城鄉二元治理、國際國內循環的改革,都成為了中國移動性治理的寶貴經驗,形成了中國人在空間劇變和重組中強調文化傳承(“鄉愁”)、在階層流動中強調安居樂業(“和諧”)、在全球貿易中強調身份認同(“中國夢、龍的傳人”)、在全球競爭中強調共同命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共識,在“共同體”中形成了具有豐富內涵和彈性的“移動性文化”。而基于互聯網、移動技術帶來的治理難題,中國高度正視這種“移動性”社會現實,積極適應并擁抱移動通訊技術變革,在政治、經濟、文化、娛樂、社交等領域,萬物互聯、場景革命、大數據應用等不斷取得突破,也使政府的空間治理不斷向網絡化、虛擬化、數字化、實時化邁進,這為在緊急狀況下的移動治理提供全面的技術支持和充分的制度保障;同時,從1994年中國全面接入互聯網,到今天10億用戶駐扎,形成“全球最為龐大、生機勃勃的數字社會”,中國用了不到30年時間,更在數字技術接受、數字化生存、大數據應用與交換、數字社會治理、數字服務民生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移動性”文化認知和共識。
中國對“移動性”社會的治理,恰是正視“移動性”帶來的“空間”風險,強調上下參與,共同治理。中國抗疫過程中,集體利益和個人風險結合,體現出一種高效的社會治理與個體自我管控的相輔相成,讓我們再一次看到中國同其他向現代化大幅度邁進的國家的差異和特性,也給予了我們在全球化語境中反身思考信息社會里媒介治理轉型的機會和可能。有效的政府管理有賴于民眾默契配合,多層次的自我管理和有序移動應運而生,蔓延到中國的各個地方、社會的角角落落,從繁華都市到偏僻鄉村,從繁忙運轉的車船碼頭到熙熙攘攘的購物天地,從工農學兵商到跨國群體。這樣的移動性,是一次自上而下的“移動”管理過程,也是一個“自下而上”的民眾民主參與、自我管理的過程。正是在這樣的數字語境中,移動性正為社會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也讓移動性社會下的治理成為難題:我國不僅有6億農民從農村到城市的大遷徙,有2000多個城市的快速崛起、城市景觀的不斷刷新,有飛機場、高鐵、高速公路構成的交通系統帶來的快速移動,有全球化、“一帶一路”中形成的中國力量,有信息高速公路發展和4G、5G時代的移動互聯,使中國語境中的移動性速度前所未有、移動性規模無可匹敵,移動性導致的不確定也無以復加,新冠病毒傳播帶來的考驗更是空前。因此,中國果斷的“封城”和2021年提倡“就地”過春節,是以人民生命作為最高的目標,是對中國春節超大規模“移動”的現實考量,是從“移動性”治理經驗出發科學切斷病毒“移動”。據《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20》顯示,我國流動人口在2019年的規模達2.47億人,占總人口的18%。而在2020年第一季度,我國農民工外出務工人數為1.22億人,同比減少高達5400萬,限制流動,減少病毒傳播的幾率,及時將病毒的危險通過有序“移動”的方式排除。所以,我們用一個多月的時間初步遏制了疫情蔓延勢頭,用兩個月左右的時間將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個位數,用三個月左右的時間取得了武漢保衛戰、湖北保衛戰的決定性成果,又不斷打贏局部地區聚集性疫情殲滅戰,成為我國“移動性”治理乃至治理現代化的重大戰略成果。
“移動性也許可以被當作一種管理方式,或者我們可以把移動性用作一種分析概念”。因此,今日中國的抗疫實踐,有對中國“移動性”現實的充分考量,有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流動性”治理經驗的積累,也有對病毒“移動”和“傳播”的科學思考,這是中國社會“移動性”治理科學性和有效性的集中展示。可以說,“移動性”治理也是偉大抗疫精神里“尊重科學”的突出體現。
(二)以人民生命健康為本,加強“移動性”治理的現代化
首先,在“移動性”的政治理念上,始終強調人民生命健康為根本,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在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為了保護人民生命安全,我們什么都可以豁得出來!”從“人命關天”的仁愛傳統,到中國共產黨“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理念,高度體現了中國在移動性治理中對人民生命的關注。同時,中國在有效動員民眾參與中破解“移動”治理意識形態困境。這一次新冠疫情,不僅讓我們看到了病毒快速流過“地球村”的恐怖,也讓我們看到“病毒”移動背后的地域“鴻溝”,更讓我們見識了不同社會語境下對待病毒傳播的巨大差異。“移動性有意義的和意識形態的編碼可以反映一定背景面的社會態度和社會實踐”。面對世界共識:“公共衛生機構認為,在受影響的國家進行強制性隔離有助于阻止潛在的災難性流行”,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的疫情應對讓世界大為驚詫,也讓無數生命遭遇傷痛折磨:美國從剛開始的切斷與中國的聯系,到歐洲后院的輸入;從防護物品的短缺,到各州防疫的各自為政;從特朗普對于疫情“fake news”的傳播和辯解,到疫情的一再反復和感染人數、死亡人數的全球第一;從國內移民歧視造成的全國抗議,到國際上美國不斷“甩鍋”和“退群”,也讓全世界的逆全球化、種族歧視、保護主義、國家主義、民粹主義、民族主義乃至地緣政治沖突不斷加劇。美國和許多發達國家在疫情背景下的政策應對,以及基于移動性治理的失控,對疫情“政治化”的處理,不僅無助于世界的共同抗疫,更引發了民眾思想的“傳染”和“震蕩”,讓人意識到:“移動性與自由和普遍主義的意識形態相關聯,存在嚴重的缺陷”。
其次,借助數字化技術規范和治理社會“移動性”。伴隨著媒介技術的更新迭代,“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新與舊難分彼此的時代。盡管有時候有些人預測說媒介最為基礎的功能正在衰落,但我認為實際上它仍在發揮作用。……舊媒介很少會死亡,它們只不過是退到了背景中或幕后,變得更加本體化(ontological)”。多重媒介方式在生活中的并存,不僅深刻影響著人們的生活,也潛移默化中推動著社會各方面的變遷:“從口語文化到書面文化,再到電子信息處理,技術進步必然引發社會、經濟、政治、宗教等結構的變遷。”社會學家趙鼎新也提出:“現代化帶來了全球化、城市化和信息化,導致任何傳統意義上的控制手段都難以為繼……面對現代化所帶來的種種訴求和問題,一個時代必須產生與之相應的家庭關系、社區政治、族群政治和國家政治等。”而進入21世紀,以通訊技術為代表的信息革命,帶來的不僅是“地理的消亡”或者“去疆域化”,更是重構了私人與公共、地方與全球的邊界,形塑了“去領土化”和“再領土化”的人文語境。卡斯特曾提出:“網絡建構了我們社會的新社會形態,而網絡化邏輯的擴散實質地改變了生產、經驗、權力與文化過程中的操作與結果。”新的技術范式更是為社會組織的網絡形式滲透擴張到整個社會結構提供了物質基礎,也出現了“移動的私人化”和“私人化的移動”等趨勢。“今天的數字技術已超越‘擁有’(Having)和‘存在’(Being)的范疇,已經到了萌生新社會秩序的‘生成’(Becoming)階段。即隨著數字化時代進入成熟期,辯證哲學家黑格爾指出的‘生成即存在,存在即生成’(becoming is being and being is becoming)這一充滿生機的社會環境已成為現實。”立足數字化社會的現實,借助互聯網和人工智能革命的成果,不斷地適應、規范和加強社會空間的移動性治理,成為今天中國日常數字生活的一部分。在中國疫情防控過程中,無論是公路系統對車輛的準確定位,還是位置媒體對活動軌跡的捕捉,以及大數據技術的預測與篩查,都為切斷病毒傳播鏈和規范“移動”起到了關鍵性作用。面對現實世界和虛擬世界的移動性,不僅需要研究新形式的溝通和移動性文化,更需要在移動性治理中思考“誰擁有控制能力,無論是連接還是撤回和斷開能力”,因為這將影響移動治理的效果,更決定健康移動性文化和治理現代化的實現。
(三)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本,構建全球的“移動性”文化
突如其來的疫情,不僅沖擊著信息“流動”的秩序,更考驗著全球命運與共、團結抗疫的決心和行動。在中國抗疫過程中,無論是武漢早期防控的網絡議論,還是關于《方方日記》引發的論戰,以及民眾對“信息疫情”的抵制,都顯示著越來越多的民眾借助虛擬空間和虛擬移動,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參與公共空間建構的可喜趨勢和內在力量,也是我國構建疫情信息有序“流動”場域的強大動力。在疫情發生以后,政府以“中國速度”組織馳援、快速建設雷神山、火神山等專門醫院;醫護人員逆向而行,用生命守護生命,踐行著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借助高速發展的互聯網經濟,通過電子購物、網絡娛樂、虛擬社交等手段,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人們日常生活、社會交往和文化娛樂的需要,虛擬空間的“流動”更是彌補身體“移動”受阻帶來的不便,實現對病毒最大程度有效阻隔。更為重要的是,恰恰是疫情下整個社會按下的“暫停鍵”,讓商品鏈的“流動”更清晰地展現在世人面前,讓國人看到商品鏈的高速運轉和商品快速流動構筑起的強大抗疫屏障。同時,中國作為制造大國源源不斷地支持著世界的抗疫活動,成為世界經濟停擺中一道“移動”的風景,成為疫情發生以來第一個恢復增長的主要經濟體,也是2020年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中國發揮全球抗疫物資最大供應國作用,發起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援助時間最集中、涉及范圍最廣的緊急人道主義行動。正如吉登斯所評價的那樣:“中國廣泛使用了人工智能,建立了完善的追蹤系統,這在20年前是不可能做到的……不是說世界在發展,然后病毒突然降臨,而是所有我們正在經歷的變化都是交織在一起的”。
今天,新冠疫情讓世界的移動性現實和移動性風險擺在世人面前,也讓數字化時代的移動性治理成為一個必須面對和亟需解決的課題。因此,需要對移動性機制有更深入的認知和把握,對移動性風險要有更加精確的預判和防范,對移動性的治理要建立在更加科學的數字治理上:
第一,對移動和自由的關系要深入認知和準確把握。移動和自由是同義詞,但是移動是“客觀性”的描述,自由是一種意識形態的裁量,這需要在“移動性”不斷加劇的社會中,充分認識到公共衛生方面減少感染同“呆在家里”、社會流動同保持“社交距離”的“內在矛盾”和“潛在沖突”,對虛擬社會中戴維·莫利所謂的“公共話語的全網絡超級流動”保持足夠的警惕,這也正是韓炳哲在總結東亞抗疫經驗時表達的擔心。因此,需要注意對“自由”的傷害和技術對人的鉗制,還需要通過更加細致的機制和立法來讓技術更好、更安全地為個體發展保駕護航、為個體的生命健康和自由移動提供保障。
第二,對虛擬社會中的“移動”要深入認知。在今天的數字革命當中,“虛擬”語境下的信息移動可以做到“海量”“同步”“互動”“非真”,這需要人們認真辨識和深入拓展。這不僅牽涉到媒介幻境下身體禁錮的困境,牽涉到大數據精準“畫像”形成“信息繭房”的擔憂,還牽涉到數字沉浸下主體性喪失的憂思,更有數字鴻溝所帶來的“不平等”和“選擇局限”等問題。因此,處理好現實和虛擬環境下的“移動”,在疫情控制中實現現實和虛擬的良性互動,才能建構更加健康的媒介環境和信息傳播環境,也才能更好地凝聚社會的共識,共同對抗病毒的侵害。
第三,對移動文化認知要拋棄意識形態偏見。新冠病毒造成了無數生命的離去,也引發了世界政治生態的變化,尤其是借助病毒的“移動”和全球化人的“遷徙”,很多的意識形態加入到對“移動”文化的偏見認知當中,造成了在不同的社會語境下,對“移動”治理認識的偏見,對移動文化認識的偏差,也造成新冠疫情控制效果的巨大差別。意識形態偏見所造成的傷害還在全球不斷蔓延,這不僅影響到自身的防疫和民眾的健康,也影響了全球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正確認知。
席卷全球的疫情,是人類遭遇病毒侵襲的悲劇,也是數字社會下人類“移動性”治理的挑戰,戴維·莫利希望在這個后疫情時代,“在地球的各個角落,科學和神奇、技術和傳統都可以通過嶄新的方式相互融合和共同發展”。筆者深以為然,更希望我們所居住的地球村能夠互相借鑒,不斷破除掉意識形態的藩籬,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精神與勇氣來共同抗擊疫情,迎接人類嶄新的未來。
注釋:
②⑤ [英]戴維·莫利:《后疫情時代的全球化:封鎖中的流動性》,王鑫譯,《國際新聞界》,2021年第3期,第7、8頁。
③④ [愛爾蘭]安·布蒂默:《地理學與人文精神》,左迪、孔翔、李亞婷譯,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204、102頁。
實驗組經新輔助放化療后,出現骨髓抑制 3例、惡心 2例、嘔吐 2例、乏力 3例、腹瀉 1例、肛周皮膚反應3例,不良反應發生率為26.42%,經對癥處理后均順利完成后續手術治療。
⑥ 見[加]哈羅德·伊尼斯:《帝國與傳播》,何道寬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頁。
⑦ Painter,G.D.WilliamCarton:ABiography.New York:G.P. Putham’s Sons. 1976.p.176.
⑧ [英]齊格蒙特·鮑曼:《流動的現代性》,歐陽景根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