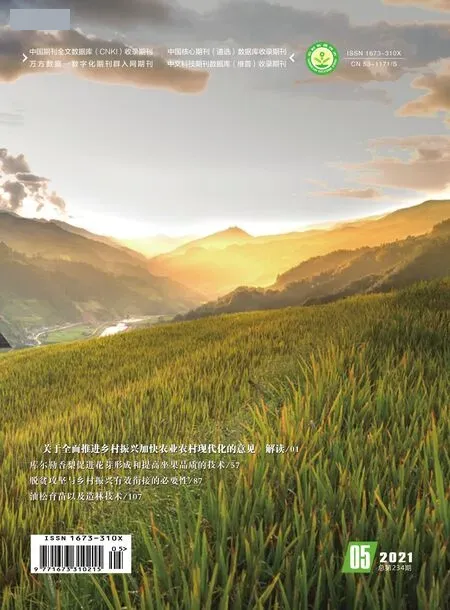韌性視角下鄉村振興實踐路徑探析
趙 靜
(南京理工大學,江蘇 南京 210094)
隨著我國城市化的發展,城鄉之間的發展差異逐漸明顯,與城市化中所帶來的人口擁擠、住房緊張、交通堵塞以及環境污染等問題相反的是鄉村的衰退。在面臨自然擾動與人為擾動時,鄉村系統的脆弱性與不穩定性逐漸凸顯出來。在韌性視角下通過鄉村自身的轉型來提升其韌性和適應能力,采取針對性措施以真正實現鄉村的可持續發展。
1 文獻梳理
在文獻梳理中我們可以發現對于韌性的研究大部分集中于西方發達國家,西方韌性城市和韌性社區的建設實踐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經驗。韌性主要包含著兩次轉變:工程韌性——生態韌性——演進韌性,在西方發達國家“韌性”的研究中,應用最多的是Holling的適應性循環模型,該理論認為社會生態系統在經歷外在或人為的擾動后會經歷“更新-開發-保護-釋放”四個階段。
目前,國內學者大都是以防災減災為出發點,通過提高城市在未來應對災害時自身的適應力與恢復力來提升城市的治理能力。學者們大都認為建立“韌性城市”為實現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實踐提供了一種新思路[1],未來應該加強對多尺度災害韌性研究[2]以增強城市韌性[3]。公共管理視角下的研究可以分為城市韌性和鄉村韌性的研究,他們大都是在總結國內外建設韌性城市的經驗的基礎上,探討建設一條具有中國化的韌性城市的道路。學者們致力將韌性城市與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結合起來,開啟一種公共安全治理的新模式[4]以此降低城市自身的脆弱性[5]以及增強城市對災害能量的吸收和恢復能力[6],最終達到風險治理和減災的目的。2017年6月,中國地震局提出“韌性城鄉”計劃,是我國提出的第一個國家層面上的韌性城市建設計劃,同時也是我們意識到將韌性理論與鄉村社會生態系統研究相結合的關鍵點。
由此可見,學者們逐漸意識到從公共治理的角度對韌性理論進行研究和推廣使用,但是在鄉村治理實際應用中還沒有引起學者們的重視。鄉村系統與城市系統相似,都具有完整的韌性主體與韌性對象,在一定程度上鄉村居民與城市居民一樣都具備外在與人為的抗干擾性,可以通過增強自身的學習和適應能力來提升鄉村韌性。
2 韌性視角下的鄉村振興實踐
首先選取的案例是一些因自然或是人為的擾動而使得鄉村系統演進更新,鄉村由此從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化的社會進行轉變,給當地居民的生活以及當地的產業帶來了改變;在此基礎上,再選取出那些本身就具有良好生態系統的鄉村,在經受外在擾動之前,鄉村也擁有特色產業維持自身的發展。由此,本文選取安徽毛坦廠鎮和四川九寨溝鎮兩個典型鄉鎮進行分析。
從經濟韌性看,毛坦廠鎮依托“全國高考夢工廠”品牌效應,著力打造具有教育特色的鄉村旅游小鎮;另一方面,政府積極出臺相關政策促成“旅游+”產業的融合發展。同時,政府利用良好企業的輻射作用帶動當地經濟的發展,實現了傳統以第一產業為重的鄉村向第二、三產業發展的轉變。九寨溝鎮在受到自然因素擾動的情況下,利用恢復“空窗期”對原有產業反思整治,創新旅游發展策略,對當地旅游產業以及基礎設施升級,村民與政府的收入都逐年增加。
從文化韌性看,毛坦廠鎮不斷對明清老街等古建筑、古文化遺址加以維護和管理,它們承載著當地村民獨特情感并成為了一種村落文化的象征以及精神支柱,在鄉村中形成一種凝聚力支撐著鄉村的發展。同時,勞動力回流使村民在當地進行一些商貿活動來獲得收入。但是與此同時對當地的社會關系網絡造成一定影響,影響了當地村莊的社會凝聚力的形成與保持。九寨溝鎮村民地震后重視保護當地的生態環境,鄉村凝聚力得到增強。村民收入的快速增加以及當地脫貧摘帽,政府得到了群眾的認可,樹立了良好的政府形象以及政府公信力。
從社會韌性看,毛坦廠鎮中學招收政策的變化,由此帶來了商品經濟受眾群體數量的減少,對當地經濟造成影響,因此一部分村民又開始流出鄉村進入到城市尋找工作機會維持自己的生活,村民的收入增長速度與當地政府的收入增長速度不相符,無法達到令村民滿意的地步。由此,政府雖通過政策支持、招商引資的方式與村民協同建設鄉村,但是在遭遇外在擾動時仍然會受到影響,因此其并不具備實質意義上的鄉村韌性。九寨溝鎮政府通過對村民的技能培訓,開創“精品化、綠色化”的鄉村旅游發展之路,這種“造血式”發展方式增強了鄉村建設的韌性,實現農村的可持續發展。
從生態韌性看,毛坦廠鎮政府圍繞鄉村生態環境整治,建立健全以政府為主導、上下聯動、政策配套、協調有力的工作機制,積極推進保護和改善鄉村生態環境,全面提升人居環境質量,推進鄉村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九寨溝政府按照自然修復與人工治理相結合、生物措施與工程措施相結合的方法最大程度保護和維護生態環境的完整性和原真性,將生態文明基因植入重建全過程,形成一條科學的重建之路。
3 韌性視角下鄉村振興行動邏輯
通過案例對比,我們發現在韌性視角下的鄉村振興之路具有一定運作邏輯,為實現鄉村振興提供一種新的思路。
3.1 倡導政府與社會的協同發展
在鄉村振興的建設中僅僅依靠政府的扶持是遠遠不夠的,這其中缺乏一種韌性。我國政府縱向發包與橫向競爭高度統一,地方官員的晉升往往與其績效緊密相關,在行政逐級發包制中,任務被逐級分配到最基層的官員身上。因此,部分政府往往選擇一種 “輸血式”扶持方式,利用有限生態資源實現短期績效,“攤大餅式”的鄉村拓展雖然鄉村居民能夠獲得一定的收入,但是往往形成新的發展沖突點。因此,這需要政府、社會與人民實現協作治理。首先政府可以利用特色政策吸引社會資本的流入,打破資源之間的壁壘,在政府的監督作用下開發出具有鄉村特色的產業項目來發展當地經濟,破壞最小化以保護生態韌性;其次可以通過揮鄉村精英的重要性,賦予他們權力參與到政府決策與治理中,結合實際需求制定出具有個性的發展策略;最后發揮非正式組織的作用,實現暢通信息交流。通過建立一種具有包容性的社會協同治理機制,形成一種團結意識、整體意識提升鄉村的韌性建設。
3.2 注重培養鄉村居民學習力
在當下政府越來越重視城市的韌性建設,在近年來也開始學習理論將韌性思想與鄉村振興相融合,但是要實現鄉村韌性建設不僅僅需要政府部門的重視,還需要鄉村居民的重視。自身創造力與適應力的培養。“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村民通過學習其他城市與鄉村的發展經驗、及時掌握社會的發展潮流,總結尋找出當地發展的關鍵突破點,通過自身的嘗試打造具有當地特色的產業項目。同時,利用“熟人社會”這一龐大的社會關系網,在鄉村中形成一種相互借鑒學習、相互分享經驗的氛圍,實現村民之間互幫互助的友好關系和一種鄰里之間守望相助的良好氛圍,以此樹立起一種共同的理念信念,在鄉村內部形成鄉村凝聚力。眾所周知,人并不能完全避免自然災害以及人為災害,這種漸進式的學習方式使得大家能夠不斷增強自身的適應能力,能在外界因素的擾動影響下快速恢復到原始狀態甚至是形成一種新的積極狀態,這也便是本文一直所強調的韌性意識。
3.3 積極完善鄉村基礎設施
近年來我國也成為了一個旅游消費大國,政府科學的規劃也是鄉村振興中韌性建設的一個重要環節,合理的科學規劃包括基礎設施的提供、組織制度的建設以及對于空間的合理優化。一方面,建立系統的鄉村交通運輸網絡與信息溝通網絡夯實旅游發展的基礎,加強鄉村與外界的溝通聯系以及產業融合。另一方面,政府通過制定具有長遠發展意義的規劃,在面對不同的發展困境時設立不同的發展目標、做到因地制宜,而非“在非常時期用非常方法”。政府不再僅僅依靠于地方管理者的個人經驗,不斷提升鄉村治理的社會化、專業化水平。
3.4 保護鄉村生態資源環境
在當下很多政府面臨著在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之間的“囚徒困境”,如何才能將有限的資源實現價值最大化呢?鄉村振興應該以生態保護為發展底線,仔細發掘鄉村產業發展的“引爆點”,在遵循生態發展規律的前提下用生態資源促進經濟發展,用經濟發展來促進生態保護,增強鄉村發展的韌性來延續鄉村的發展,最終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轉變發展觀念,及時采取措施保護生態資源,最大限度收獲社會效益。
4 結語
通過兩個案例的比較分析我們發現,在鄉村韌性建設中,政府與社會的支持以及對村民韌性意識的培養在鄉村可持續發展中起著重要作用。真正實現“鄉村振興”戰略還有很長的一段要走,要改變“鄉村病”還需要我們不斷尋找新視角來創新鄉村可持續發展的路徑,以此能夠更有效應對發展過程中各種新型矛盾風險的挑戰,取得鄉村發展新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