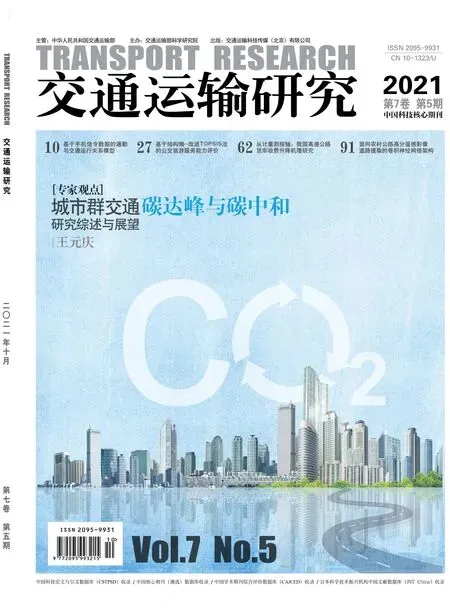基于改進社會力模型的客運樞紐行人換乘組織仿真與優(yōu)化
韓笑宓,鄭維清,楊 權(quán),盛 濤
(交通運輸部科學研究院,北京 100029)
0 引言
客運樞紐是客流集散的主要場所,樞紐內(nèi)的乘客換乘組織水平反映了樞紐的整體服務水平。當前,仍有相當一部分客運樞紐存在換乘客流集中、換乘效率低等問題,亟待通過調(diào)整樞紐內(nèi)的設施布局及配置優(yōu)化客流組織。由于乘客行為的復雜性,很難利用數(shù)學模型對優(yōu)化方案的實施效果進行全面、直觀地評估,而仿真技術(shù)能夠通過模擬行人在樞紐內(nèi)部走行、路徑?jīng)Q策等行為,再現(xiàn)真實的旅客換乘場景,用于研究綜合客運樞紐設施布局下乘客整體的換乘效率,為交通樞紐布局設計的評估與優(yōu)化提供科學依據(jù)。
目前,較為典型的行人仿真模型主要有元胞自動機模型、社會力模型、格子氣模型等。社會力模型是一種連續(xù)空間行人仿真模型,將行人抽象為粒子,描述行人在連續(xù)二維空間運動的動力系統(tǒng)方程。與元胞自動機模型和格子氣模型相比,社會力模型能夠較好地描述行人的微觀運動與群體行為之間的相互關系,而且在體現(xiàn)行人的智能性以及動畫的逼真性方面具有很大優(yōu)勢。很多學者利用社會力模型在行人仿真方面開展了大量研究。周侃等[1]引入視野影響因子,增加行人結(jié)伴同行算法,構(gòu)建了改進的社會力模型及其仿真平臺。李文新等[2]基于改進的社會力模型,利用Anylogic 仿真軟件,考慮樞紐內(nèi)部設施設備數(shù)量與布局等對換乘效率的影響,對樞紐站內(nèi)旅客換乘行為進行仿真。王愛麗等[3]考慮行人間的相互影響,引入“行人防止穿透決策規(guī)則”,以社會力模型為基礎,建立了乘客行為仿真模型。劉曉慶[4]建立了以社會力模型為基礎的Anylogic行人仿真模型,對軌道交通換乘站內(nèi)行人的行走過程進行仿真,并提出相應的優(yōu)化改進措施。慕建康[5]對地鐵站內(nèi)行人走行的社會力仿真模型進行改進,對車站站臺直行段行人的避讓行為和單向通道直線段行人超越行為進行仿真,驗證了模型的有效性。何民等[6]引入融入Agent 的實時感知與動態(tài)避讓算法對模型進行改進,更加真實地模擬了行人步行行為。曹潔等[7]以社會力模型為基礎,對蘭州站的站廳層客流組織進行仿真模擬并提出優(yōu)化方案。李洪旭等[8]利用Anylogic 建立仿真模型,提出了城市軌道交通車站布局優(yōu)化的建議。謝冰如[9]通過Anylogic對成都東站兩個時段下的排隊交叉沖突和設施通過能力進行了仿真優(yōu)化。
已有的研究中,以社會力模型為核心算法的Anylogic 仿真軟件應用較為廣泛,在綜合交通樞紐行人仿真優(yōu)化領域的研究已經(jīng)取得了很多成果,但由于社會力模型中的行人間作用力不能有效防止碰撞的發(fā)生,所以在仿真過程中,高密度行人流區(qū)域存在同一空間多個行人重疊甚至互相穿越的現(xiàn)象,與現(xiàn)實情況不符。在實際運動過程中,行人的走行速度以及面對潛在沖突時的沖突角度各異,很大程度地影響其采取避讓行為的作用力。針對這一問題,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考慮行人速度和沖突感應的各向異性,引入行人沖突避讓機制對社會力模型進行改進,并通過仿真軟件實現(xiàn)某綜合客運樞紐的仿真模擬,分析行人在樞紐內(nèi)部的換乘瓶頸,提出樞紐布局設計優(yōu)化方案并驗證優(yōu)化效果。此外,開展敏感性分析,對道路客運電子客票推廣應用這一背景下的行人進站效率進行評估。
1 考慮行人沖突避讓的社會力模型改進
1.1 社會力模型的適用性
社會力模型對于行人仿真的適用性體現(xiàn)在以下兩點:
(1)可以解釋行人自組織現(xiàn)象。通過相互的行為作用機制,自然地形成成股人流,或通過演化,形成不同方向的行人流線(同向行人之間壓力較小,異向行人之間壓力較大)。
(2)可以解釋交叉處的行人振蕩現(xiàn)象。人流交叉處會出現(xiàn)行人逗留的情況,在仿真場景中顯示為“行人‘振蕩’現(xiàn)象”,即行人間或行人與障礙物之間的徘徊、反復運動[10-11]。
針對綜合客運樞紐內(nèi)旅客流線較多、旅客行為復雜的特點,相較于其他行人仿真模型,社會力模型能夠深入、細致、逼真地描述綜合客運樞紐內(nèi)旅客行人流演化過程中的復雜現(xiàn)象[12]。
1.2 社會力模型的基本原理
社會力模型利用牛頓第二定律描述行人的運動狀態(tài)。在該模型中,考慮了行人的運動行為受三種力的驅(qū)使,分別是:行人的自驅(qū)動力,行人與周圍行人之間的作用力,以及行人與障礙物之間的作用力[13]。社會力模型的表達式為[13]:

(1)行人的自驅(qū)動力
行人在運動過程中,若沒有受到外界因素干擾,會以其期望的速度徑直行進至目的地,這個過程中所受到的力就是行人自驅(qū)動力,表達式為:

(2)行人間的作用力
行人間作用力包括行人間的心理排斥力和接觸排斥力,表達式為:


式(4)中:Ai為作用力強度;Bi為作用范圍;ri,rj分別為行人i和行人j的作用半徑;dij為行人i與行人j間的質(zhì)心距離;為行人j對行人i作用力的單位矢量。

式(5)中:k為身體擠壓力系數(shù);μ為滑動摩擦系數(shù);為切向相對速度,表示行人i與行人j在切線方向的速率差;為切向單位向量,方向垂直于;g(x)是用于判斷行人i與行人j之間是否存在身體接觸的函數(shù)。
(3)行人與障礙物間的作用力
行人與障礙物間的作用力包括行人對障礙物的心理排斥力和接觸排斥力,表達式為:


式(7)~式(8)中:diw為行人i的質(zhì)心與障礙物w邊界之間的距離;表示障礙物對行人i作用力的單位矢量。
1.3 社會力模型的改進
社會力模型仿真過程中可以發(fā)現(xiàn)多個行人碰撞重疊的問題[14]。本文考慮行人的沖突避讓機制,對社會力模型加以改進。在社會力模型中,行人的避讓行為來源于行人的心理排斥力,而在實際的行人走行場景中,行人具有主觀能動性,面對潛在的沖突對象,會根據(jù)其與潛在沖突對象的速度對比以及雙方?jīng)_突角度大小改變走行意愿。因此,本文借鑒社會力模型中行人間作用力的建模思路,考慮當行人j進入到行人i的沖突感應范圍內(nèi)時,行人i的走行速度對避讓意愿的影響,以及沖突感應的各向異性,得到行人i產(chǎn)生避讓意愿作用力的表達式如下:


可以看出,當行人j的速度大于行人i的期望速度時,行人i不產(chǎn)生避讓意愿作用力;當行人j的速度介于行人i的當前速度與期望速度之間時,在自驅(qū)動力的驅(qū)使下行人i的運動狀態(tài)受限,從而產(chǎn)生避讓意愿作用力,直至行人j的速度低于行人i的當前速度時,行人i的避讓意愿最為強烈。

式(11)中:θij為行人i的走行方向與行人j對行人i排斥力方向的反方向之間的夾角;σ為作用力的各向異性參數(shù),參考相關文獻[15-16]后確定該參數(shù)取值為0.2。
行人所受到的其他行人的排斥力與自身行進方向的角度與其對潛在沖突的避讓敏感度之間也存在著非線性關系。當夾角為0時,在行人i的沖突感應范圍內(nèi)的行人j對行人i產(chǎn)生的排斥效果最明顯,行人i的避讓意愿最大;當夾角為0~90°或270~360°時,行人i的避讓意愿要比夾角為90~180°時大。
2 案例分析
2.1 仿真的實現(xiàn)
本文以某綜合客運樞紐為例,對考慮行人沖突避讓的社會力模型展開應用研究。該綜合客運樞紐毗鄰高鐵站,主體部分包括長途客運站場、綜合客運樞紐換乘大廳、旅游集散中心、公交站。該綜合客運樞紐的總體平面布置方案如圖1所示。換乘中心布設于高鐵站正北方向,長途客運站布設于換乘中心的東側(cè),游客集散中心、公交站布設于換乘中心西側(cè),不同交通方式間的換乘活動均集中在換乘中心內(nèi)部。

根據(jù)綜合客運樞紐平面布置圖,在Anylogic仿真軟件中繪制仿真場景(如圖2 所示)。利用Anylogic 中的行人行為模塊建立不同客流來源的旅客換乘行為邏輯圖(如圖3所示),利用其中的多智能體參數(shù),實現(xiàn)改進的社會力模型。




圖3 行人換乘行為邏輯
結(jié)合仿真場景,對仿真模型進行參數(shù)設定:
(1)仿真場景參數(shù)設置
長途客運站設人工售票窗口3 個、自動售票機3 個、安檢機2 個。將出租車車輛數(shù)換算為行人服務臺數(shù)進行仿真,單次服務的出租車為3輛,按照每輛出租車服務1.6 人計算,則出租車上客區(qū)單次服務旅客人數(shù)為5人。
(2)行人設施參數(shù)設置
本項目中涉及的連接類設施包括換乘通道和自動扶梯。設定行人在自由流狀態(tài)下的速度參照默認值,即5km/h;自動扶梯速度為0.5m/s,寬度為1m。
為旅客在換乘過程中提供服務的交通設施包括售票處、安檢機、檢票口和出租車上客區(qū)等。對以上設施的服務排隊參數(shù)設定均通過調(diào)用函數(shù)實現(xiàn)。排隊服務選取較短的隊列。調(diào)用函數(shù)類型及參數(shù)根據(jù)客運站實際服務時間分布確定。
(3)到達客流設置
通過對客運樞紐的實地調(diào)查,推算高峰小時通過不同交通方式到達綜合客運樞紐的行人OD 矩陣,作為模型中客流到達速率的數(shù)據(jù)來源。
(4)行人參數(shù)標定
通過對樞紐內(nèi)高峰期進出站乘客相關特性的數(shù)據(jù)采集,確定本仿真模型中行人初始速度為Uniform(0.3,0.7)(單位為m/s),舒適速度為Uni?form(0.8,1.3)(單位為m/s),行人直徑為Uniform(0.5,1.0)(單位為m)。
2.2 仿真結(jié)果分析
下面主要對行人的平均換乘時間、典型交織區(qū)的客流密度這兩項指標進行仿真模擬,并與實際場景作比較分析。仿真結(jié)果與實際觀測數(shù)據(jù)的對比如表1所示,仿真誤差小于6%,表明本模型采用的仿真參數(shù)合理,符合實際情況,能夠有效用于樞紐內(nèi)的行人仿真分析。

表1 仿真結(jié)果與實測數(shù)據(jù)對比
分析行人的沖突避讓行為,可以發(fā)現(xiàn)很少出現(xiàn)行人重疊的情況。圖4 是截取的換乘大廳東南側(cè)一高密度客流區(qū)域的行人仿真過程。可以看到,行人1 與行人2 在走行過程中識別到彼此間的潛在沖突,在避讓意愿作用力的驅(qū)使下,行人1減速避讓,行人2改變走行方向,直至沖突解除。如此從微觀層面分析樞紐內(nèi)較為典型的多向客流交織下的行人行為,可以提高客運樞紐行人換乘組織仿真模擬的準確性,也驗證了社會力模型改進的有效性。

圖4 行人沖突避讓過程仿真
客運樞紐服務水平可由行人密度及設施服務能力體現(xiàn),將二者作為主要評價指標,得到的仿真結(jié)果如圖5 所示,不同色塊分別對應6 個密度等級A~F,紅色填充部分行人密度最高,擁擠情況嚴重。總體來看,換乘大廳服務水平較高,密度等級主要為B、C級,有多源客流交織處可達D級,E、F級的高密度區(qū)域集中在長途客運站的購票、安檢、候車區(qū)域及連接二層高鐵進站的扶梯處。同時,統(tǒng)計長途客運站內(nèi)服務設施平均排隊長度可知,自助售票機處平均排隊人數(shù)為6.126人,安檢處平均排隊人數(shù)為12.345 人,排隊現(xiàn)象均較為嚴重。

圖5 優(yōu)化前地上一層行人密度分布圖
3 討論與建議
根據(jù)仿真結(jié)果,本文提出以下優(yōu)化措施:
(1)為緩解長途客運站內(nèi)售票區(qū)、安檢區(qū)的擁堵,將3臺自助售票機增加至6臺,2臺安檢機增加至3 臺,并略微向東移動安檢機位置,提高服務設施通行能力。
(2)長途客運站開辟面向站前廣場的進站口,承接來自站前廣場及客運站出站口的換乘客流,減少其繞行距離。
(3)高鐵站西側(cè)增設1 部扶梯,東側(cè)設置2部進站扶梯,承接部分換乘高鐵的客流。
根據(jù)優(yōu)化措施對仿真軟件內(nèi)相關參數(shù)進行調(diào)整,得到優(yōu)化后地上一層行人密度分布如圖6所示。

圖6 優(yōu)化后地上一層行人密度分布圖
可以看出,開辟長途客運站北進站口后,來自長途客運出站口及站前廣場的旅客無需進入大廳即可直接換乘長途客運,疏解了換乘大廳內(nèi)的部分客流,緩解了長途客運站南進站口的客流壓力,同時減少了換乘大廳內(nèi)東側(cè)的客流交織,該區(qū)域范圍內(nèi)的服務水平明顯提升。地下一層的出租車、社會車輛客流可直接通過新設的高鐵站東側(cè)進站扶梯換乘高鐵,減少了與高鐵出站口客流的交織,高鐵出站口附近行人交織區(qū)域的B 級密度區(qū)域范圍擴大,高鐵站西側(cè)進站扶梯處的擁擠情況也得以緩解。長途客運站內(nèi),隨著服務設施的增加,售票區(qū)、安檢區(qū)的服務水平明顯改善。
優(yōu)化前后乘客所需換乘時間如表2 所示。可以看出,長途客運換乘長途客運的時間和站前廣場換乘長途客運的時間都明顯減少,開設長途客運站北進口極大地縮短了上述換乘流線旅客的換乘距離,優(yōu)化效果最為顯著。由于地下一層的旅客可就近搭乘西側(cè)扶梯換乘高鐵,減少了換乘大廳東南側(cè)區(qū)域的沖突交織人流,出租車和社會車輛換乘高鐵的時間分別減少了56.46%和43.14%,高鐵換乘長途客運的時間減少了14.12%,旅游巴士、高鐵、長途客運換乘出租車的時間減少了15~22s。由于仿真的隨機性在合理范圍內(nèi)上下波動,其余換乘時間變化不大。

表2 優(yōu)化前后換乘時間對比
目前,國內(nèi)多地啟動了電子客票試點,旅客可直接通過互聯(lián)網(wǎng)購票時的有效身份證件或電子客票憑證乘車。為驗證電子客票試點的實施效果,本研究以10%的步長改變電子客票憑證檢票比例,得到不同場景下的旅客到達長途客運站候車區(qū)域的進站耗時。為了減小仿真誤差,不同比例下重復仿真5 次,取平均值,結(jié)果如圖7 所示。在乘客使用電子客票憑證進站乘車的比例由0 增加到60%的過程中,其與乘客進站耗時之間呈負相關關系。電子客票提升了旅客出行體驗,但隨著電子客票比例的持續(xù)增加,乘客進站時間出現(xiàn)反彈,原因在于安檢設備的通行能力與改善后的聯(lián)網(wǎng)售票服務能力不適應,對旅客的進站效率產(chǎn)生抑制作用。

圖7 長途客運電子客票比例與乘客進站耗時的關系
4 結(jié)語
本文引入沖突避讓機制對社會力模型進行改進,在此基礎上利用仿真軟件對某綜合客運樞紐進行了行人換乘組織仿真試驗,驗證了仿真模型的有效性,并對樞紐設施設備布局與配置進行了優(yōu)化設計。仿真結(jié)果表明,優(yōu)化方案能夠大幅改善長途客運換乘長途客運、站前廣場換乘長途客運、出租車換乘高鐵、社會車輛換乘高鐵、高鐵換乘長途客運等換乘流線的換乘效率,可為綜合客運樞紐的一體化布局設計提供科學依據(jù)。另外,電子客票憑證檢票比例的敏感性分析結(jié)果表明,隨著道路客運電子客票的推廣應用,乘客購票乘車的便捷性顯著提升,但乘車流線中安檢、檢票等服務設施的通過能力需要同步匹配,避免產(chǎn)生瓶頸。客運樞紐內(nèi)行人的換乘行為較為復雜,本文對行人在服務設施處的行為進行了簡化處理,沒有考慮行人根據(jù)隊列長度變化更換隊列的行為,后續(xù)可對此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