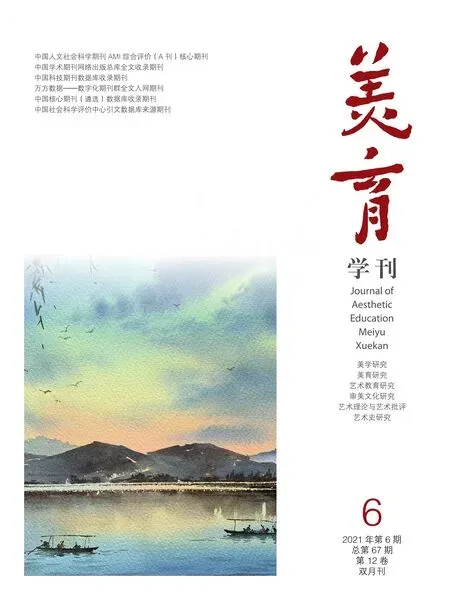羅斯科“可塑性”概念與繪畫空間
應雨芯,李慶本
(杭州師范大學 藝術教育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1121)
一、反對闡釋:圖文之間的裂隙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取代歐洲成為世界政治經濟發展中心。與此同時,馬克·羅斯科(也譯為羅思科,Mark Rothko,1903—1970)、杰克遜·波洛克(Jackson Pollock,1912—1956)、巴奈特·紐曼(Barnett Newman,1905—1970)等一批藝術家在“抽象表現主義”的名稱統帥下迅速崛起于紐約。作為戰后美國最早的現代藝術流派之一,它以鮮明的形式特征和先鋒姿態使美國在藝術上取得世界話語權。根據表現形式的不同,抽象表現主義被分為“行動繪畫”(action painting)與“色域繪畫”(color-field painting)兩塊陣地,羅斯科便是色域繪畫的代表人物。
羅斯科的藝術生涯無疑是十分成功的,繪畫為這個來自俄羅斯鄉下的移民贏得了巨大的財富和名聲。1969年,耶魯大學授予羅斯科藝術榮譽博士學位,稱贊他為“少數幾名可以被稱為美國新畫派創始人中的一位”,“在美國藝術上創造了一個永久的地位”[1]252。但是,與時代對他的青睞不同,羅斯科對當時的藝術評論界始終保持著抗拒態度,認為他們從未真正理解他的畫作:“我們的繪畫是不可解釋的”[1]64;“我不是一個形式主義者”[1]128;“我并沒有對色彩感興趣”[1]140;“我從不考慮民族主義的問題,我考慮的是人”[1]235。他的對抗姿態數十年如一日,幾乎否定了所有主流闡釋,包括集體性的共名批評和對他個人作品的評價,甚至有時因為反對的觀念過多而顯得故弄玄虛。所有這一切,似乎都暗合了蘇珊·桑塔格在《反對闡釋》一書中所提出的“闡釋無異于庸人們拒絕藝術作品的獨立存在”[2]的結論。
誠然,羅斯科之反對闡釋所體現的就是保持其藝術作品獨立存在的姿態。盡管在批評與資本的合謀面前,他的作品本身蒼白無力,他的抗拒也只能淪為裝點畫作的又一神秘幔紗。但這一反抗者形象無疑是值得深思的,因為它證明了這一時代的藝術批評和羅斯科的創作間存在的巨大裂隙。那么,在羅斯科身上,圖文之間的這一裂隙究竟存在于何處?為何他畫著極度抽象的作品卻否認自己是一個形式主義者?最重要的是,他的抗拒是輕浮的還是沉重的,是商業策略抑或嚴肅思考?他分散的反抗話語背后又是否有一個自我立場?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有必要將煩冗的闡釋話語和抽象的色塊暫時剝離,將目光投向羅斯科的另一創作身份——藝術哲學書籍《藝術家的真實》(TheArtist’sReality:PhilosophyofArt)的寫作者。較之于其他簡短的公眾言論,這本書的篇幅和長達數年的創作時間都使得它能夠展現更為復雜、成體系的羅斯科思想。該書在羅斯科生前并未出版,被存放在倉庫的文件夾中,直到2004年,羅斯科逝世后的第34年才由其家人整理面世。書的編者之一,羅斯科的兒子克里斯托弗·羅斯科(Christopher Rothko)猜測這是出于他父親對觀眾直接體驗藝術品的重要性的思考,他擔心觀者在得到結果后便不再親身感受畫作的意義。雖然羅斯科未曾在書中直接闡釋自己的畫作,但是作為其個人藝術理念的自我陳述,它和繪畫分享著共同的藝術理想,呈現出一致的哲學傾向,對于羅斯科此后數十年的繪畫道路有著神奇的預見性。在此書中,羅斯科通過對藝術批評的批判性思考和對尼采思想的深度化用,創造出了自己獨特的藝術理論話語,呈現出一個激情澎湃而又不失深邃的思考者形象。
本文接下來將圍繞其書中“可塑性”(plasticity)、“空間”(space)等主要概念對羅斯科的藝術理論進行梳理,以期能撥開抽象的迷霧,發現他與時代的背離姿態的根源,為理解羅斯科提供新的線索。
二、詞義延異:造型性與可塑性
在《藝術家的真實》中,“可塑性”這一概念貫穿全書,并發展出“可塑性元素”(plastic elements)、“可塑性經驗”(plastic experience)等詞語,頻繁出現于羅斯科對藝術史和藝術品的評論中,儼然成為他理解藝術的獨特視角。因此,厘清這一概念的由來與含義是進入羅斯科藝術世界的重要前提。
Plasticity一詞與藝術向來關系緊密,它的本義是形容某些物質所具有的延展性或可塑形性,在藝術領域多用來形容陶土、石頭、金屬等材料。它的形容詞plastic的使用更為廣泛。1766年,萊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在《拉奧孔》中提出“Bildende Kunst”,英譯為“Plastic Art”,即“造型藝術”。因為涉及藝術分類問題,該詞在隨后的幾個世紀不斷被加以討論,囊括的范圍幾經變化,但基本都是從宏觀層面進行思考。真正將Plastic和Plasticity作為理解藝術的關鍵詞的是形式主義批評家羅杰·弗萊(Roger Fry),在他對現代藝術的評價中,Plasticity被視為作品的核心價值,沈語冰將之譯為“造型性”。[3]在弗萊的批評理論中,理想的繪畫被視為是建筑的想象化、平面化,他認為繪畫應具備像建筑一樣的三維性,并且,體積和團塊在圖畫空間中應得到和諧配置,這種造型體塊的藝術(the art of plastic volumes)是他心目中真正的藝術(the art of Art)。后印象派畫家塞尚(Paul Cézanne)的晚期畫作被弗萊視為這一藝術的典范。他從印象派繪畫中汲取了對視覺經驗的重視,但并沒有完全忠誠于視覺自然,而是以對色彩的造型性和堅實的構圖追求超越了印象派,由再現的科學邁向表現性構圖的科學。他通過靜觀提煉出簡單的幾何形體,架構起知性的腳手架,最終使畫面呈現出結晶質的外貌,富有堅實感與立體感。
弗萊的批評回應了當時后印象派藝術的困境,他意識到再現科學的印象派已然喪失了吸引力,藝術正逐漸拋棄模仿,走向抽象和主觀表現。但是,他仍試圖平衡抽象與再現性成分。在《繪畫的雙重形式》中,他為再現辯護道:“人們必須考慮到建筑是三維的,而抽象繪畫只有兩維這一事實。我認為,這里存在著抽象繪畫缺乏情感感召力的真正原因,因為很明顯的是,對由扁平畫布提供的任何空間深度的暗示,都是緣于一種透視效果,也就是說,源于對藝術品之外的某種東西的再現。不參照再現,人們就無法在畫布上構建體量或空間。所以,回到我的要點,盡管存在著抽象的嘗試,但大體而言,繪畫一直是,或許仍將保持為一種再現性的藝術。”[4]顯然,弗萊認為在重構外部世界的過程中保留一定的再現性元素有助于提升繪畫的感染力。這段論述展現出弗萊對于抽象藝術的保留態度,也讓我們更好地理解他的造型性概念,這一概念是弗萊對于二維平面應如何呈現三維空間的回答。因此,沈語冰將造型性解釋為“一種從現象中提煉出形式的三維形式感”[5]。
同樣面臨著從三維空間到二維平面的挑戰,羅斯科對造型性展開了更為靈活的思考。雖然沒有在書中明確提及對弗萊的閱讀,但他幾乎承襲了弗萊對后期塞尚的評價,稱之為“發現色彩的結構性作用”[6]84,“完成了繪畫的結構性重建”[6]85的畫家。但是,羅斯科面對的藝術世界更為復雜,隨著立體主義、超現實主義乃至康定斯基等人的純粹抽象繪畫不斷涌現,繪畫藝術呈現出愈發抽象和主觀的特征,弗萊對于再現和體積的強調顯然不再適用了。與此同時,弗萊、貝爾(Clive Bell)等人形式主義解讀的盛行使得繪畫面臨著淪為裝飾品的危機,這是羅斯科不能接受的。他曾在與芝加哥藝術學會展覽總監凱瑟琳·昆的通信中表達了這一點:“在漫無邊際的展墻上,繪畫有可能變成一片裝飾性區域。這樣便歪曲了我作品的意義。我的作品抗拒裝飾性,它既表現隱秘性,又表現強度。”[1]162因此,羅斯科的目的絕不僅止于立體的、和諧的形式,他的畫家身份使他要面對“繪畫的雙重性”難題,而抽象繪畫面臨的裝飾性危機進一步迫使他思考形式與內容的抵牾,那么,他是如何理解造型性概念,使之適用于如今的繪畫平面?換句話說,他是如何處理三維空間,使之以合適的方式呈現為二維圖畫空間?
弗萊從未明確造型性的含義,只是通過不斷地使用這個概念來令其擁有較為清晰的輪廓。羅斯科在這里顯得更為嚴謹。盡管他仍然使用與弗萊同樣的詞“plasticity”,卻賦予了不同的含義。為了加以區分,我們不妨按照《藝術家的真實》中文譯者島子的譯法,將其譯為“可塑性”。在《藝術家的真實》中,羅斯科明確定義了自己的“可塑性”概念:“可塑性就是在繪畫中表現出運動感的特性。這種運動可以由物理上具有真實觸感的后退或前進的感覺所激發,或者可以通過涉及我們對事物向后或向前看起來怎樣的記憶而實現。”[6]104可以看出,羅斯科不再強調立體感,而是以更為抽象的運動感取而代之。由此,“plasticity”一詞的詞義在羅斯科那里便從“造型性”延異為“可塑性”。
他以一朵金屬花雕塑為例,當金屬通過人的捶打、切割而逐漸呈現出傾斜的花瓣、凸出的花蕊時,“這些下陷和突出,不僅僅呈現了花朵的外表,還制造出一系列富有韻律的動作,這些動作讓我們的眼睛能夠隨著花朵的發展進程,向上向下,向里向外,這一切都讓我們享受了一場空間之旅……在繪畫中,就像在雕塑中一樣,必須對這些運動進行組織……我們可以通過創造出相對于畫布所在的空間平面向前或向后的感覺而達到可塑性。事實上,藝術家邀請觀賞者在畫布的領域中踏上旅程”[6]93。羅斯科強調了觀看藝術作品時的視覺運動過程,當觀者的目光沿著花朵的外表運動時,感官運動的空間取代了藝術品外觀的立體空間,這使得主觀的空間感受取代了客觀的物體體積,可塑性的適用范圍便突破了三維空間的限制,獲得了更為強大的解釋力。這一概念重心的遷移大約也便是譯者島子將其譯為“可塑性”而非“造型性”的原因所在。
為了進一步說明運動感在繪畫中的可行性,羅斯科將“畫家們用于創造這些空間中運動效果的方法與手段”[6]93統稱為可塑性元素,包含色彩、線條、紋理、明暗等繪畫的形式要素。“所有這些元素本身都具有創造出這種運動的潛能。色彩上的前進和后退。線條可以指明方向、高度以及形狀的傾斜”[6]94,它們創造出的運動都能構成觀看者可塑性經驗。通過對色彩、紋理等更為純粹的形式要素的引入,羅斯科想說明的是引起運動感的繪畫不一定具備再現性或立體的視覺效果,即使是純粹運用色彩的繪畫平面也能通過感官的運動達成可塑性。由此,他將弗萊造型性概念中對再現與三維形式感的強調轉化為了可塑性對繪畫空間中運動感的直接體驗。這一抽象的可塑性概念的達成,也為羅斯科將來繪畫風格的改變埋下了伏筆。
羅斯科的思考并沒有停止于繪畫的形式層面,相反,他試圖賦予作品更深層的意義,可塑性元素在這一探索中承擔著橋梁的作用。他將繪畫視為“藝術家使用可塑性手段對自己真實概念的一種表達”[6]60,“最終藝術的目的還是創造出某種內在的東西……這些可塑性元素僅僅是達到目的的一種手段,它們本身不是目的”[6]93。形式因素在這里被手段化地處理了,成為意義的承載者和交流的通道。羅斯科對于形式主義的否認也體現于此,形式從來不是他的最終目的,也不是繪畫得以成立的全部理由。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過程中,可塑性的適用范圍進一步拓展了,它不再指向單一的審美趣味(如弗萊以塞尚為標準),而是成為羅斯科理解藝術的多樣性及藝術史中審美變遷的基礎概念。它被羅斯科視為判定藝術優劣的標準:“可塑性是一種優點……只有那些包括可塑性特質的繪畫作品才能被認定為出色的作品。”[6]87但是,不同個體的審美趣味千差萬別,不同畫派之間往往也難以互相認同,可塑性要如何作為評判標準整合不同立場?羅斯科認為,這些差異從根本上源于每個人如何看待真實的本質。一個人形容某幅繪畫具有可塑性,就是在說它符合自己對真實的定義。因此,每一個個體對于可塑性的定義與其對真實性的看法具有一種同構關系。在這個意義上,羅斯科并非一個極端的反形式主義者,他對可塑性的強調恰證明了形式在繪畫意義建構中的重要作用。
三、兩種繪畫空間:視覺的與觸感的
通過可塑性概念,羅斯科不想統一所有人的觀點,而是試圖分辨各種形式所表達的真實,并在此基礎上辨明自己的繪畫之路。那么,我們不可避免地追問這個問題:羅斯科是如何看待真實性的?他的真實性觀念在他選擇可塑性元素時起了什么樣的作用,又對他的繪畫道路產生了怎樣的影響?羅斯科通過將繪畫區分為兩種空間類型:觸感派空間(tactile space)與視覺派空間(illusory space)[7]56,并對表現其空間特性的可塑性元素進行分析,給出了他的答案。
羅斯科以佛羅倫薩畫派的代表人物,也是文藝復興藝術的開山鼻祖喬托(Giotto di Bondone)的繪畫為例。喬托被譽為“西方繪畫之父”,他最大的貢獻體現在對繪畫空間的透視處理上。通過直接觀察自然,喬托在繪畫中開創性地使用了斜面等角透視法與空氣透視法,并對畫面進行明暗對照處理,使得圖畫空間具有了一定的縱深感與空氣感,建筑與人物更為立體,更趨近人們的客觀視覺真實。這種繪畫方式改變了拜占庭繪畫平面化、裝飾性的風格,畫面顯示出了更多現實主義與人文性因素。
基于喬托的繪畫,羅斯科列舉了兩種相悖的觀點。布拉什菲爾德(Ewin Blashfield)并不認為喬托展現了真實,他提到喬托對繪畫細節處理的錯誤,“喬托還沒有學會如何真實地描繪衣服褶皺”,而且他對草葉的描畫也過分細致了,現實世界中的草葉并不會像他畫中那樣顯示出過多細節。“當壁畫對這種場景進行表現時,我們看不到畫中單獨描繪每片草葉,一種總體上的數量感會表現出真實感。如果喬托能夠做到這一點,他也就領略到了真實的本質”[6]97。而貝倫森(Bernhard Berenson)對喬托的繪畫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它們展現出了觸覺的真實感。在《藝術家的真實》中,羅斯科大段轉引貝倫森的相關論述:“心理學已經證明了,視覺不能給我們真正的三維空間感……畫家必須非常清醒地意識到我們在無意識中進行的工作——構筑他的第三維度。而只有當他像我們一樣為視網膜所產生的印象賦予具有觸感的價值時,才能夠完成自己的任務。”[6]88
從兩者的觀點中,羅斯科提煉出了兩種對于繪畫真實的基本理解。面對著畫紙與自然空間的根本矛盾,無疑他們都想在圖畫中尋求一種具有說服力的存在感,只是因為對真實的理解不同而產生了分歧。
布拉什菲爾德忠誠于再現視覺的真實,他追求的是通過視覺的可塑性元素營造出的繪畫空間,羅斯科稱之為“可塑性視覺派/錯覺派”(the visual/illusory type of plasticity)[7]54。在這種空間中,圖畫渴望創造出一種與注視三維空間相似的錯覺,從而確認自己的有效性。事實上,這一自然主義的繪畫理想就是從喬托開始的,正是他首先以質拙的透視畫法捕獲了些許客觀世界的真實。但是處于中世紀與文藝復興的交界時期,受到所處時代的科技水平限制,喬托對于空間的描繪更多來自目測而非科學規律的總結,因此他的繪畫中時而可見多個滅點同時存在,時而出現相互矛盾的空間關系,這種創作方法總體而言是本能的而非科學的,這是導致布拉什菲爾德不滿的主要原因。直到喬托之后的數百年,人類知識與科技的進步推動透視法則不斷完善,繪畫對現實的摹仿越發逼真,布拉什菲爾德的繪畫理想才得以實現。羅斯科顯然是不贊成這種真實性觀念的。他意識到錯覺派繪畫過度模仿表象世界,導致圖畫的意義與美感依賴于外在世界而存在,繪畫的重點已經在繪畫本身之外了,這導致了繪畫本體價值的喪失。
貝倫森將圖畫空間中可以觸摸的真實感視為繪畫的本質,他曾明確地說:“我大膽地把這種激發觸摸意識(tactile consciousness)的力量稱為繪畫藝術中最本質的東西。在這方面,喬托是大師。”[8]羅斯科將這類繪畫稱為“可塑性觸感派”(the tactile type of plasticity)。[7]54與視覺派不同,觸感派并沒有明確定義繪畫的可觸摸感,準確地說,觸感派應是在與視覺派相對立的基礎之上才能夠成立的,它表達的是對于視覺派所代表的知識理性在繪畫中過度使用的不滿。
在羅斯科對觸感派的論述中,有兩點值得關注。首先,觸感派繪畫并非摹仿的繪畫,它不以再現現實為目標,具有了更大的自主性。“觸感派可塑性的畫家們希望圖畫本身能夠美麗。換句話說,圖畫本身是目標——這也是美感存在的地方。”[6]119此為兩派最大的區別所在,觸感派擺脫了視覺派對摹仿現實生活的無盡追求,也因此擺脫了繪畫的視覺真實性賽道,進入更為內向的精神世界與更加自律的形式領域。這必然導致繪畫發生不同程度的變形,轉向表現主觀真實的世界。聯系羅斯科對文藝復興和印象派繪畫歸屬于視覺派的指認,我們不難想到觸感派繪畫所暗示的現代藝術道路就是從塞尚的結構性變形開始的。
其次,羅斯科強調了色彩在觸感派繪畫中的重要性。“喬托的顏色創造出了強烈的真實存在感。所有觸感派畫家都根據色彩的觸感特性來運用他們。這一點與錯覺派畫家相反,他們所創造出的后退的錯覺,是通過隨著距離的后退使色彩不斷變淡而實現的……然而,色彩在本質上具有給出后退和前進的力量……冷色調會后退,暖色調會向前……它們能夠賦予空間一種可以觸摸的黏液般的特性。”[6]109在這里,羅斯科將觸感派與視覺派使用色彩的方式進行對比。視覺派運用色彩的典型形式是文藝復興時期的色彩透視和隱沒透視法則,也是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經過科學實驗得出的結論。當畫面空間向遠處伸展時,空氣呈現出淡藍色,物象也會褪色,變得模糊不清。通過這種理性手段達成的空間運動,很顯然是羅斯科所反對的。而在觸感派繪畫中,對于色彩的使用沒有科學規律的介入,只是按照色彩本身給人的生理感受,也就是羅斯科所說的“色彩的感官特性”進行使用,這樣的繪畫才能達成羅斯科認可的真實。“如果以前的抽象類似當代對科學與客觀事物的關注,我們的抽象將在圖畫中找到人類對更復雜的內在自我的嶄新知識與了解。”[9]這一觀點同樣出現在他對塞尚的論述里。在繪畫走向成熟的過程中,塞尚最初是通過厚涂色彩的方式制造出物理意義上的立體感,“然后他放棄了這種方法,因為他意識到色彩本身就具有觸感的作用,因此這種真實的立體感是不必要的”[6]84。
在羅斯科的理論中,色彩作為可塑性元素同時具備了“感官特性”與“物理特性”的雙重內涵。與知識理性的發展相伴隨的物理特性被貶抑了,而感官特性因其表達了主體感受得到了青睞。這似乎預示了羅斯科此后的繪畫道路。在此之后有數十年的時間,色彩占據了他繪畫的所有空間,橙色和紅色帶著與生俱來的前進感沖刺突進,黑與灰是沉默后退的,當綠色突兀出現在明黃的色塊上時,畫面呈現出憂郁的凹陷。這些顏色都有著獨特的性格,層層疊疊,充滿戲劇性和沖擊力,他們內在的張力仿佛要突破畫框,將觀者也吞噬進去。
事實上,這種將形式因素與觀者的身體感知聯系起來的繪畫觀點在羅斯科的書中頻頻出現,從對“可塑性”概念中感官運動效果的強調,到“視覺派”與“觸覺派”的畫派分類,再到色彩的“物理特性”與“感官特性”的區分,羅斯科的傾向性十分鮮明,他的論述背后也一直有一個統一的“真實性”指向,即以身體和感官的真實來反抗知識理性在繪畫史上不斷膨脹的權威。
四、結語
在時代與藝術的碰撞間,也許是出于為當下反叛性藝術的合理性抗辯的心態,抑或是面臨著對自我藝術道路的迷惘,羅斯科自覺深入了解弗萊這位現代主義批評先鋒的思想,試圖從中尋找理論支撐。但是,他和弗萊的精神源頭終究是不同的。弗萊的現代形式主義美學理論一定程度上受到康德形式美學的影響,而羅斯科的思想深處站立著尼采非理性的精神人格。
在耶魯求學時,羅斯科就閱讀過尼采的著作《悲劇的誕生》,并于此后一生中反復重讀。[10]他對自己畫作悲劇性的指稱已為人熟知,然而在更深的層面上,羅斯科對尼采的接受體現在他對知識理性的反思和對非超越性的身體的指認中。尼采批判蘇格拉底功利性的工具理性割裂了知識與生命,開創了西方理智反本能的傳統。這種盲目的知識信仰演化為啟蒙理性后,以知識萬能的傲慢姿態閃動于西方現代社會的每個角落。
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的形式主義批評便是其中典型。他的現代主義藝術理想是理性主義的,他將羅斯科等人納入了繪畫平面自覺的邏輯進路,并以此接續了馬奈以來的現代繪畫脈絡。[11]表面上看,羅斯科通過貶抑線性透視而符合了他的定義,但是,涌動于平面外觀之下,羅斯科對透視法與科技發展的關聯的指認和他對色彩生理特性的強調被誤讀或忽視了,后者傳達的正是對邏輯理性暴行的反抗。可以說,羅斯科的思考恰恰站在了現代性賴以存在的基礎——理性主義和知識崇拜的對立面。在此意義上,他的繪畫絕非是形式主義的,他的反抗也不是粗淺的,而是堅定了立場之后的無奈之舉。
通過尼采,羅斯科溯回至抽象誕生之處。他贊同柏拉圖的命題:世界并非它們看起來的那樣。但與柏拉圖不同,他的真實性無法通過邏輯思辨展現,而是和他的精神導師尼采一道,潛入了身體的觸覺感性中去。這種真實性表現在繪畫形式中,就是不符合透視的變形和摒棄視覺真實的巨大色塊,它們共同構造出羅斯科的可塑性繪畫空間。羅斯科的戰斗策略與尼采十分相似,都是“以身體性反抗觀念性”,“以藝術性反抗真理性和道德性”[12]。如他自己所說,“我的繪畫秘訣就是借用阿波羅,在光的爆發里隱含著酒神精神”[1]231。因此,在羅斯科看似理性、和諧的色塊之下,是狄奧尼索斯的叛逆與狂歡,也是對現代理性的深刻反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