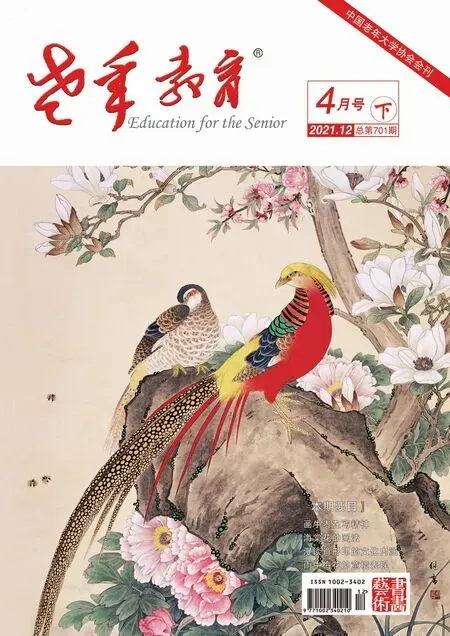懷念父親趙望云
□ 趙季平
我是在父親的筆墨中,度過了自己不知事的童年和充滿理想又歷經迷茫的青年時期。小時候,我家里客人絡繹不絕,幾乎都是為著父親的畫名而來。父親善良隨和,從不忍心讓來訪者空手而歸。更有黃胄哥、(方)濟眾哥、(徐)庶之哥索性吃住在我家,隨父親習畫。這是一個熱鬧而充溢著溫馨與生機的大家庭。那個時候,我不諳中國畫的門道,只是特別喜歡看父親畫畫,跑前跑后當個小聽差也覺得十分快樂。許多人以為我會隨父親學畫,但父親從未強迫我一定得走他的路。
父親一生大部分時間都在外旅行寫生,即使在那段最困難的日子也沒有歇腳。他幾乎走遍了大半個中國,特別是面向大西北,沿著古絲綢之路深入祁連山的崇山峻嶺、八百里秦川的鄉間地頭、秦巴山區的林場民居體驗生活,創作出大量反映人民生活的傳世之作。張大千曾說:“我畫馬不及悲鴻與望云,悲鴻的馬是奔跑的馬,望云的馬是勞作的馬。”老舍先生說:“趙先生的山水畫本來很有功夫,可是他不喜歡山水里那些古裝老翁,所以就在鄉間細細地觀察,深深地揣摩,要把活人活事放在圖畫里,以求抓住民間的現實生活,使藝術不永遠寄存在虛無縹緲之間。”的確,父親的畫作與勞動人民息息相關,構圖中既有理性的審美觀,又有豪放自由的筆墨,更有濃郁的生活氣息。
每次站在他身邊專注地看他作畫,我心里都會產生隱約的音樂線條。這是一種神奇而美妙的感覺,這種感覺隨著父親筆墨的變化和線條的流動而涌現。在父親的畫案旁,鬼使神差地堅定了我成為一名作曲家的決心。上小學時,我經常召集院子里的小朋友拿出家里的鍋碗瓢盆,組成一支樂隊。我指揮大家用不同的節奏敲出不同的鼓點,還進一步向往著怎樣把單旋律的歌曲變出點花樣。父親一直鐘愛中國戲曲音樂,拉得一手好京胡,他早就發現了我在音樂上的天賦和超常愛好。
小學畢業后我一直想考西安音樂學院附中,父親極力支持我。考試結束后,雖然成績很好,可由于特殊原因,我依然落榜了。酷愛音樂的我,哪能經受住這樣的打擊!父親摟過我,用自己的經歷鼓勵我說:“你既然熱愛音樂,就應該認認真真地愛,切不可屈服于眼前的小挫折,時間長著呢。”父親溫暖的懷抱和親切的鼓勵更堅定了我學習音樂的決心。努力了三年后,我終于再次以優異的成績進入音院附高學習作曲。在這學習的過程中,父親似乎離得很遠,又似乎站得很近。我覺得自己猶如父親手中的風箏,他掌握著方向,引領我飛向蔚藍的天空。
大學畢業后,我留陜西戲曲劇院秦腔團工作。這和我做一名作曲家的理想有相當落差。父親卻獨具慧眼。他認為“到秦腔團工作是一個學習民族民間音樂的絕好機會,中國戲曲音樂是民族民間音樂的根,不論你學了多少西洋作曲法,中國民族民間音樂是你今后音樂創作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只要你安下心來把它弄明白,將會終身受益。”父親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地說服我。于是,我開始用大量時間了解秦腔、碗碗腔、眉戶,了解它們的板路曲牌形式、唱腔結構、鑼鼓特點等,并與其他劇種如京劇、豫劇、晉劇、川劇等作比較。父親看在眼里,愛在心上,因為他發現兒子已經開始成長。他以期許的目光告訴我:“美術是凝固的音樂,希望有一天你能用自己的音樂為我的畫注入活力。”
我崇拜父親,雖說他對我生活上的關照并非事無巨細,但他的藝術才華和堅韌不拔的內心情愫卻是我一生的榜樣。在壓力最大的年月,父親很少說話,只是在精神稍好的情況下不停地作畫,累了便靠著床頭、搭著小棉被、微閉著雙眼,手中的香煙忽明忽暗。這個時候誰也不會打擾父親,我們知道他雖然停下了手中的畫筆,可他心中的筆卻從未停住。一家人共同守護著父親心靈的創作凈土。在那片凈土上,父親拖著病殘的身軀創作了上百幅系列作品。這些作品是父親靈魂深處對美好生活的追憶與吶喊,他如交響詩一般沖撞著我的心靈,激勵著我的創作。遺憾的是,父親沒能在有生之年聽到我的作品,這是我一生都無法填補的缺憾。
為了告慰父親的在天之靈,在他去世五周年的紀念日里,我傾情創作了《絲綢之路幻想曲》。這也是履行我對父親的承諾——用自己的音樂詮釋他的作品。我想,他一定能聽到兒子遲到的樂聲。我熱愛父親,是他的給予讓我收獲了多彩人生。如今,父親依然像巍巍高山矗立在我心中。當我被各類獎項、掌聲、鮮花簇擁時,我心靜如水,唯感寬慰的是父親的藝術主張在我的音樂中延續著,延續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