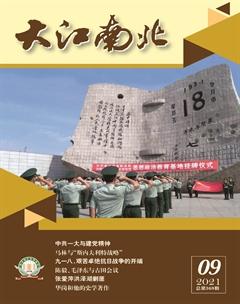從浦東到浙東
顧國平
今年,是浦東抗日武裝南渡浙東,開辟浙東抗日根據地80周年。
魂魄托日月,肝膽映河山;黨是引路人,南渡載史冊。80年了,在浦東、在浙東一方革命前輩血染的土地上,一直傳頌著浦東抗日武裝南渡浙東的壯麗篇章。
抗日戰爭時期的浦東,廣義上是原奉(奉賢縣)南(南匯縣)川(川沙縣)和現閔行區的部分區域,與浙東的三北地區(鎮海北、慈溪北、余姚北)隔杭州灣相望,唇齒相依。
1941年5月至1942年9月間,900余名浦東抗日兒女分期分批橫渡杭州灣,從浦東到達三北,和浙東抗日軍民一道,拋頭顱灑熱血,親歷大小戰斗640余次,開辟了浙東抗日根據地,屢建功勛。 300多名浦東兒女長眠在四明山麓、姚江兩岸、三北大地、大魚山島……樹起了一座不朽的歷史豐碑,可歌可泣,永留心懷。

基于史實,基于情懷,基于傳承,這些年,我們在思考,我們在感悟---浦東抗日兒女是有文化、能戰斗、有情懷的英雄兒女,浦東抗日武裝是一支黨的武裝,是一支鐵軍隊伍,在艱苦的抗戰歲月里,彰顯了“堅信黨的領導,服從黨的統一指揮的精神;遵循黨的政策,靈活運用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精神;堅持群眾紀律,團結依靠群眾,秋毫無犯的精神;舍小家顧大家,恪守全國抗戰一盤棋的精神;拋頭顱灑熱血,英勇頑強,舍生忘死的精神”。
1941年1月,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之后,日軍為了鞏固對占領區的控制,決定對蘇南、浦東等地進行殘酷的“清鄉”,妄圖撲滅抗日烽火。同年4月,日軍發動了寧紹戰役,連陷紹興、鎮海、寧波、慈溪、余姚等城,三北地區處于十分混亂的狀態。在上海、在浦東,當時的抗戰形勢十分嚴峻。為了消滅共同的敵人,為了保存我抗戰實力,為了謀求力量發展,根據黨中央南進戰略部署,中共浦東工委決定以海上游擊隊為基本力量,同時征用社會船只,浦東抗日武裝分期分批南渡浙東三北。
5月10日,姜文光和朱人俠率領50多人,首批南渡,在相公殿登陸。6月16日,受譚啟龍和中共路南特委、浦東工委指示,由蔡群帆、林有璋率領淞滬游擊隊五支隊一大隊和四大隊的各1個中隊134人南渡,在相公殿登陸。之后,陸續多批次南渡。浦東抗日武裝到達三北后,積極尋找地方黨組織并取得聯系。為了加強對浙東抗日武裝和黨組織的統一領導,1941年10月,中共路南特委根據譚震林的指示,成立中共路南特委軍事委員會浙東分會,呂炳奎任書記,王仲良、蔡群帆為委員,先后與地方黨組織的楊思一、王文祥、張光建立了聯系。1942年6月20日,譚啟龍、連柏生、顧德歡等百余人南渡到達三北后,成立了中共浙東行動委員會,譚啟龍任書記,并成立三北工委,王仲良任書記,統一領導三北的黨組織和抗日武裝。之后,何克希、張文碧、劉亨云等一批軍政干部到達三北,浙東區黨委成立,譚啟龍任書記,何克希、張文碧、顧德歡為委員(后增楊思一),加強浙東黨的領導;不久成立三北游擊司令部,何克希任司令員、譚啟龍任政委、連柏生任副司令員、張文碧任政治部主任、劉亨云任參謀長,形成了浙東抗日武裝的領導機構。浙東區黨委建立后,即對黨組織和部隊進行組織整頓和調整,浦東抗日武裝全體指戰員堅決服從組織調整和人員安排,為浙東抗日根據地的開辟、發展、壯大作出了卓越貢獻。
浦東淪陷后,多種勢力錯綜復雜,在敵偽軍、頑軍、地方武裝內,均有我同學、朋友、親戚關系,為我黨開展統一戰線工作創造了條件。尤其是金子明接替陳靜任浦東工委書記后,帶來了黨中央關于加強統一戰線工作的政策文件,成立了中共浦東工委偽軍工作委員會,朱人俊任書記。浦東工委的統一戰線工作如虎添翼,分別在忠義救國軍6團、偽13師50團開展策反和爭取工作。通過統戰,安排我共產黨員打入敵人內部,分化、瓦解、教育敵軍官兵,在偽50團里建立了秘密黨的工作委員會和黨支部,積極發展黨員和黨的活動積極分子,基本控制了這些武裝,為之后周振庭率忠義救國軍6團400多人集體反正,從偽50團拉出300余人到浙東抗戰打下了良好基礎。同時,積極與駐淞滬的國民黨軍隊上層以及當地著名紳士發展關系。做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為我黨抗日武裝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作出了貢獻。
浦東抗日武裝南渡到達三北后,將浦東的統一戰線工作經驗帶到浙東,與宗德辦事處的薛天白、忠義救國軍的陸安石等部建立了統戰關系,取得了國民黨部隊的番號,又積極與三北地區的知名士紳建立聯系,緊緊依靠當地黨組織和人民群眾的支持,狠狠打擊敵人,站穩了腳跟,抗日武裝力量得到了快速發展。
初來乍到時,飽受各種反動武裝勢力凌辱的三北群眾對浦東抗日武裝不了解,持懷疑、觀望、排斥的態度。1941年6月16日,當林有璋、蔡群帆率領的130多名“五支四大”在相公殿登陸時,一走進村子,周圍群眾紛紛外逃,十屋九空,有些房子里只有老人和孩子。據此,指揮員一面安排兵力守衛村口,部隊戰士一律不準進入群眾家里;一面派出人員向群眾宣傳,說明我們是抗日的隊伍,廣泛宣傳抗日的道理,把群眾動員回家。晚上,當地保長殺豬宰羊,辦了十多桌酒席,招待部隊。這樣的宴請,被林、蔡嚴詞拒絕。后經了解,酒席用的食物全是從人民群眾家搜刮來的,于是將保長狠狠訓斥一頓,并責成其把搜刮來的東西立即歸還給人民群眾。三天后,林、蔡指揮部隊在相公殿伏擊前來襲擾的日寇,打響了三北淪陷后的抗戰第一槍,打死打傷日寇16人。5月27日,部隊又在相公殿與日寇作戰,將日寇打回敵據點。
1941年10月22日,計劃在橫河伏擊日寇棉花運輸船的暫三縱第三大隊,當計劃落空后準備組織部隊在橫河鎮上街進行宣傳群眾、發動群眾的工作。部隊毫無防備,集隊行進中,遭日寇反伏擊,血戰一個半小時,大隊長姜文光、大隊副姚鏡人、軍需主任姜文煥等29人犧牲在“七星橋”。
浦東抗日武裝嚴格執行群眾紀律,秋毫無犯。每到宿營地,幫助老百姓挑水、打掃衛生、制鹽、干農活,和群眾打成一片。離開宿營地時,上門板、捆稻草、清掃駐地、歸還用品。部隊嚴明的群眾紀律和真正的抗日行動,極大地教育和影響著三北的人民群眾,贏得了人民群眾的愛戴和信任,建立起了深厚的軍民魚水情。浦東抗日武裝不僅在三北站穩了腳跟,而且和三北人民群眾團結一心,掀起了浙東抗戰熱潮,為建立浙東抗日根據地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在黨的領導下,浦東抗日武裝與日、偽、頑及土匪、惡霸進行艱苦卓絕的斗爭,全力保護浦東父老鄉親的生命和財產安全。在各種反動勢力的夾縫中求生存,有時一天變換幾個宿營地,后勤保障嚴重不足。抗日武裝始終得到家鄉人民的支持和幫助,不斷發展壯大。連柏生的保衛四中后擴編為南匯縣抗日自衛總隊第二大隊、國民黨第三戰區淞滬游擊隊第五支隊,有500多人、槍。
這支在浦東土生土長、始終與家鄉父老鄉親同生死共患難的武裝,當奉命南渡浙東、開辟和建立浙東抗日根據地時,全體指戰員顧全大局,義無反顧,有的瞞著父母和兄弟姐妹、妻子兒女,告別生我養我的浦東,踏上三北大地,迎接新考驗。1943年秋,時任經委會東區分會主任的孫瑞琪,妻子抱著幼女孫亦華先后兩次南渡杭州灣來到浙東,力勸丈夫回家。但孫瑞琪對愛人說:現在抗戰任務很重,待趕跑了日本鬼子再回家,最后不幸被慈溪縣保安團團長宋慶云(漢奸)殺害,并割下其頭顱掛在城墻上示眾。第三支隊支隊長林有璋30多歲了,家里親人希望他早日結婚成家,他卻說:革命未勝,江山未定,何以為家?直到犧牲仍然單身。有很多的浦東兒女血灑三北,長眠他鄉,再也沒有“回家”。
在浦東抗日武裝創建浙東抗日根據地的日子里,大小戰斗640余次,比較著名的有“相公殿大捷”“橫河戰斗”“長溪嶺戰斗”“龍鳳山戰斗”“龍旗山遭遇戰”“陽覺殿戰斗”“筋竹岙戰斗”“宓家埭戰斗”“洪魏戰斗”“梁弄攻堅戰”“朱家店之戰”“北宋突圍戰”“大魚山島戰斗”等等。
相公殿大捷,是林有璋、蔡群帆率領的浦東抗日武裝南渡杭州灣,到達相公殿后僅幾天,得悉有一股日本鬼子從庵東開來,部隊立即決定狠狠打擊這股日寇。當鬼子進入我伏擊圈,我軍用簡陋的裝備打擊敵人。日本鬼子霎時慌成一團,倉促應戰,死命抵抗。激戰數小時,打死打傷日寇各8名,敵人被迫逃回庵東據點,我無一傷亡。相公殿一戰,是三北軍民打響的抗日第一槍,點燃了三北的抗戰烽火。
浦東抗日武裝親歷的、發生于1944年8月25日的大魚山島之戰,被譽為“海上狼牙山之戰”,威名遠揚。為了配合太平洋戰爭,我海防大隊奉命開辟海上游擊區。海防大隊第一中隊76人在大隊副陳鐵康率領下,從古窯浦出發,進占海上大魚山島,遭到數倍于我的敵偽500多人的圍攻。海防大隊第一中隊孤軍奮戰,激戰7個多小時,消滅敵人近百名,但終因彈盡糧絕、寡不敵眾,副大隊長陳鐵康、中隊長程克明和指導員嚴洪珠等40多人壯烈犧牲。
南渡浙東的烽火歲月,浦東抗日武裝作出了巨大犧牲。英烈們的英名將永載史冊,英烈們的精神與日月同輝,我們將永遠緬懷他們!
今年2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給上海市新四軍歷史研究會百歲老戰士回信中指出:“中國革命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常讀常新”,“多講講中國共產黨的故事、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今天,當我們再次回望浦東抗日武裝南渡浙東這一段偉大而永恒的歷史之時,特別提醒著我們要銘記歷史,以史為鑒,賡續鐵軍精神和優良傳統,共同創造美好燦爛的明天!
(編輯 韓鴻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