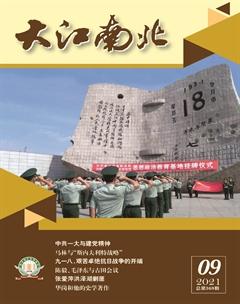異峰突起的“逆行者”
汪瀾
回首上海交大東京審判研究中心(以下簡稱“中心”)創建十年走過的歷程,向隆萬教授是一個關鍵性的人物。有年輕學者稱程兆奇和向隆萬是“中心”的兩根“擎天柱”:程教授作為研究中心主任,無疑是學術研究的領軍人物;向教授則是東京審判中國檢察官向哲濬之子,是“中心”創立的推動者,也是“中心”對外交流和宣傳的使者。“中心”建立以來,他倆的配合可謂珠聯璧合,相得益彰。
2021年2月4日,立春的第二天。上午十時左右,“中心”微信群里,程兆奇教授上傳了一則向隆萬老師手書的調寄《千秋歲引》 詞,大家方知今天是向老師的八十周歲生日,群里立時熱鬧了起來,天南海北的同道和朋友們紛紛留言表達祝賀。程教授不無遺憾地說:若不是因為疫情,真應該做個儀式慶賀一下。向老師說:寫這首“打油詞”正是為了“表達感慨和感謝”。向隆萬的《千秋歲引》 全文如下:
“摯友家人,同歌壽曲,耄耋之年始今日。回眸此生何幸運,滄桑巨變俱親歷。換人間、經風雨、隨家國。 避倭湘南匆隱匿,負笈泰西奮求習,三尺講壇紙和筆。微分積分常伴我,晚年史跡從頭覓。步先慈、溯真相、頌勛績。”
向隆萬教授的八十人生,雖沒有經歷父親向哲濬那段“驚天地泣鬼神”的傳奇,但同樣豐富而精彩。詞的后半部分,寥寥數筆,勾勒出他人生的幾個重要階段。“避倭湘南匆隱匿”,說的是他的童年。1941年2月,向隆萬出生在日本侵華的血腥歲月。出生不久,母親帶著他和姐姐輾轉去湖南老家避難。1946年2月他隨母回到上海時,父親已經接受東京審判中國檢察官的任命去了東京。那時向隆萬剛滿5歲。父親這一去就是兩年多,等到圓滿完成任務回到祖國時,國內的時局正在發生改天換地的變化。他曾被國民政府任命為司法院大法官。但他更樂意從事教書育人的工作。從1949年開始,他先后在東吳大學、大夏大學(華東師范大學的前身)、復旦大學任法學教授。法學專業撤銷之后,他成為上海社科院的首批成員,1960年被上海財經學院(今上海財經大學)聘為外語教研室主任直至退休。在向隆萬兒時的記憶里,父親從來就是一個溫文爾雅的教書先生。
1958年,向隆萬高中畢業準備報考大學,他最初的志向是學歷史或中文。父親問他:你是不是數理化很差?向隆萬說其實都不錯。父親說,現在國家建設很需要人才,應該學數理化。于是他改了志愿,考上了同濟大學建筑工程系,后來因國家亟需培養數學物理等基礎學科人才,被轉到復旦數學系代培。1963年他從復旦畢業,分配到西安交通大學數學系任教。1984年,為了照顧年邁的父母,他調回上海交通大學,直至退休。“三尺講壇紙和筆,微分積分常伴我”,正是他40載教學生涯的寫照。父親對向隆萬的影響還體現在對外語的重視上。父親早年在清華學堂完成英語啟蒙后,被派往美國耶魯大學文學院和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院學習,不僅精通英美法律,而且打下了扎實的英文基礎。上世紀50年代大陸高校取消法律專業之后,他的英文專長也算派上了用場。向老先生對教人學英文不僅熱衷,而且十分執著,即便在“文革”中也樂此不疲。

向隆萬在西安交大任教時,父親鼓勵他用英文寫信,每收到一封信,父親都用紅筆逐字逐句地批閱修改,然后再寄回給兒子。1979年教育部選拔公派留學人員,向隆萬順利通過了英文測試,這才有了他“負笈泰西奮求習”的一段經歷。80年代初,向隆萬先后赴哥倫比亞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深造,他說:“是父親的‘函授’,幫我打下了英文基礎。”“晚年史跡從頭覓,步先慈、溯真相、頌勛績”,說的是向隆萬退休至今,投入巨大熱情和精力去干的一件“大事”,這件“大事”,成就了他人生的異峰突起。
促使他去干這件事情的機緣出現在2005年的秋天。這一年是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9月間,北京舉行了隆重的紀念活動,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講話中說了這樣一段話:“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的審判,使發動侵略戰爭、雙手沾滿各國人民鮮血的罪魁禍首受到應有的懲處,伸張了國際正義,維護了人類尊嚴,代表了全世界所有愛好和平與正義的人民的共同心愿。這是歷史的審判!這一審判的正義性質是不可動搖、不容挑戰的!”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家最高領導人第一次對東京審判作出歷史性的高度評價。
媒體打聽到向隆萬是東京審判中國檢察官向哲濬之子,紛紛找到他,想從他嘴里挖一些父親參與東京審判的獨家秘聞,沒想到他“一問三不知”。這也難怪,父親向來做人低調,加之曾為國民政府檢察官、法官的身份印跡,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他對自己親歷的這段歷史三緘其口,生前幾乎沒有跟子女說過任何關于東京審判的事情。向老先生生前唯一一次在公開場合提及東京審判,是1983年上海法學學會、國際關系學會的一個座談會上。他引用當年南京審判日本BC級戰犯軍事法庭庭長石美瑜的話“我已經是活不久的人了,但我一定要為歷史作證”,向老重復道:“我們都要為歷史作證。”遺憾的是此時向老已是91歲高齡,由于健康的原因,他已無力留下更多的文字記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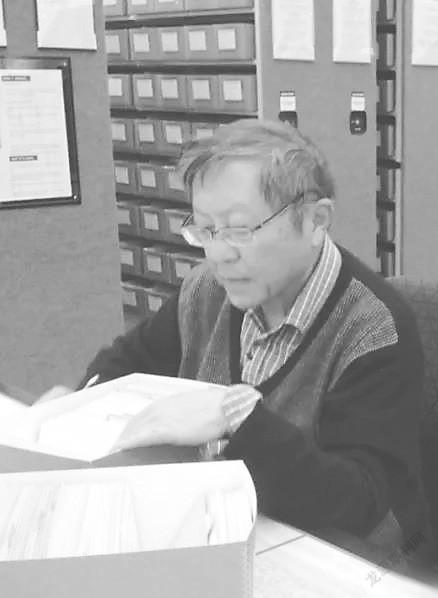
雖然向隆萬沒有從父親那里得到關于東京審判更多的信息,但作為參與這一重要歷史事件的法學先驅的后人,對這段歷史的“無知”,多少讓他感到窘迫和愧疚。給他帶來更大觸動的是不久后國產影片《東京審判》的熱映。向隆萬曾受邀參加影片的首映活動,他說看完影片的感覺是喜憂參半,喜的是東京審判終于重回國人視野,喚起人們對中國參與東京審判的法學界前輩艱苦卓絕工作的重視;憂的是片中父親的形象與本人相去甚遠。尤其讓他憂慮的是,影片為了追求戲劇效果杜撰了一些情節,如日本右翼暗殺梅汝璈的行動,還有讓梅法官和向檢察官在小酒館互通情報、商議庭審策略等等,殊不知東京審判開庭后,是嚴格禁止法官和檢察官有任何接觸的。這些硬傷,深深刺痛了向隆萬,他擔心這樣的敘述會誤導公眾對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認知,甚至會給日本右翼提供口舌。影片問題多多,但向隆萬感覺實在難以怪罪編導,因為當時可供參考的史料少得可憐,當事人也大都離世。作為東京審判重要親歷者的后人,他意識到,自己有責任去追尋,去挖掘這段歷史的真相,同時借此加深對父親的了解。
這時向隆萬剛剛從上海交大退休不久,他有意用自己的余生,來做這樣一件“從頭覓”“溯真相”的事情。從2006年開始,向隆萬多次自費赴美,在哥倫比亞大學、美國國會圖書館和國家檔案館,憑著在資料索引中輸入“向哲濬”和“東京審判”等關鍵詞,在浩瀚如大海的史料中一點一點尋覓相關線索。這位沒有絲毫歷史和法學背景的數學教授,硬是憑著意志力和最原始的“笨辦法”,一步一步接近東京審判的核心史料。
在美國國家檔案館,他找到并復印了100多頁父親的講話記錄稿,包括10次在法庭上的講話和證詞,翻拍了數十張珍貴的法庭現場照片,還查找到兩段父親法庭演講的錄像資料。東京審判最初階段,圍繞日本東亞地區侵略罪行的起訴時間有過激烈的爭論。日本方面辯稱:中日宣戰是在珍珠港事件以后,之前的皇姑屯、盧溝橋等事件發生時都沒有宣戰,既然沒有宣戰,就不存在戰爭。對此,向檢察官在1946年5月14日的發言中予以嚴辭駁斥:“從1931年9月18日以后,日本在中國采取了戰爭性的行動,殺死了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包括士兵和平民……還有兒童、婦女和無助的平民——非戰斗人員。我認為那些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實。如果這不是戰爭,我想問:還有什么是戰爭?”
這是他第一次從鏡頭里看到那個年代父親的真實影像,看到父親擲地有聲的詰問,向隆萬頓覺心跳加速,淚水模糊了眼睛,原來父親不僅是位溫良恭儉讓的好好先生,他還有為了民族大義剛直不阿、正氣凜然的那一面。
回國后,他將收集到的第一批父親在法庭上的演講翻譯成中文,連同母親的回憶錄,一起編進了《東京審判·中國檢察官向哲濬》一書,于2010年由上海交大出版社出版。2011年5月,上海交大東京審判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向隆萬出任中心名譽主任,然而他并未止步于這個“名譽”身份。“中心”成立以來,他參與了多個基礎文獻出版的大項目,同時繼續著他自己對這個領域的探究與挖掘。2014年,向隆萬出版了《向哲濬東京審判函電及法庭陳述》一書,其中向哲濬的法庭陳述,從上一本書的10篇擴展到20篇。2019年,向隆萬推出了他的第三本書《東京審判征戰記——中國檢察官向哲濬團隊》。這是一本面向公眾的普及讀物,人們稱它是梅汝璈法官親撰,梅小侃、梅小璈姐弟整理的《東京審判親歷記》的姐妹篇。與《親歷記》的法官視角不一樣的是,《征戰記》以大量生動鮮活的材料,詳細描述了向哲濬帶領中國檢察官團隊,一路披荊斬棘,“征戰”東京審判的全過程。
近年來,他還多次代表“中心”赴歐美及我國香港、澳門等地區,參加有關東京審判的國際研討和“中心”研究成果的對外發布、推廣活動。他還先后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以及國內數十所大學和社會團體作了幾十場講座。從2013年起,“中心”面向全校學生,開設了《東京審判》通識教育課程,由向隆萬和“中心”青年講師趙玉蕙主講。這是東京審判第一次進入高校課程。讓人意外的是,這一相對冷門的課,竟受到學生們的熱捧,選課時若下手晚了,常常會因滿員而被拒。趙玉蕙回憶說,有一個學期約有200多個學生選了這門課,因為人多,上課被安排在一個400座的梯形大教室,16學時的課程向老師講前半段,她講后半段。趙玉蕙清楚地記得上半段課程即將結束的那一天,向老師作內容小結,講著講著情緒突然激動起來,他說:“若沒有當年先輩們在法庭上艱苦卓絕的努力,就不可能有對日本A級戰犯的嚴懲,也就不會有我站在這里為大家授課。同學們愿意學習了解這段歷史,我十分感動,先輩們也會感到欣慰的。謝謝你們!”說到這里,向老師向同學們深深地鞠了一躬,同學們愣了一小會兒,然后使勁地鼓起掌來。親眼目睹這一幕的趙玉蕙被深深震撼了,前輩授課時的激情投入,以及不經意間展露出的品格風范,深深烙印在她的記憶里,這樣的言傳身教,對踏上教職崗位不久的年輕教師而言,不啻是永生難忘的一課。

向隆萬對東京審判歷史的普及推廣,還登上央視大平臺。2015年,央視社會與法頻道《法律講堂》欄目策劃推出了5集《東京審判》系列講座,向隆萬應邀擔任主講嘉賓。節目播出后獲得不俗的收視率,并獲得該頻道的年度優秀節目獎。去年下半年,當年節目的編導孫輝剛又找到向隆萬,希望制作新一季《東京審判》講壇節目,計劃在今年9月抗戰爆發90周年紀念日前后播出,新節目依然由他擔綱主講,向教授欣然應允。
整個夏天,向隆萬都在撰寫、打磨講稿。這一季節目最初框定為10集,可他一氣寫了18集,容量是第一季的三倍多。編導孫輝剛用“驚喜”二字形容他讀到講稿時的感覺,如果說第一季是關于東京審判的簡述,這一次則是詳述,里面出現了更多重要的歷史細節和人物故事,敘事聚焦點也從上次著重反映中國法官檢察官團隊,及日軍對華暴行的審理,擴展為對東京審判全方位、多視角的講述。
去年10月至今年1月,根據節目組的安排,向隆萬先后三次赴京錄制節目。秋冬時節的北京城并不太平,其間曾多次暴發疫情。1月中旬向先生赴京錄最后一批節目時,正值順義區、大興區先后發現本土病例之際。在此非常時刻,向隆萬“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讓家人和朋友們為他捏了一把汗。1月23日到24日,在央視演播廳,向教授一鼓作氣錄完了最后7集節目。最多的一天連續錄了4集,從上午7點半出門去電視臺化妝,一直到晚上12點半才收工。這樣的工作強度,莫說是8旬長者,就是攝制組的年輕人也絕不輕松。讓編導孫輝剛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向隆萬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認真勁頭,直到錄制前夕,他還會為一句話、一個用詞反復斟酌推敲……
說向隆萬“逆行”一點不假,不僅疫情期間如此,他晚年所干的這件“大事”又何嘗不是如此?80歲,相信這個年齡段的老人,即便身體健康,也大多是含飴弄孫、安享晚年的狀態。可向隆萬卻“逆”時間而行,“逆”生命周期而行——硬是在退休之后闖入一個全新的領域,攀上人生的又一座高峰。這樣的傳奇,能不叫人感慨,能不叫人欽佩贊嘆嗎?
(作者為文匯報原副總編輯、上海作家協會原黨組書記兼駐會副主席)(編輯 韋 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