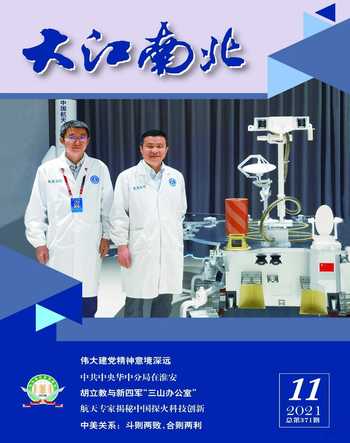航天專家揭秘中國探火科技創新
鄭蔚
1182米!這是我國“祝融號”火星車創下的火面行走最新記錄。中國航天科技集團有限公司第五研究院“天問一號”火星探測器總設計師孫澤洲日前告訴記者,這是至9月7日止“祝融號”累計的里程數,目前火星車已圓滿完成規定的90個火星日的巡視探測任務。
“祝融號”是我國著陸火面的第一輛火星車,它的巡視探測任務成功完成,宣告了我國首次探火就創下了“繞、著、巡”三項任務一次完成的世界紀錄。
直到今年年初,火星上著陸的8個探測器都是美國人研制的。10年前,擔任美國眾議院撥款委員會主席的共和黨眾議員沃爾夫,鼓動美國國會出臺了禁止與中國進行航天合作的立法,禁止美中兩國之間發生任何航天科研活動。而更早前,美方就對華實施各種出口管制,并嚴格限制在衛星技術以及國防領域的合作。2011年“沃爾夫條款”推出后,美方更是以法律法規的形式對中美航天合作嚴加限制。
這就不難理解中國探火每一步的成功都來之不易。肩負重任的我國航天科學家面臨著怎樣的挑戰和風險,他們又是如何堅持科技自立自強,精心推進這一重大工程的呢?日前,記者采訪了孫澤洲總設計師以及他領導的研發團隊。
“天問一號”火星探測器于2020年7月23日發射升空,在它長達4.74億公里的探火實際飛行過程中,航天專家們什么時候最緊張?
航天五院探火團隊幾乎所有專家的答案都是一樣的:最緊張的是今年5月15日早晨七八點鐘它沖進火星大氣層著陸的那一刻,又叫“恐怖9分鐘”。
其實,從5月13日起,孫澤洲他們就有四五十個小時沒有好好睡過覺,心弦繃得太緊了。最累的時候,抽空瞇一會兒,不用同事叫,猛地一個激靈就自己醒了。自探火項目2016年立項以來,整整5年多的時間,盼的就是把“祝融號”駛上火面這一刻!
進入艙總體主任設計師董捷告訴記者,“天問一號”環繞器和著陸巡視器先執行降低近火點高度的變軌,約3小時后完成兩器分離,著陸巡視器經巡航飛行后以25馬赫的高速進入火星大氣層。這一每秒4.8公里的速度雖然低于神舟飛船返回艙再入大氣層的速度,且火星大氣層的密度也只有地球大氣層密度的1%,但它依然會產生1000℃的高溫。而且,火星大氣的組分與地球大氣的組分不同,它二氧化碳占了95%、還富含氮氣、氬氣、甲烷等物質。高溫燒蝕下,進入艙的化學和物理反應將更加復雜,為此采用了能有效保護進入艙特殊需求的抗燒蝕材料。
為什么我們已經有了成熟的月面著陸的經驗,對在火面著陸還如此審慎?董捷說,兩者差別很大。首先,月球沒有大氣,因此落月過程為發動機反噴和緩沖裝置著陸這2個階段:先通過著陸器提供的主動動力,將著陸器的速度從每秒1.7公里降到每秒1-2米,最后依靠著陸器本身的緩沖裝置完成在月面著陸。
而火星有一個稀薄的大氣層包裹,雖然密度只有地球的1%,但也必須加以利用。所以著陸火星是4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氣動減速,利用進入艙的氣動外形進行減速。我們進入艙大底的直徑為3.4米,是人類有史以來第二大的火星進入艙。該階段持續時間約為279秒,要降低91.8%的降落速度,將速度從原來的每秒4.8公里,降到每秒396米;第二階段,使用降落傘減速,這是我國首次在地外天體應用降落傘減速技術。它將著陸速度降低到每秒61米;第三階段,使用進入艙的主發動機減速,其間懸停避障,將速度降到每秒1.5米;最后階段是依靠進入艙著陸緩沖裝置緩沖減速。這4個階段環環相扣,一個階段完成,立即切換進入下一個階段,因此對每個設備的可靠性和整個系統的可靠性要求極高,只要有一個環節出現故障,下面一系列動作就無法完成。

其次,在火面著陸與在月面著陸的另一個比較大的不同是,月球距離地球30萬公里,信號的時延大約為1秒鐘,因此在著陸的過程中,萬一發生意外情況,我們地面飛行控制中心還是來得及干預的,所以我們準備了充分的月面著陸故障預案;但火面著陸時,地球火星距離達3.2億公里,時延長達約18分鐘,也就是說,當我們看到環繞器傳回地球的信息時,事情已經在約18分鐘前就發生了,肯定“無可挽回”了。這是最大的差別,即使準備再多的故障預案都使不上。所以探火團隊必須制定出萬無一失的飛控方案。
進入艙到達預定馬赫數后,立即打開為落火特制的降落傘。可別小看了火星降落傘的難度,雖說通過神舟載人飛船、嫦娥探月三期月球采樣返回飛船的研發,我國已掌握了多種返回地球大氣層的降落傘,但火星的大氣非常稀薄,開傘的充氣形狀高頻變化、沖擊載荷大,因此進入地球大氣層的降落傘型并不適用火星。歐洲太空局與俄羅斯聯合研制的ExoMars2022火星探測器,就因降落傘設計缺陷導致延期發射。
為此,航天五院的專家針對進入艙落火時大阻力系數氣動外形在跨超聲速段固有的不穩定性,新研發了具備能在超音速時快速開傘的鋸齒形前端構形、V型雙層結構加強帶“盤-縫-帶”傘。進入地球大氣層的降落傘的打開方式是連續完成拉出引導傘、減速傘、主傘的動作;而進入艙使用的降落傘沒有引導傘,必須在約2倍火星音速時直接打開用于減速的降落傘。考慮到傘剛打開時進入艙會出現擺動,研發團隊還在地球上進行了仿真模擬試驗和針對性設計,保證了器上所有設備即使在角速度達到800°/秒的極限狀態時,仍能精準無誤運行。
“天問一號”的進入艙,與我們之前登月的“嫦三”“嫦四”登月艙有什么區別呢?火星車總體主任設計師陳百超告訴記者,“天問一號”是我們中國人首次“探火”,而且要一次性完成“繞、著、巡”的任務,因此,進入艙的質量盡可能輕一些,以盡可能地將有效載荷讓給火星車和它搭載的科學載荷。因此,進入艙沒有攜帶太陽翼。而“嫦三”“嫦四”著陸器隨身攜帶太陽翼,它能在月面持續保持工作狀態。沒有太陽翼的進入艙著地后,它的電力主要源于攜帶的電池,所以必須在幾個小時內自主完成著地后的一系列工作,而不能等待建立與地球測控中心的聯系后再由地面發出指令。
進入艙平安著陸火面后,最重要的就是釋放火星車。但它沒有自主旋轉、調整方向的功能,萬一著陸后發現前方原定的坡道方向不合適,怎么辦?研發團隊讓它具有坡道前后方雙向自主展開功能,既可向前方展開,也可向后方展開。通過進入艙對坡度的預估,選擇合適的展開方向。
“祝融號”火星車是向東駛入火面的。美國“好奇號”“毅力號”都是1噸級以上的火星車,而“祝融號”的質量只有240公斤,但它是個“智慧的小個子”,在行駛和越障性能上,與別的火星車不相上下。“好奇號”能爬坡30°,而30°的坡我們“祝融號”也能爬。
火星表面主要是沙石性土壤,堅硬而尖銳的巖石分布較多,容易損壞車輪。研發團隊針對性地采用了鋁基碳化硅一體化成型車輪,雖然質量較輕,但強度高、而且高耐磨,增強了“祝融號”車輪的可靠性。
火星車一般的時速是多少?陳百超說,如按照它將地面信息傳回地球,地面為它規劃行走路徑,它再執行“盲走”的方式,可以達到200米每小時的速度,如果讓他自己找路行走,可以達到50米每小時速度。
沒有想到的是,2008年5月25日才著陸火星的“鳳凰號”,僅工作了30多天,就因為火星的低溫而“凍死”,地火信號中斷。可見火星車的保溫并非易事。火星存在大氣衰減,到達火星表面的太陽輻射強度僅為不到0.3個太陽常數,地球表面每平方米的太陽輻射常數是1367瓦,而火星表面僅為589瓦。
針對這一挑戰,研發團隊突破納米氣凝膠材料制備和結構-熱控一體化集成工藝,采用高效太陽能利用技術,創新實施了“太陽能集熱器”熱控方案。傳統的方式是將太陽能轉化為電能,再由電能轉化為熱能,這個轉化過程的轉換效率大約為30%;而他們的創新讓太陽的光能直接轉化為熱能,轉換效率可達到80%左右,并采用了有特殊涂層的吸熱板,吸熱系數很高而散熱系數很低。
新研發的行星際測控通信技術,是“祝融號”上的又一項科技創新。陳百超說,無線電信號衰減與距離的平方成正比。地球與月球距離30萬公里,地球與火星最遠距離是4億公里,兩者距離相差1000多倍,那信號的衰減就是10002,也就是100萬倍,這意味著同樣的一個信號,從地球到火星的強度比從地球到月球的強度要低100萬倍,所以必須突破數字化高靈敏度深空應答機技術,突破高靈敏度高動態信號接受,我們做到了。
目前,火星在距離地球最遠4億多公里的位置。陳百超說,這種情況每2年出現一次。
在火星軌道上運行的“天問一號”環繞器和火面上的“祝融號”還面對“火星合日”的考驗。何為“火星合日”?就是太陽對火星的連線與火星對地球的連線兩者之間的夾角較小,又稱進日凌;夾角變大后,為出日凌,這種天文現象大約每26個月出現一次。日凌期間,從地球上看不到火星,因為太陽將其完全遮蔽。而太陽強烈的輻射會干擾甚至切斷地火之間的無線電信號,所以在日凌期間,科學家通常會暫停火地通信。

陳百超說,現在火星正逢夏季,我們還調整了火星車的朝向,讓它向東,用火星車的桅桿遮擋一部分陽光,在日凌期間給火星車降降溫。
火星夏天的氣溫是多少?陳百超說,火星白天空氣的溫度是-20℃,但火星的地面溫度卻超過10℃。為什么火星空氣溫度和地面溫度的溫差那么大?那是因為火星的空氣密度只有地球的1%。而地球上空氣密度大,所以空氣溫度和地面溫度的溫差通常不會這么大。但到了晚上,即使是夏天火星的地面溫度也會下降到-95℃。為此,“祝融號”又做了必要的保溫措施,使艙內保持安全的環境溫度。
目前雖是日凌期間,“祝融號”暫不執行火面巡視及科考任務,但孫澤洲率領的五院探火團隊,仍在為環繞器和火星車出日凌后繼續執行探測任務而精心優化設計方案。
孫澤洲最后對記者說,“天問一號”火星探測任務圍繞“火星表面土壤特征與水冰分布”等五大科學目標,開展環繞探測和巡視探測,實現深空探測技術的跨越和科學的新發現。
“天問一號”,我們期待著你為祖國,也為人類帶來科學的新發現、新認知!
(編輯 韋 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