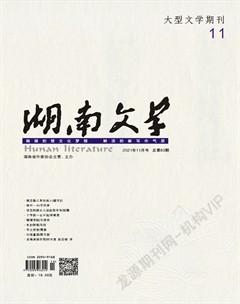風景中的故鄉
謝新茂
白云巖
多少年前的一天,母親背著一身沉重的暮色歸來,興奮地說,她上了白云巖。
正月里,父母請了一個巫師,半夜時分偷偷摸摸在家里打卦。巫師一頓念念有詞,然后說,得去南岳燒香,請送子菩薩保佑。母親生了好幾胎,只成活了我和妹妹兩個。父母慢慢年紀大了,面對人丁稀薄,心生惶恐,荒落落地要向巫師討教添丁之法。
巫師一臉肅然,口里吐出很深奧的幾個字,伸出兩只雞爪般的手指,撮了地面上兩只紫檀木課卦塞在懷里,攏了一個紅包,提了敬神時宰殺的大公雞,泰然而去。母親最終沒有前往南岳大廟。老家離南岳天遠地遠,家境艱難,湊不齊去南岳的盤纏。在家鄉風傳中,白云巖的送子觀音很靈驗,母親便上了白云巖,敬了觀世音菩薩。白云巖上有三座寺院,從下到上分別是牧云寺、毗盧寺、妙音寺,參差住著尼姑師父,中有一個法號明德的,頗有聲名。當時,邵陽城里退休的大嬸老奶奶,每年端午至中秋期間紛紛召喚乘車去南岳大廟敬香。從南岳返回,再從邵陽城北行四十多里來到白云巖上的寺院“燒回香”。她們或乘車,虔誠者干脆步行。我那時在新田鋪鎮上上中學。新田鋪是邵陽前往白云巖的必經之處,上學放學,時常與這些提著香籃,步行去白云巖燒回香的大嬸奶奶們相伴而行,記憶最深的,是她們臉上虔誠的神色沐浴在早上嘩嘩流淌的陽光里,纖毫畢現。
母親只到白云巖上燒了回香,菩薩不靈,她的添丁之念也就沒有結果,最終依然只有我和妹妹兩個陪伴他們一輩子。
不僅是父母,附近的鄉親家里有什么事,第一個念頭,也是到白云巖上去打卦抽簽燒香。燒香歸來,他們的臉頰上大都浮上一層興奮的神色,仿佛所求之請已得到白云巖上眾位菩薩的親口許諾。但結果大多讓他們失望,該貧還是貧,該病還是病,該出意外還是出意外。生活中的一切,并沒有沿著他們心中向往的軌跡前行。
整個少年時代,白云巖留給我的記憶,就是深山老林里的一座廟。這座廟已經破落,一點都不靈驗。
那個時候我還不知道,故鄉所在的縣,能夠稱為風景區的,唯有這座白云巖。還在明末清初,寶慶府城內一班有山水情懷的文人湊了個“寶慶十二景”,白云巖就忝列其中,名曰“白云樵隱”。是本縣境內唯一入選者。
然而,名為“白云樵隱”,其實是頗為尷尬的。這個名字聽起來很清靈,頗有仙風道骨的味道,深究起來卻有點悲涼。白云當然是有的。這個地方是邵陽丘陵向雪峰山過渡的第一波高山——板竹山。從邵陽城里望去,板竹山就是一排威武的哨兵,橫亙在北邊的天際。沿著板竹山北偏西方向去新化,翻過第一個埡口,就是白云巖下的白云鋪。群峰環繞之中的山槽就是一口巨大的陶缸,除了初秋云淡風輕,一年四季,黑夜里從半空中滴落下來的雨霧被高山所阻,翻不過山巔去山外云游四方,只能如關在羊圈里的雪白群羊,擁擠在山凹里左沖右突翻滾升騰。站在白云巖上的山巔,只見整個山槽里的云海掀著巨大的波浪推向前面的山峰,又呼嘯著被遠處的山峰擋回來。清麗的陽光覆蓋著白云,夢幻般的霓虹花朵在波浪的浪峰上燦爛地盛開。只有座座陡峭的山巔立于云海之上,猶如大海中的孤島,隨著白云浮沉。
“白云巖”之得名,大抵是來于此吧。
除了云,還有茂密的山林。白云是森林的肥料,把山上的樹木養育得粗大壯碩。刺向天空的青松、楸樹、楓木,一個個身材挺拔,三五年就成了英俊的小伙子,即使是緣地而生的灌木叢,也是一年半載就將山坡的縫隙鋪陳得嚴嚴實實。在當年,木柴是生活中最不可或缺的能源,山外附近的人家進山到白云巖所處的板竹山砍柴,是打小時起就必須實踐的功課。余生也遲,沒有到板竹山砍柴的苦難經歷,但我的父親,從七八歲上就開始進山砍柴,脖頸處挑柴磨起的肉瘤一輩子都沒有褪盡。而山里人,將砍好的上好木柴或者燒制好的木炭挑到城里去售個好價錢,是他們謀生最重要的手段。我小的時候,還能夠經常看到他們挑著木柴或者木炭到城里叫賣的身影。這些賣柴翁或者賣炭翁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瘦削的身材頂著一張烏黑的臉,卑賤的笑容里永遠彌漫出一股汗堿浸發出來的酸臭味道。
在白云巖,漫天的白云把樵夫的身影隱去了,只有他們斫柴的橐橐聲在白云深處孤單而沉重地回響,猶如白云中抽出的血液在一點一點地滴漏。這樣的一幅風景,與其說是仙風道骨,不如說是訴說生活的酸楚。
白云巖離我的老家不遠,近二十華里。但我在上大學之前,一次也沒有去過。我正當年少,無求于白云巖上的菩薩。家貧,每天除了上學,就是撅起屁股在田野里抽絲一般抽取一些能夠飽肚皮的糧食。大米飯、紅薯,各種各樣的桃木李果,甚至野地里長出的馬鞭草的嫩莖,都是我當年垂涎三尺的珍饈,能夠叫我的雙眼發光。白云巖上不靈驗的菩薩和險峻的大山不能填飽我的肚皮,是激不起我半點興趣的。
我第一次上白云巖,是在我大三的那年暑假。一幫子大學同學來我家玩,他們要看看附近的風景,我便帶他們去白云巖爬山。
進山的路還沒有修。從山腳下的白云鋪拐進去,在田壟中走過一大段田墈路,攀爬一大段曲折陡峭的山間荊棘小道,終于到達半山腰上白云巖的山門前。其時我的心情已迥異于蝸居鄉下時的心情,作為所謂的天之驕子,初夏時節滿山的青翠就是我們嘹亮的前程。心情好,風景才美。邁進山門,踏云履月走上架在山間小溪上的會仙橋,我們就是人們要覲見的仙人。蹦跳著來到毗盧寺的大堂,對正堂內莊嚴的佛座正眼也沒瞧一眼,巡視一般左望望右摸摸,又風一般出來,輕盈跑過被歲月洗刷成幽青色的石板路,一路嘯聚而行,全然不顧寺院的住持和一眾香客投來側目的眼神。當時還是八十年代初,破敗的寺廟未曾修繕,蒼老得有點歪斜的粉墻和籠罩著一層煙熏而成的黑翳的碩大菩薩,寥落地散發出歷史的幽光。我們沒有興趣拜見它們,只有毗盧寺與妙音寺之間那些參天樟木撒下的濃蔭,才讓我們稍事停留,回望一下山腳如畫片一樣玲瓏的田野。清涼的山風從溝壑間的縫隙里吹著激越的哨音卷過來,蕩滌著我們的胸懷。我們哦嗬連天,跑過毗盧寺,越過最上邊的妙音寺,又手腳并用,往妙音寺后的山頂上爬去。
通往山頂的石階還沒有修建,只有一條若有若無的樵夫砍柴攀爬出來的小道。但這難不住我們。我們像兔子一樣在山道中穿行,所到之處百蟲噤聲,百鳥飛離,只有藤蔓上結出的緋紅的野泡,燈籠一樣照耀著我們。離山頂不遠處,一面高可盈丈的壁立懸崖迎頭擋在面前。我們稍事休整,搭起人梯,下面的同學把上面同學的雙腿一托,上面的同學立即輕盈地攀爬了上去。幾乎沒費什么力氣,我們一干人等就來到了山頂。
作為風景,白云巖的妙處只有站上最高峰才可領略。目光往南越過板竹山最后一道屏障,一望無際的湘中丘陵畫卷一樣從山底向遠方的天際線鋪去。夏日酷暑的煙塵中,金黃的、青蔥的或者是明鏡般的稻田,正被不知疲倦的農人們一筆一筆地描摹。那些匍匐于田野之間的青黛丘陵山岡,安靜地依偎于田野的四周,成為農人們最好的休憩之地。田野和丘陵之間,大都是農民的土坯房,在煙塵中與田野的顏色融為一體,午后裊裊升起的炊煙,傳遞著生生不息不絕如縷的夢想。往北望,則是波浪一般的連綿大山。群峰之中并無樵夫砍柴的橐橐聲,只有綠色的森林在火焰般舞蹈,偶爾有叮當的牛鈴聲從森林的縫隙中傳來。云是少不了的。夏天的云朵有點稀薄,一絲絲,一朵朵,如輕盈的少女在山峰的溝壑里緩緩飄蕩,晶亮的眸子把陽光映照出千絲萬縷的夢幻。白云飄忽,牧笛橫吹,目光所及的一切風景,全是一幅安詳卻又生氣勃勃的模樣。
所謂看風景者,展現的其實是自己的心情,也展現著自己的生命處境。第一次上白云巖的心情,讓我對這道故鄉的風景一改過去灰暗落后的記憶,并一直充滿了好感。此后,我不知道上過多少次白云巖,有事無事,我都愿意到白云巖看看,讓自己的內心與故鄉的山水做一次親切的交流。
山上的寺院幾經修繕,現在已煥然一新。新修的旅游公路直達山門,山門口的賓館氣派也頗巍峨。寺院的尼姑在住持的帶領下,潛心向佛,除了接待四方香客,竟日青燈黃卷目不斜視。就在今年四月,我最近一次上白云巖,走進上庵妙音寺的大堂,一個年輕的小尼正跪在觀音塑像前,虔誠地誦讀著《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面對游客的議論與指點,及游客對她好奇的注視,她連眼睫毛都沒有眨一下。她已經進入到了既無他也無我的境界了吧?此時的白云巖還沒到香火的旺季,寺院的住持已經率領著一眾僧尼到山下化緣去了,偌大的妙音寺只有她一個人在家住持。她的虔誠與慎獨,常人難以企及。
只是,我每次上白云巖,都不曾以虔誠的心禮佛。在菩薩面前雙手合十打躬作揖時而有過,但那是小和尚念經,有口無心。對佛的敬重之心倒是慢慢地生發出來,走進佛堂,不再嘻嘻哈哈,而是噤口不言,面色如水。我知道,無論是寺院的僧尼,還是敬拜的香客,他們有著自己的信仰。我不能擾亂他們,就如他們不會強加于我和普通游客一樣。我只看風景,只閱讀這一眾寺院的來歷,聆聽關于它的種種傳說。正如妙音寺大殿兩旁的對聯所述的:
云郁山峨,云是山,山是云,云卷云舒山自在
風清洞古,風生洞,洞生風,風噓風吸洞無心
白云巖上的古庵自南宋寶佑年間始建以降,不知閱盡了人間多少悲喜。然而在悲喜之中,它不發一言,自在云卷云舒,于風噓風吸之中吐故納新。我也一樣。我從不信佛,但每一次來白云巖,喝幾口清冽的山泉,吸幾口清涼的山風,我的心就安靜幾分。第一次來白云巖的輕浮慢慢地被人生閱歷剝離,留下的只有對生活的敬意。
我的父母,我的父老鄉親又何嘗不是如此呢?我的母親當年為了求子上白云巖,并未因為白云巖沒有幫她實現夢想而詆毀它;相反,母親如今依然每隔幾年都要不顧八十多的高齡,到白云巖的中庵敬上幾炷香。我的鄉親有事沒事,依然要上白云巖燒香打卦。他們都不是佛教徒,但在他們心里,白云巖卻仿佛成了內心的皈依。他們并不奢望白云巖能夠改變自己的生活境遇,只是在生活遇到波折時,讓白云巖能夠撐起內心對未來的信仰。
白云巖歷經上千年的香火氤氳,早已溶進了父老鄉親的血液里。在他們的潛意識中,白云巖的千年古剎就是生活中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是內心深處的一道風景。
白水洞
我從未見過如此熱情的山峰。出縣城一路向北,剛剛進入頎長的田壟,山巒就蹦跳著遠遠地從田野兩邊斜刺里迎了過來,簇擁著我們逶迤而行。新修的草砂路彌漫著淡淡的清香氣息,與田野上春草的香味融合在一起。山峰跳躍的身影越來越狂野,身軀也越來越高大粗壯,開始時淺淺的淡墨色漸次浸成青黛色,又幻化成濃墨色。天空被山峰不斷切割,進入兩山夾峙的公路,我們的雙眼完全被山峰占據。春光中明鏡一般的田壟逐漸被擠成窄窄的一條,又擠得只剩下一條淺淺的溝壑。
推至溝壑最深處,兩列狂奔的山峰終于迎面相撞,電光石火之下,巨大的山體轟然扭曲,麻花一般糾纏爭斗,七扭八拐地繼續向北邊奔去。濺落的碎石飛上天空,又橫七豎八地掉落在溝壑之中。沒有被撞飛的山體,已然是遍體鱗傷,似刀削,似斧劈,又如鑿子鑿開了似的。卻愈加雄壯,猶如剛從戰場歸來的衣衫襤褸的壯士,凜然而立,鐵骨錚錚的“士”的印記,鐫刻在最顯眼的山巔。
從兩山相撞的隘口往回望,那一壟在陽光下波光粼粼的田野,就是從此處拉出來的網格疏朗的漁網,舒緩地在兩岸的山腳鋪陳而下。漁網上金光閃閃的金屬吊墜,就是青山旁白墻青瓦的農舍。從漁網上滴落下來的晶亮水珠,匯聚的就是苗條如十五六歲少女的白水河了。
青山碰撞之處,就是莊稼地與風景區的分野。往外,是千百年來人類賴以謀生的土地;往里,就是開發不久的白水洞風景區。
離開故鄉之前,一直不知道有個叫白水洞的地方。那時候鄉親們最緊要的事,是尋思著怎樣填飽肚皮,即使知道這溝壑中的風景與外界大異其趣,可它產不出半粒稻米,也長不出半截紅薯,也就不會駐足欣賞。倉廩實而知禮節,富足是欣賞風景的前提。千百萬年的白水洞佇立于我們眼前,哪怕美如黛玉,可我們卻是一群焦大,都沒工夫正眼瞧她一眼。
初次聽說白水洞,大約是在一九八七年。這時候我已經上過大學,在外地一座小城當老師。暑假回鄉,某一天抽空與縣城工作的同學一起玩耍。同學提議,白水洞風景好,或可去看看。我一臉茫然,說,白云巖吧?哪有個白水洞?同學解釋,是白水洞,新發現的景點。
可我并無興趣。在我看來,所謂新發現的風景,只是原來人跡罕至之處,被好事者突然發現迥異于平常之景象,視為新奇而已。
新奇是風景的第一要素。但我此時沒有看新奇的心情。我已經沒有了饑餓之苦,但依然得幫著父母打理農事。父母正繡花一般蒔弄著農田,暑期正是莊稼地里活計最繁忙的時候,我一回家,就是最大的幫手。我不用承擔收成不好的壓力,那是父母的事,但我必須參與,不能做旁觀者。我來縣城同學處玩,是同學的友情;回家幫父母做農活,是兒子的本分。當年的白水洞,是剛發現的新奇之景,巍巍青峰吐納的霧嵐也許能夠洗滌內心的煩躁,白練飛瀑濺起的碎玉能讓你感受到少女般的調皮與野性,但和剛剛好起來的生活相比,新奇的風景還無暇顧及。我只能領謝同學的好意,在最早的那一刻與白水洞失之交臂。
這一失就是三十多年。待我首次去白水洞,已經由追風少年成了慈眉老者。
白水洞當然有它的新奇之處。我從未見過那么純凈的水。白水洞的水,從幽深的深山洞穴中叮咚而出,從高聳入云的山巔飛濺而下,遙看成泉、成練、成潭,并最終成河,近看,卻是透明得幾近于無的。魚在溪流中的石階上跳躍騰挪,石階兩旁只見清澈的河床,卻往往忽略透明的泉水。飛瀑下寬闊的清潭,映照的天空與潭底的鵝卵石和諧地融為一體,叫人分不清是天空潛入了潭底,還是鵝卵石飛上了天空。
泉水的純凈意味著環境的純凈。于山壑蛇行,參天巨石、峭壁巉崖逼目而來,不小心就會把鼻子碰扁。奇特險遠之處,攀登自然艱難,也就杳無人跡。正因杳無人跡,才有這一泓沒有半點雜質的白水。白水的背后隱藏著險與遠,這是一種相互依存的關系,正如好氣質的女人背后,除了書香相伴,還有一個好男人的百般寵愛一般。這就有了白水洞第二個奇特之處:險遠。當我終于來到白水洞的時候,經過幾十年的打理,隘口處稍平整一點的地方,已經鋪上了平整的游覽路。不能修路之處,也已在深深溝壑上架起了拱橋,在懸崖絕壁的石頭縫開鑿出了陡峭的梯級。沿著梯級一步步攀登,絕壁、亂石、從天而降的飛瀑緊貼著我的雙眼,幻燈片一樣翻過了這一張,又推出另一張。氣喘之余,我可以想象當年沒有梯階時攀登的艱難。或許有一條若隱若現長滿苔蘚的絕壁小道掛在山崖,訴說著山里人爬出大山看世界的堅韌,但倘若要從這隘口進出一趟,是需要出一身臭汗的。羸弱如我者,稍稍瀏覽了一段,領略了大致景致,也就不再攀援,就著梯階歇息一陣,再緩緩原路返回。
隘口內,純凈的泉水,陡峭的巨石,天上的飛瀑,滿眼的藍與綠、滿口的甜與香、滿身的涼與熱,叫我們領略到險要之地的新奇。與之比較,我卻更喜愛隘口外的廊橋。山外的豁口緩緩向兩邊擴散,中間是清澈的白水河。木質的廊橋沿著兩邊的山腳在白水河上時東時西穿行而下,在青色的原野和陡峭的山峰間,走在廊橋上的嘎吱聲古樸而悠遠,頗有鄉村牧歌的味道。廊橋沿著白水河一直延伸,兩岸慢慢地有了平整而頎長的田壟,又慢慢地,田壟邊的山腳處轉出一排粉墻青瓦的簇新房舍。
歲月很安靜。在安靜中卻孕育著深刻的變化。當年衰敗的木板房已經從歲月中隱去,只在慈祥老者口中留下語焉不詳的傳說。當年形容憔悴的土坯房也已基本絕跡,只有漸漸傾圮的一兩棟隱于士兵一樣錯落排列的小洋樓背后,喃喃訴說著當年。短短幾十年歲月,這依偎于山腳下的房舍風景,已經換了一茬,又一茬。站在廊橋上看到的這些寬敞房舍,正當盛裝少年。廊橋上,不時走過手牽手的情侶。他們青春的身影與遠處的房舍相得益彰,成了風景中最靈動的部分。
這平整的田野、盛裝的房舍與靚麗的少男少女,在描畫著天際線的青黛的山峰映襯下,同樣是一道美麗的風景。隘口內的白水飛瀑、嶙峋山崖,是風景區清越的獨奏;隘口之外,整飭一新的田舍、廊橋,穿著時尚的游人與當地過著安詳生活的鄉親,就是從四面八方潮水一般涌來、彌漫于整個天際線之上的最嘹亮的和聲!
四十年前,我不知道故鄉有個白水洞。所有的鄉親,也沒有誰來關注白水洞。如今我們在生活走向了安逸與富足之后,心中有了風景,并按照心中的意愿打造它。風景的有與無,折射的是生活的品質。
我老家離白水洞并不遠,也就二十來分鐘車程。每次回家,我都驚詫于自然景致的變化。家鄉的農舍同樣多是兩三層的小洋樓,與白水洞隘口外的農舍并無太大區別,也是一副盛裝少年的模樣。當年開山造田被挖成癩子一般的山巒,現在已經成了郁郁蔥蔥的松山竹海,風吹來,颯颯的涼風霎時就能將我們的內心梳理得妥妥帖帖。山巒掩映之中有一個淺淺的山沖,鄉親們說,這是建休閑山莊最理想的地盤。我想,鄉親們既然有了這個心思,漂亮的山莊也許會在某一刻突然成為現實矗立于此,松林中也會突然延伸出許多條碎石鋪就的小徑,讓鄉親們在生活之余,沿著小徑抒發自己濃郁的浪漫情懷。
責任編輯:吳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