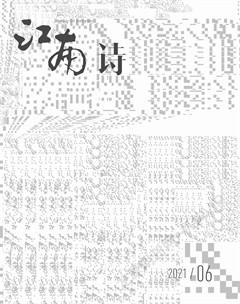人生如寄,蜉蝣一夢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
中國是有詩教的國度。
文字是有生命的,故孔子曰:文能行遠。
中國古代的詩人大多數是寫山水詩的高手,行跡所至,記游唱酬,留下來諸多膾炙人口的優秀佳作,而現代詩人已經基本上失去了這種能力。很多所謂的人除了自戀內心的一點點小情緒之外,既看不到小蝌蚪,也看不到青蛙。
我相信天地之間的人與萬物都有因果,舉凡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是有淵源的。“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山水即自然。
山水是古老的,又是常新的。寫山水詩,寫作者需要出現在現場,經過考察取得第一眼直觀的感受,這種鮮活的感受是任何閱讀都無法取代的。山水,也是文化的承載。某一山水在地域文化中的存在和變遷,只有地域的歷史的,才是獨特而準確的,但凡一個詩者,就不會只留意地理空間的山水,必定會探究其在時間中、文化中更久遠的存在。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二者不可偏廢。
有詩論家說,詩創作不外乎兩種方式:一種從里到外,從觀念出發,而化為形象;一種從外到里,從經驗感受,而得出主題。
我不是批評家,我不懂理論,我想說說自己。
我是文成人。文成在江南,溫州的西南部。
古往今來,在我們文成這樣的彈丸之地,也是出過幾個名人的。最賢者劉基劉伯溫,千古人豪,學為帝師,才稱王佐。
我的家鄉文成,全域5A,青山綠水,峽谷峰巒宛如畫境,溪瀑眾多,百丈漈飛瀑垂直落差207米,吉尼斯紀錄亞洲第一。境內洞宮山脈逶迤巍峨,四季飛紅點翠;飛云江蜿蜒浩蕩,常年淌玉溢彩。早在一千多年前,北宋地理總志《太平寰宇記》就贊其為“天下七十二福地,桃源世外無多讓焉”。文成是“生態的王國、風景的迷宮、萬物的樂園、旅游的勝地”和“天下第一氧吧”,是一片人間難覓的宜居地。文成既有清幽靈秀,又有雄強魂魄。猶如我做人渾樸,保存農民本質,也有一顆婉約的青綠心。
千古文人俠客夢。多年來,我是一個匆匆忙忙的趕路者,有時我的衣角還暗藏著浙江的波濤,而我的臉上已有北國的風沙;我的左手還殘留著新疆的白雪,而我的右手又觸摸到巫山的煙云。我差不多走遍了中國,我總在路上,總在行走,我的生命就在流動中存在。
然而,我不停地行走,卻始終在原點,仿佛我的行走是在原地踏步。因為不管我怎樣的遠離,我的心靈,我的詩歌,都停留在我的文成,我的包山底,我的飛云江。我四處游蕩,我的每一個腳步,落下來的,踩中的都是我的文成。文成就是我全部的故鄉,是一個理想的、田園的、詩意的棲息地。
我永遠是一個文成的土著。
在我的游歷中,在我的四處奔走中,我的心靈反而更加貼近我的故鄉,貼近我的生命的本源之地,我在遠離中靠近,在遠行中回歸。海德格爾說:“故鄉最玄奧、最美麗之處恰恰在于這種對本源的接近,決非其他。所以,唯有在故鄉才可親近本源,這乃是命中注定的。”能夠在本源之地詩意地棲居,我想作為寫作者我是有福的。我可以在故鄉居住,“故鄉本身鄰近而居。它是接近源頭和本源的原位”。(海德格爾:《荷爾德林詩的闡釋》)。
飛云江是溫州的一條重要的河流,也是我安身立命的一條江,飛云江從精神的底子上看,其實是一種無聲的文學。“人生開始匍匐在地面上,并逐漸失去了站立起來的精神脊梁”。這幾年來我一直在關注著她,審視著她每天從我的家門口流過。
在我的包山底和飛云江還有更大的天空和大地,我每天在這塊土地上行走,時時接受天道人心的規約和審問。當我把自己放逐在生活的飛云江畔,在這方天地間思考、追問,用我微弱的詩歌發出自己的心聲。多年來,我以飛云江和包山底為背景,用詩歌呈現飛云江流域獨特的風土人情,用詩歌反映我個人心目中的這方山水。
“求田問舍”。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如今到處圈山圈地,開發旅游賣門票。
今天的江南煙雨依舊,山水如故。但已經不是李白的江南,也不是蘇東坡、白居易、張岱他們的江南。
城市化之下,我們的老家都被拆了,假若我還有一點點的鄉愁,也已經面目全非。
城市化和工業化如同我們的鐵道運輸不斷提速、提速、提速,商品大潮又洶涌澎湃、無孔不入,這使得我們往往對身邊發生的事還未做出判斷,便已深陷危機之中。三聚氰氨、皮革蛋白、地溝油、毒大米、毒醬油、偽劣藥品、偽劣補品無窮無盡,早就不是新聞了。我們走的路,先是鋪沙子,接著鋪瀝青,然后是水泥,而且越鋪越寬廣,越鋪越看不見青草、藍天、大地、河流。每天出行,不是人包著鐵,就是鐵包著人……
我的故鄉在哪里?
故鄉,只是我的一個夢!
對于詩者而言,那就是遠方。
海子說,遠方除了遙遠,一無所有。
從大里說,詩歌有宇宙論、本體論的宏大意義,從小的說,詩歌不過就是一些個人化的零碎記錄。好的詩歌和其他藝術一樣都是個人的創造,個人情感、人生感悟、家國命運,無論大事瑣事,只要與個人的情感和美感世界發生關系,詩的境界就豁然開朗。
在當下,高速時代,我們享受著物質的聲色犬馬,面對殘山剩水,我們焦慮,痛苦,缺乏自信,不懂得如何說話。
不應該把詩歌看得太大,詩歌本身是有限的。詩人是“失落的思想的殘余物”。工業革命后,眾神紛紛走下祭壇。
我的朋友胡弦曾經為我的詩集《行者》寫過一個評論,他提到中國古代的山水詩十分發達,是中國文學和中國精神、意境的重要組成部分,名家輩出,名篇迭出。到了當代,山水詩卻處在了一種很尷尬的境地。由于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的快速發展,大量擠占了山水自然詩的發展空間,使當代詩歌里有敘事詩、口語詩等,卻已經沒有山水詩這個分類。再加上旅游業的過度發達,景區取代了山水,把山水自然給割裂了,不知不覺給寫作者一種游客心態,進而給當代詩歌寫作帶來很大的危害。胡弦說:“從慕白的寫作看,他看似隨意行走,寫的是一種‘遇見,實際在心理上,卻更像一種追尋:一種從寫作對象到自己詩歌追求的追尋。或者他對當下的山水詩境地有所思,也同時想有所矯正。”
博納富瓦在《論詩的行動和場所》里說:“詩與希望,我本想把二者結合起來,我幾乎想把它們視為同一。但這卻是一條歧途,因為詩有兩類,一類是虛幻的、騙人的和致命的,就像希望也分兩種一樣。”
人生有些事情永遠是無奈的,精神的自由或許可以讓我們保持一種平衡。寫詩這一種自覺的行為,可以把良心、道義、責任與審美結合起來,在真切的物質生活的表層下對精神世界做些探求、體悟生命,還原生活的真實面目。
《周易·盅》上有語:“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周易·履》上有語:“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安性守道,我只想做一個歸山的隱者,稟性自然,冶于真性!
以自然山水的美感,填補自己生命的每一個休閑的空間,平息種種功名利祿追盼而產生的痛苦焦慮,把生命消融在高潔優美的自然山水之中,獲以精神靈魂安頓的家園。人生之旅中,寫下的每一首詩,都是融涵著對人生深刻的反思,以深沉的哲理和濃郁的情思融匯于自然山水審美之中,表達了人生無常無奈和蒼涼宇宙意識!
尋訪山水,成為生活的一部分。我一直幻想著與先秦或者魏晉,或者隋唐的那些詩人一樣,浪跡天涯。一個人把自己嵌入山水間,成為一個自然之子,該是多么的幸福。讓自然狀態的山水,直接變成了胸中丘壑。
一個男人要走多遠,才能成為真正的男人?
正是因為讀懂了山水,山水才會賜予你別樣的生活,你也才能于此中找到一個更準確的自我。詩歌,也才是真正地發為山水之聲。把詩歌當做精神家園來經營的,在詩歌的窩里棲居。詩歌創作,是一個思考和呈現思考的過程,是個人經驗的建立,是詩人的本分。正所謂“天空沒有留下翅膀的痕跡,但鳥兒已經飛過”。
而“詩人的天職是返鄉”,在未來的日子里,仿佛是一種宿命,“誰這時沒有房屋就不必建筑,誰這時孤獨就永遠孤獨”。
詩歌入人心者佳,人間正道是滄桑。心在空中搬磚,想筑一座天空之城,收留自己疲憊不堪的靈魂。詩不僅要格調,關鍵還是看風趣。我糾結于生活,寫過虛偽的證詞,我的內心不止一只魔鬼。
面對山水,我今天羞于稱自己為詩人。
現在不僅“包山底的小溪不見了”,“公豬都住上了別墅”。每天的新聞超出了我們的想象力。
人生是空的,詩歌也是空的,很多人喜歡拼命往中心擠,可是到了中心一看,里面也是空的。
山窮水盡處,正是柳暗花明時。寫作,最重要的是另立格局,別開生面。以中國古代山水詩而言,可謂前人之述備矣,但求新,總是用“今天”告別“昨天”,而且力求構成“明天”,它的價值之一,在于通過寫作,使其存在的時代更特殊,品位更健全,道德視點更清晰,使當代山水詩在更自由的范疇內區別于前人和同輩,避免同義反復。山水,因其永恒性,仍是一門嶄新的課程。
寫作如同祭祀,山水雅集,詩歌是一個人內心真實的謊言。
我們終將落入“走過來,走過去,沒有根據地”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