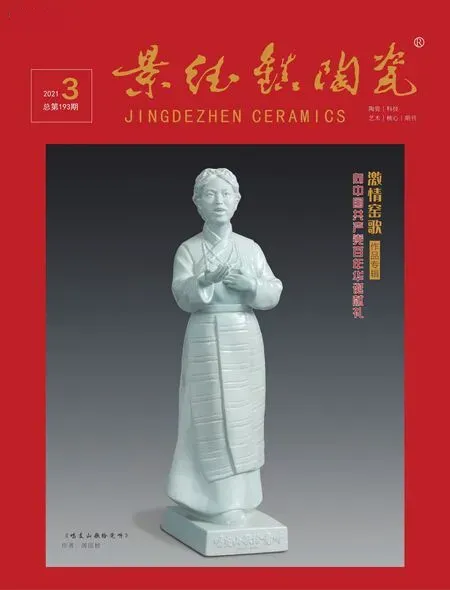釉上花鳥瓷畫的圖式表現及成因芻論
廖邦建
縱觀中國傳統美術發展歷史,花鳥題材在國畫領域占有重要地位,并在陶瓷繪畫中得到廣泛的應用。陶瓷藝術家通過不斷的實踐與探索,豐富了花鳥圖式在以陶瓷為載體的藝術形式上的運用與發展。其中,釉上花鳥瓷畫以其多樣的工藝表現技法、豐富的色彩表現形式和獨有的藝術風格,受到人們的喜愛。
一、釉上花鳥瓷畫綜述
由于受到傳統國畫的影響,釉上瓷畫所表現的事物和法則與國畫是亦步亦趨的。作為三大畫科之一的花鳥自然而然地成為釉上瓷畫的表現題材。但由于不同工藝技法在繪制、燒成上的區別,不同種類的釉上彩瓷也會呈現出不一樣的形式效果。釉上彩瓷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古彩、粉彩以及琺瑯彩瓷。
首先說古彩花鳥瓷畫,由于古彩線條硬朗且色彩深沉濃厚,使得古彩花鳥瓷畫整體呈現出古色古香的藝術風格,所畫的翎鳥植木都具有極強的裝飾韻味。琺瑯彩是皇家彩瓷,又被稱作瓷胎畫琺瑯。由于康熙年間禁海開放后,西方的工藝制品、藝術風格傳入中國,“琺瑯”通過廣州等港口流入國內的皇室、民間且受到追捧,瓷胎畫琺瑯的創燒與興起成了必然。琺瑯彩本身是屬于西洋傳入的異文化,于是琺瑯花鳥瓷畫中透著一股“洋味”,主要表現在明暗手法表現上。但是,琺瑯花鳥瓷畫作品的精神母體依舊是傳統花鳥圖式。粉彩瓷是清代康熙年間創燒的釉上彩瓷品種,它是在琺瑯彩瓷和古彩瓷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由于其獨特的制作技法,能夠使得燒制出來的成品色澤有溫潤如玉的效果。粉彩花鳥由于“玻璃白”技法的運用,使得畫面表現出“沒骨畫法”的渲染韻味,整體層次豐富,立體感強。另由于粉彩工藝的色彩柔和且豐富,所繪的花鳥呈現出秀麗淡雅的藝術風韻。
二、釉上花鳥瓷畫的圖式表現
1、題材表現
從描繪對象上來說,釉上花鳥瓷畫主要有實際客觀存在的自然花鳥,和從想象傳說而來的祥卉瑞獸這兩類。自然花鳥包括了翎鳥、走獸、魚蟲、草木、花卉等動植物,而祥卉瑞獸則來自圖騰、宗教、文學與民間傳說,像龍、鳳、仙鶴等都較為常見。
自然花鳥的選題與描繪常常伴隨著人們對自然物象本身吉祥或祈盼寓意的聯想,比較典型的動物類像喜鵲、蝙蝠、鴛鴦、錦鯉等;植物類像梅蘭竹菊、蓮花牡丹、壽桃靈芝等。釉上瓷畫中“歲寒三友”圖式流傳甚廣,比較典型。“歲寒三友”指的是以松、竹、梅為題材的花鳥瓷畫,因為這三種植物不畏風寒的堅毅精神而得名。最早的瓷上“歲寒三友”形式出現在元代的景德鎮,但當時主要以釉下裝飾為主,青花和釉里紅瓷都出現了大量這種表現圖式。在出現了五彩、斗彩、琺瑯彩以及粉彩裝飾后,三友圖的色彩形式、構圖形式和線條表現都被豐富和發展了。一般來說,三友圖的圖式表現主要以一松二梅三竹為主,“松”一般表現為粗枝盤曲;“竹”一般表現為竹節挺拔、竹葉繁茂;“梅”樹干一般干練婀娜,花苞秀麗小巧、花朵成群成簇。
祥卉瑞獸最早來自于圖騰崇拜,隨著社會的不斷演變,豐富出不同功能象征的奇珍異獸,具有政教功能和象征意義,龍畫及紋飾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龍”最早出現在舊石器時期部落的圖騰上,新石器時期也有龍紋彩陶器,戰國時期的彩陶上,龍鳳紋開始合并出現。到了漢代,龍、虎與朱雀配上祥云的圖式比較流行,常出現于彩陶壺、罐中,唐三彩更是將龍紋和龍畫不斷推向成熟。宋元時期陶瓷上龍的形態已經非常具象化了,宋代的定窯刻花龍紋缸、景德鎮窯青白釉刻云龍紋罐還有景德鎮窯青白釉云龍獅紐蓋瓶等都是典型器。元代時龍紋形式已經很多樣了,有云龍、蟠龍、立龍、龍鳳、趕珠龍等等。明清兩代是彩瓷的高峰發展時期,釉上龍鳳圖式也隨著朝代的變迭在形態上和色彩表現上獨具風韻,也出現了很多新的圖式:龍穿花、嬰戲舞龍和劃龍舟等等。
2、構圖形式
釉上花鳥圖式在構圖形式上,有純繪畫式、紋飾點綴或開光式、純紋飾式、文人詩畫式等。純繪畫式是指陶瓷畫面中只有花鳥畫,或傳統或現代,且畫面是全景構圖。紋飾點綴或開光式是畫面中有花鳥紋的點綴,但主體依然是花鳥畫。紋飾可以是頸部或底部的點綴,也可以作為開光的畫面切割,還有不具有紋飾的釉上開光花鳥瓷畫,一般是作為色地出現。純紋飾的釉上花鳥瓷畫一般出現在大批量生產的日用陶瓷上,紋飾可有節奏性地裝飾盤、碗、碟、罐。文人詩畫式釉上花鳥以“珠山八友”成就最大,一般畫面中有題詩和畫印,文人氣息濃厚。
不論哪種構圖形式,釉上花鳥圖式的主要表現對象依然是花鳥畫本身,在傳統花鳥畫圖式中,獨立成科之后的花鳥畫主要有折枝式、全景式兩種。所謂折枝構圖就是截取景的一部分,不畫全株的花卉,草木常常是穿插在畫面中的,會配以鳥禽或蜂蝶點綴。這種圖式給人浮想聯翩的想象,有弦外之音的感受。其次是全景圖式,全景花鳥瓷畫的畫面往往是比較宏大的,不像折枝圖式那樣只專注于一隅的細致描繪,而是對整個場景進行了把控,在空間表現上直追山水畫。在繪制的物象數量和種類上全景式花鳥圖式也是比較豐富的,可以繪制很多東西,有自然的熱鬧之感。
三、文化觀念和倫理蘊含是釉上花鳥圖式形成的根本成因
1、傳統文化觀念下的釉上花鳥圖式
中國傳統文化觀念是釉上花鳥瓷畫圖式的形成的內生原因,人們主觀地通過象征、類比、諧音等方式,在釉上花鳥圖式中加入對社會理想和道德品格的聯想,再現人們的內心祈望和價值觀念。
儒家文化思想長久以來植根于國人心中,以自然之物砥礪品行、寄托精神是儒家一直以來的教化方式。孔子就常以松柏舉例,來比喻君子堅毅不移的品格。還有像蓮花就被人們用來比喻君子“出淤泥而不染”的氣節;翠竹的凌寒而獨青常用來比喻不倚不懼的操守;野菊也被用于表達“寧可枝頭抱香死,不曾吹落北風中”的君子高節。具有吉祥寓意的花鳥圖式往往更加通俗且鮮明地表達人們心中的期盼,像松鶴延年、榴開百子、洪蝠齊天、喜上眉梢等等。這些往往是通過諧音或同音的漢字來進行聯想,滿足人們的情感需要。
2、倫理意義下的釉上花鳥圖式
藝術自產生以來就是具有倫理教化價值的,是創作者的規諫也是受眾者的主觀選擇。前文提及的花鳥圖式大多也具有道德勸誡的含義,而象征著福瑞祥兆的奇珍異獸就表現出來了濃厚的政教色彩。這種倫理教化不僅是針對民眾,也針對統治者。孔子所提出的“畏天命”說既為統治者提供了“天命”的合理合法性,也為君主權力和政治行為加上了“天命”的警戒與約束。這些對“祥瑞之象”的喜愛正是統治者與民眾對太平盛世的共同祈望,因此仙鶴、獐鹿、墨龍、神龜等等釉上花鳥圖式中蘊含著濃厚的倫理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