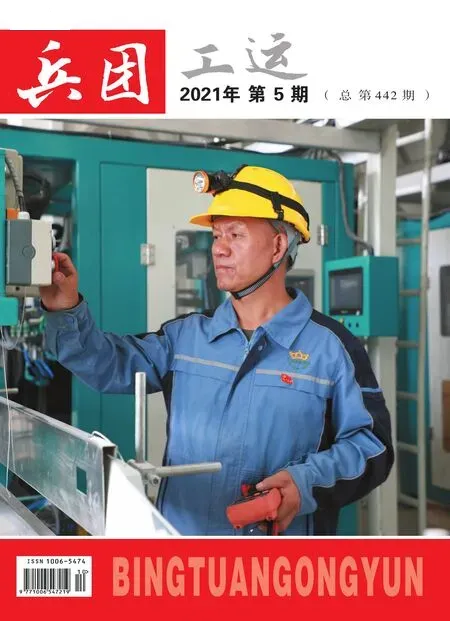英魂系家國 深情滿天山
——懷念父親李遲
□李東暉
夢里千回憶父親,醒來淚水濕衣襟。
父親已離開我們整整三年了。1000 多個日日夜夜里,仿佛父親還在書房里靜靜地讀書看報,還在他固定的沙發上準時收看晚上七點鐘的《新聞聯播》。父親的音容笑貌依然映滿我的腦海,讓我覺得父親從來就不曾離開過我們。每次回家,開門的瞬間我是多么期盼著再看到父親和藹的笑臉、關切的眼神,父親啊,您知道我們多么愛您、多么舍不得您嗎?
父親走了,雖然三年來我一直不肯接受這個現實。是啊,父親那么的愛我們,愛生活,愛工作,愛腳下這片他為之付出青春和奮斗的邊疆的土地,怎么會忍心離開呢?而我們又是那么地愛父親,他就是我們生命的源泉、人生的導師,我們怎么能舍得讓他離開呢?
這三年里,我一直想通過自己的回憶,追憶和父親一起生活的點點滴滴,還原父親歷盡艱辛、不忘初心的人生軌跡,講好先輩故事,讓兵團精神薪火相傳!
一
1932 年農歷八月十六日,父親出生在安徽省潁上縣的一個書香門第。父親從小就特別聰慧,學習成績最好,姐妹們都喜歡他。父親四、五歲時就在外祖父辦的私塾學堂開始了他的啟蒙教育,之后進入洋學堂直到高中一年級,由于家道中落,父親無法繼續完成學業。1948 年秋,父親勤工儉學考上了山東農學院畜牧專業,成為那個年代為數不多的大學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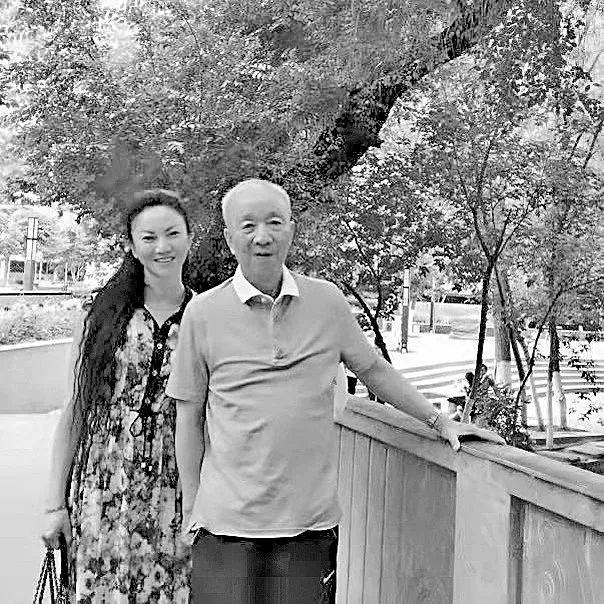
作者與父親合影留念。
1950 年初,父親報名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由于身體素質好、又是大學生,有知識有文化,父親成為華東軍區空軍第六預科縱隊學員、分隊長。駕駛著銀色的戰機翱翔在新中國的藍天上,是那個時代許多人的夢想,而這一切,即將成為父親生活中的現實。
二
天有不測風云。受家庭出身問題的影響,父親的空軍生涯很快就結束了。
1951 年,19 歲的父親在經歷了大學參軍、轉離空軍的挫折之后,毅然作出了一個影響一生的選擇: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進疆后立刻投入到了剿匪的戰役中。之后不久,組織上安排他到新疆軍區后勤部八一農場。因為父親在山東農學院學的是畜牧專業,八一農場畜牧營技術人員奇缺,所以就分到畜牧營任排長、技術員。
畜牧營遠在北塔山,部隊給父親發一匹馬,讓他自己騎馬前去報到。從烏魯木齊出發,父親騎馬走了一個多星期,人困馬乏,精疲力竭。一路上干糧吃完了,天寒地凍,狼群出沒,父親經受了饑餓、寒冷、死亡的威脅。當一匹餓狼撲向絲毫沒有躲避能力的父親時,一位好心的哈薩克牧民開槍打死了那只狼,并幫助父親抵達了北塔山牧場。從此,父親開始了67 年的邊疆生活,把自己的命運與國家、與時代緊緊地聯系在一起,把自己青春和理想、熱血和生命播撒在邊疆的土地上。
三
1953年,父親再次走進大學校園,成為新疆軍區八一農學院的學生。在校期間,父親學習刻苦認真,多次受到嘉獎,1956 年大學畢業后,留校任教兩年,但父親要求到艱苦的地方去鍛煉,被分配到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農六師勘測隊擔任技術員。從此,父親再也沒有離開過兵團。文革期間受到嚴重摧殘,但我從沒聽父親抱怨過。文革結束的那一年,父親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實現了為之奮斗已久的夙愿。從北塔山、南山牧場到八一農場、一O二團、紅旗農場、農六師機關,再到兵團機關,從技術員、股長、營長、場長、到場長兼黨委書記、師領導,再到兵團領導,父親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兵團,獻給了共和國的屯墾戍邊事業。
四
在我們的心中,父親不僅僅是個好黨員、好領導,他更是一個好丈夫、好父親。
父親退休以后,我曾經問起父親怎么和媽媽走到一起的。父親年輕儒雅,又是大學生、軍官,身邊應該有條件更好的姑娘,可是父親卻選擇了只有初一文化程度的母親,我們當孩子的有些好奇。父親告訴我,我就是看上你媽純潔善良樸實積極上進,任何工作都是拼命爭先。父親還說,你們都要向你媽好好學習,女人的優點你媽都具備了,她真是一個純粹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那個年代沒有花前月下,可父親的這番話無疑是對母親最浪漫的表白,是對半個多世紀相濡以沫的愛情的最好闡釋。在醫院的病床前,父親留給我的最后一句話是:照顧好你媽。父親最割舍不下的,就是陪伴他走過近60年風風雨雨的母親。
父親永遠是我們這些晚輩們心目中的偶像,威嚴不失親和,嚴厲伴隨和藹,儒雅灑脫,良師諍友。我們家有個不成文的規矩:我們從小到大家里吃飯都必須圍坐飯桌,而且每個人的位置是固定的,吃飯時很少說話,父母親落座后才能開飯,父親動了筷子其他人才能夾菜。當時特別羨慕那些端著碗到處串門的孩子,認為父親有些刻板,現在我們已經把這個習慣傳承下來。倉廩實而知禮儀,中國的“禮”學傳承,靠的就是一代代人的耳濡目染、潛移默化。
孩提時代生活艱苦,父親工作繁忙,可是父親從來沒有因此忽略了對我們的教育。父親只要有時間,就會給我們講《西游記》《水滸傳》、陪我們背唐詩、背“老三篇”,分辯關在籠子里的雞和兔子各多少只;弟弟小小年紀父親就給他講歷史故事、教他寫日記……
從小父親就教育我們,不要隨便收別人的東西,不說謊話,生活要樸素。作為一個女孩子,那時候我因為喜歡穿得漂亮一些,經常被父親批評,說我不夠樸素。那時候年輕不懂事,總覺得父親對自己有偏見。現在我已為人母,對父親當初的教導,也會給自己的孩子傳授,踏實做事、誠實做人、樸素生活已經成為代代相傳的家訓,流淌在我們的血液里。
五
父親最開心快樂的時光,不是當上了師領導、兵團領導的時候,而是他在紅旗農場工作的那段日子。1978 年12 月,父親由六師一〇二團調紅旗農場任副場長,1981年2 月任場長、黨委副書記,1983年11月調農六師任副師長。在紅旗農場工作了5年時間,側重做了五個方面的事情:一是落實政策;二是機構重建;三是開渠整地;四是科學種田;五是土地承包。
父親擔任兵團領導后,曾分管工業交通商貿流通領域工作。當時正逢兵團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轉型階段和結構調整期,工作千頭萬緒,壓力很大,吃不好睡不好,人也消瘦了許多。這期間,父親和同事多方努力,成立了兵團供銷合作總公司、成立了鄉鎮企業局,為推進兵團鄉鎮企業的發展及建立起兵團新時期商貿流通體系,貢獻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父親把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了這片土地,奉獻給了屯墾戍邊事業。一直到他退休后,依然心系兵團事業發展、關心職工群眾的生產生活。
2003 年夏季的一個周末,烏魯木齊下了一場大雨,之后接著是冰雹。整個天氣變化過程,71 歲的父親一直都呆呆地站在窗邊看著。作為女兒,我知道他又想到了團場的作物、職工的生活……而到了冬季,那飄雪的日子,父親臉上便會露出孩子般開心的笑:瑞雪兆豐年啊,團場豐收大有希望,職工生活有了保障。
從工作崗位上退下來之后,父親時常思念他曾工作生活過的地方。但為了不給基層添麻煩,父親總是讓兒女們開車陪他去悄悄走一走、看一看,從不給基層打招呼。有一次我們開車陪父親到六師五家渠墾區看莊稼生長情況,回來時正趕上飯點,于是我們一家人在路邊找家飯館吃飯。正巧,碰到了黨校的一位領導。他認出父親和我,非常驚訝地問我,領導出行怎么沒通知六師或者黨校?我說父親不讓通知,怕給大家添麻煩。從黨校那位領導看父親眼神里,我看到了他對父親油然而生的敬意。那一瞬間,我也理解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真正含義。
這就是晚年的父親。
相伴不知時光短,離別方覺日月長。父親啊,我們還沒來得及回報您,還沒有好好在您膝下盡孝,還沒有好好陪您聊一聊不平凡的人生,還沒有實現我們乘火車去歐洲觀光、五臺山看景的約定,您就匆匆離開了我們,親愛的父親!
往者已逝,來者猶追。我們定當化悲痛為力量,更加勤勉做事、寬厚為人,賡續精神血脈、傳承紅色基因,不會辜負您對我們的期望。在新時代兵團奮斗的路上,有堅定的目標、擔當的情懷、前行的腳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