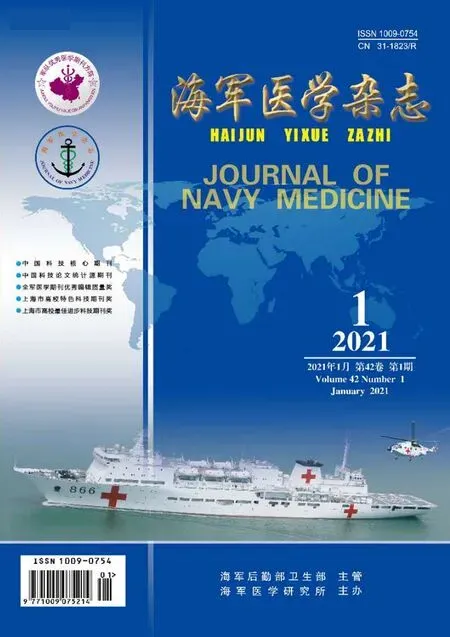軍隊護士戰創傷救治核心能力需求的質性研究
徐立,張笑平,李子文,湯淑敏,胡敏
衛勤保障是軍隊保存和恢復戰斗力的重要支撐,護士是衛勤保障體系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1]。當今國際形勢復雜多變,區域性戰爭或沖突接連不斷,做好軍事斗爭準備仍是我軍軍事醫學發展的主要任務[2]。目前各種現代化武器的使用使傷員傷勢呈現多元化特點,即損傷部位多、創傷面積大、晚期并發癥多、救護難度不斷增加等。同時,在和平年代,創傷的發生率也在逐步升高,其早期病死率高,誤診、漏診發生率高,感染發生率高[3]。本研究通過現象學方法對戰創傷救護專家進行訪談,整理出軍隊護士戰創傷救治中所需的能力,為制訂科學、適用的戰創傷急救護士培訓方案提供參考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2018年6-8月,采用目的抽樣法,選擇10名戰創傷醫護專家進行訪談,分別來自某軍醫大學的3所附屬醫院,其中男6名,女4名;人員類別:軍人8名,非現役文職2名;年齡:37~45歲;職稱:高級職稱4名,中級職稱6名;學歷:博士4名,碩士2名,本科4名;工作科室:普外科2名,麻醉科3名,急診科2名,骨科2名,燒傷科1名;從事戰創傷救治領域13~20年。采用方便抽樣原則,將每所醫院定位為1組,分為3組。納入標準:(1)長期從事戰創傷傷病員的救護;(2)執行過軍事衛勤任務,任務時間超過6個月;(3)有良好的溝通交流能力,語言表達清晰,愿意參加本研究。樣本量的確定以受訪者的資料重復出現,資料分析時不再有新主題呈現,即資料達到飽和標準。
1.2 方法
本研究運用質性研究中現象學研究法,采用面對面、個體化深入的焦點小組訪談形式收集資料,以錄音形式記錄資料。在訪談前對訪談對象進行訪談目的及內容的告知,在征得訪談對象同意后進行訪談及錄音。因本小組采用的是小組訪談形式進行,故選擇在場地稍大、不受干擾的自然環境中進行。訪談過程中由1名研究者進行提問并引導訪談主題,時間為45~60 min。訪談結束后,由現場訪談研究者反復回放錄音,逐句進行文字轉錄,并與另外1名研究者共同對內容分析整理。
1.3 訪談提綱
本次訪談圍繞“您認為參與戰創傷救治護士需要有哪些核心能力?”這一主題進行。訪談提綱如下:(1)您認為參與戰創傷救治護士需要哪些專業技能能力?(2)您認為參與戰創傷救治護士需要怎樣的護理管理能力?(3)您認為參與戰創傷救治護士需要什么樣的專業發展能力?
2 結果
2名研究者將轉錄文字進行分析總結,提取與本研究相關語言,按照一定內在關聯進行主題重構,共萃取6個主要概念:創傷救治專業態度、創傷專業實踐能力、創傷應急思維能力、創傷護理管理能力、交流溝通能力、創傷護理發展能力。
2.1 提升護士戰創傷救治的業務核心能力
2.1.1 戰創傷急救專業知識核心能力培訓需求 受訪的10名專家都表示,希望參與救治的護士能夠進一步加強戰創傷急救專業知識的學習,提升護士在救治過程中的能力水平。專家A:“護士在參與創傷救治之前最好能夠進一步系統性地學習一下創傷傷員的病理生理以及傷員在救治過程中可能出現的臨床癥狀及體征,便于護士能夠整體評估和救治傷病員,在戰創傷急救中同樣需要具備一定的創傷基礎專業知識后才能進行整體評估和救治傷病員。”專家D:“在搶救過程中,希望護士對于常規的急救藥品有所了解,尤其是戰場上可能涉及到的藥品,能夠明確藥品的作用、使用途徑、常規劑量以及副作用,進一步保證傷員搶救過程中的藥物使用安全。”專家J:“就我個人而言,還是希望護理團隊可以針對戰場環境下的傷員傷情進行系統及專業急救知識培訓,例如如何進行傷情評估、有效的傷情檢查、針對性的實施緊急措施及安全的后方轉運……”專家B:“對于不同傷情的創傷傷員,明確其每個階段的觀察重點和護理要點,不能以偏概全……”
2.1.2 戰創傷救治專業技能核心能力培訓需求 在訪談過程中,受訪專家都表示需要對護士進行有針對性的戰創傷技能培訓,并且應加強特殊的戰場專業技能如洗消技術、骨髓腔穿刺技術的培訓,提升護士在救治過程中的實戰操作能力。專家C:“在救治創傷傷員時,我希望護士能夠準確地實施急救措施,比如開放氣道,護士除了能夠知曉開放氣道的幾種方法,更應該明確每種方法適用于哪種創傷傷員,因為在戰場上突然出現大批量傷員時,護士可能需要在沒有醫生指示的情況下給傷病員立即實施緊急救治措施。”專家E:“目前,臨床護士對于戰創傷急救的四大技術熟悉程度不夠,不能夠及時有效地配合醫生進行救治,戰創傷急救技術應該需要加強訓練。”專家F:“在進行核、化、生戰創傷傷病員綜合救治演習過程中,我們發現護士對于核化生概念模糊,隔離衣的穿脫以及洗消等基礎操作幾乎不會。”專家G:“戰創傷救治的護士一般只有理論上的認知,沒有進行實踐培訓過,某次模擬張力性氣胸傷病員的救治,護士能夠描述緊急救治的過程,但實際操作卻不盡人意。”專家H:“針對戰創傷傷員的特殊救治情況,希望護理團隊能夠與時俱進地進行技能培訓,比如緊急情況下的骨髓腔穿刺技術,緊急壓迫止血的彈力繃帶包扎技術,出血傷員的填壓止血技術……”。
2.1.3 戰創傷救治業務核心能力培訓模式需求 戰創傷救治培訓模式有別于其他培訓模式,在訪談過程中也了解到受訪專家都傾向于情景模擬培訓模式。專家B:“只有在真實環境中,護士才能感受到急迫感,可以采用情景模擬教學法,模擬戰場環境,醫護互相配合完成救治。”專家D:“針對戰創傷救治的特殊性,我認為對護士的培訓不是進行個體培訓,而是以團隊形式進行情景模擬培訓,培養團隊的默契性……”專家G:“開發一些信息模擬軟件,在進行實際模擬培訓前,先進行計算機情景模擬,能夠讓護士直觀感受錯誤的操作會給傷員帶來怎樣嚴重的后果。”
2.2 提高護士戰創傷救治中護理管理的核心能力
2.2.1 戰創傷急救護士應急思維核心能力培養需求 戰創傷傷員的救治區別于其他傷病員,參與救治的護士應在醫生到達之前準確判別傷員的傷情,給予能力范圍以內的評估和緊急救治措施,對救治方案及效果做出科學判斷。專家B:“我作為創傷總值班曾組織過一次成批傷員的救治,護理團隊讓人印象深刻,現場負責協調的護理值班長在醫生達到前就已經啟動成批傷應急預案,對于傷員的病情做出初步判斷。在救治過程中,護理值班長還能夠對救治效果進行監控,整個救治過程都比較流暢。參與救治的各科醫生對于整個救治過程都比較滿意。”專家D:“曾參與過一次創傷急救,參與救治的護士能夠在我到達之前就已經測量出傷病員的生命體征,不管是血氣還是心電圖或B超均已完善檢查,到達現場后,不需要再等待相關檢驗結果,為傷員的救治節約不少時間。”
2.2.2 戰創傷護士協調溝通核心能力培養需求 戰創傷傷員的救治一般是多學科的相互配合,共同救治,協調溝通就顯得尤為重要。專家F:“對于創傷傷員的急救,救治環境非常重要,有效的溝通,不僅能夠安撫傷員,更能保障救治環境的有序性,為急救爭取更多的時間。”專家C:“在整個救治過程中,護士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傳遞信息,溝通病情,醫護不良的溝通定會產生不必要的誤會,提升護士的溝通交流能力,有助于創傷傷員救治的順利進行。”專家H:“在創傷救治過程中,我經常會發現,平時參與科室管理的護士對于搶救傷員的節奏把握得非常好,人員安排以及各項檢查落實都比較及時,銜接比較緊密,醫生都很喜歡和這樣的護士一起搶救。”
2.3 戰創傷護士業務發展核心能力培養的需求
護士需要在不斷探索學習過程中獲得創傷救治的新理念及新技術。專家A:“戰創傷護士需要不斷地進行業務技術的革新,學習新理念,便于更好地救治傷病員。”專家E:“創傷護理業務能力較強的護士,可通過經驗交流提升整體的戰創傷護理質量。” 專家F:“目前國內外一些戰創傷優質課程陸續推出,如國際創傷生命支持課程(international trauma life support, ITLS)、國家災難生命支持課程(national disaster life support, NDLS)、院前創傷生命支持(pre-hospital trauma life support, PHTLS)等,可以派遣護士參與學習,之后分享給其他護士,并在戰創傷救治中積極應用。”專家G:“科室可以組成戰創傷救治團隊,收集國內外先進的理念及技術,以不同的形式(小講課、操作示范等)授課給全科護士。”專家D:“作為戰創傷團隊的一員,個人非常希望護理人員能夠把成功經驗撰寫成論文供其他醫院參考,同時也非常愿意和護理同仁一起進行戰創傷護理的研究。”
3 討論
3.1 戰創傷救治護士核心能力質性研究的結果
研究中,眾多專家認為創傷護士首先需要在現有的護理知識基礎上增加創傷專科醫學知識的學習,以便于更好地救治創傷傷病員;其次,創傷護士需要能夠識別相關輔助檢查的檢查結果,并做出準確的反應;之后,專家們也認為創傷護士需要增加實踐操作能力的針對性訓練,以便在緊急情況下及時救治傷病員;最后,在應急思維方面,專家們一致認為有效的護理管理和醫護溝通尤為重要,不僅能夠管理好創傷就診環境,提升醫護工作滿意度;更能減少各種等候時間,提高創傷救治的效率。雖然目前國內大多數戰創傷護士的培訓依托急診護士的核心能力而構建[13],但通過專家的意見反饋可以發現,創傷急救護士能力要求還是區別于急診專科護士。創傷護士在專業知識上需要掌握更加全面的創傷專科醫學知識,對于創傷醫學檢查或檢驗結果能夠做出準確判斷以及實施相應緊急救治,同時對于創傷救治中的護理管理,專家也對創傷護士提出了更高的能力要求。
3.2 戰創傷救治護士核心能力培養模式的思考
在質性訪談中,專家團隊對戰創傷護士核心能力的培訓模式給予高度的關注。通過文獻檢索發現,國內外一般采用模擬訓練的方式進行培訓,如美國不僅在國防醫療戰備訓練研究所設置了相關戰場急救手術課程[4],而且美軍還開展了包括巨蝮蛇野戰訓練[5]、模擬環境(wide area virtual environment, WAVE)訓練課程[6]、創傷技能中心(center for sustainment of trauma and readiness skills, C-STARS)訓練課程[7]、高級創傷計劃(advanced trauma training program, ATTP)訓練課程[8]、基于馬迪根模型的戰術戰傷救護(tactical combat casualty care, TCCC)課程[9]等新訓練模式;法國的軍事衛生署制定了包括建立骨內通路、氣胸減壓、環甲膜切開術等前線戰傷救治(sauvetage au combat, SC)標準化培訓練習方案[10];以色列的醫學模擬中心為預防化學武器戰爭制定了有針對性的實踐培訓[11];泰國的phramongkutkla軍事醫學院的課程亮點是以“Operation Petcharavut”為代表的戰場模擬操作訓練[12]。雖然近幾年我國戰創傷救治發展迅猛,有些軍事院校和衛勤保障單位以情景模擬的形式還原救治的現場[3,13],使得受訓對象能夠感受戰場氛圍,但是并未在所有軍隊醫院進行推廣和開展。因此,已經開展戰創傷情景模擬并獲得成功經驗的院校和單位應總結經驗、發表文章或者開班授課,不斷提高我國戰創傷護士核心能力培養。
3.3 戰創傷救治護士核心能力研究的重要性
我國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引進職業核心能力的概念,2005年衛生部指出要根據臨床專科護理領域的工作需要,有計劃地培養臨床專業化護理骨干,建立和發展專業護士[14]。隨著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創傷傷病員越來越多,創傷救治問題就越發突出。伴隨醫療的迅猛發展,貫穿整個救治過程的護理人員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戰創傷急救護士核心能力的研究不僅能夠反映出護士在急救過程中各種能力的需求,為后期培訓方案的制定提供科學依據,更能夠為戰創傷護理的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