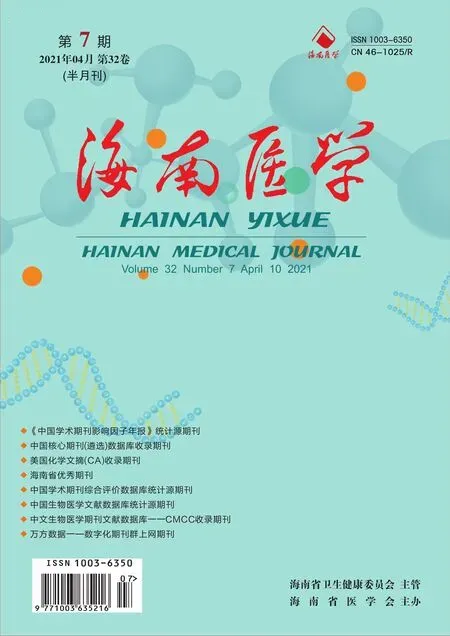系統(tǒng)性紅斑狼瘡合并重癥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診治體會(huì)
曹金鐘,吳松,王慶軍,李毅
1.天津市第三中心醫(yī)院分院呼吸科,天津300250;
2.天津市胸科醫(yī)院呼吸與危重癥學(xué)科,天津300222;
3.天津市泰達(dá)醫(yī)院內(nèi)科,天津300457
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又稱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作為一種按甲類傳染病管理的法定乙類傳染病[1],其危重癥病例多伴有慢性基礎(chǔ)疾病且預(yù)后不良[2-4]。系統(tǒng)性紅斑狼瘡(SLE)是一種多系統(tǒng)受累、病情呈復(fù)發(fā)緩解相交替的慢性過(guò)程的疾病,且國(guó)內(nèi)目前尚無(wú)針對(duì)SLE的標(biāo)準(zhǔn)化慢性病管理模式[5]。SLE患者繼發(fā)感染的風(fēng)險(xiǎn)明顯增多,感染性肺損害的比例約為34%[6-7]。文獻(xiàn)檢索有關(guān)SLE合并COVID-19的臨床報(bào)道不多。筆者隨天津支援湖北醫(yī)療隊(duì)在鄂工作期間,曾收治1例SLE合并COVID-19的重癥病例,現(xiàn)將有關(guān)病情特點(diǎn)及治療體會(huì)報(bào)道如下:
1 臨床資料
患者女性,51歲,因“干咳18 d,伴發(fā)熱、進(jìn)行性呼吸困難10 d”于2020年1月31日入武漢市某定點(diǎn)醫(yī)院。既往確診SLE病史2年余,一直規(guī)律服用硫酸羥氯喹片(賽能)400 mg/d、白芍總苷膠囊1 200 mg/d、甲潑尼龍6 mg/d維持治療,病情平穩(wěn),否認(rèn)其他基礎(chǔ)病史和藥物過(guò)敏史。患者于入院前18 d始出現(xiàn)干咳癥狀,無(wú)咯痰、胸痛胸悶及咯血,無(wú)發(fā)熱,未特殊重視。于入院前10 d逐漸出現(xiàn)進(jìn)行性呼吸困難,伴有發(fā)熱,體溫大致在37.1℃~38.2℃波動(dòng),胸部CT顯示雙肺多發(fā)片狀密度增高影、磨玻璃影,血常規(guī)結(jié)果不詳,外院給予對(duì)癥支持治療。入院前4 d呼吸困難癥狀較前加重,胸部CT顯示雙肺彌漫性病變較前顯著進(jìn)展,外院給予靜滴莫西沙星0.4 g/d、甲潑尼龍40 mg/d,連續(xù)治療3 d癥狀無(wú)明顯緩解,血常規(guī):白細(xì)胞(WBC)7.26×109/L,淋巴細(xì)胞(L)0.56×109/L,血紅蛋白(HB)105 g/L,血小板(Plt)222×109/L,新型冠狀病毒核酸檢測(cè)陽(yáng)性,遂轉(zhuǎn)至該定點(diǎn)醫(yī)院治療。
入院時(shí)患者呼吸困難,伴有精神萎靡、食欲減退及顯著疲乏。體溫37.8℃,呼吸35次/min,脈搏110次/min,血壓118/78 mmHg(1 mmHg=0.133 kPa),面罩吸氧5 L/min下,血氧飽和度(SpO2)在76%~80%波動(dòng),最低達(dá)67%。神志清楚,未見(jiàn)皮疹,表淺淋巴結(jié)未觸及腫大,雙側(cè)球結(jié)膜無(wú)水腫,口唇發(fā)紺,雙肺叩診清音,腹軟,無(wú)壓痛反跳痛,Murphy征-,雙下肢不腫,周徑對(duì)稱,無(wú)中軸及四肢關(guān)節(jié)腫痛,四肢肌力大致正常,SLE疾病活動(dòng)度評(píng)分(SLEDAI評(píng)分)0分。患者病情符合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重癥病例標(biāo)準(zhǔn),參照《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七版)》[1]指導(dǎo)意見(jiàn),入院后予以持續(xù)氧療,視SpO2調(diào)整吸氧流量,必要時(shí)加面罩;積極對(duì)癥支持治療;結(jié)合院前治療,嘗試給予阿比多爾0.2 g tid,連花清瘟顆粒1袋tid抗病毒,繼續(xù)靜脈點(diǎn)滴莫西沙星0.4 g/d控制潛在混合感染(考慮本次住院前治療的連續(xù)性以及心電圖等未發(fā)現(xiàn)明顯異常表現(xiàn),謹(jǐn)慎應(yīng)用),維持SLE的基礎(chǔ)藥物治療不變。依據(jù)呼吸困難程度、呼吸頻率、SpO2等臨床指標(biāo)及患者本人治療意愿,入院后第1天、第2天予靜滴甲強(qiáng)龍40 mg/d,第1天、第4天給予丙種球蛋白10 g/d,病情漸改善,無(wú)發(fā)熱,SpO2可基本維持于90%左右(面罩吸氧3~5 L/min)。于第5天停用阿比多爾及連花清瘟顆粒,繼續(xù)維持氧療、羥氯喹等基礎(chǔ)藥物及對(duì)癥治療。于第7天患者呼吸困難癥狀減輕,復(fù)查化驗(yàn):WBC 8.29×109/L,L 1.8×109/L,HB 107 g/L,Plt 341×109/L,C反應(yīng)蛋白(CRP)25.1 mg/L,谷氨酰轉(zhuǎn)肽酶(GGT)189.8 U/L,白蛋白(ALB)30.86 g/L,堿性磷酸酶(ALP)153 U/L,其余大致正常;SpO293%~95%(鼻導(dǎo)管吸氧3 L/min),呼吸18次/min,脈搏74次/min,治療有效,加強(qiáng)心理護(hù)理。于第10天進(jìn)行新型冠狀病毒核酸檢測(cè)顯示陰性。
患者于第13天無(wú)明顯誘因下出現(xiàn)喘息加重,輕度咳嗽,無(wú)胸痛咯血,無(wú)咯痰,呼吸24次/min,脈搏90次/min,SpO2降至85%左右(鼻導(dǎo)管吸氧5 L/min);查體:無(wú)皮疹,球結(jié)膜無(wú)水腫,口唇發(fā)紺,雙肺叩診清音,腹軟,無(wú)壓痛反跳痛,雙下肢不腫,周徑對(duì)稱。復(fù)查化驗(yàn):WBC 4.87×109/L,L 0.89×109/L,HB 134 g/L,Plt 478×109/L,CRP<5 mg/L,GGT 160.8 U/L,ALB 32.39 g/L,ALP 127 U/L,D-二聚體3.34μg/mL。綜合分析病情加重原因?yàn)榧?xì)菌性感染引起,可證據(jù)不足,故仍以免疫性肺損傷為主。治療中停用莫西沙星,給予連續(xù)3 d靜脈滴注甲潑尼龍40 mg/d,SLE相關(guān)藥物繼續(xù)維持。第16天患者癥狀明顯好轉(zhuǎn),呼吸平穩(wěn),SpO293%(未吸氧),活動(dòng)耐力仍較差,復(fù)查化驗(yàn):WBC 10.17×109/L,L 1.79×109/L,HB 109 g/L,Plt 222×109/L,繼續(xù)維持SLE基礎(chǔ)用藥。第19天復(fù)查新型冠狀病毒核酸檢測(cè)陰性。患者于第29天、第40天先后復(fù)查胸部CT,均吸收好轉(zhuǎn)趨勢(shì),臨床癥狀明顯好轉(zhuǎn);于第43天出院,轉(zhuǎn)至相應(yīng)隔離點(diǎn)繼續(xù)隔離觀察。隨訪患者(第66天)病情平穩(wěn),無(wú)憋氣喘息,無(wú)狼瘡相關(guān)癥狀,精神狀態(tài)良好。
2 討論
2.1 SLE合并COVID-19的臨床特征70%~80%的COVID-19患者病情特征表現(xiàn)為發(fā)病早期出現(xiàn)淋巴細(xì)胞計(jì)數(shù)減少,免疫功能下降[8],重癥患者發(fā)病年齡多在40~70歲,且男性患者相對(duì)更常見(jiàn)[2,9]。合并慢性基礎(chǔ)疾病的COVID-19患者重癥比例更高,更易出現(xiàn)肝臟和心肌損害[2]。SLE作為一種多系統(tǒng)損害的慢性系統(tǒng)性自身免疫病[10],存在長(zhǎng)期甚至終身炎癥狀態(tài),其死亡的主要原因是感染[11]。本病例呈現(xiàn)以下特征:①首發(fā)癥狀為干咳,1周左右出現(xiàn)呼吸困難進(jìn)行性加重,第14天出現(xiàn)嚴(yán)重呼吸衰竭;發(fā)熱以低熱表現(xiàn),全部病程均未出現(xiàn)高熱;伴有精神萎靡、食欲減退及顯著疲乏等明顯全身癥狀,與文獻(xiàn)報(bào)道[2]類似,推測(cè)可能與病毒感染加重SLE即已存在的肺損傷,致全身多系統(tǒng)嚴(yán)重缺氧有關(guān)。②該患者在抗瘧藥及低劑量糖皮質(zhì)激素等維持治療控制下,病情持續(xù)平穩(wěn),SLEDAI評(píng)分0分,新型冠狀病毒核酸檢測(cè)陽(yáng)性,治療有效,故臨床診斷為SLE合并病毒感染,不符合病毒感染誘發(fā)SLE病情活動(dòng)的特點(diǎn)。
2.2 SLE合并COVID-19患者針對(duì)“SLE基礎(chǔ)病”管理 針對(duì)COVID-19重癥患者的治療原則[1]特別強(qiáng)調(diào)對(duì)基礎(chǔ)疾病的治療。SLE的治療首先應(yīng)達(dá)到全身癥狀的緩解,盡量控制疾病最低活動(dòng)度,并預(yù)防復(fù)發(fā)[12]。糖皮質(zhì)激素仍然是SLE治療中重要的基礎(chǔ)用藥,在緩解期低劑量維持用藥可預(yù)防SLE復(fù)發(fā)[13-14]。但在SLE治療中因激素的長(zhǎng)期應(yīng)用亦存在慢性器官損害等副作用,因此最小劑量(甲潑尼龍≤8 mg/d)或零劑量激素治療仍是目前SLE病程中研究的重點(diǎn)[12,15]。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HPA軸)功能紊亂與風(fēng)濕性疾病的發(fā)病機(jī)制有關(guān)[14]。針對(duì)SLE的治療,激素過(guò)度應(yīng)用或使用劑量不足,均會(huì)給患者的健康造成損害[15]。嚴(yán)重感染可引起HPA軸負(fù)荷增加、疲勞甚至衰竭,最終導(dǎo)致死亡[16]。本例患者病情危重,針對(duì)SLE采取維持基礎(chǔ)抗風(fēng)濕藥物、按需短程增加激素用量、謹(jǐn)慎性應(yīng)用激素策略,維持HPA軸功能,取得較好臨床收益。
2.3 SLE合并COVID-19患者針對(duì)“病毒感染”的管理SLE可累及呼吸系統(tǒng)引起肺損傷,且出現(xiàn)于疾病的任何階段,主要的發(fā)病機(jī)制為炎性細(xì)胞浸潤(rùn),并通過(guò)抗原遞呈細(xì)胞激活區(qū)域淋巴結(jié)內(nèi)的B和T淋巴細(xì)胞,實(shí)現(xiàn)肺部免疫損害[6,17-18]。有證據(jù)表明合并慢性基礎(chǔ)疾病的COVID-19患者具有更嚴(yán)重的炎癥反應(yīng)[2,19-20]。迄今為止,尚無(wú)針對(duì)COVID-19的特效抗病毒治療被批準(zhǔn)[21]。對(duì)于COVID-19重癥病例的治療根本仍在于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統(tǒng),避免細(xì)胞因子風(fēng)暴可能是關(guān)鍵所在[22]。全身性皮質(zhì)類固醇激素作為經(jīng)典的抗炎癥藥物,有時(shí)可用于嚴(yán)重的感染性疾病[21],但具體劑量尚需依據(jù)病情權(quán)衡利弊。有研究發(fā)現(xiàn)吸入皮質(zhì)類固醇激素環(huán)索奈德可減輕肺內(nèi)的局部炎癥反應(yīng),抑制病毒的增殖,呈現(xiàn)一定的抗病毒活性(其他吸入激素尚未發(fā)現(xiàn)有類似作用),并具有較好的性價(jià)比[21]。
2.4 SLE合并COVID-19患者針對(duì)“抗瘧藥物應(yīng)用”的問(wèn)題 目前有關(guān)COVID-19與風(fēng)濕病之間的相互關(guān)系,以及風(fēng)濕病的標(biāo)準(zhǔn)治療是否對(duì)COVID-19的臨床病程具有影響,都是值得探究的問(wèn)題[23]。體外實(shí)驗(yàn)證實(shí)抗瘧藥物羥氯喹(HCQ)通過(guò)多種機(jī)制發(fā)揮抗病毒作用,并兼有免疫調(diào)節(jié)活性,可作用于病毒感染細(xì)胞以及侵入細(xì)胞后的各個(gè)階段[24-26]。但對(duì)于HCQ是否在預(yù)防COVID-19方面具有潛在價(jià)值仍有爭(zhēng)議[24,26-27]。一項(xiàng)觀察17例長(zhǎng)期接受HCQ治療的SLE患者合并COVID-19臨床病程特征的研究顯示:伴有肥胖和慢性腎病等共病的SLE患者可能更易罹患重癥COVID-19;長(zhǎng)期HCQ治療雖未能減少SLE患者罹患COVID-19風(fēng)險(xiǎn),但可能對(duì)COVID-19期間狼瘡癥狀的穩(wěn)定有益[27]。對(duì)于需要HCQ維持治療的SLE患者,一旦停用HCQ可能導(dǎo)致疾病活動(dòng)或惡化,甚至危及生命,這也是必須考慮的倫理問(wèn)題[24]。本例為SLE合并COVID-19重癥患者,總體病情特征與MATHIAN等[27]研究相符,且預(yù)后較好,但有關(guān)抗瘧藥物本身的抗炎屬性、是否有助于提高機(jī)體清除病毒速度等問(wèn)題仍值得進(jìn)一步關(guān)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