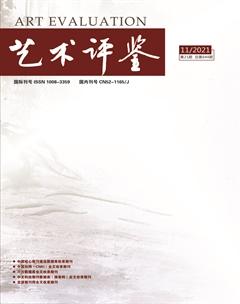貴州少數民族古箏獨奏曲《黔中賦》的藝術特色解讀
李海燕
摘要:我國的箏樂有著悠久的發展歷史,早在春秋戰國時期,這一藝術形態已經盛行于我國的很多地區。經過了上千年的發展和創新后,古箏藝術已經廣泛地存在于我國的嶺南和東南沿海等多個地區。在其發展過程中也積累了大量具有代表性的曲目。其中,《黔中賦》是1987年由徐曉林創作的,這首古箏獨奏曲能夠充分展示出貴州的少數民族音樂形態,我國大部分古箏演奏者都會將其作為演出曲目,并且也有很多學者對《黔中賦》演奏技巧和本體構成進行了研究。本文首先闡述了貴州少數民族古箏獨奏曲《黔中賦》的創作背景,而后對其本體情況進行了深入分析,最后又對《黔中賦》的藝術特色進行了詳細解讀。
關鍵詞:《黔中賦》? 創作背景? 本體分析? 藝術特色
中圖分類號:J632.32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3359(2021)21-0063-03
一、《黔中賦》的創作背景及本體分析
《黔中賦》這首由徐曉林在1987年創作的箏樂作品,主要創作靈感來源于貴州地區少數民族的代表性音樂元素,從那時被創作出來一直到現在都是我國各類古箏比賽中的指定彈奏曲目,在我國的古箏演奏領域中,很多作品其主旨都是在表達作者的個人情感,但《黔中賦》這首箏曲作品不同,其不但有效融合了侗族和苗族等少數民族的民間音樂元素,同時也很大程度地創新了古箏的演奏技巧,其更多展現出來的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的民族大愛精神。
(一)《黔中賦》的創作背景
在對徐曉林相關資料的研究過程中,我們可以明確的是,箏曲《黔中賦》并不是在刻意地模仿貴州的民間音樂,其主要的創作靈感來源于對民間生活的真實感受,在創作過程中還將貴州舞蹈和民歌等元素有效的融合,其表達的主題是更多地向民間學習。徐曉林在創作《黔中賦》這首箏曲作品時,由于其自身對貴州民間音樂有濃厚興趣,同時他還與貴州著名的苗族歌唱家阿旺進行了積極的溝通和交流,在這兩種創作動機的影響下才出現了《黔中賦》這首優秀的箏曲作品。徐曉林曾經在上海音樂學院進修過,而彼時阿旺也是上海音樂學院的一名學生,并且與徐曉林是同班同學,當時徐曉林親耳聆聽阿旺演唱一些苗族歌曲,她非常熱愛這種音樂風格,也樂于親自去感受貴州少數民族的文化和生活。在建國后的一段時間里,徐曉林去了貴州很多次,真實地感受了當地的生活,在貴州采風的那段時間,她聽了大量的侗族和苗族音樂,徐曉林自己也明確地說過她曾多次去現場欣賞當地少數民族的舞蹈和歌曲,在當地音樂人演奏琵琶曲時,她通常都會在遠處觀察,并感受音樂中的情感。從我國民族音樂學的理論知識去看待這一創作過程時,其在考察和接觸這種音樂風格時的客體身份可以總結為“完全觀察者”和“參與觀察者”,她是從更加客觀并且公正的角度去看待和感受貴州的民族音樂,她在創作過程中也不是在刻意模仿貴州的民族音樂,其主要還是從藝術特色的角度去摘取音樂中的表現手法、節奏和曲調等元素,同時在充分結合我國箏樂自身特點的基礎上創作了這首融合了多種文化的《黔中賦》。
(二)《黔中賦》的本體分析
為了更好地將貴州民族音樂的整體特點充分展示出來,徐曉林在創作時所用的節拍和調式與傳統箏樂曲的節拍和調式是有著明顯不同的。以《黔中賦》的調式為例,其調式定弦科學地融合了苗族飛歌音階排列中下行半音的特點,傳統箏曲中音階通常都具有五聲D宮調的規則,而《黔中賦》就是以此為基礎并結合了苗族音樂的特性來定弦,傳統箏曲中經常會用到的商音的五聲徽調幾乎都被降低了半個音階的角音所替代,從而出現了更具特色的人工調式音階,其與貴州民族音樂的實際音響特色也是最為接近的。與此同時,為了將我國各個少數民族音樂中存在著的大量豐富的節奏形態展示出來,徐曉林在創作《黔中賦》的節拍時,還經常交替使用到了各類不同拍號的記譜方式,比如,為了展現出貴州少數民族音樂舞蹈中的韻律和節拍特點,其大部分都采用了5/8的節拍。《黔中賦》很好地創新了那個時期我國箏樂的演奏方法,在模仿木鼓的音響時更是創造性地選用了掃和捂的演奏技巧,《黔中賦》這首古箏獨奏曲充分結合了我國少數民族音樂的各類元素和傳統箏的音色,創作中運用的多種創新手法也是促使其到現在都能成為古箏音樂演奏中的一首經典作品的根本原因,其不但將貴州地區的景色體現出來,更是表達出了豐富的情感,因此,《黔中賦》也被稱為我國古箏領域中的“高山流水”。
對《黔中賦》的曲式結構進行研究時,我們能清楚地看到這首古箏獨奏曲中蘊含著我國傳統音樂中十分常見的自由變奏體和多段體相結合的內容,可以將其整體形式分為三大結構,分別為《琵琶詠》《木葉舞》和《黔水唱》,而這三大結構并不是獨立存在的,它們都選用了很多侗族、苗族的舞蹈和音樂作為素材,這三大結構也在這些舞蹈和音樂素材的影響下產生了緊密聯系。整個樂曲的發展與這三大結構的速度變化情況是有著密切關聯性的,《琵琶詠》的樂曲風格更多的是緩慢的散板,而《木葉舞》是快扳,最后在《黔水唱》變成了急板,并且曲目在最后的高潮中結束,從展示到發展變化一直到最后的高潮,這種邏輯發展關系是十分嚴謹的。所以,徐曉林在創作《黔中賦》的同時是想要展示出兩方面音樂元素的,既要合理借鑒先進的西方樂曲形式,更要體現出我國傳統民族樂曲中的結構風格。
二、《黔中賦》的藝術特色解讀
(一)合理地運用了貴州侗族的琵琶歌
《黔中賦》三大結構中的第一個結構就是《琵琶詠》,這首樂曲為了凸顯“詠”的意境,主要采用的是緩慢而自由的散板藝術表現手法,在對“詠”這個字的理解上,我們可以把它理解為“吟唱”,其中“吟”還包含了語言表述的方式,我國古代文學中對于“詠物”也是早有記載的,最早的資料記載于先秦時期,其就是指人類對世界的認知、觀察以及思考,而《琵琶詠》則是同時兼具了“吟”和“唱”這兩種含義,在對《黔中賦》首個章節《琵琶詠》的節拍進行深入研究后,我們發現徐曉林在作曲時多次采用了左手小三度和大二度的傳統式按滑音,而為了將語言的音調真實模擬出來,其采用的藝術手法為裝飾性按滑音和小二度按滑音相結合的方式,整首樂曲的語言音調十分細膩,將《琵琶詠》中的“詠”字體現得淋漓盡致。
徐曉林自己也曾說,創作《琵琶詠》的最主要靈感就是她之前聽到過的琵琶歌,作為我國侗族人民最常見的樂曲形式,琵琶歌的尾音拖唱時往往都會帶著小彎兒和顫音。以前在侗族人生活居住的地區幾乎能夠隨處看到他們抱著小琵琶進行彈唱,徐曉林在小時候曾經親耳聽到過琵琶歌,那時就給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她也是根據自己的記憶并結合琵琶歌的韻味和風格特點寫出了《琵琶詠》,而其吟唱風格則是來自于她的同窗好友侗族歌手阿旺的演唱。侗族語言的聲調復雜并且多變,侗族人常常會將滑音、倚音和顫音等裝飾音加入到琵琶歌的演唱過程中,這樣能夠更清楚地理解所唱的內容,同時也大大提升了旋律的美感。徐曉林并不是照抄侗族民族歌曲的旋律創作的《琵琶詠》,其在創作過程中采用了大量裝飾性旋律,同時利用二度、三度、四度的音調表現手法將琵琶歌曲的內在精神準確展現出來。《琵琶詠》中具有大量裝飾性演唱音調和濃烈說唱韻味的特點,其有效地融合了我國侗族民歌與古代“詠物”的文化傳統。
(二)合理運用了貴州苗族吹木葉及木鼓舞音樂
《黔中賦》三大結構中的第二段結構是《木葉舞》,其主要的創作靈感便是貴州地區苗族的吹木葉和木鼓舞,木葉就是指我們常見的樹葉,我國很多少數民族都會使用一些天然的物質作為樂器,樹葉就是一種常見的樂器,壯族、白族、彝族、瑤族、侗族和苗族用吹樹葉的聲音作為音樂的一部分,常采用的樹葉有楓葉、桔葉、楊葉和柚葉等,從一些資料中我們能夠看到,幾千年前就已經有吹樹葉這種音樂文化,特別是我國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是非常流行吹樹葉這種古老的音樂文化的。貴州地區的侗族和苗族人民在娛樂和勞作時很喜歡吹樹葉,大家在舞蹈表演和演唱歌曲時,也通常以吹樹葉的方式進行伴奏,徐曉林在對《木葉舞》這一章節的音樂創作時,為了將吹木葉的音效模擬出來,主要采用的是高音旋律的尖銳音響藝術手法。
苗族的木鼓舞也被稱為反排木鼓舞,它是我國重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最早是在一些苗寨中出現的,并且從大量的資料研究可以感受到,木鼓對于苗族人民來說并不是一個簡單的樂器,更是他們存放祖靈的場所,可以說是宗室家族血緣精神的重要體現。其主要原因是從古至今苗族人民都認為祖先的靈魂存在于木鼓中,對待木鼓就如同對待祖先一樣,苗寨中每隔七年就會舉辦一次大型的祭鼓儀式,而在儀式中必須跳木鼓舞,其核心的音樂元素是鼓和鼓點,在鼓和鼓點節奏的指引下,苗族人民通常都會圍著木鼓跳舞和歌唱。
在創作《黔中賦》中的《木葉舞》時,徐曉林主要采用了傳統古箏技法中的花指,同時,為了將木鼓的聲音準確地模仿出來,他還極具創意性地在古箏上采用了非樂音的音響。由于苗族舞蹈都是較為粗獷和奔放的,徐曉林為了凸顯出這種效果,多次到苗族人民居住的地區實地考察苗族舞蹈的實際形式和節奏,在《木葉舞》這一章節中,她大量采用了貴州樂曲中十分常見的5/8拍子,同時也交替使用了5/8和3/4這兩種節拍,整段樂曲的律動更加生動和輕快,徐曉林自己也曾說過,《木葉舞》的創意并不是要去刻意模仿木鼓舞的韻律和節奏,其主要思想是想要將苗族人民的樸實性格以及木鼓舞的原始風格表現出來。
(三)合理地運用了貴州苗族的“飛歌”
《黔中賦》中的最后一段是《黔水唱》,這是整首樂曲的高潮部分,也是最能將貴州地區少數民族音樂特色展現出來的部分,徐曉林自己表達過這一章節主要是想創作一首贊歌,其想稱贊的是貴州地區的美好發展前景,在各個民族人們的共同努力下,貴州的未來一定是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黔水唱》的歌曲旋律主要靈感來源于苗族飛歌的元素,當然,她并不是完全照搬了飛歌的旋律,而是將苗族飛歌這種音樂形式進行變體,其更多的是要突出苗族人民的精神。貴州苗族地區的人民在田野和高山等自然環境中是非常樂于放聲高歌的,而飛歌就是這樣一種抒發感情的山歌形式。飛歌的節奏較為舒緩,音調高亢,歌唱過程中常使用滑音,長音可以隨意延長,其在句尾的收音是極具特色的,幾乎都會用一聲尖銳的“哦火”來收尾。
《黔水唱》中所設計的古箏節奏也很有特色,其主要的藝術形式是緊打慢唱。樂曲主要想將我國貴州地區河流縱橫以及高山綿延的地理環境描繪出來,《黔水唱》剛開始的演奏為左右手分別塑造出不同形象,左手主要是用非常快速的方式彈奏三連音,從而將奔騰的流水聲生動地展現出來;而右手則采用長搖的演奏技巧,將濃郁高昂并且氣韻悠長的奔放旋律展示出來,從而將苗族飛歌高亢悠長的特點充分傳達給聽眾。在《黔水唱》還采用了大量下行半音,這也是苗族飛歌特色音調的重要構成元素。在樂曲的末尾又采用了兩次掃弦創意形式,其生動詮釋出了飛歌用甩音收尾和高聲吶喊結束的特色,徐曉林在創作時有效地組合了多種演奏技法,樂曲一經問世就在古箏領域大受歡迎。可見,《黔中賦》的三大結構都是有著各自的特點和表達重點的,第一段重在描繪旋律,第二段重在突出節奏,第三段則是要抒發情感,每一個結構都是循序漸進的關系,彼此之間又是緊密相連的,整個樂曲有著磅礴的氣勢,并形成了一個統一整體,將我國黔東南等少數民族聚集區的音樂文化充分地展示出來,是我國古箏界中一首極具代表性的作品。
三、結語
通過以上的論述,我們對《黔中賦》的創作背景、本體分析及《黔中賦》的藝術特色解讀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和探討。對于我國少數民族的樂曲來說,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黔中賦》以其獨特的結構設計和極具創意性的藝術特色充分展示出了我國少數民族的音樂文化,其對我國傳統音樂文化的創作和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1]陳為兵.貴州少數民族古歌文化內涵及功能[J].貴州民族研究,2014(12):87-90.
[2]蘇曉紅.黔東南反排木鼓舞的文化傳承與發展路向[J].貴州大學學報(藝術版),2009(01):11-13.
[3]梁景麗.古箏獨奏曲《將軍令》的作品演奏技巧和情感表達[J].山西青年,2017(04):263.
[4]胡小會.貴州苗族音樂文化的特點與藝術價值——以苗族飛歌與蘆笙為例[J].藝術品鑒,2020(23):56-57.
[5]宋心馨.從古箏獨奏曲《云溪》看現代箏曲中的中國傳統元素[D].北京:中央音樂學院,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