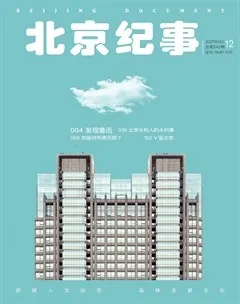車輿究竟是何時叩開了北京的大門
丹妮

車輿,人類最珍寵的尤物之一。它不僅改變了人類生活,也改變了世界的命運。自從有了輪子,整個社會就有了飛翔的動力。作為文明古都的北京,究竟是什么時候出現(xiàn)了車輿,從而進入了車輿時代呢?由于遠古史料的匱乏,對于車輿的追蹤溯源,只能從截取的并不清晰的鏡像說起了。
黃帝為北京留下了第一道轍印?
軒轅黃帝雖是傳說中的人物,但自有文字以來,各種典籍都把黃帝視作中華五千年文明的始祖。他始終牢牢坐定了一個民族分量最重的第一把交椅。頭頂中國紀傳體通史第一大伽桂冠的司馬遷,在他的千古名著《史記》中,開篇第一個記載的人物就是黃帝。
那么,人們?yōu)槭裁匆堰@位無所不能的神明冠以“軒轅”之名呢?在古代,“軒”是指帶有篷子的車,而“轅”則指駕車的轅木。軒轅就是泛指車輿。東漢著名史學家班固在其經(jīng)典之作《漢書》中有這樣的解釋:“昔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班固認為,船(獨木舟)和車子都是黃帝所創(chuàng)造。北宋李昉等學者編纂的《太平御覽》卷七七二引《釋名》也確認了這一說法:“黃帝造車,故號軒轅氏。”據(jù)說黃帝先后發(fā)明了舟車、耕種、醫(yī)藥、制衣、畜牧等等農(nóng)耕社會所需要的眾多技能,人們唯獨把“軒轅”冠在他的名號前,足以說明車輿對于當時社會有多么重要。由此可以推斷,車輿于四五千年前就在華夏大地出現(xiàn)了。
黃帝在世時,為了百姓的福祉遍走天下,四處征伐挑起戰(zhàn)事的部族首領(lǐng)。阪泉大戰(zhàn)和涿鹿大戰(zhàn)是統(tǒng)一天下最為著名的兩大戰(zhàn)役,而它們都在當時北京的轄屬區(qū)域展開。前者在今北京市延慶區(qū),后者在今河北省張家口市涿鹿縣,而涿鹿縣歷史上始終歸屬北京區(qū)域下轄,直到1949年才劃到河北省。
這兩場戰(zhàn)爭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車輿,黃帝取勝的法寶之一是應用了先進的戰(zhàn)車。《史記》對這兩場戰(zhàn)爭的地點和過程都有明確記載。
就此推斷,車輿最早出現(xiàn)在今北京地區(qū)是在四五千年前,該不是捕風捉影之事吧。遺憾的是,黃帝當時發(fā)明的車輿是什么樣,人們無從得知,只能寄托于考古學者和歷史學家的努力了。
商王朝時期北京已是車水馬龍?
殷商時期,車輿已全面介入人們的生活,進入車輪時代。僅從出土的大量殉葬的車馬坑,就可窺見一斑。自20世紀30年代起,至今已在河南安陽、洛陽,以及陜西、山東等殷商的諸侯方國地區(qū)發(fā)現(xiàn)70多座車馬坑,其中安陽殷墟就有50多座。那個時代車輿是財富和地位的象征,達官貴人去世都要有車馬殉葬。
可以想見,北京地區(qū)古燕國的街頭,那時也會是車水馬龍景象。遺憾的是,至今我們還沒有殷商時期的車輿出土,就難以得知北京地區(qū)的車輿究竟是什么樣子了。不過當時古燕國與殷商王朝關(guān)系密切,且路途不遠,車馬往來應該十分頻繁,興許還有交互性的車輿買賣市場。因此,兩地的車輿形制恐怕相差不多,甚至基本一致。
殷商時期,甲骨文、青銅器銘文和陶文都出現(xiàn)了不少“車”的象形文字,這也讓我們得以一窺3000多年前“車”的秘像。
甲骨文有多種“車”字寫法,足見車輿制作的繁榮,從以下三個“車”字,我們不難作出判斷——當時的車輿已經(jīng)有車篷或是車廂,大多是雙輪車,兩馬駕車也很普遍。
從殉葬車馬坑中可以得到更為具象的了解,這是一輛載客的車輿:其形制為雙輪、獨轅,方形車廂,轅的后端與車軸相連,轅的前端兩邊各有一匹或兩匹馬,車廂后面留有開口,便于乘客上下。載貨車則比較簡單,少有裝飾,而車廂較大。
商王朝的用車制度有著嚴格的等級規(guī)定,例如只有“士”以上的人才能乘坐用紅顏色裝飾的車輿,普通人不能使用兩馬駕車,等等。對道路的管理也有遠苛于今日的規(guī)定,譬如:“棄灰于公道者斷其手”,即把灰土隨意扔在公共道路上,是要斷其手的,遠苛于今日之數(shù)百元罰款。不過,在如此殘酷法令的背后,看到的是道路和車輿的高貴及神圣不可侵犯。
盡管古燕國不屬商王朝管轄,但其相關(guān)的制度也不會偏差太多。
有朝一日,古燕國的遺址或墳冢破土而出,有關(guān)車輿的一切猜想都將大昭于天下 。
房山驚現(xiàn)2000多年前的車馬坑
北京人真正有幸親眼看到上古時期的車輿,還是在1974年。考古學者在房山區(qū)琉璃河發(fā)掘西周燕國都邑城遺址時,發(fā)現(xiàn)了一號車馬坑。這一重大發(fā)現(xiàn)令史學界著實興奮了好大一陣。車輿的興盛,將會撬動國家政治、經(jīng)濟、文化、科技的多元裂變。這些沉眠多時的睡神,無疑為我們提供了一條窺視那個年代北京社會的秘徑。
人們看到,坑中車輿的形制與殷商時期變化不大,只是輪距變窄,車轅縮短,輪上輻條的數(shù)目也有所變少。這可能是考慮提高行進的速度和便利性。
在其后發(fā)掘的1100號車馬坑中,有同樣制式的獨轅、雙輪車5輛,考古學者從眾多出土碎片中,拼裝出了2000多年前北京地區(qū)車輿的完美圖形。這5輛車的車輪直徑都在1.35米左右,輻條18-24根不等;從轅首到車踵全長2.9米,轅首上翹,車轅后部置于車上,上面是車廂;車廂平面為長方形,前部寬1.3米,后部寬1.38米,前后長度為0.9米;車廂四壁均豎有欄桿,后壁有寬41厘米的可供上下的車門;車廂上立有直徑為1.5米的傘蓋,固定在車廂四角的木柱上。所有的一切都在日臻趨向于完美和科學。

房山區(qū)琉璃河出土的西周時期車馬坑
琉璃河共出土西周燕國墓葬200余座,大中型墓穴都陪葬有車馬,隨墓主人生前身份高低,陪葬車馬的數(shù)量有所差別。專用車馬坑30余座,最大的車馬坑葬有42匹馬、10多輛車。有的是將馬殺死后與整輛車埋入坑內(nèi),有的是將車拆散后葬入。車輿皆為獨轅雙輪,馬匹排列整齊。坑內(nèi)還有眾多的銅質(zhì)車馬器。少數(shù)車馬坑有殉人、殉狗現(xiàn)象。讓今人不禁為奴隸制度的野蠻唏噓。
出土的眾多車輿中,沒有發(fā)現(xiàn)雙轅馬車,車軸也沒有用上鐵鍵。時間在等待著車輿進一步更新的腳步。
為了迎合車輪時代的到來,西周時期北京的道路也得到長足發(fā)展。那時四馬并駕的車輿一般都要4米寬,也就是說當時的道路至少是4米以上的車馬大道。如果是上下雙車道,那么路寬起碼就應該8米以上了。《詩經(jīng)·小雅·大東》不吝溢美之詞,歌贊西周道路:“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像磨刀石那樣平坦,箭矢飛馳那樣筆直。這樣的道路真是讓人神往。
西周時期包括北京地區(qū)的道路管理,有著不容逾越的律條。例如那時規(guī)定:“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其意是,道路兩旁必須栽植樹木,以指示道路所在,同時沿途還設(shè)有為過往車輛提供飲食的廬舍。不過,《詩經(jīng)·小雅·大東》有這樣的解說:林蔭大道為“君子所履,小人所視”。也就是說,那些寬敞的路,都是供統(tǒng)治者使用的,平民百姓只能在一旁看看而已。

秦始皇陵出土的1號銅車馬
秦始皇第一個駕乘來京的天子
上古時期,北京地區(qū)處于遼寧西部紅山文化圈與黃河中游仰韶文化圈的交界處,或者說是兩大文化區(qū)域的邊緣地帶。那時,北京沒有太多的驚艷表現(xiàn),用以吸引世人眼球。以至于有史可考的,第一個御駕親臨今北京城的天子是秦始皇。然而,秦嬴政還不是奔著北京來的,他的心之所向是渤海邊的碣石,到那里尋求長生不死的仙丹。不管怎樣,北京百姓終于得以目睹天子的御駕,而北京的車輿史也得以留下不尋常的一頁。
豪華精致的車輿,蹄下生風的馬隊,是秦始皇炫耀皇威的得意之舉。在他當政的11年中,大規(guī)模巡游有五次。每次要出動大小車輿80多輛,官吏兵丁1000多人,浩浩蕩蕩,其規(guī)模遠勝于今天美國總統(tǒng)的出行。公元前215年,是秦始皇第四次巡游。他到碣石往返都途經(jīng)北京。去時,經(jīng)今河北省邯鄲市,進今北京市宣武區(qū)一帶,向東過通州區(qū),再經(jīng)今河北省薊縣東行,最后抵達碣石。回來時,沒有走原路,而是從今北京地區(qū)的懷柔、密云向西,過今昌平區(qū)關(guān)溝、延慶區(qū)南,穿過河北省,返回咸陽。
值得一提的是,他乘坐的御駕確實驚世駭俗。1980年在陜西秦始皇陵西側(cè)發(fā)現(xiàn)了秦始皇銅車馬坑,坑內(nèi)葬有兩輛大型彩繪銅車馬,是真車真馬的1/2。
考古學家經(jīng)反復考證,認為這正是秦始皇當年出巡用車。
一號車為立車,即立乘的前導車,也叫高車。單轅雙軛,套駕四馬。輪徑較高,車廂較小,顯得輕巧又靈便。車內(nèi)配有多種兵器,顯然這是開路前導的衛(wèi)戍車。
二號車為安車,系雙輪、單轅,四馬駕車。車輿的外形和今天的轎車頗為相像,車頂為橢圓形。車廂分前后兩室,前室是御手居處,后室十分寬敞,估計真車的寬度在1.5米以上,進深1.7米以上,輿廂四壁均有窗戶。這種車行駛穩(wěn)定性好,速度很快,冬暖夏涼,乘坐其間舒適愜意。銅車馬的制造工藝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鑄造、焊接、沖鑿以及各種機械連接等等,都很精湛。雖然埋在地下2000多年,各種鏈接機關(guān)仍舊非常靈活。車身上繪有精致的彩色花紋,并以大量金銀作為裝飾,共有金質(zhì)飾物747件,銀質(zhì)飾物817件,青銅鑄件1500多個,極為奢華。安車無疑是為秦始皇預備的。
秦始皇出巡時,高車在前,安車在后。為了防止有人行刺,車隊中有5輛一模一樣的安車。
車輿,可以改變一座城市的氣質(zhì)。應該說在西周之前,車輪那隆隆轉(zhuǎn)動的聲音,就在強勁推動著北京城向今天進發(f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