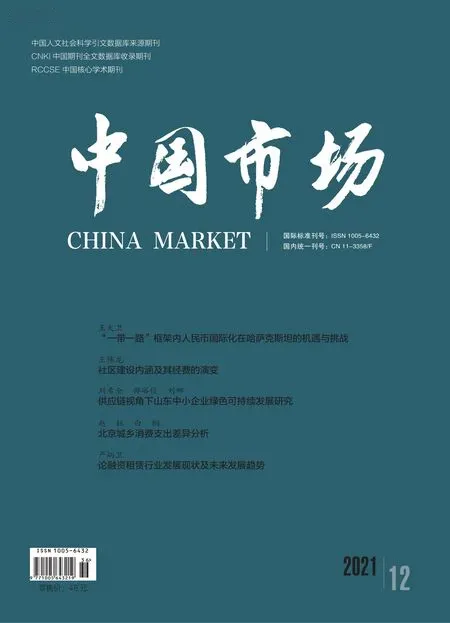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構建生態治理共同體的路徑研究



[摘 要]良好的生態環境是長三角地區高質量一體化發展的基礎和保障。示范區三地在生態治理一體化上開展了很多探索,尤其在聯合治水上取得了突出成效,但是仍然存在很多不足,必須進一步構建生態治理共同體,從行政主體、生態要素、多元主體同頻共振等方面進一步加強協同。
[關鍵詞]長三角一體化;示范區;生態治理共同體
[DOI]10.13939/j.cnki.zgsc.2021.36.029
長三角一體化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重大戰略,良好的生態環境是長三角地區高質量一體化發展的基礎和保障。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下文簡稱示范區)的生態環境治理戰略定位非常明確,要建設成為區域一體化生態環保聯治示范區,為我國區域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提供新樣板、新方案、新路徑。當前三地雖然已經在生態協同治理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仍然存在很多共性問題,生態治理一體化水平有待提升。
1 生態治理共同體的特征
西方最接近生態治理共同體概念的是協同理論。西方發達國家較早面臨生態問題,西方學者面對全球性生態危機進行思考,認為協同治理是解決公共管理困境的有效工具,代表性理論的主要有協同機制理論、整體性治理理論、多中心治理理論等。其中協同機制理論奠定了協同治理的基礎,整體性治理偏重于政府主導,多中心理論側重于社會自治。協同治理已經成為共識,國外生態協同治理可以為長三角一體化生態治理共同體的構建提供借鑒,但是由于各國國情不同,一些理論還有待提出更加適合中國語境的解釋。
生態環境具有顯著的跨區域、公共性的特征。根據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實際,習近平同志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體”,“應當全方位、全地域、全過程”開展生態文明建設,生態治理不能從一時一地看問題,不同部門、不同地區應當樹立大局觀、系統觀,做到統籌兼顧、整體施策。“共同體”顯然是比“協同”更為緊密的關系,它是“協同”發展的高級階段。與協同理論相比,我國的“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體”理念更加深刻地揭示了生態治理的系統性、整體性,更能契合一體化語境下的生態協同治理需要,是長三角生態協同治理的理論指針,近年來長三角在實踐中已經取得了一些寶貴經驗。結合國內學者的研究,“區域生態治理共同體”應該具備三個方面的特征(見圖1)。
1.1 行政主體高度協同
行政區域的分割性是生態一體化面臨的最大難題,地方政府普遍存在“搭便車”思想。現有的研究既有對單一政府主體行為的研究,也有對多主體行為的研究,但均承認政府在生態治理中的主體地位。如宗翮(2015)研究了長三角地區政府間生態協作的發展歷程,呼吁地方政府拋棄傳統各自為政的觀念,積極合作。郎鵬(2019)指出“生態綜合治理首先要解決各地政府之間和政府內部各部門之間組織結構、權利結構以及行政職能的協同整合”,多數學者認為必須推動區域地方政府之間形成共同決策、共同執行政策的機制,其中生態補償和利益沖突也是關注和博弈焦點,因為“受益”和“受害”的標準往往很難界定。
1.2 生態要素高度協同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我們要“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生態是一個大系統,尊重自然規律是保護生態環境的前提和基礎,既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也不能“大躍進式”造景,搞生態形式主義,必須提升生態治理能力。郭永園(2018)提出借鑒美國州際生態治理的經驗,開展綜合治理、多元治理、市場化治理,“立足于實際,因地制宜地創新區域生態治理模式”。
1.3 多元主體高度協同
在政府發揮引領作用的前提下,政府與其他多元主體呼喚一種更加緊密的協同關系。彭祥(2020)認為政府必須發揮好引領作用,但只依靠政府力量開展收效甚微,應當發揮社會和公眾等主體的能動性。崔晶(2019)以祁連山生態治理為案例,分析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中繼者”及公眾等主體間關系,提出了集體行動框架。田學斌(2020)在研究京津冀跨區域生態治理現狀的基礎上,提出政府、市場、社會三元主體協同模式。劉新宇(2019)等就長三角跨區域生態環境體制機制創新和聯防聯控提出了建議。施懿宸(2020)構建了長三角生態治理市場化平臺模型,并特別關注社會力量的參與。
2 示范區構建生態治理共同體的做法及成效
2.1 破除行政邊界,合力構建三方“智慧網”
一是共商共討,統一合作規劃藍圖。2019年5月,三地政府簽訂《關于一體化生態環境綜合治理工作合作框架協議》。框架協議的簽訂標志著三地生態環境聯防聯治工作從原有圍繞太浦河為主拓展到了全域,范圍擴展到水、氣、土全覆蓋,圍繞共建改革開放新高地、生態價值新高地、創新經濟新高地、人居品質新高地的目標,研究探索以“上游主動保護下游,下游支持上游發展”為核心的多元化、綜合性橫向生態補償機制,努力實現三地生態共建、共保、共治。
二是求同存異,奠定共治制度基石。三地政府在支委會牽頭下,反復溝通,擱置客觀差距,放大共同目標,不斷深化共識。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理事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中明確了要做到監測統一、標準統一、執法統一等“三統一”。在經過三級八方多次溝通、多輪征求意見之后,目前,兩省一市生態環境部門會同執委會已聯合印發《示范區生態環境管理“三統一”制度建設行動方案》,這是統籌三地生態治理政策、提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核心制度創新。
三是聯防聯控,協同保障重大活動。為切實保障世界互聯網大會、杭州G20峰會、蘇州中日韓環境部長會議、上海國際進口博覽會、六五世界環境日等重要會議和重大活動環境質量,各地在重污染天氣涉氣污染源應急管控、飲用水安全保障、突發環境事件應急處置等方面不斷深化區域聯防聯控。
2.2 重視要素協同,疏通全域水體“經絡網”
在2300平方千米的示范區內,水域面積就約占350平方千米,占比約15.2%。嘉善與同為示范區的青浦、吳江水域互有交界,域內主要交界水體共47個(見表1),示范區三地同屬江南水鄉下游,水體治理一直備受關注。
(1)推動水源地協同保護。響應長三角一體化號召,積極參與區域協商與溝通,會同相關部門及省、市環境、水文、水資源專家召開上海金澤水庫新增取水泵站項目對嘉善水源地取用水影響評價專題會議,進一步深化上海、嘉善兩地太浦河水源地的雙向互通與合作,提升雙方共同應對水源地環境風險事件互通和應急能力。
(2)推動跨界水體聯保共治。2020年9月,兩省一市八個相關部門及執委會聯合制定的《示范區跨界水體聯保專項方案》(以下簡稱《方案》)印發,《方案》在原有水污染治理合作經驗的基礎上,以示范區和協調區47個跨界河湖為重點,其中太浦河、淀山湖、元蕩湖、汾湖“一河三湖”是加強跨界水體聯保共治的重點,從河湖長制、聯合監管、執法會商、監測體系、數據共享、聯合防控六個方面創建了三地一體化治水新模式,為今后三級八方環保和水利部門扎實推進示范區水污染防治、水生態修復、水資源保護提供具體指導和工作依據。
(3)開發聯合河長制信息化平臺。2020年,示范區聯合河長制信息化平臺上線,區域治水一體化格局加快形成。構建一張水系圖,推動區內水系統統一展示,統一規劃;構建河長聯合巡河平臺,三地互相開放河長巡河端口,將巡河中發現的問題上傳共享,上下游聯動,共同處置邊界河湖問題;構建三地聯合執法巡查平臺,實現跨區域、多部門聯合執法和巡查;構建三地水葫蘆聯合防控工作平臺,在重要水體上下游布控視頻監控系統;構建水生態聯合監測及數據共享機制,對區內交界河湖及重要水體水質進行數據監測,為聯合河長巡河提供技術支撐。
2.3 探索主體多元,編織生態治理“聯動網”
組織開展企業環境信用等級評定,示范區三地組織開展轄區重點工業企業“綠、藍、黃、紅、黑”環境信用等級評定,與日常環境管理、評優評先等掛鉤,聯合共建“一處受罰,處處受限”的跨行政區域環境信用體系。嘉善與吳江、青浦、金山等地還多次聯合開展邊界環境執法檢查行動,及時發現并查處了企業環境違法行為,三地企業關注生態、保護生態積極性不斷提升。為提升公眾參與度,還探索青嘉吳三地生態互訪活動,三地志愿者代表參觀了太浦河長白蕩水源地、現代農業文化園,開展經驗互學。
2.4 示范區生態共同體建設取得突出成效
2016—2020年青浦、吳江、嘉善PM2.5平均濃度均逐年下降,2020年分別為41微克/立方米、30微克/立方米,30微克/立方米,比全國平均水平略高,三地空氣質量天數優良比例逐年上升。當然,成效最為突出的還是水質變化:民主水文站斷面是上游江蘇吳江——浙江嘉善的入境斷面(見圖1)。2017年以來,交接斷面水質類別均達到Ⅲ類,而且水體中的主要污染物(以氨氮含量為例)呈現明顯下降趨勢,表明在協同治水中吳江地區的水體治理效果良好。嘉善縣縣級以上斷面Ⅲ類水從2017年的71.40%上升到2019年的85.7%。2020年嘉善縣控以上斷面Ⅲ類水比例已達到100%,全縣11個市控以上地表水常規監測斷面水質綜合類別為Ⅲ類,所有斷面都滿足功能類別要求。自2018年起,嘉善縣到上海的出境水中COD數據逐年下降,出境水COD含量明顯低于入境水COD含量,表明流經嘉善縣的水再流向上海時,水質明顯提高。(見圖2)
3 示范區構建生態治理共同體存在的問題
3.1 行政主體協同機制不夠完善
雖然三地政府對于生態治理一體化認知較為一致,但是由于各地原有標準不統一,短期內在執行上還很難同步。一是空間分類管控不一致。嘉善與青浦吳江,在生態保護紅線劃分上有差異,導致空間分類管控不一致。比如太浦河,嘉善、青浦定位為飲用水源,納入生態紅線予以保護,而吳江區將其功能定位為排澇泄洪,導致太浦河飲用水水源保護區不完整。二是污水處理廠尾水標準不統一。流經嘉善縣的大多是過境水,來水水質對出境斷面水質影響較大。經梳理三地的污水處理廠排放標準,嘉善污水處理廠執行浙江省城鎮污水處理廠污染物排放標準,尾水COD排放30mg/L,吳江執行《太湖地區城鎮污水處理廠及重點工業行業主要污染物排放限值》中一二級保護區標準限值,尾水COD排放40mg/L,青浦執行《城鎮污水處理廠污染物排放標準》一級A及A+標準,尾水COD排放50mg/L,可見,上游吳江的污水處理廠尾水排放標準低。生態環境標準首批確定清單中并未將污水處理廠排放標準納入統一標準范疇,與水環境協同治理理念不符。三是環境數據共享機制未建立。浙江省區域內完整的環境數據共享機制尚未建立,無法實現跨區域共享互聯。目前示范區內也僅建立了微信工作群,缺少完整的數據共享平臺。
3.2 生態要素協同治理能力有待提升
目前示范區三地生態治理一體化多體現在水環境質量改善方面,大氣和固體廢物污染協同治理均未深度進行,還存在難題。一是大氣污染治理聯防聯控機制根基尚淺。目前,示范區區域性大氣復合污染問題的污染機理尚未研究透徹,現有研究成果仍不足以全面支撐區域大氣污染控制,特別是聯防聯控的需求。目前大氣污染聯防聯控主要根據生態環境部出臺的相關文件,針對示范區的聯防聯控機制尚未建立。而且區域污染監測、傳輸和影響評估綜合平臺等尚未構建,導致示范區的區域聯防聯控機制根基尚淺,也無法在短期內有明顯成效。二是廢氣排放標準尚未統一。目前,示范區的大氣環境標準不完全統一,青浦主要是執行上海市地方排放標準,嘉善主要執行浙江省地方排放標準,而吳江則主要執行國家標準,地方性排放標準嚴于國家排放標準,排放標準值存在差異。大氣環境標準的不統一往往會造成標準嚴格地區的企業向周邊標準寬松地區轉移,造成“你保護,我污染”的局面,削弱了區域大氣環境治理的整體效果。三是固廢污染協同治理機制未建立。嘉善縣現有危險廢物經營單位4家,利用處置能力19.06萬噸/年。青浦現有危險廢物經營單位2家,處置類別涉及19個大類,利用處置能力約6萬噸/年。吳江區現有危險廢物經營單位8家,處置類別涉及25個大類,利用處置能力17.32萬噸/年,但在醫療廢物處置及焚燒處置危廢方面還存在空白,蘇州市吳中區固體廢棄物處理有限公司可以處置醫療廢物,青浦和吳江區均已審批危廢焚燒處置產能。目前,示范區三地之間廢物協同處置還沒有實質性進展。
3.3 多元主體同頻共振的局面尚未形成
一是沒有形成系統的宣傳機制。政府層面開展了一系列宣傳和活動,但是三地之間聯合宣教機制還未完全建立,力量和資源整合還有待提升,宣教工作往往局限于各自本土。同時,大型宣教活動較少、頻次低,覆蓋面廣、內容豐富、有深度的精品活動還有待打磨;重復性、表層化宣傳較多,形式新穎、吸引眼球,深入解讀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和治理理念的“新鮮干貨”還不多。二是環保社會組織力量不強。中國的環保社會組織帶有明顯的官辦色彩,自主性不夠、活力創新不足,長三角各地也是如此,目前主要由政府主導開展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的宣教工作,社會組織參與的不多,自主開展相關活動的更少。社會層面缺少引領生態新風尚的自發力量,也沒有形成濃厚的主動參與生態文明公益活動的氛圍。三是沒有充分發動基層群眾力量。由于缺少基層宣傳,還有一部分群眾對于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和生態治理的相關知識和內涵不知道、不理解,對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的重要意義認識不深,對當前變化感受不強,對未來愿景期待不多,覺得與自己工作生活關系不大,認為生態治理是政府的事情。還有一部分群眾對于生態環境改善等有著一定認識和體會,但是關注的焦點停留在醫療、教育和投資等方面,對于如何主動參與比較茫然。
4 結論
4.1 初步結論
示范區在生態治理一體化上所面臨的問題,也正是整個長三角區域生態協同治理的問題,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國生態文明建設過程中存在的共性障礙之所在。時代呼喚一種比生態協同更加緊密的關系,打造生態治理共同體是當前長三角跨區域生態治理的客觀需要,示范區必須遵循“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體”理念指引,融合一體化體制機制創新,在長三角乃至全國范圍內探索構建生態治理共同體的路徑。
4.2 政策建議
4.2.1 深化行政主體協同,健全生態環境聯動共保機制
三地與執委會應當積極進行“三線一單”(生態保護紅線、環境質量底線、資源利用上線和生態環境準入清單)編制工作的對接,加快建立統一的飲用水源保護和主要水體生態管控制度,三地共同構建生態空間、生態環境和綠色發展新格局。不定期聯合開展異地交叉大排查、大執法行動,嚴肅查處一批環境違法(犯罪)案件,打造長三角執法最嚴區域。加快重點領域排放標準統一,確保示范區三地執行最嚴格的污染物排放標準;統一環境監測監控體系,建立區域生態環境和污染源監測監控“一平臺”;統一環境監管執法,制定統一的生態環境行政執法規范,以“一把尺”實施嚴格監管。加快建立統一考核體系,探索建立區域生態基金,對水環境治理實行生態獎懲機制。
4.2.2 普及綠色發展理念,完善多元一體的生態治理機制
建立三地生態綠色聯合宣傳機制,加強交流溝通,共享資源、互補不足,統一打造宣傳品牌,聯合開展活動,進一步提高生態宣傳的投入、產出效果。進一步豐富宣教形式,加強宣教基地建設,打造微信公眾號、自媒體等多種形式的宣教平臺,積極挖掘各類更接地氣、更高效的宣教方法,努力提高宣教覆蓋面和實際成效。鼓勵公眾主動參與示范區生態治理一體化宣傳工作,引導企業環保管理人員或有相關經歷人員到企業宣講、熱心生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的群眾到社區宣講,讓廣大基層群眾深入了解一體化治理理念,也可以進一步提升公眾對生態環境的認知度、參與度、獲得感和滿意度,通過志愿者活動的宣傳和推廣,在民間層面形成一致的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和治理理念。
4.2.3 逐步有序推進,擴大生態治理一體化要素范圍
區域大氣污染協同治理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現代化信息技術、物聯網、互聯網以及大數據等資源,為消除“數據孤島”“數據煙囪”的狀況,建立從數據采集到環境監測再到智能分析與信息共享等多種功能的大氣環境數據綜合平臺,實現區域環境狀況評價、變化趨勢分析、預測預警及綜合監管。同時,開展相關標準研究,為區域聯防聯控機制的推行提供運行保障,加快廢氣、固廢污染協同治理機制。特別是針對印染、電鍍、表面處理等廢氣重點監管行業要加快制定示范區統一排放標準。
參考文獻:
[1]宗翮.長三角區域生態治理政府間協作研究[J].江南論壇,2015(4):20-22.
[2]郎鵬,董顏,趙楠,等.京津冀生態環境協同治理研究[J].環渤海經濟瞭望,2019(10):74.
[3]劉新宇,胡靜,沈愛萍.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生態環境管理機制研究[J].中國發展,2019,19(6):1-5.
[4]田學斌,劉志遠.基于三元協同治理的跨區域生態治理新模式——以京津冀為例[J].燕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21(3):88-95.
[作者簡介]陳晨,女,嘉善縣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