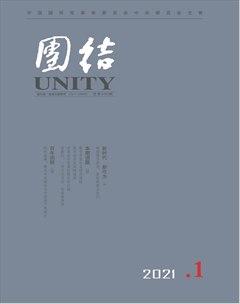進入“中華經典”的世界
李廣良
張祥龍教授有言:“20世紀的中國是一個沒有經典的國度,只有西方科學——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和技術(高科技)的至高無上和無處不在。”對此我們不難提出質疑:20世紀中國真的“沒有經典”嗎?我們不是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嗎?不是有《毛澤東選集》嗎?不是有從蘇聯到中國的許多“紅色經典”嗎?怎么能說“沒有經典”呢?
不過,張祥龍所謂的“沒有經典”其實別有所指:“在前一個世紀中,經典及其傳統被以一些可怕的罪名——包括‘吃人’——流放、戴帽、勞改、批斗、判死刑,以十字架或藍色文明的名義來詛咒,這些都不是可怕的虛構。”他指的是隨著“中國古文化正從我們的生活主流中加速消失”而來的“中華傳統經典”的“沒落”。
以我之見,20世紀的中國并不是“沒有經典”。其實,20世紀的中國對待“經典”的態度是相當矛盾的:一方面,人們以種種名義對傳統經典尤其是儒道佛經典進行“鞭尸”“批判”和“解構”等;另一方面,又以“新文化”“啟蒙”“革命”“現實主義”等“現代性”精神重新塑造出種種“新經典”。這些“新經典”不僅包括現代中國人如毛澤東、魯迅等人的作品,還包括來自德國、蘇聯等異域國家的某些“經典著作”,甚至包括中國古代的非主流作品如所謂“四大名著”等(這些在古代并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東西之所以成為“經典”,其實是經歷了一個復雜的“經典化”運動的重構,對此我們還需要重新展開研究)。在這種內在矛盾中,我們既是“有經典的”,又是“沒有經典的”:前者指的是經過“現代性”構建的各種“名著”;后者指的是傳統中國的“經書”,如“四書五經”、《道德經》、《金剛經》等。我并不否認前者的“經典性”,但對“中華民族”來說,中華傳統經典顯然具有更重要的意義。
經典其實有兩種:一種是本源性的、在“影響一個悠久文明走向的文本源頭”意義上的經典,是從上古和“軸心時代”綿延至今,具有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活命真身”的經典;另一種是非本源性的,即在某個專業領域的“名著”,此種“名著”具有影響學科進步和世道人心之功,但并非文明之源頭,并不能讓人“體驗到最初的、邊緣上的取向如何發生,并由此而生出某種邊際處的敏感”(張祥龍)。顯然,這兩種經典是難以相提并論的。前者是一個文明的“根本”,后者是一個文明的“枝葉”,根本固而枝葉茂,根本衰則枝葉枯。故本文以下所談的“經典”都是第一種意義上的。
張祥龍又說:“21世紀的中國,最需要經典的回歸。”這里的“經典”就是作為中華文明之“文本源頭”的本源性經典,其中主要是“儒家的古經典”,但也包括其他各家經典。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我們經歷過“傳統文化熱”“國學熱”等,這些曾經盛極一時的“熱”并沒有帶來“經典的真實回歸”:“經典的真實回歸,不會出現于自欺欺人的‘繁榮’、‘盛世’,不會出現于壓抑精神深層創傷的強迫遺忘和輪番炒作,因為這種無罪感、無悲痛、無悔恨、無招魂的重塑金身,只是尸身的水晶棺化和為己所用而已。”沒有“信仰”,沒有“懺悔”,沒有經歷“精神生命”的痛苦,無論是于丹的“雞湯式”《論語》解讀,還是“《論語》一百”的機械背誦,帶來的都只能是經典的敗壞。只有去驕去泰,洗心革面,“虛壹而靜”,才能打通我們與經典之間的障礙,從而真正進入經典的世界之中。
“真正進入經典的世界之中”,意味著一種真正的“經典生活”。“經典生活”是我發明的詞,意指一種“朝向經典本身”的生活方式。“朝向”不是“背離”,而是“向著”,即向著經典走去,專注于經典本身,融入經典,與經典合一。通過與經典的合一,覺悟宇宙的大道、歷史的真實、自然的奧秘和心靈的內蘊,從而洗滌人生的污濁,提升人生的境界,開發人生的本有智慧。這種“經典生活”并不限于讀經之時,而是在經典的滋潤之下,讓生活自然地具有經典的靈性。所謂“腹有詩書氣自華”,就是經過《詩》《書》的化育,改變氣質,涵養性靈,使生命之“氣機”流動,讓人生之“氣韻”“生動”起來。這樣的生活一定不是“單向度的生活”,而是本真的、具有無限可能性的生活。
但是處在“一種互為他者的、有親疏遠近之別的‘經典間’的生存格局”之中,我們要“回歸”和“朝向”的是“自家的經典”—— “中華經典”。我們當然也要對別家的經典開放,但這要以對自家的經典開放為前提,如果不能對自家的經典開放,我們也就不能對任何一種經典開放。而對于“中華經典”,我們既須把握其“經典性”,又須把握其“中華性”。所謂“經典性”,是指其“本源性”、“真理性”、“神圣性”和“永恒性”,對此毋庸贅言。但對“中華性”我們則需深入體會。我國之全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中國”,“中國”是一個“國家”,一個自立于世界民族國家之林的“大國”。但“中國”不僅是一個“國家”,而且是“中華”之“國”。“中”者,“中央”、“中正”、“中庸”、“中道”、“中和”也。“華”者,“冕服采章”也,“草木榮華”也,“日月光華”也,“華胥氏”也。若以“中”為“天地之間”,以“華”為“文明之光”,則“中華”意味著“獨得天地之精華,立于天地之間的文明之光”也。這是我們的國名之隱喻,是“中華經典”的“核心價值”,是“中國人”的使命擔當。明乎此,方知“中國人”絕不是此星球上的一個“族群”,“中華文明”也絕不是一個“地方性的”文明,而是普遍的“人類文明”本身。明乎此,才可以真正進入“中華經典”的世界。
進入“中華經典”的世界要從進入“漢語世界”開始。任何經典皆存在于某種“語言世界”之中,如希臘經典存在于“古希臘語世界”,古印度經典存在于“梵語世界”,猶太經典存在于“希伯來語世界”,阿拉伯經典存在于“阿拉伯語世界”,德國經典存在于“德語世界”等等。“相比于現代科技的工具化,經典是語言化的;相比于現在進行時的口語,經典更傾向于那讓過去(陰)和將來(陽)交織的構象書寫。”(張祥龍)“中華經典”是古漢語經典,存在于“古漢語世界”之中。在這個拼音文字占統治地位的星球上,漢字是最為奇特的文字,其中蘊含著“天命”的偉大力量,漢字的構成不僅符合“六書”的原理,而且符合先天八卦之“易數”“易理”。只有在這種“天命”的語言文字中,“中華經典”才成其為經典。進入“漢語世界”,固然要從識字開始,但真正重要的是體會漢字的美、靈性與力量,領悟漢字所承擔的“天命”,繼承漢字所書寫的“絕學”。
進入“中華經典”世界并不是只進入“某一本書”,“中華經典”從來就不是唯一的。如張祥龍所說:“只有一本經典,等于無經典,因為唯一的經典只是憲章或神諭,其中無語言和書寫的生命。華夏文化世界自古就沒有某一本經典的獨霸。四書五經都是經典,三教九流皆有經典。”儒家有“四書五經”,道教有《道德經》《南華真經》《沖虛真經》《黃庭經》《陰符經》等,佛家有《金剛經》《法華經》《華嚴經》《阿彌陀經》等,兵家有《孫子兵法》,弈家有《棋經十三篇》,武術家有《太極拳經》等。所有這些經典都要讀,只有對儒、墨、道、法、名、陰陽、兵、農、醫、佛各家的經典有廣泛的研讀,我們才可能打通各家思想的界限,尋找其“一氣之貫通”,從而真正理解“中華”的本質,真正覺悟“中國智慧”,真正承擔起“中華”的“天命”。而在上述各家中,首須進入的是儒道佛三家的“經典世界”。儒、道、佛三家是“中華文化”的主流,其中儒家和道家都是從虞、夏、商、周以來的傳統中生發出來的,都是中華思想文化的正統。兩漢之際傳入的佛教則是由印度文化系統孕育出來的,但經過消化吸收之后最終融入了“中華文化”,并最終形成了“三教合一”的經典教化系統。儒道佛之外,《墨子》由于其“思維方式的現成性”,《韓非子》由于“得人勢而未得天勢”,皆只可一觀而不可“沉入其中”也。
進入“中華經典”世界須把握“中華經典”之“奇特性”。所謂“奇特性”是指“中華經典”中的每一部都是獨一無二、不可替代、無可復制的,因為這些經典皆有其獨有的形式結構、思想義理和神奇意象。如“中華第一經”的《易經》,就是由卦象符號和表意文字組成的獨特的符號系統,由此符號系統模擬萬物之運動結構,洞察事物之未來發展趨勢,精微奧妙,深不可測,宇宙之玄理和萬物之結構皆在其中。僅憑此一經,中華民族即可稱世間第一智慧民族。其他如揭示宇宙形上之“道”及下貫之“德”的《道德經》,“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的《南華真經》”,由上古政治文獻組成以“時”和“孝”為正治之源的《書經》,看似“斷爛朝報”實則“萬物之聚散皆在其中”的《春秋經》,以及以“思無邪”為根本原則的《詩經》,以“禮”之制度與精神為生命的《禮記》等等。這些經典皆“廣大深沉”、“奇絕險峻”、“上天入地”、“規模宏遠”,其中無盡意象鉤鎖連環,具有無窮的解釋空間,由此形成歷代以來生生不息的經學傳統。雖說經學之長盛不衰是因其對統治或“治理”有用,但真正原因恰在于經典本身的思想和學術空間,在于經典的內在結構、廣大智慧和充盈的生命力,在于其奇特的本源性魅力。隨著經學傳統的中斷,完整的經典教育不復存在,所有的經典被各種現代學科所宰殺分解,“中華經典”的“奇特性”也就湮沒不彰了。
要重新開顯“中華經典”的“奇瑰壯麗”,可能需要新的閱讀和書寫方式。就閱讀來說,不應再是漫不經心的“默讀”或“朗讀”,而應當用“聽之以氣”的工夫去“聽”,“聽天地之氣滾滾而來”,“聽陰陽之氣緩緩溢出”,“聽恍兮惚兮大音希聲”,這是只有經過嚴格訓練才能重新養成的“聽經”工夫。就書寫來說,我們提倡一種“開端意義上的書寫”,這種書寫既是一種“變異書寫”,也是一種“本真書寫”。所謂“變異書寫”者,既不是訓詁注釋的,也不是哲學分析的,而是一種奇異的“對話式的”;所謂“本真書寫”者,直接描述和分析經典中的“現象”本身,進行最徹底最純粹的懸置,以實現真正的“朝向事情本身”。
在這個否隔困厄的時代,也許只有“中華經典”才是我們得救的希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