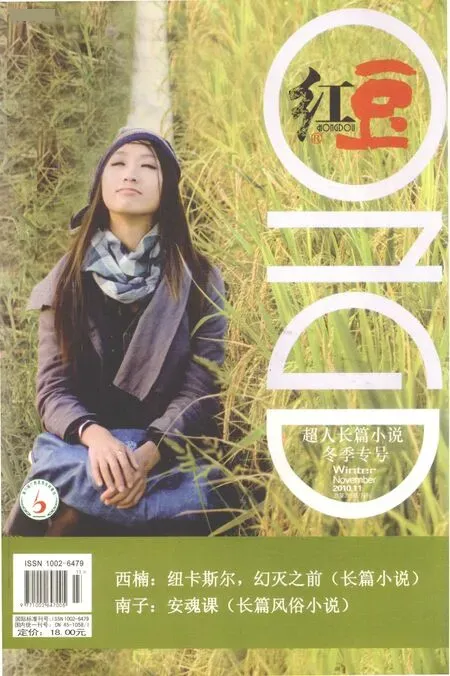聆聽陽光的淺唱
梁安早
去年落葉飛舞的一個初冬早晨,我正在電腦前噼噼啪啪地敲擊鍵盤,手機響了。
我拿起手機一看,是一個來自南方某個沿海發達城市的陌生號碼。
接通后,我問:“哪位?”
電話那頭說:“您是不是藍知曉老師?”
我說:“是,你是?”
對方頓了一下說:“藍老師,找您的電話找得好辛苦啊,起碼問了不下二十個人才問到。估計您不記得我了,我是朵河寨的秋生,您二十多年前的學生吶。”
啊,原來是他這個小鬼頭!
我們各自敘說分別后這些年的歷程,拉扯了近一個小時。末了,秋生說他打算下個月回來,屆時請我到他的老家去坐坐,順便看看寨子的新貌,看看我原來工作過的地方。
我說:“好啊,自從離開你們的寨子后,我就再也沒去過。”
秋生說到時順便到縣城接我。他還說,有好幾年沒回老家了。
掛掉電話后,我在朵河寨小學工作的一些陳年舊事從記憶深處跳了出來。
二十多年前我師范畢業后,被分配到離家八十多公里遠的朵河寨小學任教。去學校的那天,一路上我不斷猜測朵河是一座怎樣的村莊。是那種依山傍水、青磚灰瓦、雕梁畫棟、飛檐反宇安臥在蒼茫煙雨里的江南村落嗎?如果是,那村前的臨河上一定少不了幾棵遒勁蒼黑的古樹;如果是,那村里一定有縱橫交錯、幽深逼仄的石板街道從歲月深處蜿蜒而來;如果是,在橘紅的黃昏時,古巷里一定少不了一位眼神有點幽怨的年輕紅衣女子,或是在淅淅瀝瀝的小雨清晨,小樓前一定有滴雨的翠綠芭蕉,在暮色降臨時,村落應處于半河槳聲半河燈影,還有燈影里瀲滟的流水……
在我浮想聯翩時,汽車忽然“蹦”了起來,接著左搖右晃,簡直像在跳搖擺舞,人坐在里面,被顛得像兔子似的一蹦一蹦的。我絲毫沒有準備,腦袋連續撞在玻璃上面,疼得我把所有美麗的遐想變成一連串詛咒聲。
坐在我旁邊的一個黑臉大叔嘆了口氣說:“什么時候把路修好,坐車才不受這種罪?”
轉了四趟車,穿行三個鄉鎮,折騰了四個多小時,終于來到朵河寨所在的鄉。一路顛簸下來,我腰酸背痛,渾身骨頭幾乎要散架了。
在街上吃了碗米粉,問明去朵河寨的路徑后,離開了鄉街,往朵河寨的方向步行而去。
沿江而上的馬路開始時比較平坦,還能見到稀稀落落掩映在樹林中的房屋。漸漸的,房屋越來越少,路也越來越小,森林卻越來越茂密。大約一個小時后,房屋消失,放眼是連綿的群山和綠色的林海。
拐過一道彎,一道峽谷出現在眼前。清澈湍急的河水蜿蜒向前奔流而去,河面上是一座由五根杉木做成的木橋,路到了對岸變成了一條小道,像一條黑色的繩子,在叢林中時隱時現。
我小心翼翼地過了木橋,踏上通往朵河寨的林間小道。
小道兩邊的樹木茂盛、高大,陽光從樹葉的縫隙間漏下來,照在幽暗、潮濕斜斜向上延伸的路面上,有些斑斕。
我背著沉重的行李,翻過兩座山頭后,雙腿就如注鉛般越來越沉重,膝蓋酸脹,口干舌燥,臉皮發燙,汗流浹背。
我的腳步聲和喘息聲在寂靜的叢林中回蕩著,對朵河寨的美麗幻想在喘息中化為烏有。
又翻過兩座山頭,越過一條幽深的山澗,衣服幾乎可以擰出一把水來,有一種虛脫的感覺。
此時已是夕陽西下,蒼茫的霞光萬丈,將黛色的叢林染得金黃金黃,如同佛光,整個世界變得非常圣潔。
又翻過一座小山頭后,我來到一條不寬的河流邊,河水清淺,岸邊一棵盤龍遒勁的古樹斜臥其上,河上有一座木橋。
此時的情景,立刻使我想起馬致遠那首膾炙人口的小令《天凈沙·秋思》。老樹、流水、人家、西風、昏鴉、小橋、古道是有了,那瘦馬呢?也許,那瘦馬馱著古人,穿越時空隧道,緩緩進入歷史的塵埃里。
對岸,是一塊平坦的地,上面有一座古老陳舊黑乎乎的瓦房,房子的周圍,有十來棵虬曲蒼勁、濃綠如云的古樹。
我再看,這塊平地上除了這座房子外,再也沒有其他的房子。
我開始還以為這是一座廟,后來才知道這就是朵河寨小學,確實是由一座破廟改建而成的。而且,朵河寨小學只是一個教學點,周圍沒有居民,離學校最近的那戶人家,也得要走半個小時,
在昏暗的暮色中,我孤獨地打量著這所學校。它恐怕是世界上最簡陋的學校了,四周是碧綠的群山,不通電,不通路。自來水是通了,不過,那是用竹子剖成兩半打掉里面的關節做成水槽,一節挨一節架在叉形的木樁子上,將山澗里的溪水引來的。學校沒有大門,沒有圍墻,哦,錯了,有圍墻,就是那些長在學校四周的參天大樹。有些大樹的樹冠彼此搭在一起,像朋友一樣相互搭著肩膀。教學樓墻體斑駁。由于山里空氣潮濕,灰瓦上長滿青苔,積葉厚的地方,還長了一棵小樹。緊挨著它的廂房,估計以前是供點燈念經的和尚居住,現在改成老師的臥室兼辦公室。操場是一塊坑洼不平的黃色空地。晴天時,風一吹,黃土漫天;雨天,泥濘不堪。在操場的一頭,豎著一根三米多高、碗口粗的筆直杉木,這就是旗桿;另一頭,有一個用木頭做成、掉了兩塊籃板的籃球架,鐵質的籃球圈銹跡斑斑,兩根木頭柱子已經腐朽,上面長著一簇簇白色的木舌。我來這里的半個月后一個刮大風的晚上,籃球架在風中轟然倒塌。
在這里,我開始了為期一年的艱苦的教學生涯。
在這里,我認識了秋生等學生。
從他們的嘴里,我才知道朵河的意思。“朵”在瑤語中是捉迷藏的意思,這是一條在叢林里與人捉迷藏的河流。有時候,這條河流被兩岸茂密的叢林遮掩住,讓人無法看到它;有時候,它鉆出叢林,來到平坦的地方,露出一截身子,而后又一頭鉆進叢林里消失不見。
秋生告訴我,全寨七十多戶并不居住在一起,七零八碎分散在九溪十八澗中,要想找一個小伙伴玩,得翻幾座山。他還說,別看同學們來學校只有一條路,可走二十分鐘后就開始分岔,分成無數條小路伸向不同的地方。他打了個形象的比喻,學校就像人的心臟,那些分開的小路就是它身上的血管。
秋生他們經常問我:“藍老師,你住在這樣的寨子里,最希望的事是什么?”
我說首先當然通電。我來的時候不知道朵河寨不通電,只帶了手電筒,沒買蠟燭,寨子里的人幫我準備的木柴里有松明子,照明不成問題。
晚上燒松明子照明,我可沒有宋朝蘇軾《夜燒松明火》一詩中所表露出來的那種樂觀坦蕩的情懷。雖然松明子在燃燒時會散發出松脂特有的清香味,可是冒出的煙太過濃厚,濃煙彌漫整個狹小的廚房,不長時間,廚房被熏得黑乎乎的,人的臉也被熏得像木炭,吐出的口水都是黑的。
我不敢在晚上用松明子照明。
每天放晚學后,到天黑前這段時間中,我必須要將作業批改好,備好課,寫好教案,做好飯并吃下肚子。
我又說,其次是通路。
每次回家,我都為穿行在叢林中的羊腸小道發愁。每次走在這樣的小道上,我都會想起李太白的詩歌《行路難》:“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
是啊,朵河通往外面世界的大道何時能實現呢?
秋生他們的看法與我相反,他們說:“寨子里的人最希望的還是通公路。因為,朵河寨的大山是金山銀山,錢都藏在叢林里、樹葉下,扒拉開就可以撿到,不通路,藏在叢林里和樹葉下的錢就會漚爛成泥。”
我去秋生家走訪的那天天氣不錯,漫山一片秋黃。在滿眼的秋黃中,星星點點地點綴著一簇綠或是一簇紅,讓人感覺到樸素、平淡的秋季原來也是這樣的美麗。在秋日和煦陽光的照耀下,山間散發出一種清新而又成熟的味道,聞起來令人愉快。
我走在秋日的山路上,迎面吹來的秋風,像一條毛茸茸的小狗尾巴,在我的臉上不停地拂蕩著,麻麻的,酥酥的,癢癢的,我忍不住笑了起來。
很快,我就笑不出了。山間的小路又窄又陡,走起來很費勁,即使像我這樣強壯的小伙子,走一段路也不得不停下來歇息一會兒。我似乎看到,在嚴寒酷暑中,在崎嶇的山路上,二十多個瘦小單薄的身影,用孱弱的肩膀、瘦弱的后背,背著書包和硬邦邦的飯團在艱難地行走。我不由得感慨,山里的孩子讀書多么不容易啊,同時也敬佩他們的頑強和堅毅。我也明白,朵河寨的人為什么那么迫切地想修一條公路。
路上有許多條岔道,分別通向不同的人家。
我知道,那時一些地方的瑤族同胞并不是聚集而居,他們都是分開而住,單門獨戶。這與他們的生活習俗有關。在很久以前,瑤族同胞不堪忍受統治階級和地主劣紳的歧視、壓迫,被迫躲進深山老林之中。由于生產技術落后,生產工具簡單,他們只知道燒山開荒。種玉米時,用棍子在地上戳一個洞,把玉米種子丟進去,然后蹚平;種紅薯時,也用棍子戳一個洞,將薯苗插進洞里。種下之后,又不懂得施肥,幾年后,這片土地變得貧瘠種不出作物,只得另外燒山開荒。所以一戶人家需要很大一片林地。
我看到前面的坡地上長著一棵古老、紅葉似火的楓樹,秋生說站在楓樹下就能看見他的家。
我站在楓樹下,隔著腳下一道很深的箐溝,看到對面山坡上一片在秋季里依舊綠意盎然的竹林中,隱隱約約露出一角灰色屋檐,還有縷縷升上藍天的白煙。
直線看起來,到秋生家好像不過就是十來分鐘的路程,可是我知道,朵河寨地無三尺平,如果要真正走到他的家里很不容易,下山過河,爬坡翻梁,路途遙遠。我想起了幾句那時在農村流傳很廣的俗語:“喊得應,走半天;看見屋,走到哭。”通訊基本靠吼,交通基本靠走。
臨近放寒假時,讀師范時一個玩得最好的鄰縣同學來學校看我,打趣地說,朵河寨的山嶺這么陡峭,什么都種不穩。種點紅薯吧,從土里面一挖出來就往山下跑了,追都追不到。他的話在我腦海中形成這樣一幅無比生動的畫面:傾斜的山坡上,一個紅薯在前面像兔子似的骨碌碌往山腳下跑去,一個人伸著兩手在后面追,風吹得他的頭發往后倒,衣服獵獵作響。以至于好多年過去了,只要我一想起同學的那句話,這一幅畫面就會鮮活地從我的腦海中蹦出來。
…………
回憶到這里,我起身揉揉酸痛的腰部,目光似乎穿過莽莽的時空,看到朵河寨的人們,借助嶺與嶺之間的空隙,踏出一條山間小道,肩挑背扛馬馱,在叢林中艱難地穿行;看到稚嫩的學子們,背著沉重的行李,帶著殷切的希望,在林間小道上踽踽而行,在學海里泛舟;聽到山間的鳥鳴聲響過千年歲月……
我離開朵河寨后,在二十多年的時間里,竟然沒有再回去看望過,它和我始終隔著一輪秦時明月,一座漢時關隘。
一個星期六上午九點左右,我關掉電腦,準備出門到河邊去走走散散心,剛剛換好鞋子,手機響了,一看,是秋生打來的。
秋生問我是否在家。
我說正準備出門。
秋生說估計還有半個小時他就到縣城了,叫我別出門,先收拾一下,到時來接我。
我收拾好行李,手機鈴聲又響了。
秋生說他已經到了我居住的小區樓下。我走到窗前探頭往下看,院子里站著衣著光鮮的男士。
我住在二樓,推開玻璃窗,喊:“秋生,是你嗎?上來坐坐啊。”
那人聽到我的喊聲,抬頭張望著,辨別我所處的位置。
我又喊了幾聲,他說:“知道啦,馬上就來。”
外面響起敲門聲,我和妻子將秋生迎進門。
上次秋生打我的電話后,我們便添加了微信,之后通過他又陸續添加了好些我曾經教過的朵河寨小學的學生微信。
通過聊天,我知道秋生在廣州一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上班,混得不錯,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孩子。
有時候我也去學生的朋友圈看看,見過他們各種各樣的照片,仿佛歲月未曾在他們身上留下痕跡。
現在見到真人,秋生與照片上完全是兩碼事。秋生遠比照片里的胖多了,有了啤酒肚,不過,頭發梳得一絲不茍,西裝革履,里面白襯衫,一派成功人士的模樣。
我問他,怎么不帶家人回來?
秋生說他妻子要加班,請不了假。
我們寒暄了一會兒,秋生說時間不早了,得動身趕路。
我和妻子留他吃了午飯再走,秋生說他早就打電話通知他的父母了,說我要去,叫他們在家里準備午飯。
他又極力邀請我的妻子也去,但是她要照顧生病的岳母,去不了。
從縣城到秋生他們那個鄉的通鄉公路現在變成了一條寬闊平坦的二級公路,車子在路上平穩地飛馳著,一個小時不到就到了鄉街上。可在二十多年前,這是一條彎曲、坑坑洼洼的泥路,從縣城到鄉街上差不多要三個小時。
我們繼續往朵河寨進發。
行至通往朵河寨過河那里,我看到河上凌空飛架了一座平坦的混凝土大橋,而二十多年前我經過的那座木橋還保存完好,還能看到上面近段時間維修過的痕跡。
我想,將那座舊橋保存下來,不外乎有兩個原因,一是以備需要之時,可以重新啟用;二是讓它見證朵河寨的變遷。
我問秋生,果然如此。
以前通往朵河寨的羊腸小道如今變成了水泥路,路面鋪有五米多寬的混凝土,外面的路邊安裝著護欄,開起車來平穩、安全。
轉了幾個彎后,前面忽然出現一排排漂亮的兩三層平房,有五六十棟之多,這些房子坐落在一條河流的兩邊,以及一塊平坦的地里。它們好像經過規劃,井然有序。
我懷疑到了一座小鎮上。
秋生說:“這是原來朵河寨小學的所在地。”
我仔細打量了一番,沒有看見學校,圍繞在校園四周的那些參天大樹不見了,地形地貌也有了改變,但周圍的大山還是有些眼熟。
我問:“學校呢?”
秋生告訴我:“在我調走的第六年,為了響應上級提出整合教育資源的號召,朵河寨小學合并到村中心小學去了。”
他又補充說:“那時朵河寨到村委的道路也修通了。由于通了公路,藏在叢林里的錢都找了出來,好多人都買了摩托,接送孩子方便多了。”
我們說著,秋生開到一座很有氣派的房子前停下,聽到車子的聲音,他的父母從屋里走出來。
雖然他的父母身體還是那么硬朗,但歲月在他們的額頭上、眼角處刻下了許多痕跡。
“藍老師,終于把你這個貴客盼來啦。二十多年不見,你還是那樣年輕。”秋生的父親走上來握著我的手說。
我說:“還年輕啊,別人都叫我大伯了。”
我們熱乎說著話,我突然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說:“藍老師啊,你這一走就是二十多年,也不回這個山窩窩來看看。”
我回頭一看,是一個紅光滿面的老人,雖然滿頭銀花,胡子斑白,卻顯得很有精神。
從他身上,我依稀看出當年村委會主任老根的樣子。
我說:“原來是老根主任啊。”
秋生的父親說:“到屋里去坐著聊吧。”
我和老根聊了一些當年的話題,然后老根聊到朵河寨這些年的變化。
從老根的話中,我拼湊出朵河寨這樣一幅二十多年來簡單的變化圖:我離開朵河寨的第四年,修通了公路。通路之后,朵河寨的竹子、木頭、蘑菇都可以賣錢了,日子漸漸地好了起來。特別是前些年實施精準扶貧后,政府指導他們利用有利的區域優勢大力發展種植業和養殖業,而后又動員他們搬遷到一起居住。
老根說:“其實,大家早就想住在一塊兒,有什么事好相互幫助。”
我問他:“黑石為什么到現在還沒來?”
黑石是我在朵河寨小學任教時的一個學生,他在微信里告訴我,今天我到了朵河后,他一定要陪我好好喝幾杯。
秋生在微信里早就告訴了我,黑石長大后去了部隊,在部隊待了十多年,轉業后本來可以安排工作的,但要自己創業。由于他做事有魄力,創業有方,帶領大家致富,三年前當選村支書。
老根說:“估計黑石還在山里,他承包了幾千畝山地種植高產油茶和獼猴桃,采用‘公司+基地+農戶參股的經營模式,帶動朵河寨群眾發家致富。”
我們正聊著,老根的電話電話響了,是黑石打來的。
黑石說:“我還有事要處理,中午就不來秋生家吃飯了,晚上再來。”他問老根我到了沒有。
老根說我到了。黑石要我接電話。
“藍老師,非常抱歉,中午不能陪你用餐啦,晚上一定補上。”
“先將你手頭的事忙清了再說吧,晚上見。”
吃午飯時,秋生忽然問我:“藍老師,你還記得當年我去豺狗坪采蘑菇的事嗎?”
我說肯定記得,只是不明白他為什么要提起這個話題。
秋生笑了笑,說:“我準備在那兒種錢。”
種錢?我的腦筋一時沒有轉過彎來。
秋生說:“我和黑石已經商量好,準備與他合作,在那兒搞一個紫蠟蘑種植基地。”
“好呀,非常歡迎我們朵河寨走出去的人回來為家鄉做出貢獻!”老根帶頭鼓掌。
飯后,我要秋生帶我到黑石的種植基地去看看。
我們沒走多遠,就聽到秋生的家里傳出陣陣山歌聲:
過去窮,
羊腸小道車不通,
生產物資挑肩上。
住宅多半是茅房。
現在好,
大車小車真熱鬧。
穿戴時髦住新房,
家家戶戶喜洋洋。
過去難,
五黃六月吃兩餐。
別人講我吃得細,
螺螄肚里幾多彎。
現在爽,
一日三餐幾多樣。
孤寡困苦有依靠,
下鄉領導解危難。
…………
秋生笑著說:“寨子里的這些老人,一旦空閑下來就坐在家里唱山歌。”
經過一戶房子特別漂亮的人家時,看到屋頂上插著一面紅旗,秋生說:“這是黑石的家。”
我看到,那面紅旗猶如一團烈火,靜靜地燃燒在朵河寨的上空。我似乎也聽到了陽光在低吟淺唱:
凡間喜歡唱山歌,
你唱山歌我來和;
我要接過你歌喉,
放開嗓子唱新歌。
唱得青山永不老,
唱得朵河泛清波;
唱得藍天飄彩霞,
我唱山歌永不落!
責任編輯? ?韋毓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