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會議:對中國革命認識的深化
潘越
1922年8月29日至30日,在黨的二大結束后僅僅一個多月,二大中央執行委員會在浙江杭州召開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第一次特別會議,史稱“西湖會議”。西湖會議對于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對于中國革命都具有比較重要的歷史意義。
西湖會議是為了解決以何種形式與國民黨進行合作而召開的一次特別會議。
在黨的一大通過的第一個黨綱中,中國共產黨明確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張,即:“中國共產黨徹底斷絕同黃色知識分子階層及其他類似黨派的一切聯系。”①在黨的第一個決議當中,甚至還提出“對現有其他政黨,應采取獨立的攻擊的政策”。
一年后黨的二大召開,大會根據列寧殖民地半殖民地學說和共產國際遠東大會精神,分析了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狀況,討論了黨的任務。二大宣言指出,在中國這個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革命的首要任務是反帝反封建,而不是直接進入到社會主義革命階段。
在對國內形勢和黨的任務認識有了更符合當時中國實際的基礎上,黨的二大通過的《關于“民主的聯合戰線”的議決案》中,對國內形勢作了進一步分析:
“中國名為共和,實際上仍在封建式的軍閥勢力統治之下,對外則為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勢力所支配的半獨立國家,在這種政治經濟狀況之下的無產階級……更有加入民主革命運動之必要”②。即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無產階級應加入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
“民主派對于封建革命是必要的,無產階級倘還不能夠單獨革命,扶助民主派對于封建革命也是必要的,因為封建武人是無產者和民主派公共的仇敵”③。
“我們共產黨應該出來聯合全國革新派,組織民主的聯合戰線,以掃清封建軍閥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④。
中共二大提出了與國民黨進行合作,采取的方式是“黨外合作”,而不是“加入國民黨”的“黨內合作”。
與國民黨進行“黨內合作”,最早是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提出的。
馬林曾經長期在印度尼西亞從事革命工作。印尼共產黨最初力量很弱小,而當地宗教組織——伊斯蘭教聯盟人數龐大卻十分松散。于是馬林提出解決印尼共產黨自身發展的建議,即讓兩個組織的成員互相加入,但同時又保留各自原來的身份。印尼共產黨員很快進入伊斯蘭教聯盟的領導核心,并快速壯大了自身組織,從而推動了印尼的民族解放運動。馬林認為,可以借鑒印尼的做法,中國共產黨員在保留身份的前提下,加入國民黨。這一提議,遭到了陳獨秀的堅決反對。這與陳獨秀希望黨能夠獨立發展的想法是分不開的。
由于兩人誰都說服不了對方,1922年4月,陳獨秀給馬林的上級維經斯基寫了一封信,希望他能夠向共產國際執委會反映自己的意見。
為了讓陳獨秀接受自己的意見,馬林專程返回莫斯科,并向共產國際寫了一份書面報告。馬林還與自己的上級維經斯基進行了長談。7月18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作出決定,贊成支持馬林的意見。7月底,馬林帶著共產國際的文件回到了上海。
此時,黨的二大已經結束。為了統一黨內特別是黨的領導層思想,馬林提議召開一次中央執委會會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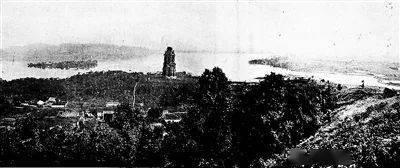
這樣,就有了西湖會議這次特別會議。這也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次以特別會議的方式來解決自身面臨重大問題的會議。
如果說黨的二大解決了與誰合作的問題,那么,西湖會議就是解決了怎樣進行合作的問題。
黨的二大作出建立民主聯合陣線的決定。但孫中山從一開始就不同意黨外的平行合作方式,而只“允許在其黨內進行共產主義宣傳”。
所以馬林認為黨的二大作出與國民黨“黨外合作”的決定,是“犯了左派幼稚病”。馬林在《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中提出:“我建議我們的同志,改變對國民黨的排斥態度并在國民黨內部開展工作,因為通過國民黨同南方的工人和士兵取得聯系要容易得多。”⑤
事實上,作為中共領導人的陳獨秀對于“黨內合作”的態度,從開始到二大前后,也在逐漸轉變。
1922年4月,陳獨秀在廣州會見了青年共產國際委派來華的代表達林。達林談到遠東會議的精神,提出共產黨的整個組織都應該加入國民黨,但前提是要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的獨立性。⑥遠東會議精神、達林的建議,促使陳獨秀進一步深入思考這一問題。
在西湖會議上,一開始對于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大多數人是反對的。但李大釗的看法是:“國民黨的組織非常松懈,無政府主義者加入國民黨已經多年……依舊進行無政府主義宣傳……足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同樣不會受到約束。”⑦李大釗認為在現階段聯合戰線不容易實現,而加入國民黨卻是易于行通的一個辦法。
此時的陳獨秀,提出中國共產黨應該有條件地服從共產國際的相關決定,即:“取消打手模和宣誓服從孫中山等原有的國民黨入黨方法,并根據民主主義的原則改組國民黨。”⑧這樣,既可以實現國共合作,又避免了對孫中山個人的絕對服從,從而保證了中共黨員政治上的獨立性。
經過西湖會議與會者的反復討論,會議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但取消打手模和宣誓服從,并提出要根據民主主義原則對國民黨進行改組。這也正是此時陳獨秀的態度。
西湖會議后不久,李大釗、陳獨秀等首先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1922年11月,共產國際四大召開。陳獨秀等人代表中國共產黨參會。在會上,劉仁靜因為英語流利,作為中國共產黨代表進行了發言:“為了消滅在中國的帝國主義……就必須建立反帝的統一戰線,我們已決定和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了,其形式是我們的黨員以個人名義參加國民黨。”⑨1923年1月,共產國際執委會作出《關于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系問題的決議》,對國共合作起了推動作用。
從以上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統一戰線政策從提出到實現,西湖會議是個重要轉折點。在此基礎上,國共兩黨實現了第一次合作,推動了國內革命形勢的發展,也在合作中壯大了各自的力量。這一點僅從中國共產黨黨員隊伍的發展上就可見一二:中國共產黨成立后的兩年,也就是從1921年7月成立到1923年6月三大召開時,黨員從50多名發展到420名。而從三大到1927年4月五大召開時的近四年,黨員人數已達57967人。
在1923年召開的黨的三大上,陳獨秀專門講述了西湖會議及其會議精神。他說:“從這時起,我們黨的政治主張有了重大變化。”⑩也就是說,西湖會議是黨的政治主張轉變的標志。
西湖會議也是中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運用馬列主義基本原理,特別是運用列寧的民族與殖民地理論,正確分析了中國現實問題,作出了符合中國實際的具有重大歷史意義決定的一次特別會議。
列寧在《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中談到共產黨的基本任務時,提出“在民族問題上……應當是:第一,準確地估計具體的歷史情況……”,也就是共產黨要根據具體歷史情況確定基本任務。
列寧指出,相對落后的國家和民族,要特別注意:“各國共產黨必須幫助……資產階級民主解放運動。”
列寧在共產國際二大上所作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委員會的報告》中提出:“無產階級政黨……不在實際上支持農民運動,就能在這些落后國家里實行共產主義的策略和共產主義政策,那就是空想。”
可以說,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理論的提出,為中共二大制定黨的最高、最低綱領提供了理論指導。在馬列主義理論的指導下,二大正確地把中國革命分為了兩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義革命,第二步才是社會主義革命。
而西湖會議決定了共產黨員以個人的名義加入國民黨的合作方式,為實現兩黨的首次握手與合作奠定了基礎。1923年6月,黨的三大進一步正確估計了孫中山的革命立場和國民黨進行改組的可能性,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以實現國共合作,明確規定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時,黨必須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保持自己的獨立性。黨的三大正式確認了西湖會議的方針,并使之成為黨的工作中心,使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這是中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指導下,把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初步探索出一條符合當時中國國情革命道路的一次重要實踐。
除了討論加入國民黨這個核心問題外,西湖會議還討論了另外一個問題,即對以張國燾為首的“小團體”的活動,提出了嚴肅的批評。
黨的一大后,張國燾擔任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黨的二大后,張國燾試圖使勞動運動獨立于黨的領導之外,把組合書記部當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變形,一切事情由組合書記部發命令找活動分子去作工,不用經黨的通過。這便造成了事實上黨的不團結,削弱了黨的力量。西湖會議的一個重大貢獻就是對黨內團結問題的高度重視,取消了“那個小團體”,避免了黨內可能的分裂。這對于黨的長遠發展來說至關重要。
對于黨內的“小團體”、黨內存在的不團結、黨內潛在的分裂問題,西湖會議給予了足夠的重視,這對于剛剛成立不久的中國共產黨來說,意義和影響都十分重要。無數的歷史事實告訴我們,堡壘往往容易從內部被攻破。團結對于一個政黨、一個社會的發展都是至關重要的。黨內團結是個非常嚴肅的問題,它影響著黨風黨紀,影響著黨的政治規矩的形成。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初就對這一問題高度重視,是難能可貴的。
西湖會議為了加強黨的理論研究和思想宣傳,決定出版發行《向導》周報,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第一份中央政治機關報。《向導》周報于1922年9月13日創刊。主編先是蔡和森,后是瞿秋白擔任,由陳獨秀領導。直到1927年汪精衛叛變革命后停刊,共出201期。
《向導》創刊后,中國共產黨發揮這個輿論陣地的作用,大力宣傳黨的二大提出的民主革命綱領。《向導》公開闡明了黨所領導的現階段的革命性質為國民革命,向群眾提出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軍閥的口號,意義可謂重大。在宣傳黨的民主革命綱領和以國共合作為中心的統一戰線政策、方針、策略等方面,《向導》作出了重大貢獻。
陳獨秀、毛澤東等人都在《向導》周報上陸續發表自己的理論研究和對時事看法的文章。1923年2月27日,陳獨秀在《向導》第20期上發表《統一的國民運動》一文,指出只有把散漫的各個斗爭匯成統一的國民運動,才能打倒軍閥。文章提出:“要打倒軍閥,散漫的各個斗爭是不濟于事的,必須是各階級各部分爭自由爭民權的各種勢力,在一個統一的目標之下集中起來,成為一個有組織的廣大的國民運動,才有充分反抗軍閥的力量”。文章強調了統一戰線的重要作用,宣傳了黨的統一戰線思想。
《向導》被時人頌為黑夜沉沉的中國的“一線曙光”,是指導千百萬苦難同胞前進的“思想向導” 。1923年12月,在北京大學成立25周年紀念日舉辦的民意測驗中,《向導》周報獲得各界讀者愛讀全國周刊第一名。
總之,西湖會議使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第一個統一戰線政策,以符合實際的方式得以實現;它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并與中國的國情相結合,從而制定了符合中國國情的政策,實現了對中國革命道路探索的初次成功;它強調黨內團結的重要性,取消了存在分裂黨的危險的“小團體”;它還提出要重視理論研究與宣傳,為理論強黨的實現開了個好頭。
(本文作者 吉林省社會主義學院教授)
注釋:
①《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頁。
②《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2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19年版,第331頁。
③《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2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19年版,第331頁。
④《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2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19年版,第332頁。
⑤《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2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19年版,第253頁。
⑥ 祝彥:《陳獨秀與西湖會議》,《黨史研究與教學》2009年第5期。
⑦《張國燾回憶西湖會議》,《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2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19年版,第365頁。
⑧《張國燾回憶西湖會議》,《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2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19年版,第365頁。
⑨ 葉永烈:《紅色的起點》,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403頁。
⑩ 葉永烈:《紅色的起點》,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406頁。
《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2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19年版,第124頁。
《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2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19年版,第127頁。
《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2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19年版,第134、136頁。
駱小峰:《對西湖會議的再認識》,《上海黨史與黨建》201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