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羅庚:一生踐行愛黨愛國
蘇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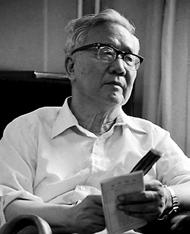
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上,一代又一代科學家以國家民族命運為己任,勇攀高峰,無私奉獻,為科學技術進步、人民生活改善、中華民族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涌現出來的卓越科學家中,享譽國際的數學家華羅庚,開創了中國現代數學學派,培養出陳景潤、王元、陸啟鏗等一批杰出科學家,并深入廠礦農村大力推廣“優選法”、“統籌法”,用一生書寫了愛黨愛國的光輝篇章,留下了許多感人故事。
華羅庚的愛國之心不是偶然的,生長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他,從小耳聞目睹列強的欺凌、國家的孱弱,激發了他為中華之崛起而奮發圖強的決心。家貧輟學、在雜貨鋪打雜的他自學完成高中和大學低年級的全部數學課程,后在上海《科學》雜志發表論文,得到清華大學數學系主任熊慶來的賞識。1930年,熊慶來打破常規,讓20歲的華羅庚來到清華大學工作學習,華羅庚迎來了人生的重要轉折。
1936年,華羅庚被派到英國劍橋大學進修,租住在一間簡陋便宜的房屋。有一天,房東夫婦剛從倫敦看完一場國際田徑比賽回來,興致勃勃地向華羅庚談起比賽的盛況。房東不經意問道:“華先生,怎么沒看見貴國代表隊呢?”這個問題深深刺痛了華羅庚的心。華羅庚心想:“我不能在體育場上為祖國爭光,為什么不能在數學賽場上奪取榮譽呢?”于是,他更加忘我學習、刻苦鉆研,向科學高峰發起猛烈進攻,用智慧和汗水奪取了一個又一個數學制高點,在劍橋大學的兩年間,他完成了十幾篇高水平論文,開始在國際數學界贏得聲譽。
回國后,正值全面抗戰時期,華羅庚在西南聯大任教。當時生活條件極端艱苦,他住在昆明郊區一個牛棚上面的閣樓里。每當牛在下面柱子上擦癢癢時,閣樓就開始搖晃擺動。晚上沒有電燈,他就往一個小碟子里盛一點桐油,放兩根棉線做燈芯。就是在這樣極其簡陋的環境里,從1939年到1941年,在微弱的桐油燈光之下,華羅庚寫出了數學經典著作《堆壘素數論》,在數學界引起轟動,后被翻譯成多種文字出版,以華羅庚為首的中國數學學派已舉世公認,實現了他在數學賽場上為祖國爭取榮譽的決心和愿望。
華羅庚不僅自己奮發治學,還思考中國科學發展的前途。他認為,抗戰期間應先打好純粹科學這個基礎,這是治本所在,將有利于20年后純粹科學與應有科學兼顧的科技發展思路。這一真知灼見與新中國建立后的科學發展路線可以說是遙相呼應。他強烈的愛國精神和切實的愛國行動,為此后的人生道路奠定了基調。
1946年9月,在數學界聲名鵲起的華羅庚到美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訪問,后被美國伊利諾伊大學聘為正教授。此時的華羅庚,雖然身在美國,心卻始終牽掛著祖國,思考著中國數學與科學發展的大問題。他對美國朋友說: “中國是一個大國,也是一個偉大的國家,而且我想我們能夠趕上去。”
新中國成立后,政務院總理周恩來邀請海外學子回國參加建設,引起強烈反響。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成立辦理留學生回國事務委員會,高教部設立歸國留學生招待所。1950年2月,華羅庚舍棄美國的汽車、別墅和豐厚薪水,帶著妻兒踏上了歸途。他和朱光亞、王希季等幾十位中國留學生乘坐“克利夫蘭總統號”輪船回國,在香港逗留期間,他發表《致中國全體留美學生的公開信》,通過新華社于3月10日向全世界播發。信中寫道:“受了同胞們的血汗栽培,成為人才之后,不為他們服務,這如何可以謂之公平?如何可以謂之合理?”“朋友們!‘梁園雖好,非久居之鄉’,歸去來兮!”最后發出號召:“為了選擇真理,我們應當回去;為了國家民族,我們應當回去;為了為人民服務,我們也應當回去;就是為了個人出路,也應當早日回去,建立我們工作的基礎,為我們偉大祖國的建設和發展而奮斗!”
公開信中,華羅庚引用“梁園雖好,非久居之鄉”,感染力很強,成為在留學生中廣為傳頌的佳句;他發出的號召“我們應當回去”,影響和帶動了一大批知識分子回國,引發了留美學生的歸國熱潮,成為華羅庚人生中的一大壯舉。
1979年,華羅庚赴英國講學,回國后講了一個故事:“有一位朋友悄悄問我: 你從美國回中國是不是后悔呀! 因為他覺得去美安家落戶當教授的人是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他現在所求的卻正是我當年所棄的。論生活差距,中美比英美更大,所以他不能理解 1950年初我的行動。但當我說出為人民服務是第一位的,個人生活享受是第二位的時候,他不禁脫口而出: ‘這真偉大! ’”
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救國救民的道路,往往都從樸素的愛國情感出發,上下求索、諸路皆走不通之后,最終都會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旗幟下。作為一名富有愛國精神的科學家,華羅庚走的也是這條道路。
早在中學時期,華羅庚就與兩位老師、共產黨員王時風和錢聞關系親近,三人亦師亦友,友誼保持了終生。1935年一二·九運動時,25歲的華羅庚已是清華大學教師,盡管小時候因為傷寒病沒有得到及時醫治導致左腿殘疾,他仍然拄著拐杖,拖著一條殘腿,走在隊伍前列。國民黨后來大搜捕,華羅庚還在自己家中掩護地下黨員和進步學生,躲過當局搜查。
抗戰期間,華羅庚一直與地下黨組織保持聯系,1940年前后,他還曾想去延安。1946年春,華羅庚訪問蘇聯三個月,很受觸動,回國后他積極在《新華日報》和一些公開場合介紹蘇聯先進興旺的科學、教育、文化和社會主義建設。1947年《時與文》雜志連續刊登他長達3萬字的《訪蘇三月記》,其中寫道:“參觀莫斯科大學,當我一進巍峨的大門,第一眼看見的就是一座列寧像,他手里捧著的卻是一本書! 先到圖書館參觀,四壁掛的是相片”,“走近一看,原來都是科學家、文學家和藝術家,科學家有蘇聯大數學家維諾格拉朵夫和卡皮察等蘇聯的大物理學家……文學家托爾斯泰等。”
1950年3月,從美國歸來的華羅庚回到北京,擔任清華大學數學系主任。1952年7月任中國科學院數學所首任所長,9月加入民盟。1955年被選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1958年夏,華羅庚向黨組織提出入黨請求。這年,華羅庚調任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兼數學系主任,并走上了為生產實踐服務的應用數學道路。他創造的統籌法和優選法(即“雙法”)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歡迎,在管理運用和科學實驗上,大大優化了各方面建設事業,取得巨大的經濟社會效益,廣泛提高了國人的科學素養。為此,他與毛澤東還曾書信往來,毛澤東兩次親筆寫信給他,予以支持和鼓勵。1964年3月,華羅庚收到毛澤東親筆回信:“華羅庚先生:信已經收讀。壯志凌云,可喜可賀。”第二次是1965年7月,“華羅庚同志:你現在奮發有為,不為個人而為人民服務,十分歡迎。”這封信上,毛澤東把對華羅庚的稱呼從“先生”改為了“同志”。
1979年3月,華羅庚應邀赴歐洲講學前,再一次遞交入黨申請書,寫道:“雖然現在蒲柳先衰,心顫、眼花、手抖、頭發白,但決心下定,活一天就為黨工作一天,活一小時就為黨工作一小時。”6月13日,在英國講學的華羅庚收到被批準加入中國共產黨的通知。這位69歲的“新黨員”興奮得一夜難眠。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到英、荷、法、德四國講學,盡管關節經常疼痛,但一想起這是為黨爭光,就講得起勁多了。”
1980年元旦,鄧穎超見到華羅庚,祝賀他實現入黨夙愿,夸他是“老同志,新黨員”。華羅庚很感動,對周圍的人講:“這六個字是對我一生最好的總結。”并寫下“五十年來心愿,三萬里外佳音”的詩以奉答鄧穎超,還寫道:“實干、苦干、拼命干,黨員本色;空話、大話、奉迎話,科學罪人。”
1959 年,華羅庚開始轉到研究應用數學和推廣應用。他一直就倡導純粹科學與應用科學兼顧的科學發展理念,他明白應用數學的巨大價值,并別具慧眼地提出數學工程、數學技術等重要觀點,認為“應用數學是一種技術,現在人們沒有認識到,將來會認識到的,等將來國際上一旦有人提出數學技術的觀點時,你就說我華某人早就看到了”。1958年后,全國興起到工農中去、到生產實踐中去的社會運動,華羅庚也想為此作出貢獻。他在訪問一些工廠和農村后,發現這些地方管理工作極其落后,決定更直接地為人民服務,把“雙法”作為應用數學的突破點。
他曾對工作人員說:“在回國以后較長的一段時間,我和許多從舊社會過來的科學工作者一樣,仍習慣于灌注式的教學和經院式的科研,在課堂上講的是‘厚本本’、‘大套套’,在書齋里鉆研的是別人越不懂越玄妙越好,這種脫離生產勞動、脫離工農的道路,和新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制度越來越不相適應。”這是他發自內心的真實想法,科學要為生產服務、要為人民服務,他也是這樣做的。
整個20世紀六七十年代,華羅庚選擇優選法、統籌法作為運籌學的推廣應用重點,在全國20多個省區市進行生產工藝上搞優選、生產管理上搞統籌的普及活動,他下農村、去廠礦,不辭勞苦、不遺余力,足跡遍布大半個中國。他一次次病倒又一次次爬起來,人們勸他注意休息,他卻回答:“生產若能長一寸,何惜老病對黃昏!”
1975年,65歲的華羅庚在大興安嶺推廣“雙法”,積勞成疾,第一次發作心肌梗塞,昏迷了6個星期,一度病危。出院后,他仍然堅持工作,僅在1976年到1977年初就兩次到山西。每次出門,必備氧氣袋,就是在這樣的身體狀況下,華羅庚仍堅持奔波在各地推廣應用數學,他透支著自己的生命,燃燒著自己的才華與熱情。
20世紀80年代初,華羅庚在不同場合數次提到,選擇科學方法進行普及推廣要注意四點:要適應我國經濟和工業的實際情況;應該盡量采用現代方法;要經得起實踐的檢驗;要從理論的高度進行分析。
關于采用現代方法,華羅庚可謂富有遠見。1969年,他出版的《優選學》提出,將人類生產、設計、制造等技術與計算機技術結合起來。當時正值第三次科技革命剛剛興起計算機電子技術,華羅庚敏銳地看到了這一尖端科技的前景。改革開放初期,當時計算機電子技術在國外已經開始微型化,華羅庚意識到這是應用數學新的發展契機,積極推動成立應用數學研究所,支持組建中國運籌學會、中國優選法統籌法與經濟數學研究會。這些前瞻性重大決策為我國應用數學的深入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華羅庚不僅是一位蜚聲國際、為國爭光的數學大師,還在人才培養、數學科普等方面為黨和國家作出了出色的貢獻。他胸懷祖國、服務人民,他潛心研究、推廣應用,他甘為人梯、獎掖后學,可以說是科學報國的典型代表,是科學家精神的突出代表。
新中國成立之初,由于國民黨敗退臺灣時把原有數學研究方面的物資都搬去了臺灣,再加上帝國主義封鎖,研究工作面臨困難。在異常艱苦的工作與生活條件下,肩負著新建中國科學院數學所重任的華羅庚發揮出色的組織領導才能,數學所上下團結一心、艱苦創業,不到五年就初具規模,涌現出一批出色的科研成果與專業人才。
華羅庚對培養人才很有一套,最突出有效的便是組織討論班,這源于總結自身學習經歷和國內外教學經驗。在西南聯大時期,他就組織了一個討論班,在其中受到教益成為著名數學家的有段學復、閔嗣鶴、樊畿、徐賢修等人。20世紀50年代初,他又在新建的中科院數學所組織了兩個數論討論班,一個是基礎性的,由他每周講一次,講義交給學生分別負責,反復討論后再定稿;另一個是哥德巴赫問題討論班,由學生輪流報告,凡有疑難之處,他都要當場追問清楚,激發學生不斷思考和解決問題。節假日,他還常到宿舍找學生談數學問題,常常用“天才在于積累,聰明在于勤奮”的話鼓舞大家。受他直接領導成長起來的學生有越民義、萬哲先、陸啟鏗、龔升、王元、許孔時、陳景潤、吳方、魏道政、嚴士健與潘承洞等。這些人后來都成了院士或教授,有些是國際著名數學家,受過他影響的數學家更是不計其數。
華羅庚不僅培養數學專業人才,還特別重視推廣數學競賽活動、出版通俗讀物,激發廣大青少年對數學的熱情。1956年,在華羅庚倡導下,我國首次開展數學競賽,北京、天津、上海、武漢四大城市舉辦了高中數學競賽。50年代北京的歷次數學競賽活動,華羅庚都熱心參與組織,曾親自擔任北京市競賽委員會主席,從出試題,到監考、改試卷都親自參加,還多次到外地去推動這一工作。比賽前后,他都親自給中學生作報告進行動員,當時稱為“數學通俗講演會”。在這些報告的基礎上,華羅庚出版了一批通俗讀物,如《從楊輝三角談起》、《從祖沖之的圓周率談起》、《從孫子的“神奇妙算”談起》、《數學歸納法》等,不僅普及數學知識,更富有啟發性,也是很好的愛國主義教材,這些書一版再版,在青少年中廣為流傳并影響至今,成為他們最喜歡的課外讀物之一。
華羅庚一生拼搏不斷奮進,曾以“老驥恥伏櫪”自勉。1979年,已近古稀之年的他指出:“樹老易空,人老易松,科學之道,戒之以空,戒之以松,我愿一輩子從實以終。”即使臥病在床,仍然堅持工作,“我的哲學不是生命盡量延長,而是工作盡量多做”,“最大希望就是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980年春,華羅庚開始醞釀遺囑稿。主要內容有:死后喪事從簡,骨灰撒到家鄉金壇縣的洮湖中;我國底子薄、基礎差,要提倡多干實事、有益的事,少說空話大話;發展數學,花錢不多,收益很大,應該多加扶持;死后,所收藏的圖書及期刊贈送給數學所圖書館。
這一時期,華羅庚不顧年老體弱多病,不僅繼續到各地推廣應用數學,更是發揮自身影響力,活躍在國際數學界,帶領中青年骨干到國外積極開展學術交流活動,為中國科學界走出國門追趕世界貢獻力量。1983年在美訪問期間,有人建議他利用這次出國機會治療心臟病,他則認為,“先把工作搞好”,“為黨為國為人民更努力,獻出僅有的余力”。1984年8月,華羅庚在病榻上寫下《述懷》:“即使能活一百年,36524日而已。而今已過四分之三,怎能胡亂輕拋?……為人民服務,鞠躬盡瘁而已。”
1985年6月12日,75歲的華羅庚在東京大學向日本數學界作題為《理論數學及其應用》的演講,因突發急性心肌梗塞,于當晚與世長辭,一顆數學巨星就此隕落。畢生馳騁在“數學王國”的華羅庚,是在數學講壇上走完生命最后一程的,踐行了他生前的志向: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華羅庚的一生,矢志踐行愛黨愛國。人生的序幕、開篇是個人的數學理論水平達到世界高峰,而發展、高潮卻無一不與國家命運、應用數學、社會價值息息相關,在人生結尾處,又以“理論數學與應用”落下帷幕,這也正是“老同志,新黨員”、“人民科學家”華羅庚75年光輝人生的最恰當詮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