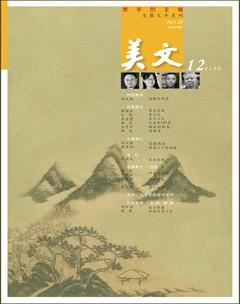神居山下的淵源

周榮池
高郵小城依運河與高郵湖而生。縱貫南北的河湖又將小城分為東西兩個區域。河之東為廣袤的里下河平原引首地區,是城市的主體部分,常稱為“運東”。河之西,濱湖的鄉土之地,常稱為“湖西”地區。汪曾祺在《我的家鄉》中提及湖西,充滿對此處鄉土之地的神往:
我們有時到西堤去玩。我們那里的人都叫它西湖,湖很大,一眼望不到邊,很奇怪,我竟沒有在湖上坐過一次船。湖西是還有一些村鎮的。我知道一個地名,菱塘橋,想必是個大鎮子。我喜歡菱塘橋這個地名,引起我的向往,但我不知道菱塘橋是什么樣子。湖東有的村子,到夏天,就把耕牛送到湖西去歇伏。我所住的東大街上,那幾天就不斷有成隊的水牛在大街上慢慢地走過。牛過后,留下很大的一堆一堆牛屎。聽說是湖西涼快,而且湖西有茭草,牛吃了會消除勞乏,恢復健壯。我于是想象湖西是一片碧綠碧綠茭草。
湖西有山,名神居山,當地人又多稱為天山,為“淮南眾山之母”。天山名氣雖大,其實高不過數十米,實是因神而名的“山不在高”。汪曾祺在《我的小學》中提及“神山”:
“神山爽氣”是秦郵八景之一。“神山”即“神居山”,在高郵湖西,我沒有去過,“爽氣”也不知道是一種什么樣子的氣。
神山之神到底為何神眾說紛紜。有說堯帝生于此,有說東晉宰相謝安和南齊亙公先后在神居山上修煉丹藥,有說穆桂英曾率兵在此駐扎。這些都不是神仙,是些神奇的人間傳說。此山雖不高但名滿天下,充滿神韻,曾有釋道潛、胡儼、秦觀、鄭板橋等名家興會詠作詩詞百首之多。宋代樂史撰的《太平寰宇記》中記載:“排牙石,在高郵之神居山,石齒如排牙,人數之,自始至終,其數必增,自終而始,其增愈甚,竟無能知其數之確者。” 排牙石的傳說,更給神居山增加了幾分“神”采。
從地理空間和文化心理上講,湖西與運東地區某種程度上存在著“異質”。這既是“十里不同風”的現實情形,也緣起于湖西這個區域自身具有的神奇、神秘以及神韻。在高郵城的版圖上,湖西地區像是一枚引首的神奇閑章。這處鄉土之地像某種源流,連接著揚州與下河的深厚淵源。
一
汪曾祺生活的東大街,當時也是商旅云集之地。城市與鄉土、本地與他鄉、今時與舊日,錯綜復雜地交融在混雜的鄉音之中。就方言而言,東北鄉與興化等下河地區相像,西南湖西與揚州音近,高郵城內又猶如方言孤島,自成一派。雖然交流并無障礙,但語調和音色的細節依然像是相互區別的密碼,有顯而易見的差異。湖西地區的村鎮中,最為特別的是菱塘鄉。這個如今江蘇獨有的民族鄉是由來已久的回民聚居地。在汪曾祺生活于高郵的歲月里,他已在人的長相、不同的風俗上對老家的風土有了自己的一些認知。在《雞鴨名家》中,菱塘人是這樣出場的:
鴨掌、鴨翅是剛從雞鴨店里買來的。這個地方雞鴨多,雞鴨店多。雞鴨店都是回回開的。這地方一定有很多回回。我們家鄉回回很少。雞鴨店全城似乎只有一家。小小一間鋪面,干凈而寂寞。門口掛著收拾好的白白凈凈的雞鴨,很少有人買。我每回走過時總覺得有一種使人難忘的印象襲來。這家鋪子有一種什么東西和別家不一樣。好像這是一個古代的店鋪。鋪子在我舅舅家附近,出一個深巷高坡,上大街,拐角第一家便是。主人相貌奇古,一個非常大的鼻子,鼻子上有很多小洞,通紅通紅,十分鮮艷,一個酒糟鼻子。我從那個鼻子上認得了什么叫酒糟鼻子。沒有人告訴過我,我無師自通,一看見就知道:“酒糟鼻子!”我在外十年,時常會想起那個鼻子。剛才在雞鴨店又想起了那個鼻子。現在那個鼻子的主人,那條斜陽古柳的巷子不知怎么樣了……
汪曾祺記憶里開雞鴨店的人,便是當地的回民,他們聚居在菱塘。回民因為獨特的飲食習慣,雞鴨以及牛羊是他們的肉食來源,因此打理和制作雞鴨牛羊是回民的拿手本領。汪曾祺是美食家,走遍各地,嘗盡風味,自然還是舌尖上的家鄉味道最為深情,那是童年就留下的味道秘境,盡管“一個人的口味要寬一點、雜一點,‘南甜北咸東辣西酸,都去嘗嘗。對食物如此,對文化也應該這樣。”汪曾祺做菜和寫文章一樣也出了些名氣,家鄉的吃食自然也跟著“出鏡”,更有人們有心制出“汪氏家宴”。 淮揚名廚陳萬慶,除是鐵桿“汪迷”外,也是汪曾祺先生的高郵同鄉。陳萬慶還原部分汪曾祺書中描述過的家鄉小菜,題名《不過一碗人間煙火·汪曾祺家宴》,中有涼菜八味:煮蠶豆、咸菜小魚、南乳蝦、界首茶干、小蘿卜、咸風鵝、蓑衣黃瓜和鹵味拼盤,其中咸風鵝以及鹵味拼盤老鵝雜件都有鵝的影子。
菱塘人在本地善制鵝,傳統久矣。唐人姚合在《揚州春詞》中描述揚州是“有地惟栽竹,無家不養鵝。”揚州老鵝在外的名氣與在里巷餐桌的普及可謂壯觀。此“老鵝”專指鹽水鵝,黃玨、菱塘等鄉的味水尤為出名。鹽水鵝是汪曾祺所言的“熏燒攤”上的大菜之一。據說本鄉原是制作鹽水鴨的——鴨也是本地出名的“羽翅”族類。但鴨乃雜食,需吃糧食,后便選只食草的鵝鹽水制之。所謂“熏燒”乃下河周邊縣市中的一種特色叫法,其實并非熏或者燒,實是鹵煮(又或本是熏制后經改良,也無從考)。《異秉》中的王二就是做熏燒的:“不知從什么時候起,他就在保全堂藥店廊檐下擺一個熏燒攤子。‘熏燒就是鹵味。”而那時“熏燒”的主要食料是:“這些玻璃匣子里裝的是黑瓜子、白瓜子、鹽炒豌豆、油炸豌豆、蘭花豆、五香花生米、長板的一頭擺開‘熏燒。‘ 熏燒除回鹵豆腐干之外,主要是牛肉、蒲包肉和豬頭肉。這地方一般人家是不大吃牛肉的。吃,也極少紅燒、清燉,只是到熏燒攤子去買。這種牛肉是五香加鹽煮好,外面染了通紅的紅曲,一大塊一大塊的堆在那里。”
善做牛羊肉也是菱塘鄉民的特色,此鄉專有“清真宴”,鹽水鵝也是一道重要的味水。菱塘并非全無豬肉入席,這處回漢聚居的湖邊鄉土之地,“熏燒攤”上的豬頭肉也極好吃。與運東地區不一樣的是,這里的豬頭是紅湯老鹵所鹵制,色味較下河更濃郁。同是鹵味,鹽水鵝有一套單獨的瓢盆碗盞,以遵回民習俗。作為地處蘇中唯一的回民鄉,這里依舊保持著長期以來獨有的民族習慣——所謂風味獨特,始于風俗,味不同矣。
《高郵州志》歷代版圖中,自明代就有舊稱菱塘橋,但其歷史應肇始于唐。學人劉水研究,公元605年,隋煬帝在邗溝的基礎上開挖貫通南北五大水系的大運河,位于南北交通樞紐上的揚州一躍成為東方繁榮之地。阿拉伯、波斯商人由海上絲綢之路到廣州、泉州、揚州經商,伊斯蘭教隨之傳入揚州。舊有“一賢傳教于廣州,二賢傳教于揚州,三賢四賢傳教于泉州”之說。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往來、居住于揚州,從事海上貿易,經營珠寶、香料等。到中唐時期,已有許多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在揚州經商,統稱“胡商”。唐肅宗上元元年(760年),唐朝大將田神功大掠居民財產,殺波斯胡商數千人之多。危難之際,揚州城里部分胡商選擇來到三面環湖、位置偏僻、亂軍不至的高郵菱塘避禍定居,過上漁牧耕織的鄉土生活。宋代菱塘人煙漸稠,回漢文化交相浸染。南宋咸淳年間,阿拉伯伊斯蘭教先賢普哈丁來揚州傳教,創建仙鶴寺,把天方福音廣播運河沿線包括高郵、菱塘在內的周邊城鄉,歸信者日益增多,當時稱伊斯蘭教為大食教,據傳彼時菱塘已有三百多大食教民定居。
元代菱塘回民定居一帶又名“回回灣”。宋元戰爭時期,元朝軍隊中有一支叫做“探馬赤軍”的精銳部隊,在野戰和攻打城堡時充當先鋒,戰事結束后即屯戍被征服地區,所謂“上馬為軍,下馬為墾”,過著兵農合一的生活。探馬赤軍中加入了一支原中亞穆斯林組成的“西域親軍”,隨軍駐防各地。其中有的就屯駐在揚州、高郵沿湖一帶地沃灘闊處。元朝統一中國后,下令“探馬赤軍與民同編”,散布于各地的回軍屯區也就變成了回民聚居村落,由此留下回回營、屯、寨、凹、村等眾多地名。
及明清至今,菱塘設為民族鄉,成為神居山下一處風情獨特的湖邊鄉村。盡管風俗有異,但湖西與運東,回民與漢族,今日與舊時,民眾因生產生活的現實所需,從來沒有隔膜與區別——地理、風俗、鄉音是抵制不了生活本身之溫暖的。在鄉土世界有一種很現實的規則,一切要有利于生產和生活的組織。在物質匱乏的時候,即便是族群之間有不同觀念,也會實現一定程度上的退讓和融合。不同風土之間的影響,取決于自身的強大以及生活對人們的要求。取舍趨向于“致用”,這也是一種非常樸素實用的觀念。汪曾祺小說《禮俗大全》中的“李成模”便是菱塘人:
呂家人口簡單。呂虎臣中年喪妻,沒有再娶。沒有兒子,只有個女兒。女兒叫呂蕤,小時候放鞭炮,崩瞎了一只左眼。因此整天戴了深藍色的卵形眼鏡。有個女婿叫李成模,菱塘橋人。女婿不是招贅的,而是從小和呂蕤訂了婚,為了考大學,復習功課住到丈人家來的。小兩口很親熱。呂蕤很好看,缺了一只眼睛還是很好看。他們每天都在門前閑眺,看人打魚,日子過得很舒心自在。有一次互相打鬧,呂蕤在李成模屁股上踢了一腳。正好呂虎臣從外面回來,裝得很生氣:“玩歸玩,鬧歸鬧,哪兒有這樣鬧法的!叫過路人看見了笑話!”呂蕤和李成模一伸舌頭。
對于沒有去過的湖西,特別是菱塘這個地方,汪曾祺充滿著自己的關注和興致。他所寫的這些地名和人物是小說家的借用,也是對現實里某一地域的獨特青睞。
二
汪曾祺的人生旅途中,昆明是一個重要節點。遠在西南邊陲之地,這里也有一個若隱若現的“高郵朋友圈”。在散文《自報家門》的自述中,汪曾祺幾乎是以一種戲劇性的情節開始了他的昆明之旅:
一九三九年,我從上海經香港、越南到昆明考大學。到昆明,得了一場惡性瘧疾,住進了醫院。這是我一生第一次住院,也是惟一的一次。高燒超過四十度。護士給我注射了強心針,我問她:“要不要寫遺書?”我剛剛能喝一碗蛋花湯,晃晃悠悠進了考場。考完了,一點把握沒有。天保佑,發了榜,我居然考中了第一志愿: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
他到昆明,是同鄉人的幫助讓他如愿以償。在山高水遠的昆明,汪曾祺同樣幸運地得到鄉人的幫助。學人陸建華在《汪曾祺的回鄉之路》中記道:“當年從高郵去昆明的路很不好走。因為戰爭,汪曾祺必須先到上海,與當年一道在江陰縣高中讀書、如今又都有意報考西南聯大的同學聚合,然后由上海經香港,到越南,再乘滇越鐵路到昆明。進出越南得有法國領事館的簽證,這不是件容易事。由于汪曾祺從高郵出發時已經遲了幾天,到上海僅他一人還沒有簽證,差點走不成。后來幸虧一位姓朱的同學幫忙,他的爸爸是醫生,給黃金榮看過病,硬是通過這層關系,憑黃金榮的一張名片到法國駐滬領事館突擊辦好了簽證。”
這位“姓朱的同學”便是高郵同鄉朱奎元,一位菱塘人。他與朱奎元的同學關系實是小學校友。朱奎元高汪曾祺兩個年級,初中畢業后從商。在昆明最初的日子里,汪曾祺還能與家里聯系,家里寄來的錢和信,維持著東大街對他物質和精神上的補給。但隨著時局的緊張,他與家中的聯系變得困難。正如俚語所言:“一段籬笆三根樁,一個好漢三個幫。”在生活無以為繼的時候,他得到了這位起初并不十分熟悉的同鄉的幫助。據學人徐強在《汪曾祺年譜》中所述,汪曾祺很有可能是與朱奎元同一艘船去的昆明。因汪曾祺在1944年5月22日致朱奎元信中曾說:“昆明又是雨季了。據說昆明每隔五年,發水一次,今年正是雨多的時候。你還記得我們來昆明那年,翠湖變得又深又闊,青蓮街成了一道澗溝,那些情形不?今年又得像那個樣子了。”
此中所講“我們來昆明那年”,是不是指他們同船抵達難以考證,不過他們此時親密的關系已經相當清楚了。汪曾祺囊中羞澀的時候便與朱奎元暫借,所欠錢款又由在高郵的父親汪菊生如數還給當時在菱塘的朱奎元母親朱大老太。朱奎元長汪曾祺五歲,本也住高郵城內,后因藥店的營生舉家遷到菱塘。朱奎元是高郵中學一九三二屆校友,同濟大學機械系畢業,曾在昆明高等工業專科學校實習工廠負責。正是此時,汪曾祺在西南聯大讀書,不時幫助朱奎元處理文務,朱奎元也想學寫文章,所以他們便有了更多的交往。后來,朱奎元到云南桐梓學習煉鋼,他們之間又有許多信件來往,《汪曾祺全集》中收錄有十數封。
朱奎元去桐梓是為謀生,也因心里“不自在”,所謂“煉鋼”只是借口。實情是因為一個叫陳淑英的女子。汪曾祺信中幾次提到此人。陳是新加坡人,西南聯大外文系學生,是朱奎元、任振邦同追的對象。陳淑英周旋于二人之間,令朱奎元十分苦惱,汪曾祺勸他“得作癡人,斯能免俗”。 任振邦是高郵臨澤人, 1933年高郵中學畢業后考入上海教會學校,學習英語會計,畢業后入上海信托銀行工作,后到信托局昆明分局。任振邦與汪曾祺也有較多來往,曾經請汪曾祺教他學寫詩詞,汪曾祺身無分文的時候也會向任振邦暫借。
汪曾祺的昆明“高郵朋友圈”中,多是江湖救急的好朋友。朱奎元因為心中“不自在”而去桐梓,也是去尋一位高郵同鄉師長,那是他與汪曾祺共同的老師顧錫鏞。顧錫鏞(1907 -1976),畢業于中央大學數學系,是汪曾祺、朱奎元的數學老師,數學教得很好。顧先生曾經同汪曾祺開玩笑,說其做的幾何題是“桐城派幾何”。顧錫鏞建國后以號“調笙”行世,故人稱“顧調笙”。 顧錫鏞有位女學生名李湘,小他9歲,與汪曾祺、朱奎元是初中同學。她便是汪曾祺與朱奎元信中所稱的“李小姐”。李湘初中畢業后入江蘇省護士學校,畢業后積極進步,要求去延安抗大學習并入黨。顧錫鏞深深愛著她,李湘回到國統區后與其成婚。1944年,顧錫鏞、李湘夫婦到了貴州桐梓,顧先生任桐梓一中校長。朱奎元覺得在昆明“不自在”,于是就對汪曾祺說到桐梓學習煉鋼,實際是投奔老師以躲避人生。汪曾祺知道顧錫鏞已有兩個孩子,其時日子也不寬裕自在,所以在1944年4月18日去信勸朱奎元:
到了那邊怎么樣呢?顧先生自然歡迎你,不然你沒有理由到那里去。自然也不歡迎你,他信上說得明白懇切。你必不免麻煩到他,這種出于意料的事,照例令人快樂,也招人煩惱。我不知道你所遭到的是什么。如果他的招待里有人為成分,希望你不必因此不高興。如果他明白他的麻煩的代價是非常值得的,以那種小的麻煩換得十分友誼,減少一點寂寞,他會高興的。
汪曾祺的勸說是符合世情的,他甚至從另外一個很有意味的角度勸說朱奎元離開桐梓。在同年7月29日的信中,他寫道:
我十分肯定的跟你說,你必須離開,離開桐梓,離開那邊一切。
我覺得那是個文化低落的地方,因為一個中人意的女人都沒有。這是一個絕對的真理,文化是從女人身上可以看出來的。雖然女人不是文化的核心,核心是男人。這很簡單,你走到一個城里,只要聽一聽那個城里的女人說些什么話,用什么樣的眼色看人,你就可以斷定這座城里有沒有圖書館,有沒有沙龍。你記得有一次來信說你也陪了許多女人出去玩過么?你只要回想一下那次經驗!
那么一個地方,除了打算永久住下去,你不能有一刻不打算走。我不知道你的書念得怎么樣了,即使念得很好,你也得離開。如果念得真好,你更該離開。因為你根本不是個念書的人。你之不能念書,正如我之作不了事情。我也還有點好動,正如你也還有時喜歡一個人靜處(像你在紫藤沒有開花的時候),但是我的動和你的可不同。你的靜是動的間歇,我的靜則是動的總和。你必須出來,出來作點事。
汪曾祺的這個勸說非常有意思,說一個地方文化的落后,竟然是因為一個中人意的女人都沒有。后來朱奎元離開桐梓到重慶、蚌埠的兵工廠工作,二人就沒有再通信了。1949年朱奎元到了臺灣開廠經商,直到1988年兩岸通航才回到家鄉菱塘。其母朱大老太已經去世,朱奎元以母親的名義在家鄉學校設立了圖書館,后又以顧錫鏞的名義在與汪曾祺共同的母校設立獎學金,并捐助建設“神山數位圖書館”——這位神居山下菱塘橋走出去的游子,始終牽掛著自己的家鄉,這一點與汪曾祺的游子情是一樣的,或者說,天下哪有不想家的孩子呢?
朱奎元遠走他鄉,但是在昆明時與汪曾祺的信件一直帶在身邊收藏。這是他們友誼的見證,字字句句親切真摯。1986年10月4日至15日,汪曾祺隨中國作家代表團赴香港訪問,朱奎元在臺灣得知了這一消息,專程從臺北到香港與汪曾祺一晤敘舊。1991年10月,汪曾祺與夫人施松卿回高郵,與朱奎元在高郵得以再聚首,但據說此次晤見他們并未多言。1993年朱奎元去北京又見過汪曾祺一面,據說此時兩人言語更少,甚至有傳汪曾祺對其“不是特別友好”。后來學人徐強先生向汪曾祺長子汪朗求證此事,實為訛傳。
人老了,很多話就不必再說了。更何況他們年輕時說過那么多話,彼此還有什么不懂呢?以后幾十年不相見,未必就行同陌路,而沒有交集的世界再說什么又能怎樣呢——該說的話已經說了。以汪曾祺淡泊自守的脾性,他也不會“不是特別友好”。朱奎元與汪曾祺香港的那次見面,朱奎元要送汪曾祺“三大件”的票據,可以在北京提貨,汪曾祺婉謝了。那時,內地的電器“三大件”(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還要憑票供應,而汪曾祺也確實需要這些家電。他在1987年8月31日致信施松卿時曾提到:
……《大公報》稿費不高,七篇才給了360元,彩電和錄像機一套大概需要港元5000左右,可以在國內提貨。等我回國經港時再買吧。不過古華說國內無磁帶,買錄像機等于一個擺設。到美國后在信中再商議此事吧……
三
汪曾祺神往的神居山是福地。他沒有去過的菱塘橋,那里走出的鄉人卻給困難時候的汪曾祺深情的恩惠。在《我的小學》中他回憶了縣立第五小學的校歌歌詞:
西挹神山爽氣/東來鄰寺疏鐘/看吾校巍巍峻宇/連云櫛比列其中/半城半郭塵囂遠/無女無男教育同/桃紅李白/芬芳馥郁/一堂濟濟坐春風/愿少年/乘風破浪/他日毋忘化雨功。
神居山實在是一座神山,它隱藏了太多的秘密——它曾將一個偉大朝代的細節埋藏于此。
1979年,神居山西漢墓葬被發掘。其墓葬面積比湖南馬王堆漢墓大18倍,內有代表古代最高禮儀的葬禮“黃腸題湊”,并出土金縷玉衣殘片。墓主人系西漢廣陵王劉胥,是夫婦同塋異穴合葬墓。漢墓出土了玉器、銅器、漆器、陶器、木俑等大量器物。隨葬品中的漆器、木雕制作異常精美,特別是漆塌、木履和成套的浴具為漢代考古少見。出土的四座西漢石坑木槨墓,黃腸題湊結構細密,儼如方城。
公元前194年,漢高祖統一天下后封侄兒劉濞為吳王,建都廣陵城。漢武帝時,以廣陵郡部分地置廣陵國,“分沛、東陽置臨淮郡”。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封其子劉胥為廣陵王,都廣陵。廣陵王是古代王爵,歷朝封廣陵王者17人。劉胥在位64年,宣帝五鳳四年,因“巫祝祖上”案發被究,綬帶自縊,廣陵國除,改為廣陵郡。高郵湖西菱塘、天山一帶即在當時的廣陵國屬地內。菱塘一帶不僅是郵驛要沖的邊壤,廣陵王國的鄉邑,緊鄰神居山,還以“無美不收”“諸吉咸備”而被擇為劉胥陵墓之地。
董仲舒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提出“獨尊儒術”,《董仲舒傳》中記載了董仲舒提議“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武帝紀贊》中記載了漢武帝的做法是“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對于“儒”而言,汪曾祺的內心是認同甚至推崇的,他在《我是一個中國人》里寫道:
中國人必定會接受中國傳統思想和文化的影響。我接受了什么影響?道家?中國化了的佛家——禪宗?都很少。比較起來,我還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
而在《自報家門》中,他說得更清楚:
有評論家說我的作品受了兩千多年前的老莊思想的影響,可能有一點,我在昆明教中學時案頭常放的一本書是《莊子集解》。但是我對莊子感極大的興趣的,主要是其文章,至于他的思想,我到現在還不甚了了。我自己想想,我受影響較深的,還是儒家。
……須知世上苦人多。我覺得儒家是愛人的,因此我自詡為“中國式的人道主義者”。
一切其來有自,對于一個作家的成長而言,地方文化一定是重要的精神準備,尤其是在生命和精神成長的早期,這種影響會更加深刻。最早的精神喂養最為直接,很少會受到主觀世界的任何自主性選擇。對于高郵小城而言,在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時期文明之前,這處被稱為“江淮文明之光”的處女地還沒有文字,漢代以降,政權逐步入主這塊土地,神居山下才有了真正的文化積淀,可以說神居山舊地是這片土地的精神源頭。
這片土地的繁榮之始,當歸功于吳王劉濞。此地與當時的東越等蠻國接壤,民風剽悍,勇而好戰。《史記·貨殖列傳》中記載:“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說是先秦時期廣陵的民風和北地彪悍的徐州類似。高祖十一年(前196年),劉邦親率大軍平定淮南王英布叛亂,任命年僅19歲的劉濞為騎將隨同作戰。劉濞不負厚望,身先士卒,作戰勇猛,屢立戰功。叛亂平定的第二年,劉邦改當年劉賈所封的荊國為吳國,封劉濞為吳王,統轄東南三郡五十三城,定國都于廣陵,開此地繁華之始。
劉濞是猛而有謀且有為。據鄉人沙永祥研究,此時的吳國地區農業落后但資源豐富,劉濞一反 “重農抑商”的傳統國策,制定了以“工業”掛帥,推動商業發展,再反哺基礎設施和農業建設的總體方略,使吳國從各諸侯國中迅速脫穎而出。劉濞關注的冶礦業、鹽業、造船業三大支柱產業,正如今天的“實業興國”。與此同時,劉濞在古邗城遺址上大興土木,建設廣陵城。《漢書·地理志》云:“廣陵為吳王濞所都,城周十四里半。”就是廣陵城的四周周長有14.5里 (秦漢時期一里約451.8米)。城墻很高,上糊著紅泥,既牢固又美麗,四面還建備有烽火望樓。城內建筑物頗多,最重要的是章臺宮,又有顯陽殿、宮園等。按照南北朝文人鮑照“車掛轊,人駕肩”的描述,此時的揚州已經從鄉土之地成長為車水馬龍、摩肩接踵的東南都會。劉濞在水上交通建設方面也讓吳國真正實現了“走出去”:疏通并截彎取直邗溝,專門用來運鹽,嚴禁居民日常通行;在寶應以北修建一條既可以運鹽又可以灌溉的黃金水道;開挖運鹽河,即今通揚運河。這些舉措對今天的揚州城依舊影響深遠。
劉濞治下的廣陵城,“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是“兩手抓,兩手都要硬”。 劉濞在廣陵大規模建設“歌堂舞閣之基”。鮑照在《蕪城賦》里歌頌劉濞統治下的廣陵:“當昔全盛之時,車掛轊,人駕肩。廛闬撲地,歌吹沸天。”廣陵城內,吳、蔡、齊、秦各地的音樂匯集,歌唱吹奏之聲喧騰沸天,先秦時期,貴族士人才能享用的音樂走進了揚州尋常百姓家。從司馬遷所說的“其俗類徐”,到“揚州,江、吳大都會,俗喜商賈,不事農”(《新唐書·李襲譽傳》),再到“揚州土地膏沃,有茶、鹽、絲、帛之利。人輕揚,善商賈,鄽里饒富,多高貲之家”(《宋史·地理志》),一切都在水一樣的文化浸潤下生長著。
此時的吳國人,已經不再是勇猛好斗的莽夫,而是變得風流婉約。儒雅之氣在鄉土原野上茂密地生長起來。司馬遷說:“吳之王,由父省也。能薄賦斂,使其眾,以擅山海利。”劉濞在吳國免除農民賦稅,實行官府買役制度,關注窮苦百姓乃是其仁心德政的體現。后世房彥謙評價吳王劉濞:“濞集蚩尤、項籍之驍勇,伊尹、霍光之權勢,李老、孔丘之才智,呂望、孫武之兵術……不應歷運之兆,終無帝主之位。”作為一位善于治國且又多有仁術的王,劉濞治下的吳國形成了一種風氣,這種風氣影響著后人的心性和觀念。
這處遠在大湖之西的神奇土地,這些從鄉土生長出來的精神原料,雖然“在鄉”卻并不“土氣”,相反,它是那么深厚,那么高貴,那么迷人。
(責任編輯:孫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