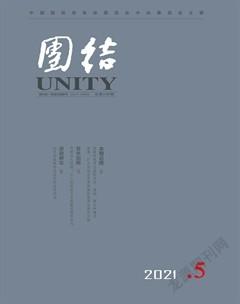風雷洗禮鐵騎: 工人階級經辛亥覺醒后握手馬列
王杰 賓睦新

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中國工人階級的成長過程,與其自身鮮明的特點相依存:它投世于內憂外患,背負著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三重壓迫,生活水深火熱;正是由于其所受的壓迫和剝削無以復加,蘊藏著與生俱來強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斗爭性。他們的抗爭與覺醒運動從無到有,與日俱增;他們的發展壯大和自為的革命運動,成為催生中國共產黨誕生的助產婆。
工人階級的誕生與成長
毛澤東指出:“中國無產階級的發生和發展,不但是伴隨著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發生和發展而來,而且是伴隨著帝國主義在中國直接地經營企業而來。所以,中國無產階級的很大一部分較之中國資產階級的年齡和資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會力量和社會基礎也更廣大些。”{1}工人階級的誕生,是工業革命和機器大生產的產物。鴉片戰爭之前,中國傳統社會以農業為主,輔以手工業和商業,“士農工商”的社會形態比較穩定。鴉片戰爭以降,英國以堅船利炮轟開中國的門戶,列強在侵略蹂躪中國的同時,也帶來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香港、澳門、上海、廣州、天津、廈門、寧波等通商口岸,由西方人創辦的茶廠、繅絲廠、印刷廠、輪船運輸公司、機器修理廠等新式企業,招收了中國最早的產業工人。這些工人大多來自失地農民,以及因受西方商品傾銷而破產的商人和手工業者,他們比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誕生得更早,是列國侵掠的受困人和見證者。
直面西方列強先進“器物”之強勢,林則徐、魏源等開明官員,大聲疾呼“師夷長技以制夷”。隨著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沈葆楨等采用西式槍炮,平定了“太平天國起義”,對西方“器物”的優勝,有了進一步認識。由是,以“自強”“求富”為號,引進西式機器,開辦西式企業,出現了安慶內軍械所(又稱安慶機器局,1862)、上海洋炮局(1862)、金陵機器制造局(1865)、福州船政局、上海機器制造局(又稱江南機器制造總局,1865)、輪船招商局(1873)、天津機器局、開平礦務局(1878)、金陵制造洋火藥局(1881)、津滬電報總局(1889)等官辦或官督商辦洋務企業,一些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民族企業也隨之出現和發展起來。洋務運動的興起,促進了工人數量漸次增加。據估計,甲午戰爭前50多年間,官辦工廠40多家、工人47000多人,民辦工廠100多家、工人34000多人,外國商人在中國開辦的工廠約100余家、工人約34000人,總計有工廠240多家,工人115000余人{2};其中10萬元以上的外資工業企業23家,資本總額763.1萬元,產均資本33.2萬元{3}。
甲午戰后加快了工人數量的增長。1895年,清王朝被迫簽訂《馬關條約》,日本在通商口岸開始投資設廠。歐美列強強行“利益均沾”,外國資本大量涌入中國,開設工廠、修建鐵路和開挖礦產,直接投資經營并掌握管理權的有滇越、中東、膠濟、京漢、京奉、津浦、滬寧、京綏等鐵路。到1913年,外資在中國興建了鐵路10000多公里,大型礦山20多座,加工廠增加到166個。1895年至1913年,10萬元以上的外資工業企業136家,資本總額10315.3萬元,廠均資本75.8萬元。④外資經營的航運業和電氣、自來水、公共交通等市政工業也有較大的擴展。此間,中國民族工業主要是煤鐵開采業和紡織業,商辦工業也逐漸增多。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中國工礦企業的工人計有60多萬,加上海員、鐵路工人共有100多萬。1913年至1920車,在輕工業的23個行業中,新設廠675家。甲午戰后列強加緊對華掠奪,加重了中華民族的苦難,也增加了工人階級的數量,無形中培養了反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力量,為中華民族意識的覺醒埋下伏筆。
一戰期間加速了工人階級的成長。由于英、俄、德、法等歐美列強忙于爭奪殖民地和霸權,暫時放松了對中國的侵略,無形中刺激了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工人階級的數量隨之猛增。1914年至1918年,紡織和面粉業,乘機迅速發展。以棉紡織業為例,一戰前中外紗廠為31家,1914年至1922年紗布廠就有54家,其中1920年至1922年開設了39家。⑤又如發電廠,1912年約33家,1920年增至70多家,發電容量由12000多千瓦增加到29000多千瓦。⑥“據一部分不完全的統計資料以及對沒有統計資料的地區或行業的估算,到1919年前后,全國共有產業工人約261萬人。其分布情況大致如下:鐵路工人16.5萬,郵電工人3萬,海員工人15萬,汽車電車工人3萬,搬運工人30萬,中國工廠工人60萬,外國資本家在華工廠工人23.5萬,礦山工人70萬,建筑工人40萬。”⑦工人大多分布在沿海地區,集中在工商比較發達的大城市。比如,上海工人占全國四分之一,1919年左右上海人口的五分之一是工人。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除武力奪取德國在山東的全部工廠、礦山和鐵路外,還乘機在上海、青島、武漢等地增加工業投資,興建了大批棉紡織廠。從1914~1921年的7年中,在華設立較大的廠礦有223家,這還不包括其在華掠奪的工廠,⑨工人數量由此隨之增加。
長夜難明赤縣天。受困外侮內患,于苦難中成長的工人階級,逐漸磨煉成一支不可忽視的新生力量,奠定了自己的階級基礎。她們也在探求著救國和新生的道路,找尋著救國救民的引路者。
工人階級在苦難中抗爭
苦難孕育了工人階級的抗爭精神。毛澤東指出,中國工人階級生活于社會最底層,“身受三種壓迫,而這些壓迫的嚴重性和殘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見的;因此,他們在革命中,比任何別的階級來得堅決和徹底”{10}。早期工人的反抗方式比較原始,如破壞機器、搶劫庫房、燒毀產品、與雇主吵鬧、向官府告狀等,表現出自發、分散、人數少、規模小、力量弱等特點。隨著工人數量的增加、抗爭閱歷和組織意識的增強,發展至數十人、數百人,乃至數千人的有組織、有計劃的怠工或罷工。早期的罷工斗爭,主要是謀求自身待遇的經濟斗爭。
隨著帝國主義的軍事侵略和經濟掠奪的加劇,工人的民族意識也隨之逐漸覺醒,并自發參與反帝斗爭。據不完全統計,1840年至1904年有工人反帝斗爭30多次,1905年至1913年約70多次,1914年至1919年約120多次,其中1918年就有33次,1919年有67次。僅以罷工為例,自1870年至1911年,計105次,平均每年2~3次;從1912年至1919年5月共罷工130此,平均每年16次,就趨勢而言,逐年增多,至1918年達30次。{11}其中,1918年有日期記載的罷工15次,總計罷工124日,平均每次8日多;1919年有記載的26次罷工,參加的人數達91000人。說明罷工的人數不斷增多,罷工持續的時間也在增加。不言而喻,這是工人階級的集體意識、斗爭方式和斗爭策略都有了明顯的進步,為工人運動奠定了階級基礎。
在辛亥革命期間,有工人開始成為孫中山的追隨者進而成為堅定的支持者。1894年11月,孫中山創立興中會,會員約124名,有工人36人,占總數的29%。{12}次年興中會發動廣州乙未起義,有計千名港澳苦力工人參與籌備。1905年同盟會成立,翌年發動的萍瀏醴起義,“起義者多煤礦工人”,并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13}1911年黃花崗起義,86名殉難烈士,有16名工人,比重最大。
武昌起義爆發,武漢“楚望臺軍械庫工人,就與革命發生聯系,工人群眾替革命機關廉價收買子彈和炸藥”{14}。保衛武漢戰斗激烈,漢陽兵工廠工人為了保障革命軍的軍需供應,“日夜開工趕造備用”,“平時每日造槍六十枝,現加至八十枝,夜工倍之”。{15}為了阻斷北洋軍隊增援武漢,160多名京漢鐵路工人在余大猷的率領下,拆毀鐵路,在東篁店以扳反鉈,使得軍車出軌,支援了武昌起義。武昌首義后,各地工人紛紛以罷工、游行示威、“暴動”等形式,響應辛亥革命。革命軍光復上海之戰,得到江南制造總局工人的響應和支持,攻陷清軍的堅固堡壘。武昌起義消息傳到廣東,廣九筑路工人和部分居留港九、惠州的工人組成瀛字敢死軍1000多人潛伏廣州城郊,待命攻城。{16}11月上旬,錦綸行工人乘著粵省各界紳商團體在文瀾書院集議,打出“廣東獨立”旗幟,高呼“廣東獨立萬歲”口號,并組織20000多民眾前往廣東總督署請愿,要求兩廣總督張鳴岐立即宣布獨立,與清廷脫離關系。11月9日,廣東宣布獨立。此見工人階級在資產積極領導的反清民主革命運動中之一斑。
民國成立前后,以運動工人為目標的團體誕生,象征著工人的社會角色開始受到社會關注,也揭示了工人力量的日益壯大及其在國家政治經濟生活的重要性日漸凸顯。較早意識到勞動和勞動者價值的是無政府主義者。1911年11月4日,江亢虎將上年7月11日創立的“社會主義研究會”改組為“中國社會黨”,在上海設立本部,于南京、蘇州、長沙、天津、香港、東京、馬尼拉等地設有支部,至1913年7月有支部400多個、黨員50多萬人。{17}該黨與革命黨人關系較為密切,宣言:“振興直接生利之事業,獎勵勞動家,勞動者,神圣也。農工各業,生命攸關……個人有分業,無等差。”{18}首次將長期被壓迫受鄙視的“勞動者”,尊崇到至高無上的“神圣”地位。1912年4月21日,中國第一個以工人階級為主體的政黨——中華民國工黨宣告成立(總部是1月7日在上海成立的“中華工黨社”,2月在南京、蕪湖、蘇州等地設立支部),發行《覺民報》為機關刊物。“正領袖”為擔任過東方理匯銀行買辦并在上海擁有多家工廠股份的資本家朱志堯,“副領袖”是徐企文和謝月。宗旨是“改良工業、擴張國貨、開通工人知識、灌輸愛國思想”。經一年發展,支部遍及16省及海外華人聚集區,成員多達40萬人。{19}該黨名為“工黨”,實際上是一個由開明資本家、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工人群眾組成的團體組織,主要領導人無一人是工人。{20}其奉行孫中山民生主義理念,乃是有志于我國工業發展的同盟會外圍組織,它在為工人爭取權益的同時,主張勞資調和、合力振興工界,“于吾國工業前途不無裨益”。1912年6月,中華民國工黨與中國社會黨聯合,宣稱“社會黨員與工業有關系者,同時為工黨黨員;了解并信從社會主義者,同時為社會黨員”,“社會黨或工黨對外交涉,兩黨并力行之”。{21}1913年,工黨作為革命黨的外圍組織,參與了反對袁世凱的斗爭,徐企文因起義失敗被俘犧牲,工黨被查禁,基本宣告解體。這兩個政黨團體,雖然或多或少與工人有一定的關系,在工人群眾中有一定的影響,但沒有明確提出反映工人階級訴求的目標綱領,工人階級屬于從屬和被領導的地位。
俄國十月革命后,中國深受影響,工人斗爭從自發走向自覺,工人階級逐漸理智,工人運動走向高潮,并顯示出強大的威力。據統計,十月革命后的五年多,各地工人舉行的經濟罷工達185次之多,年均34.7次;其中產業工人的罷工114次。此間,顯示出兩個特點:產業工人逐漸成為工人階級的主體和罷工斗爭的骨干力量,在罷工斗爭中的作用發揮重要作用;工人罷工有自發建立的組織領導,提出了明確的要求、條件和目標,斗爭方式更加進步了。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結合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內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外因是馬克思主義傳入,內因既有不屈于專制列強盤剝而激發的救國救民、救亡圖存的歷史使命,也有隨著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工人階級的壯大而萌生反帝反封建的內在需求。
由于辛亥革命不徹底,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并未完成,伴隨引來的軍閥割據和混戰,使得中國人民遭受苦難加深了,中國知識分子開始尋求新的救亡圖存之路。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令先進的知識階層對工人階級有了新的認識,開始由民主主義者向共產主義者轉變,并積極探求與工人階級的結合。
十月革命的鼓舞,加速了社會各階層對勞工階級的重視,有如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增加了催化劑。1918年3月,中國第一本以“勞動”命名的月刊創刊。同年11月15~16日,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慶祝協約國勝利的大會上,發表《黑暗與光明的消長》、《勞工神圣》兩篇演說,強調協約國的勝利,實為世界黑暗與光明的轉折點,“此后的世界,全是勞工的世界”,“我們要自己認識勞工的價值。勞工神圣”!{22}蔡氏的演說,影響廣泛。許德珩回憶:“天安門前‘勞工神圣’的公開演講,是破天荒的得著社會上多少人的景仰和興奮。由先生的這個指示,北大當時的校工夜班工讀互助團、校外的民眾夜校、工人補習學校、平民教育講演等類的社會服務和勞動服務,也都很快地發展起來,使那班浮游于上層政治與埋頭在書本子里面的這兩種青年,都深入到社會的內心,懂得民生的疾苦。”{23}1919年5月1日,北京《晨報》副刊出版勞動節紀念專號,是為中國報刊第一次紀念全世界勞動人民的節日。1920年10月26日,上海《民國日報》發表《“勞工神圣”的意義》,盛贊蔡元培“居然把‘勞工神圣’底標語,深印在覺悟者的腦筋中,將眾人腦筋里深深地藏著的‘勞工神圣’,一聲叫破了出來,于是眾人都被他喊著,就回答一聲‘勞工神圣’。”是年11月21日,孫中山在上海機器工會成立會上演說,稱贊“現在工人為世界中最神圣之人”,俄國革命“其實是工人之革命”,期望工人“努力前進,固結團體,以達能左右上海全體工廠主權,然后引導全國工人起而為民生之運動,由民生運動造成一民生大同之中國”{24}。此外,《民國日報》、《星期評論》等刊物,也發表了大量支持工人愛國運動的言論。
經由十月革命啟示,李大釗較早關注勞工階級的地位和作用。1918年7月,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認為“二十世紀初葉以后之文明,必將起絕大之變動,即萌芽,即茁發于今日俄國革命血潮之中”{25}。年底,即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際,李氏先后撰寫《庶民的勝利》和《Bolshevism的勝利》,指出一戰是“勞工主義的戰勝”、“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的勝利”,中國人應該“準備怎么能適應這個潮流,不可抗拒這個潮流”。1919年元旦,李大釗撰寫《新紀元》,闡釋勞工階級戰勝資產階級:“總同盟罷工,就是他們的武器,全世界勞工階級應該聯合起來。”{26}稍后撰寫《青年與農村》、《現代青年活動的方向》、《唐山煤廠的工人生活——工人不如騾馬》等文章,關注青年群體、知識階層、農民階級、工人階級,強調工農群眾的重要性,號召知識分子與工農階級相結合,提出“只要知識階層加入了勞工團體,那勞工團體就有了光明;只要青年多多的還了農村,那農村的生活就有改進的希望;只要農村生活有了改進的效果,那社會組織就有進步了,那些掠奪農工、欺騙農村的強盜,就該銷聲匿跡了”{27}。
五四運動的爆發,工人階級以獨立姿態登上了政治舞臺。1919年5月4日,“五四運動”爆發,各地學生先后響應,運動推及全國。迫于日本帝國主義的壓力,北洋政府采取了蠻橫鎮壓的措施,破壞街頭講演,拘捕愛國學生,下令各校限期復課。在學生遭受嚴酷鎮壓的關頭,工人階級挺身而出,以空前的政治大罷工投入運動,成為運動的主力軍,把“五四運動”推向新的階段。從6月5日起,一周之內,參加罷工的上海工人就有六七萬人,加上罷工的店員,總人數超過10萬人,“五四運動”的中心從北京轉移到了上海。此后,唐山、長辛店等地工人舉行罷工和游行示威,天津、南京、濟南、漢口、長沙、廣州、九江等地的產業工人和手工業工人先后舉行集會和游行。據統計,先后有20多個省的100多個城市發生了工人罷工。以工人階級為主體的全國各界愛國群眾的廣泛斗爭,給北洋政府以極大的打擊。總統徐世昌向國會提出辭職,國務總理錢能訓引咎辭職,全體內閣一并引退,巴黎和會中國代表拒絕在喪權辱國的和約上簽字。“五四運動”以勝利告終。
“五四運動”展現了中國人民尤其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偉大戰斗力量,它給人民以振奮,而給反動勢力以沉重打擊。毛澤東指出,“五四運動的杰出的歷史意義,在于它帶著為辛亥革命還不曾有的姿態,這就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封建主義”{28}。五四運動是中國新舊民主革命的分水嶺,它標志著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接近尾聲和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此后,中國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就不再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追隨者,而是一個覺悟了的獨立的政治力量,是民主革命的領導者。
五四運動促進了知識分子與工人運動的結合。由李大釗、陳獨秀等共產主義先驅所引導,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不斷聚集,隊伍不斷擴大。他們不斷研究勞工,積極向勞工靠攏,積極向勞工階級宣傳馬克思主義。1920年5月1日,《新青年》出版“勞動節紀念”專號,蔡元培題寫“勞工神圣”,李大釗撰寫《“五一”(May Day)運動史》,介紹五一勞動節的由來和國際勞工斗爭史,希望中國“三五文人的運動”和“紙面上的筆墨運動”發展為“街市上的群眾運動”;陳獨秀在上海船務棧房工界聯合會發表《勞動者底覺悟》的演說,提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貴重”,“盼望做工的人快快覺悟”,實現“勞力者治人,勞心者治于人”;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第一次舉行了勞動節紀念大會。一批以“勞動”為主題的先鋒刊物,如1920年8月15日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創辦的我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工人報《勞動界》、10月3日廣州共產主義小組創辦的《勞動者》、11月7日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創辦的《勞動音》等相繼問世。
隨著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中國共產主義先驅者開始聚攏在一起,陸續創建了一些共產主義地方組織。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和籌備,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誕生。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馬克思主義思想和中國工人運動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由理論走向實踐的發端,從此揭開了中國歷史的新篇章。■
(王杰,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民革中央孫中山研究學會顧問;賓睦新,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博士生/責編 劉玉霞)
注釋:
{1}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7頁。
{2}錢傳水:《中國工人運動簡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頁。
{3}汪敬虞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輯上冊,科學出版社,1957年,第1~2頁。
{4}同上。
{5}嚴中平著:《中國棉紡織史稿》,科學出版社,1955年,第186頁。
⑥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85頁。
{7}劉明逵編:《中國工人階級歷史狀況》第1卷第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5年,第5頁。
⑧同上,第204頁。
⑨錢傳水:《中國工人運動簡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頁。
⑩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44頁。
{11}陳達:《中國勞工問題》,《現代史復印資料》1981年,第15期。
{12}馮自由:《興中會會員人名事跡考》,《革命逸史》第4集,中華書局,1981年,第23~36頁。
{13}鄒永成口述、楊思義筆記:《鄒永成回憶錄》,《近代史資料》1956年,第3期。
{14}李春萱:《辛亥首義紀事本末》,《辛亥首義回憶錄》第2輯,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32頁。
{15}劍農:《武漢革命始末記》,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第5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74頁。
{16}胡漢賢:《廣東“瀛字敢死軍”紀略》,政協廣東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東辛亥革命史料》,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53頁。
{17}黃彥:《中國社會黨述評》,《近代中國》第14輯,上海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第120~164頁。
{18}《張錫鑾檢送中國社會黨章程黨綱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無政府主義和中國社會黨》,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76頁。
{19}王永璽:《中國工會史》,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第47頁。
{20}梁玉魁:《關于中華民國工黨的性質問題》,《歷史研究》1959年,第6期。
{21}《中國社會黨與工黨聯合布告》,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黨派》,檔案出版社,1994年,第58頁。
{22}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464頁 。
{23}德珩:《吊吾師蔡孑民先生》,蔡建國編:《蔡元培先生紀念集》,中華書局,1984年,第61頁。
{24}黃彥編注:《孫中山著作叢書:論農民與工人》,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3~115頁。
{25}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注:《李大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5頁。
{26}同上,第268頁。
{27}同上,第307頁。
{28}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69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