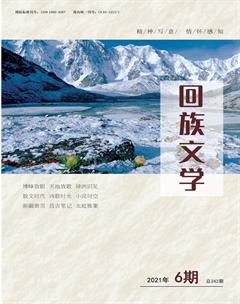連貫性在小說中的價值
徐清松
衡量一部小說優劣的標準,我分為兩個層面:一個是宏觀層面,首先思想性是否深刻,其次藝術性是否獨特,最后是時代性,作者是否準確握住時代最深遠又強勁的脈搏;另外一個是微觀層面,首先是異質性,其次是邏輯性(自洽性),再次是可讀性,最后是故事性。而連貫,則是小說內部邏輯性是否嚴密的一種體現,這也是小說家的一個基本功。
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爾維諾在其文學理論著作《美國講稿》中,將他認為21世紀的文學應該保存的價值,鎖定在輕逸、速度、精確、形象鮮明、內容多樣以及連貫這六大特質上,由于1985年他意外去世,遺留下耐人尋味的連貫。本文試圖對這一文學特質進行初步探索,以慰大師生平之憾。
從本質上講,竊以為連貫就是小說中偶然性、必然性與邏輯性之間的咬合關系,而不是指故事情節的起承轉合。也就是說,偶然性服從于必然性,必然性服從于邏輯性,邏輯性服從于小說的傾向性。
讓我們先來諦視偶然性。從古至今,偶然性在我們的敘事性文學作品中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人物關系的偶然性,一是事件的偶然性。
我并非天生排斥巧合,也并非刻意回避巧合,傳統文學中更是將“無巧不成書”作為深化人物矛盾,凸顯人物性格和命運,改變故事走向的重要手段。甚而言之,偶然性中間或也會包含必然性,反之亦然。既然如此,我為什么對偶然性這么警惕呢?因為偶然性處理不好,容易造成“失真”的閱讀感受和認知感受。對我而言,這種失去藝術真實的感受,是小說創作的大忌。我對偶然性的底線要求是:一、偶然性不能太生硬,不能有拼湊或生造之嫌;二、偶然性不能過多,不能連續;三、一個偶然性的出現,最好能夠將其成因碎片化,融合到必然性里面,灑落在文本之中,不為讀者所察覺。
關于人物關系的偶然性,我舉一個比較典型又人所共知的例子,那就是金庸在《天龍八部》中對段譽這個人物情感際遇巧合的設置。段譽遇到的女子,只要有一方動情,或者雙方動情的,幾乎都走向了“同父異母”的結局,鐘靈、木婉清、王語嫣,無不如此。這種巧合的疊加和雷同,就會產生失真之感。好在金庸在小說結尾來了個釜底抽薪,才從根本上沖淡了這種感受。即在段延慶將要殺死段譽的時候,忽聽得身邊一女子(段譽生母刀白鳳)說道:天龍寺外,菩提樹下,化子邋遢,觀音長發。當段延慶知道欲殺的段譽竟是他親生兒子時,就從根本上稀釋了段譽與三位女子“同父異母”的巧合。而我依然認為,如果僅僅在結尾,金庸以“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反轉來改變故事的走向,促成一個大圓滿,也只是停留在技巧和智力層面。在“草蛇伏線,灰延千里”中,我更看重的是,千里之始的“草蛇”在哪兒伏線。以段譽的出生為例,我們要追溯到小說的前半部分,在聾啞谷的珍瓏棋局之中,段延慶深陷其中,無法自拔,神思恍惚之際,他看到了被打殘的自己在天龍寺外以雙手爬行,在落葉紛飛的菩提樹下,他抬眼望去,發現了一位長發飄逸、身坐蓮花的觀音(即鎮南王段正淳王妃刀白鳳的影子),他伸手過去,喊著,救我,觀音大士!直到小說結尾,金庸才點出為報復丈夫用情不專的刀白鳳與段延慶在菩提樹下茍合,最后生下段譽的事實,從總體上實現了小說人物關系偶然性、必然性與邏輯性之間緊密的咬合關系。
關于事件的偶然性,我想重點表述的是:一個看似巧合的果,必須隱藏著眾多必然性的因,也就是說,因果關系不是直線連接,而是曲線的、隱形的,眾多的因,導致了一個事實上人所共見的果。道教講究的是萬事萬物的先天性和規律性,這就指向了必然性,而必然性的盡頭就會出現一個偶然性,也就是從量的變化,遞增或遞進,所產生的質的變化。我們熟知的人生四大喜事分別為: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久旱逢甘露,他鄉遇故知。后有好事者分別在喜事后面加了兩個字,就秒變成四大悲事,例如“他鄉遇故知——仇敵”。設想一下,兩個在成都市三環外金花鎮一家民房的租住戶,十年以后,他們在北京七環以外相遇,一個送快遞,一個收快遞。相遇的那一刻,倆人立馬扭打在一起。送快遞的叫喊著:“十年前在成都租房的時候,直到你搬走的那一天,我才發現你在房檐下搭了根線接到我的電表上,一直在偷我的電,偷了一年多,你還我電費來。”也許很多讀者關心的是,收快遞的究竟有沒有偷送快遞的電,也就是這個事件的真相究竟怎樣。而我的著眼點在于,作家如何處理在漫長十年的光陰后,倆人在另外一個城市偶遇的巧合性后面的必然性,這是事件得以成立的根基所在。這種三言兩語難以說清楚的偶然性,作家不必馬上給予解釋,有時候這種迫切的解釋在邏輯性面前顯得窘迫,顯得敷衍,從而流于牽強,反而有損藝術真實。但是在整個小說文本之中,它必須服從于自足的自洽性,而我想要的辦法就是,能夠將其成因碎片化,融合到必然性里面,灑落在文本之中,不為讀者所察覺。有一種說法是這樣的,小說家是上帝,是皇帝,在小說中,對他筆下的人物擁有生殺予奪的權力。小說是小說家創造的,這沒有錯誤,但是從辯證的角度來看,小說家更是小說本身創造的。經典小說更是一個龐大的藝術王國,人物按照自身命運各司其事,事件按照自身規律發展或迂回。譬如《紅樓夢》,譬如《百年孤獨》。小說家在小說中是上帝的說法,我以小人之心揣度:不過是小說家本人在現實中“失之東隅”,意圖通過小說“收之桑榆”,換言之,小說家為擺脫現實生活中的無力感和挫敗感,通過小說建立起一種虛妄的征服感和成就感,從而換取某種心理平衡。我想表達的是,小說就是小說本身,不應該成為一種政治工具,也不應該成為一種名利工具,同樣,也不應該成為一種作家泄私憤的工具。小說一旦演變成工具,則從根本上表示作家骨子里對這個體裁的輕慢。卡爾維諾在《美國講稿》中要求作者,在觀察人物時“把自己當成一個窮人,一個卑微的奴隸,畢恭畢敬地去觀看他們,觀察他們,并為他們的千種需求服務,就好像自己是親臨其境”。在觀察人物和表現人物這個單項上,此處的觀點和我不謀而合,我想要的作者視點是,“眼睛低到塵埃里,貼地而行”地觀察并表現小說中的所有人物。只有這樣,才能夠呈現常人所不經意間忽略的東西。
再來諦視必然性。從宏觀上來講,必然性和偶然性是一個矛盾統一體,在一定條件下,二者互相蘊含,互相轉化,但是從總體上來講,必然性必然遠遠大于偶然性,只有這樣,對文本而言,才具備強大的說服力和藝術真實性。我們是一個講求宏大敘事和故事傳奇性的國度,那么,作家如何昭示并把握小說人物的命運感就顯得尤為重要。這種命運感遞接的是不同人物的性格,在面對各種環境、沖突、矛盾時,對人物表現的深度開掘和刻畫。(借此,也在讀者的感知與認知中,形成了鮮明的人物形象)而小說中的人物性格(包含人物形象)得以成立的原因,遞接的是真實可信的細節,譬如孔乙己是“站著喝酒而穿長衫的唯一的人”,譬如《故鄉》中的楊二嫂,魯迅描述為“正像一個畫圖儀器里細腳伶仃的圓規”。于我而言,小說中最不能忍受的就是細節失真,這會瞬間敗壞閱讀的胃口,而我創作之時,最焦慮的也是細節問題。小說本質上是考驗作者的想象力,從細節的真實抵達文本的虛構這一建構過程。因此,從細節到人物性格、人物形象,再到人物命運感,這種環環相扣的食物鏈之間,其看不見的脈絡所在,就是必然性。
必然性考量的是小說家在行文中的內驅力,這種力量貫穿文本的始終,宛若一股真氣,在細節之間、人物之間、事件之間游走,在故事的起承轉合之間細若游絲,卻又堅韌不斷。
如果要找出一種常見的,既是必然性,又是偶然性的交點事件,竊以為只有死亡。死亡當然是必然性的,既充滿無限神秘,又呈現無限可怖。但是無論對于生活的真實還是藝術的真實,它又隱匿著偶然性的一面。在萬事萬物的蔭翳之處,裸裎著眾多的暗物質,它們在時空的黑洞中閃著幽光,也在性質的淵藪里晃動著身影。而這些暗物質(定數)到死亡的偶然性(變數)之間,就形成了一個拋物線(常數),不為人知,卻又充滿制約性。關于死亡,這世界永恒的命題,我想,主要包含兩個方面,一是生物的消亡,或有形的個體的散佚;二是事件的終結,或意義的消失或者凝結。萬事萬物本沒有意義,如果有意義,也不過是人這自我所賦予的。同樣,一部小說的意義也是小說家賦予的,小說家本人應該有能力摧毀一部小說的意義。那么,這種摧毀力一般在小說的結尾出現。蕭天佑翻譯的《美國講稿》(2012年4月第1版)第六章“開頭與結尾”第137頁中,卡爾維諾這樣寫道:
各種小說結尾中堪稱最重要結尾的,要算那種最后懷疑整個故事、懷疑小說的價值觀念的結尾,如《情感教育》的結尾。福樓拜用四百頁的篇幅幾乎“同步”描述了弗里德里克·毛漏青年時代的愛情、巴黎的生活和當時的革命情形。小說的結尾,弗里德里克和一位老朋友談起自己年輕時的一樁愚蠢而荒唐的往事:下妓院,但他那膽怯的性格壓倒了他那強烈而輕率的欲望,使其慌忙逃離那里。“那是我們經歷中的精華!”弗里德里克說道。“對,也許真是這樣。那是我們經歷中的精華!”德斯勞里埃說道。這種結尾回顧整個小說,回顧那些充滿情感、事件、等待與期望、猶豫和沖突的日子,最后這一切都化成了灰燼。
對小說意義的摧毀并非否定小說本身的價值,小說的建構過程本身就已經成就了小說的價值,而這種摧毀會讓文本回歸到人性的共性層面,或者將文本的指向升華到哲學層面,使之更加豐盈、深邃和廣博。
人物的死亡在小說中是一個比較復雜的現象,尤其是對于追求有難度寫作的小說家而言。于我而言,首先要排除一種人物死亡方式,那就是當人物之間的矛盾、沖突解決不了的時候,當小說中的人物活不下去或無法處理自我與他者的關系時,小說家窮途末路、難以為繼,只能安排人物自殺或“意外死亡”,從而繞過了原本的寫作難度,回避了某種藝術真實,這種設置容易減輕文本的分量,從而讓小說本身流于淺薄;其次是人物死亡的原因越無法確定,可闡釋的空間越大,文本的價值也就越大,這種死亡方式對于小說本身只是個誘因,或者說是小說得以生成的“入筆”;最后是小說家不必明確給出的死亡,也就是讀者通過文本自己得出的人物已經死亡的結論,這一點不會影響小說的價值和表達,多半就是營造一種氛圍,深化或升華小說的底蘊。我們來看《孔乙己》的結尾:
自此以后,又長久沒有看見孔乙己。到了年關,掌柜取下粉板說,“孔乙己還欠十九個錢呢!”到第二年的端午,又說“孔乙己還欠十九個錢呢!”到中秋可是沒有說,再到年關也沒有看見他。
我到現在終于沒有見——大約孔乙己的確死了。
如果說必然性是小說的脈絡所在,邏輯性則是小說的筋力所在。重視邏輯性并不代表我輕視反邏輯的小說,甚至反邏輯的小說更能以鮮明的形象來表達深刻的內涵。因此,我決定將小說的傾向性與邏輯性放在一起來探討。我想,經典小說在思想傾向上,應該具備多義性的特質,這種特質在邏輯嚴密的基礎上,其立意具有兩種以上可能,充滿指向上的不確定性,閱讀經驗豐富的讀者可以感知,卻無從把握。而明顯反邏輯的經典小說,它在思想傾向上,應該能夠揭示一種人類所擁有的共性,并為這具有普世價值的共性貢獻一個鮮明的藝術形象。卡夫卡在《變形記》中一開始就違反邏輯性,為我們貢獻了一個變成大得嚇人的甲殼蟲格里高爾的藝術形象。然而,在接下來的整篇敘事中,作者又嚴格按照甲殼蟲生活習性的邏輯進行了敘述:
頭幾次試站時,他都從光滑的柜子上滑落下來,最后,他用力往上一挺,終于站起來了;盡管下半身痛得死去活來,他也根本顧不得了。他重重地靠到就近一張椅子的椅背上,用他的細腿緊緊抓住它的邊緣,以此控制住了自己的身體。
盡管如此,我們也無法確定這部小說究竟是一部反邏輯的小說還是一部邏輯性嚴密的小說,應該說這是一部兩者高度統一、高度契合的小說。它們共同被“異化與自我異化”以及“親情被物化”這兩個思想傾向所牽制。無獨有偶,卡爾維諾的《被分成兩半的子爵》也是一部反邏輯與嚴密邏輯性完美結合的小說。在戰場上被炮彈炸飛半邊身子的子爵梅達爾多在被送回故鄉之前,有這樣一段文字既不符合生活真實的邏輯,也不符合藝術真實的邏輯,但是符合小說思想傾向和表現主義的邏輯:
結果是第二天早上,我舅舅(即主人公梅達爾多子爵)睜開了那唯一的眼睛,張開了那半張嘴,翕動了那一個鼻孔,又呼吸起來。泰拉爾巴(主人公故鄉)人特有的強健體質使他終于挺過來了。現在他活著,是個半身人。
一個人在戰場上被炮彈炸飛半邊身子,“右半身保留得很完整,連一絲傷痕也沒有,只有與左半身分割的一條巨大裂口”。這種描述無疑是一種天方夜譚,更匪夷所思的,是這兩個半身在小說中全部復活了,一個行善,一個作惡,在主人公的故鄉各行其是。行善的右半身接受身體的殘缺(可泛指人、事、物的不完美);作惡的左半身將所有物體劈為兩半,如樹上的梨,綠葉掩藏著的甜瓜,都只剩下半個,這種由于自身的殘缺繼而仇視完滿的事物,使之殘缺,具有恒定的意味,也具備普世價值。兩個半身傳遞的是人性與獸性的此消彼長,其作品思想傾向表面上是人性善惡的二元對立或融合,本質上則指向人性的分裂,這種分裂就在日常生活中,就在你的身上,也在我的身上。
在我眼里,《被分成兩半的子爵》和《變形記》一樣偉大,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同樣,卡爾維諾和卡夫卡、博爾赫斯一樣偉大,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卡爾維諾的小說絲毫不比后兩者的作品遜色,更為重要的是,卡爾維諾還有兩部非常專業和雄辯的文學理論著作,即《美國講稿》《為什么讀經典》。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的國度對卡爾維諾忽視得太厲害,他的價值和對文學的貢獻遠遠沒有被我們關注,更沒有被專業人士充分發掘,這也是我一個業余作者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試圖對連貫性這一文學特質進行初步探索,并論述它在小說中的價值的根本原因所在。
[欄目編輯:韓愛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