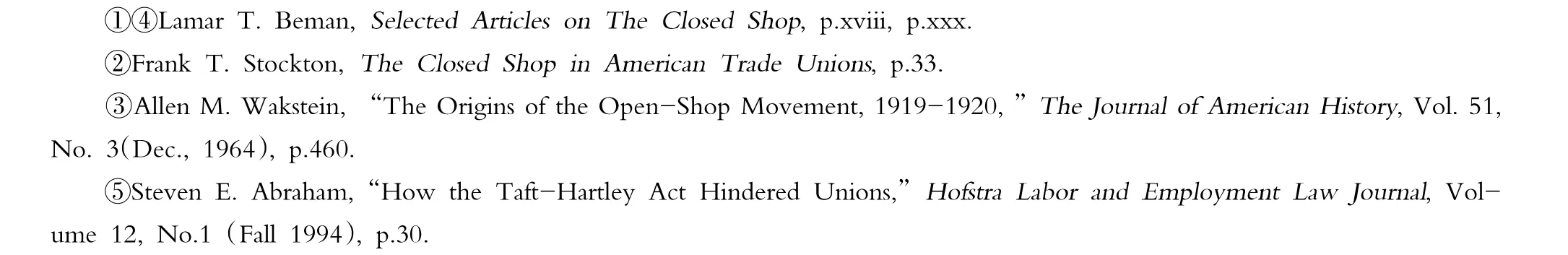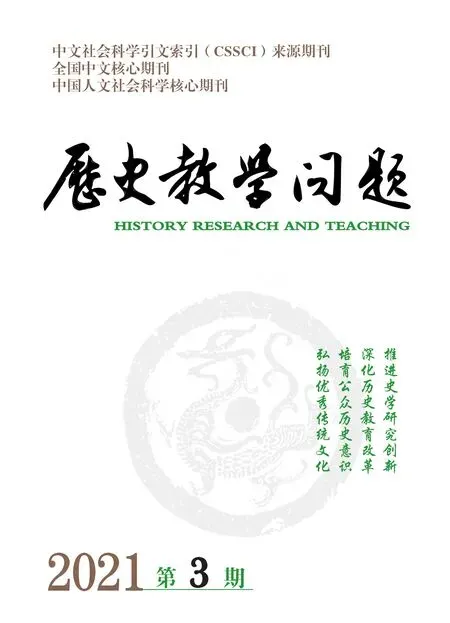美國探索調解勞資關系的曲折之路(1890—1935)
周 余 祥
面對1890—1935 年美國急劇的社會變革,在事關社會和諧穩定的勞資關系問題上,美國勞方、資方和政府站在各自不同的利益立場上開啟了構建緩和勞資關系的探索之路。這一時期工會開展的關閉工廠(Closed Shop)運動與企業主開展的開放工廠(Open Shop)運動針鋒相對,呼喚美國聯邦政府在勞資關系問題上有所作為。因此,美國聯邦政府開啟了從勞工禁令到集體協商的管制勞資關系之路。國內學者在研究美國工人運動時對此進行了相關探討。[1]國外學者的研究比較深入,但對其實踐和成效情況我們仍有探索的空間,勞動關系學者主要探究了對工會抵制的開放工廠。[2]因此,本文擬系統地研究1890—1935 年美國勞資政三方探索緩和勞資關系的曲折之路,以期從制度主義的視角客觀地認知美國構建緩和勞資關系的發展史,明晰政府探究勞資雙方都認同準則的艱難抉擇,評析勞方、資方和政府在構建緩和勞資關系中的客觀作用。

一、關閉工廠:美國勞方訴求工會安全之路
不同的美國行業群體對于關閉工廠的理解不盡相同。在木工、電工和機械工行業工會,關閉工廠的概念是:“雇主只雇傭工會會員,部分的是基于工會系統內部本身訓練和供應勞工。”雇主或承包商同意僅雇傭工會會員的原因是:“利用工會招聘走廊雇傭一定數量的訓練有素的木工或電工。”[1]因此,在木工、電工和機械工行業實行關閉工廠,這實際上得到了雇主的擁護和支持。但有的雇主對關閉工廠是持否定和反對的態度,他們認為:關閉工廠是“支持簽署關閉工廠的工會特定成員的壟斷者,”“不是一個‘真正的壟斷者’,而是一個人為和武斷的壟斷者,因為‘在關閉工廠序列之外有大量尋求就業的勞工,’因為它只能通過防止來自本源市場并與雇主相關需求相聯系的潛在供應……這種防止方式只能通過一種方式且唯一的一種方式——通過武力或脅迫的方式讓外界的勞工不接受就業或讓雇主不接受勞工的服務。”[2]學者普朗克·斯托克頓(Prank T.Stockton)認為,關閉工廠是“一家與雇主簽訂正式協議專門雇傭工會會員的工廠。”[3]美國勞工法的著名立法者之一唐納德·里奇伯格(Donald R. Richberg)卻站在明顯偏袒企業主利益的立場,他認為:工會關閉工廠是企圖“剝奪人的‘生活’基本要素(謀生的收入)、‘自由’的基本要素(自由地在工廠工作)以及‘財產’的基本要素(出售自身勞動力的能力)。”[4]通常來說,關閉工廠是指勞工工會為了維護勞工的群體利益而要求雇主僅雇傭勞工工會會員。具體來說,關閉工廠是工會安全條款的一種,要求“企業承諾只雇傭和保留其雇傭的工會勞工。”關閉工廠實際上是“通過工會招聘或者要求所有的新勞工須在就業時成為工會會員。”[5]美國的全國性工會沒有一個是在1850 年以前成立的,即使在1880 年結束時,也只有12 個工會,或占美國現有國家或國際組織的七分之一。[6]因此,關閉工廠是處于弱勢的勞工群體為維護自身的群體權益而壯大勞工工會力量的必然應對舉措,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在構建緩和勞資關系的過程中均衡勞資雙方的力量,最終促進勞資雙方開展集體談判。
但自1905 年以來,許多人反對“工會會員使用‘關閉工廠’一詞來表示不包括非工會會員的工廠。”他們聲稱正確的用語是“工會工廠(Union Shop)”。他們堅持認為:工會工廠是“永遠都不是關閉的。”[7]這說明,關于關閉工廠的內涵和定義是一直處于變動之中。實際上,19 世紀上半葉,開放工廠是指“接受工會成員的工作場所,”然而關閉工廠是指“不接受工會成員的場所。”美國內戰之后,美國工會認為:“他們更有能力堅決主張雇主拒絕雇傭非工會會員,”他們將這種職位描述為“關閉工廠。”雇主面對工會倡導的這種新概念,雇主將“雇傭非工會會員稱之為‘開放工廠’”。[8]這也從側面反映出這次關閉工廠運動的曲折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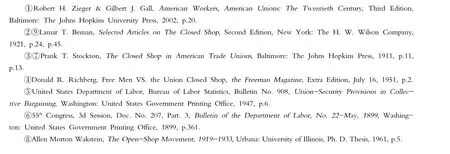
關閉工廠的理念是“勞工階級的福利與集體協商的手段密切相關,有效的成功取決于普遍的應用,而不是個體勞工承認與勞工階級福利不一致的權力。”[9]因此,勞工通過罷工等方式訴求關閉工廠協議的普遍應用,關閉工廠的影響變得越來越強烈。19世紀60 年代末以來,關閉工廠“在工會政策中的重要性與日俱增。”例如,1868—1873 年,有熟練的鞋匠組成的圣克里斯騎士團(Knights of Saint Crispin)組織了反對雇傭非工會成員的8 次罷工。從1880 年開始,關閉工廠成為了“工會的標簽。”[1]因1884—1885 年的經濟危機,美國出現了全國范圍內的罷工浪潮。1886 年勞工罷工次數驟增至1572 次,比1885 年多877 次。1886 年61.0024 萬名勞工參與罷工,比1885 年增加了35.1895 萬名勞工。為了爭取每天8 小時工作制,1886 年美國勞工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罷工運動。這一年的秣市騷亂事件(Haymarket Riot)以及鐵路勞工罷工的嚴重性直接導致了國會主動介入調查。[2]這一方面說明,當勞資矛盾糾紛激化至威脅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穩定之際,美國聯邦政府不會自由放任,而是積極地調解和干預勞資關系。另一方面說明,自1886 年以來,美國勞資關系整體的態勢呈現漸趨緊張。桑德福·雅各比(Sanford M. Jacoby)也認為:“1886—1889 這一時期是美國勞工騷動的時期。”[3]
隨著1898 年美西戰爭的爆發,美國商品市場進入了巨大的繁榮時期,而關閉工廠也由此進入了一個新時代,勞工力量也隨之壯大起來。例如,美國勞工聯合會會員人數的增長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從1897 年到1904 年,其會員人數從25 萬多名增加到160 萬多名。[4]因美國勞動力市場的巨大需求,勞工工會開始在“工時、工資和工作條件”方面尋求更大的要求。這時勞工尋求“認可勞工工會和工會規則”的罷工持續地增加。1899 年勞工的罷工次數是1898 年的2 倍,1901 年勞工的罷工次數是1898 年的5 倍。1901 年36.4%的勞工罷工是由勞工工會領導的。所有工會開始要求企業主簽署關閉工廠協議。[5]而一些工會此時已經實施了關閉工廠運動。某些工會要求企業主和其簽署的一份合同中規定:“在企業主同意雇傭單個勞工之前,這個勞工必須屬于工會”。[6]勞工工會力量是否壯大與美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程度密切相關,更與美國聯邦政府的支持和認可密不可分。美國勞工工會會員在20 世紀20 年代美國柯立芝繁榮期間最高峰值是1920 年的500 萬名,而在1933 年減少至300 萬名。但1935 年《瓦格納法》頒布實施之后,美國勞工工會會員人數驟增,1940 年增長至720 萬名,1945 年是1320 萬名,1950年是1480 萬名。[7]
面對資方開展的開放工廠運動,美國勞工工會反應各異。美國勞工聯合會反對這一運動,該聯合會主席塞繆爾·龔博斯(Samuel Gompers)認為:開放工廠主張工會勞工放棄“拒絕與非工會勞工一起工作的基本權利”,放棄這種權利意味著“奴隸化”,“是將大部分熟練和擁有技能的美國勞工奴隸化”。[8]但美國鐵路行業四大工會卻表示支持該運動,他們是火車司機兄弟會(The Brother of Locomotive Engineers)、火車消防員和機械師兄弟會(The Brotherhood of Locomotive Firemen and Enginemen)、鐵路乘務員兄弟會(The Brotherhood of Railway Trainmen)、鐵路售票員兄弟會(The Brotherhood of Railway Conductors)。[9]美國煤礦勞工聯合會主席約翰·劉易斯(John Lewis)支持關閉工廠運動,他1913 年在鋼鐵企業努力實施關閉工廠。但當大蕭條來臨時,他取消了關閉工廠運動。[10]許多工會不贊成關閉工廠協議。他們更喜歡所謂的“優惠工廠”(Preferential Shop)協議,該協議“使得工會會員在雇傭中優于非工會會員,但當勞工工會不能提供合適的勞工時,雇主有權自由地雇傭非工會會員。”[11]

除了推行關閉工廠運動之外,勞工工會也積極地多方籌措罷工基金(Strike Funds)或者防衛基金(Defense Funds)以保障其領導的勞工罷工。不同工會不同身份的會員在罷工期間獲得的罷工津貼是不一致的。例如,鍋爐制造勞工和泥水匠每周的罷工津貼是10 美元。熟練的模具勞工每周的罷工津貼是9.6 美元,但其中需扣除會費75 美分;非熟練模具勞工每周的罷工津貼是5.35 美元,但其中需扣除會費35 美分。已婚的石油勞工每周的罷工津貼是10 美元,單身的石油勞工每周的罷工津貼是5 美元。[1]這既進一步保證了勞工工會組織的罷工,又刺激了企業主推進開放工廠運動的決心和動力。
勞工工會的罷工在1890-1935 年此起彼伏,波動巨大。勞工罷工次數分別為:1890 年1897 次,1891 年1786 次,1892 年1359 次,1893 年1375 次,1894 年1404 次,1895 年1255 次,1896 年勞工罷工次數驟減至1066 次,1897 年1110 次,1898 年1098次。但自1899 年之后勞工罷工次數開始增加至1838 次,1901 年勞工罷工次數甚至高達3012 次,1904 年又驟減至2419 次,1917 年開始驟增至4450次,進入到20 世紀20 年代“柯立芝繁榮時期”,勞工工會的罷工次數驟減,在1927-1929 年期間罷工次數都低于1000 次,最低是1928 年604 次。這一時期比1920-1921 年和1893-1898 年的經濟蕭條時期勞工罷工次數都少。隨著1929-1933 年的經濟危機,1933 年又驟增至1695 次,1934 年1856 次,1935年2014 次。[2]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經濟社會是否繁榮是影響勞工工會罷工次數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我們除了認識到開放工廠運動的蓬勃發展可以遏制勞工的罷工次數,還不應忽視19 世紀90 年代和20世紀20 年代美國經濟繁榮的因素。實際上,這一時期勞資雙方都有勞資合作的意愿,這與勞工工會對資方企業的看法密切相關。例如,1923 年,鐵路工會針對衰落鐵路系統的國有化而提出了普拉姆計劃(Plumb Plan),這被印證為“勞資合作是可行的和互惠互利”。[3]這一計劃不僅帶來了企業主思考這場探索緩和勞資關系的方式和方法,而且促使資本主義國家政權反思緩和勞資關系的構建與勞資合作的關系問題。
二、開放工廠:美國資方追求自由雇傭之路
美國資方追求自由雇傭之路的指導思想是企業主給予所有勞工平等的工作權利,保障勞工自由選擇的權利。正如學者洛伊斯·麥克唐納(Lois Macdonald)所說:“企業主可以雇傭所有申請職位的任何勞工,而不考慮他們的工會隸屬身份或非工會身份”,倡導“美國人有按照自己意愿選擇工作時間和地點的權利”。[4]這實際上是企業主“處理勞工作為個體,避免實際上或隱性上干預勞工們的個人事務,將勞工們與工會是否有聯系作為他們個人的事務。”[5]這種處理方式一定程度上說明:一方面,企業主忽視勞工工會力量的存在,實際上不承認勞工工會的權力。另一方面,企業主追求的是一種自由雇傭制度,不因勞工的身份差異而有所區別對待,企業主呼喚不受任何干擾的自由經營管理的開放工廠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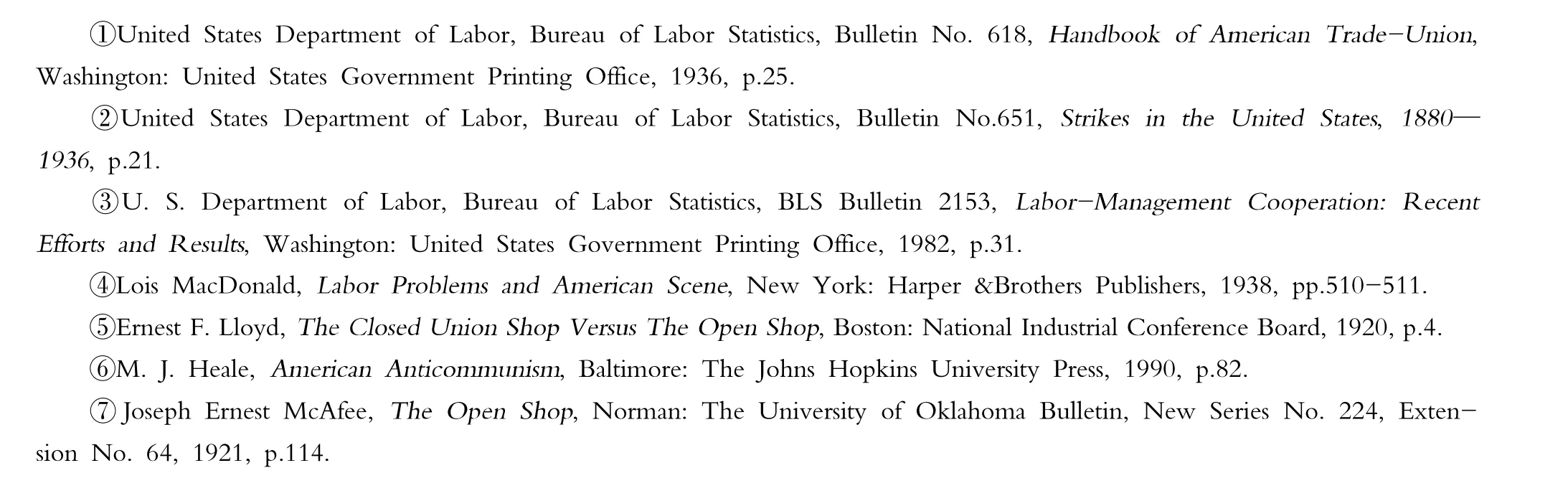
美國全國制造商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s,NAM)的一名會員曾堅決地認為:“你幾乎無法想象出一個比關閉工廠更非美國化、更反美的機構。”[6]這為資方追求自由雇傭之路找到了突破口。企業主以反對關閉工廠為名,號召維護“神圣的個人自由”,注重獨立的個體勞工,實行與關閉工廠運動截然對立的一場開放工廠運動。美國天主教福利理事會(National Catholic Welfare Council)認為:開放工廠運動的實際目的是:“破壞所有的活躍的勞工工會,以便勞工完全被企業主支配。”[7]我們可引用1902 年羅斯福總統任命的無煙煤礦罷工委員會(Anthracite Coal Strike Commission)的觀點來進一步認知開放工廠:“沒有人被拒絕雇傭,或者以任何方式歧視工會會員或非工會會員勞工,工會會員勞工將不會有歧視或者干涉非工會會員勞工。”[1]具體來說,開放工廠就是指:“企業主無差別地對待工會和非工會會員的勞工,并且企業主與工會沒有簽署專門的集體協議。”[2]筆者認為開放工廠運動實際上是美國資方以維護美國的自由為旗號,追求自由雇傭勞工,否認勞工工會的力量存在,遏制美國勞工隊伍的壯大,維持在勞資關系建構中的主導權。
開放工廠后來也叫“美國計劃(American Plan)”,這是因為企業主相信:勞工應該遵循美國的價值傳統——“粗獷的個人主義”,而不是通過工會進行勞資談判的“國外的、顛覆性的、腐化的”原則。[3]“美國計劃”這個稱謂1919 年3 月開始出現,也是為了適應當時的大環境:“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反對外國人和反對歐洲的激進主義思想。”1921年22 個州制造商協會在芝加哥會議上正式推出了“美國計劃”這一稱謂和口號。[4]企業主們使用美國計劃稱呼開放工廠的目的是“強調工會主義的國外性質。”[5]1922 年3 月25 日,美國印刷行業企業主協會的公告確認:“美國計劃”意味著集體談判的終結。[6]企業主們宣稱該計劃將給予“所有人平等的權利,沒有任何人享有特權”。[7]這實際上制定了開放工廠運動的宗旨,呼應了企業主追求自由雇傭的指導思想。
企業主實施開放工廠運動的具體措施:一是在企業內部企業主主導成立了公司工會,二是在企業外部企業主成立了企業主聯盟。企業主成立公司工會是以更加直接的方式對抗激進的勞工工會。公司工會的發展歷程與勞資關系狀況密切相關,當勞資關系和諧時,公司工會相對較少;反之亦然。根據全國工業協商委員會(National Industrial Conference Board)的統計:在騷動的1919—1924 年490 家企業建立了公司工會計劃。在平靜的1924—1928 年,僅有73 家公司建立了公司工會。[8]20 世紀20 年代,為了消除個體雇主之間的競爭,加利福尼亞和亞利桑那州“建立了勞動力交流所(Labor Exchanges)”或“勞務局(Labor Bureaus),通過標準化的工資率貫穿于整個谷物地區,并且吸收需要的勞動力。”[9]這實際上是一種變異的公司工會操作機制。1915 年,“洛克菲勒工業代表計劃”在煤礦領域得以實施,并且一年之后在科羅拉多燃料和鋼鐵公司的鋼鐵領域得以實施。一戰之后,美國實行企業主代表計劃的公司情況:1919 年是145 家,1922 年是385 家,1924年是421 家,1926 年是432 家,但在1928 年是399家。公司工會覆蓋的勞工會員人數情況:1919 年是40.3765 萬名,1922 年是69 萬名,1924 年是124.0704 萬名,1926 年是136.9078 萬名, 1927 年是154.7766 萬名。[10]我們由此可以得知:1919—1927年實施公司工會的企業數量總體上呈現增長趨勢,公司工會會員人數呈現遞增趨勢。這進一步說明開放工廠運動在這一時期迅速發展。

全國制造商協會是最著名的企業主聯盟的典型代表。全國制造商協會“強烈地反對工會主義并且極力地支持‘開放工廠’改革運動以便取締工會在工廠中的影響。”[11]全國制造商協會的標語和戰斗口號直接是“開放工廠”,其保障勞工工作權利而忽視勞工工會。[1]全國制造商協會主席戴維·帕里(David M.Parry)于1903 年4 月在國家制造商協會年會上做主席演說中抨擊工會勞工,這使得許多資方代表增加了對激進工會的敵對。例如,西部煤礦勞工聯合會。他進一步指出:“工會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不同僅僅是方法不同,工會主義依靠的方法是武力,社會主義依靠的方法是投票權以制定社會秩序,但社會主義拒絕承認‘個人和財產權利’。”他堅決地指出:“工會的最終目標將導致‘專制、暴行和奴役’以及‘毀滅文明’。”他強調:“‘自由’、‘公正’和‘進步’在于堅持舊的解放經濟自由的系統。”[2]
企業主推動開放工廠運動實踐的效果在美國各地迥異,但其確實產生了實際影響。一方面,開放工廠運動確實造成了勞工工會會員的減少,這直接打擊了勞工工會的迅猛發展,另一方面,其導致了公司工會的蓬勃發展,這使得企業主在勞資力量對比中占據了優勢地位。正如美國學者戴維·蒙哥馬利(David Montgomery)所說:“開放工廠的能動性實際上能夠在每一個城市的土地上猛擊工會的趨勢”。[3]
但這一運動實際上是不承認勞工工會的存在,更忽視了集體談判在構建緩和勞資關系中的作用。正如梅爾文·杜波夫斯基(Melvyn Dubofsky)和福斯特·瑞亞·杜勒斯(Foster Rhea Dulles)所說:“個人自由確實具有吸引力,但卻勉強地掩飾了企業主竭力推進的反對承認勞工工會和勞資集體協商。”[4]因此,開放工廠運動在一些行業的實踐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促使企業主放棄了該運動,并實行新的勞資政策。美國煤礦勞工聯合會主席約翰·劉易斯指出:“那些長期以來傾向開放工廠的城市中,他們的商會不再宣傳他們有低工資率。”[5]開放工廠運動的開展在潛移默化中逐漸地改變了企業主的觀點,使得企業主逐漸地接受了勞工工會。企業主關于勞工工會認識的轉變說明美國企業主調控勞資關系理念的變化,這一方面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緩和勞資關系,另一方面也為勞資雙方大規模的集體談判奠定了基礎,這在一定程度上開啟了美國勞資關系的新時代。
三、美國聯邦政府抉擇緩和勞資關系之路
在資本主義國家政權發展的早期,美國聯邦政府很少關注勞工領域。直到1884 年,經過勞工團體13 年的游說活動,美國國會同意在內政部內設立勞工局(Bureau of Labor)。該局的職責是“收集關于勞工工資和工時的數據,以及關于‘提升勞工物質、社會、智力和道德繁榮’的信息。”四年之后,即1888年,美國國會將其名字改為勞工部,成為“非內閣級別的獨立機構。”這是美國聯邦政府在勞資關系問題上開始有所作為。在西奧多·羅斯福總統的支持下,美國國會同意成立商業和勞工部。[6]至此,美國聯邦政府有內閣級的行政部門專門負責勞資關系問題。
面對勞資各方推動的關閉工廠運動和開放工廠運動,美國資本主義國家政權卻認為:應該引導勞資雙方在法律框架之內探索建立緩和勞資關系的標準。美國勞工部認為:“標準能夠被建立以及通過將勞方和資方引導到一個合作組織的方式來改善勞資關系。”[7]大多數進步主義的改革者“并沒有想象一個字面上沒有階級差異的社會,而是階級差異在社會中的重要性逐步地降低,并且不是政治動員的基礎。”[8]這直接影響了美國聯邦政府管制勞資關系的策略。美國國會頒布的1890 年《謝爾曼法》(Sherman Act)規定:“任何限制州際間或與外國之間的貿易或商業的契約,以托拉斯形式或其它形式的聯合,或共謀,都是非法的。”[1]該法雖然是反托拉斯法,但被當時美國聯邦法院解釋為在勞資關系領域內偏袒企業主的法律依據。自此之后,美國法院實際上開啟了通過頒布勞工禁令(Labor Injunction)來干預勞資糾紛之路,以便勞資矛盾糾紛不會背離資本主義國家的調控機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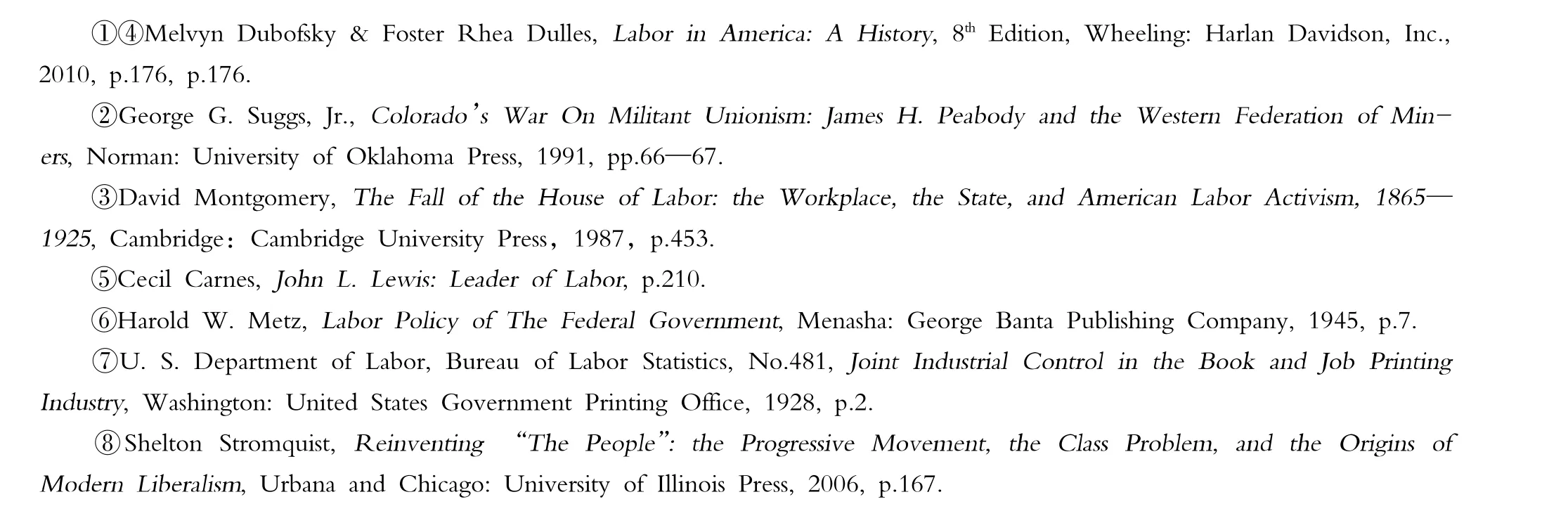
美國長期反工會的司法觀點是“非法聯合或陰謀論。”1806 年費城的法官以極端的形式陳述出來,他將制鞋勞工定為有罪,宣稱:“勞工提高工資的聯合可以從雙重角度來考慮,一方面是有利于勞工自身,另一方面是傷害那些不加入這種群體的勞工。法律的規則譴責這兩方面。”在19 世紀中葉,法院采用的觀點是:“勞工工會本質上不是非法的聯合,但勞工工會試圖達到非法的目的或利用非法的手段是非法的。”[2]
1894 年普爾曼鐵路勞工罷工期間,1894 年7 月2 日,聯邦法院頒布了一項禁令,“禁止美國鐵路工會的主要領導者,包括德布斯·尤金斯,在一些事情中‘通過強迫、或者威脅、恐嚇、勸說或暴力強迫鐵路勞工拒絕履行他們的職責’。”[3]自此之后,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牢固地建立了發布禁令的權力”以及“法院固有的懲罰他們違法的權力。”[4]自德布斯案以來,聯邦和州法庭不斷地增加使用禁令。在1922 年,聯邦勞工禁令被運用于300 多次的鐵路勞工罷工中。自1914 年以來,紐約州地方法院頒布了800 多次勞工禁令。[5]根據保守估計,在1880—1930 年間,法院至少頒布了4300 次禁令。[6]
雖然《謝爾曼法》已經適用于勞資糾紛,然而勞工問題依然嚴峻。因此,美國國會又通過了1914年《克萊頓法》(Clayton Act)。該法規定:“人的勞動‘不是商品或者貿易物品’。”該法實際上是“試圖規范禁令的發布,解釋法院權力和國會意圖之間的界限。”[7]黃狗合同(Yellow Dog Contract)是雇主反對勞工組織工會的一個具體措施。黃狗合同實際上是“勞工作為就業條件作出的承諾,在其就業期間不屬于工會;或不從事某些特定活動,如集體談判或罷工,沒有這些屬于工會的基本權利,勞工加入工會就完全沒有意義。”根據《反托拉斯法》,聯邦最高法院在1917 年希爾曼煤焦公司訴米切爾案(Hitchman Coal & Coke Co. v. Mitchell)中做出支持勞工禁令的判決以來,聯邦法院和一些地方司法機構授予雇主尋求“禁止勞工工會干預勞工的非工會合同的禁令”,相對而言是比較容易些。從法律上來說,黃狗合同“僅僅是勞工禁令主題的一部分。”[8]1919 年10月31 日,美國煤礦勞工聯合會領導了一次煤礦企業勞工的罷工運動,但法院隨后授予了政府“永久性禁令”,因此該罷工運動在1919 年11 月10 日被取消。[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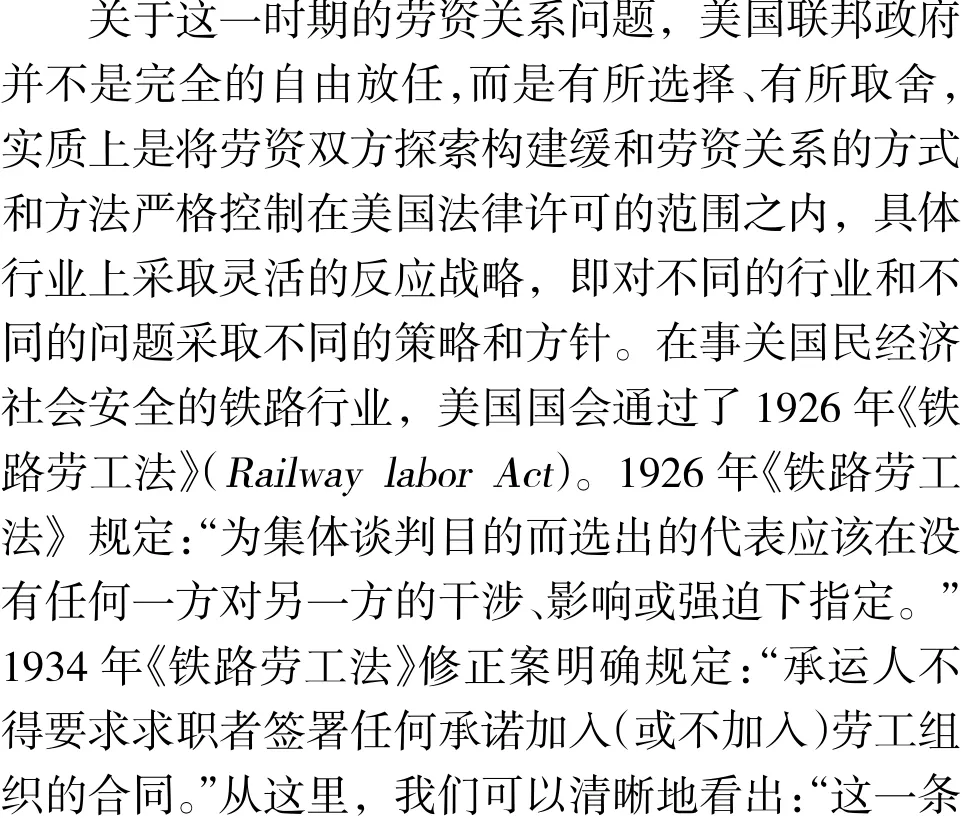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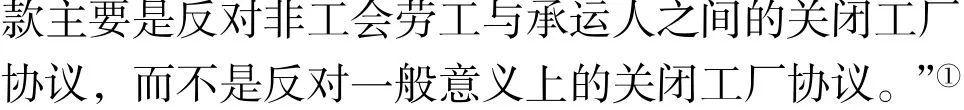
隨著1929—1933 年經濟大危機的到來,美國聯邦政府的勞資政策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1932 年《諾里斯-拉瓜迪亞法》(Norris-La Guardia Act)不僅是“反對聯邦法院頒布禁令的有效武器,”而且是“禁止黃狗合同的使用。”[2]通過1932 年《諾里斯-拉瓜迪亞法》,美國國會“再一次將勞工從《反托拉斯法》中解放出來。”該法“禁止聯邦法院在勞資糾紛中頒布禁令,”隨著聯邦最高法院的運用,聯邦最高法院“有效地將勞工從《反托拉斯法》的限制中解放出來。”該法還包含了第一個立法聲明:“勞工組織和集體談判是可取的。”[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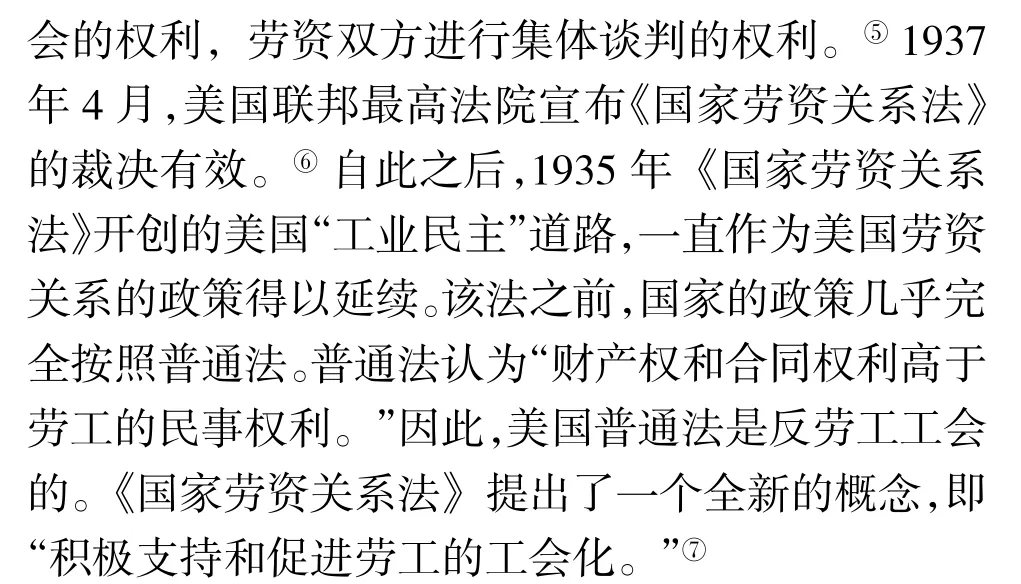
因此,1935 年《國家勞資關系法》是對經濟危機期間美國國家管制勞資關系經驗的總結和提升。這實際上明確否定了開放工廠運動所倡導的“企業主與工會不簽署專門的集體協議、不通過工會進行勞資談判”的核心原則之一,標志著美國企業主追求的開放工廠運動失去了其法理基礎,褪去了其“合法的光環”,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這一時期美國開放工廠運動的終結。但《國家勞資關系法》并沒有否決開放工廠運動倡導的自由雇傭的價值理念,依然維護美國資產階級宣揚的自由理念。而勞方推進的關閉工廠運動也漸漸地退出歷史舞臺。1947 年《塔夫脫-哈特利法》(Taft-Hartley Act)的規定“使得關閉工廠非法,并且規定只有大多數勞工投票后才允許工會工廠(Union Shop)的存在。”[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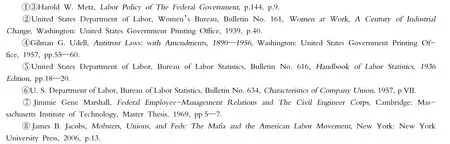
四、美國勞資關系的治理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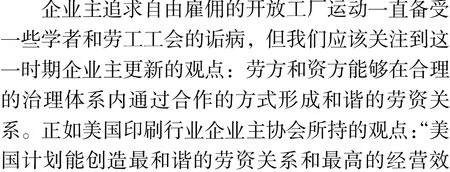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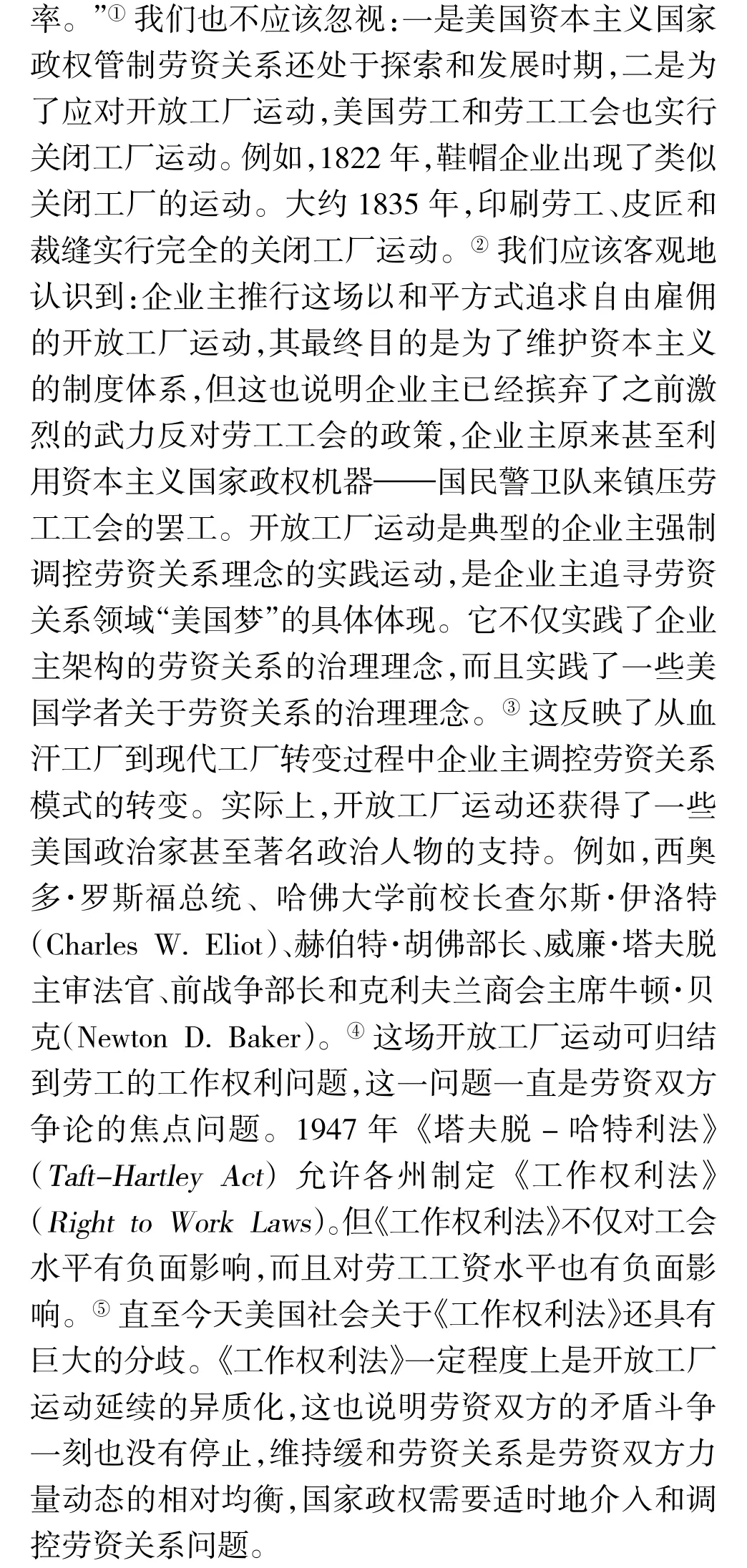
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開放工廠運動是企業主對勞工尤其是勞工工會實施的窮追猛打的策略,是企業主強勢調控勞資關系的重要舉措。關閉工廠運動僅僅是勞工維護自身的權益而不得不實行的一場運動。此時勞資雙方的博弈是非均衡博弈,這為美國資本主義國家政權介入勞資關系提供了有利時機,也為美國政府以后管制勞資關系提供了經驗教訓。實際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羅斯福政府再次建立了國家戰時勞工委員會,并再次確認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國家戰時勞工委員關于集體協商的基準。這充分說明:美國聯邦政府已經完全介入到企業勞資關系問題,充分發揮了政府在“三方協調機制”中應有的角色作用。
從這里我們進一步認識到:一國構建緩和勞資關系需要勞資雙方力量的相對均衡,為了維護這種相對均衡就需要國家政權進行干預,這就需要逐步地構建“勞方、資方和政府”三方協調勞資關系的機制。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在資強勞弱格局下的社會轉型國家中,只有國家政權對勞資關系適時地進行調節和干預,勞資關系才會達到相對和諧,社會才會達到相對均衡。一國緩和勞資關系的構建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勞資雙方和相關方都積極地參與,其中,企業主調控企業勞資關系的理念至關重要。因此,我們既需要進一步積極地實施勞工職業教育,提高勞工的職業素質和技能,為企業的持續發展提供更加高效的勞動力;同時,國家和大眾又需要鼓勵企業進行勞資關系調控方式和方法的不斷創新,不斷地更新企業主尤其是職業經理人調控勞資關系的理念,適應新的勞工群體的管理方式和方法,重視勞工合理、合法的權益訴求,以便引導企業建立更加健康、和諧和穩定的勞資關系調控機制,促進企業的持續發展,最終促進國家長久繁榮穩定。